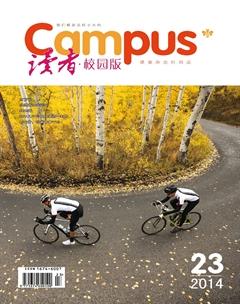你愿意和我玩吗
郑执
我家小区是三栋并排的老楼,分隔出前后两个院子,我家住在中间那栋。小区民风彪悍,两个院子的孩子痴迷互殴。低龄儿童打群架,拼的是谁人多、发育快。占上风的一伙几乎不用动手,单靠自信的眼神就把对方“杀死”了。因此,战场上常常是“秒杀”,但前期的“统战工作”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
前楼的孩子属于前院,后楼的孩子属于后院,无可厚非。但中间楼的孩子只有我一个。
星期一,前院的“军师”给我三块“大白兔”奶糖,利诱我。
星期二,后院的“护法”硬要借给我“小霸王”,笼络我。
星期三,前院的“大将军”放话要揍我,劝我投降。
星期四,后院的“总司令”给我两块钱,收买我。
星期五,开战前夕,糖也吃了,钱也花了,我还没有站好队。
开战当天,清早,我趴在后阳台上偷懒,望着远方的云发呆。我家住在六楼,我离云比别人更近。云,看够了,我习惯性地踮起脚,俯视后院的孩子玩耍。一个从未见过的小姑娘突兀地出现了,独自蹲在楼下的花坛里挖着花窖。她的头发又长又黑,扎着辫子,白裙拖地。
我急于见她的样子,顺手拿起阳台上晾的一瓣蒜,丢落她身旁,她猛然抬头,隔着六层楼的高度,直直地仰望我。
我立下决心,给后院的“总司令”家打了电话。我坚信,这就是宿命的抉择。
她的花窖越挖越深,小小的身影逐渐被墙根遮盖,我快看不见她了。于是,我搬来凳子站上去,半个身子探出窗户,还是见不到完整的她。我干脆将一条腿跨出窗框,却冷不防被一只大手迅猛拿下,臀部遭受连续重击。姥姥把我按在地上,边揍边喊:“小兔崽子,你不要命啦!”
强忍着臀部的剧痛,我写了一个小时的作业,作业没写完,就趁撒尿的工夫偷跑下楼。我在电话里答应了后院的“总司令”会准时参战,他一定以为我是为了那两块钱。
霞光烂漫的夕阳下,后院集结的人数多过前院一半,胜负已分。
我站在阵地中央,寻找她的身影。无获。
前院不战自溃,后院欢呼庆功。散场。
只有我一个人落寞地往家走,前院的孩子早就埋伏在我家楼道里,我挨了一顿揍。
回到家,我妈的袖子已撸好,我又挨了一顿揍。
臀部火辣辣的一天。
第二天清早,我又冒死趴上后窗,却不见她。
第三天、第四天,再也不见。
第五天,我突发奇想跑到前窗观望,竟见到她一个人在前院跳皮筋。
我的心跳得飞快,不顾再次被前院小伙伴狂殴的危险冲下楼,跑到她面前,问:“你愿意跟我玩吗?”
她白了我一眼,收起皮筋跑掉了。
于是,我每天在前后院轮番等她,却没见她。终于有一天,谣言四起,前院的孩子说我是后院的间谍,后院的孩子说我是前院的奸细,我成了双方眼中的叛徒,被“全世界”封杀。
孤立无援后,我整个暑假再也没见到她。
开学前一天晚上,我心中升腾起一股不甘与愤恨—我为你一天之内挨了三顿揍,险些坠楼身亡,你凭什么连跟我一起玩都不愿意?愤恨之下,我趁夜色找到她埋的花窖,掘开土,踢飞玻璃,踩烂鲜花,扬长而去。我想,等她见到了,应该会伤心吧。
渐渐地,花窖被我忘了,她也被我忘了。又过了几年,我家搬离了那个小区。
多年后,我始终怀念在那里度过的童年,每年都回去走走。
我唯一还有联系的小区孩子就是后院的“总司令”。他从未搬离那里,中专毕业后就在隔壁市场开了一家熟食店,生意兴隆。那个小女孩成了她的老婆,两人的孩子出世后,又开了一家火锅店,生意更兴隆。去年过年,我光顾过。聊起模糊的童年,我终于忍不住提起困扰我多年的疑问。
我问她:“你小时候到底住前院还是后院?”
她说:“我是隔壁小区的。”
她问我:“花窖是你毁的吗?”
我反问:“你怎么知道?”
“埋花窖那天只有你看到了啊。”她笑着说,“你小时候咋那么缺德,害得我哭了好几天。”
我不知该从何说起。于是说:“呵呵,不懂事。”
你为她翻山越岭,你为她上天入地,你为她出生入死。当你费尽心机地出现在她面前,她却费解地问:“咦,你怎么在这儿?”
有些事,说了就没劲了。你甘愿付出什么,是你的事。别人愿不愿意,是别人的事。这个道理,我用了好多年才懂。
青春期时,也曾有过很喜欢的女生,为她做过许多事,有些她知道,有些她不知道,但她始终不怎么喜欢我,甚至刻意冷落我。于是多年前的那种不甘与愤恨再次涌现—我都为你做了这么多,凭什么你连对我好都不愿意?大概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奇差,否则就可以更早地明白—这两件事中间,凭什么有必然联系呢?
原来,从来都不存在凭什么。再回想起自己当年为那个人做过的事,猛然惊醒:很多事,其实是为了自己。你不过是斟满了两杯酒,跟她说一声“我干了,你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