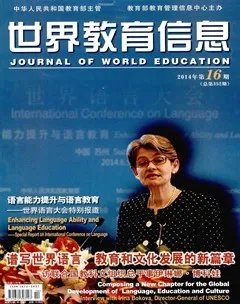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语言问题
各位来宾:
大家好!我将以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为背景,站在残疾人语言及其语言教育的角度,与大家分享语言和语言教育的话题。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签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非常有意思的是,公约中也提及了残疾人语言和语言教育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向大家重点介绍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相关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与语言和教育政策有关的特殊人群,第二个主题是语言、文化和社会和谐。下面我将以手语为案例进行分析。
一、残疾人受教育机会的缺失
正如我向大家所展示的那样,在发展中国家,太多失聪或者残疾儿童没有获得开发其潜能的机会。试想一下,一个正常人的潜能没有被开发将对他(她)产生何种影响。对残疾人而言,这种消极影响只会更大。一般来说,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成功的机会就越大。没有受教育机会的残疾人与正常人相比,差距极大。
普遍来看,获得大学本科或者以上学位的人预期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比高中毕业生更多。无论是正常人还是残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不容易落后于他人。如果一个残疾人在早期能够接受教育,并且能获得足够的后续教育机会,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追赶上正常人。正常人和残疾人工资收入的对比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数据显示,有继续教育或成人教育相关资格证书的人的预期收入要比高中毕业生高30%,获得至少一个学位的人的预期收入要比高中毕业生高60%。可以这样说,残疾人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越多,他们与正常人的差距就越小。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章第三十条指出:“缔约国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使残疾人能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使自己在创造、艺术、智力等方面的潜力得以开发”。实际上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很多残疾学生无法在学校获得语言学习的机会。一般的学校往往认为,正常的教育方式对残疾儿童来说太具有挑战性了,而且也没有适合残疾儿童的教材。这最终导致残疾儿童难以获得智力训练的机会,在教育的起跑线上就已经大大落后,更不用提获得后续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语言学习上的歧视使残疾学生站在了高等教育(语言技能作为入学的基本要求)的门槛之外。
二、语言学习的机会至关重要
然而,我必须指出的是,学校提出的“正常的教育方式对残疾人挑战过大”这一言论站不住脚,一些国家已经有兴趣或经验向阅读障碍人士甚至聋哑人提供外语教育。比如,对盲童进行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口译员。
对于这样的特殊群体,不少国家已经有提供相应的语言教学和语言疗法的成功经验。有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精通4种语言的10岁盲人女孩成为欧洲议会最年轻的工作人员。这个女孩叫做阿莱克西亚(Alexia),她2岁时因脑瘤手术而失明。虽然身患残疾,但这个小女孩却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10岁时就已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中文,并且现在正学习德语。如今,英格兰东部欧盟议员(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罗伯特·斯德第(Robert Sturdy)邀请她前往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议会体验口译员工作。
阿莱克西亚的妈妈是法国和西班牙混血,爸爸是英国人,所以她很小就掌握了三门语言。4岁时,她能用盲文阅读和写作。6岁时,她又学习了汉语。她很快便通过了GCSE(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法语和西班牙语考试,两门成绩均为A,现在她在剑桥大学学习德语。从6岁起,成为一名口译员就一直是阿莱克西亚的梦想。她获得年度青年成就奖后,罗伯特·斯德第邀请她体验欧盟译员的生活,并与顶尖的口译员一同工作。阿莱克西亚说:“这真是太棒了!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口译员,任何事情也阻止不了我。”
从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对残疾人来说,依然有许多语言学习的机会,而很多学校却以挑战过大为由没有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学习机会。
三、手语:制定语言政策,
以创造一个文化和社会和谐的典范
我也想借此机会探讨一下手语方面的情况。我想请大家相信一点,目前我们没有大力推动手语发展,但是这方面有很大发展空间,因此弥补起来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进一步制定与手语相关的政策,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意义重大。
手语是由聋人以及有听觉障碍的人创造出来的,目的是帮助聋人群体之间以及与他人的交流,但是关于聋人群体的语言和文化身份本身就有很多争议。作为残疾人群,聋人被认为是语言和文化的少数群体,而手语也没有通用语法。其实,手语的确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家庭、地区使用的手语渊源不同。但手语是由聋人群体而不是教育者创造的,有文献记载,手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学校教育产生之前;手语的语法更类似于英文和中文,有主谓宾的形式;从类型上讲,手语和正常人所用的口语存在着极大差别。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四章第三十条为手语的推广提供了参考:“残疾人特有的文化和语言特性,包括手语和聋文化,应当有权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承认和支持。”有必要再次强调,已有146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很多国家都有支持土著或少数群体的口语的语言文化社区,以保证土著口语或方言的生命力。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适用于手语的类似规定,手语没有享受到这种“公平待遇”。在教育、就业、社会、经济、公民机会等方面,聋人一直受到排斥。
因此,一些国家的土著口语支持工作做得很好,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聋人手语的境遇十分尴尬。手语没有得到充分支持,这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背道而驰。只有对手语给予足够的重视,才能够在此基础上,慢慢扭转聋人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所面临的不公平局面。
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与聋人交流(这也被贴上了“歧视”的标签)并不是因为他们聋,而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手语我们不懂。所以,应该考虑把发展手语纳入国家的语言发展政策,这方面急需更多发展和努力。
四、尊重聋人社群,保护聋人文化
聋人之间的交流无法通过听觉系统传达,因此,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优先使用完全视觉化的语言。由于聋人仍处于社会下层,相应的,其所使用的语言——手语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手语的使用也不可能被普遍传播,因为对手语感兴趣和学习手语的人并不多。聋人自认为是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少数派,但是用翻译作为中介,其依然是促进理解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手语的翻译会显得更加独特,因为翻译过程不仅仅是双语的,而且是双通道的。所以,综合考虑这些方面,我们应在界定手语的时候进一步拓宽视角。
同时,手语也增进了我们对于语言的理解。语言研究者指出,手语的确是一种语言,对手语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审视口语的核心特点是什么。语言用的是什么通道(比如是口头的通道还是手语的双通道),将会直接影响到这种语言的表达和理解。此外,对于手语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包括手语和口语)在神经层面是如何工作的。
虽然一般人对于学习手语的热情并不高,但对于有听觉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有着极强的学习手语的欲望。在英国,大概每年有5万人参加不同级别(1~6级)的手语考试。由此可见,学生学习的需求非常强烈,但现在面临的窘境是没有足够数量的手语教师。
最近几年,我们也听到了一种“聋人文化”的说法。由于聋人把自己视为少数群体,他们也在积极地探索自己的内部世界。聋人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文化,他们也在积极开发相关技术。
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些聋人文化。这是一个聋人诗人所表达的手语诗歌,诗歌没有任何翻译,是一首沉默的诗歌。他在这首诗歌里面表达的是感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和视觉。通过对每一种感觉进行描述,用诗歌化的手势,用手的不同形状、方位来表达,就像口语表达中不同的声调、语气。最后,他还基于人体的一个特点——无名指无法单独工作,人们有时会觉得无名指比较笨拙——借此表达了如果有一个感官失效,其他感官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而各个感官之间又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聋人文化的探索被归结为“Deafhood”(这是聋人文化的术语,倡导的是“聋”也有其积极意义,这和现在普遍使用的“听觉障碍”有所不同,聋人认为这并不是障碍)。聋人群体有其身体特性、基因遗传和社会身份,聋人文化是艺术、成就和财产。
五、未来残疾人语言教育优先考虑的事项
最后,我想谈谈未来残疾人语言教育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首先,我们要抛弃残疾人就是“不健全的人”的观点。残疾人是拥有自己文化的特殊群体,能够对这个世界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所以不应当把他们视为异类。
我们要做到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序言中所要求的那样:“确认无障碍的物质、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医疗卫生和教育、信息和交流,这些因素对残疾人能够充分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至关重要。”当前政府采取的个人主义(主要在医疗方面)的观点抑制了交流、语言和文化的认可程度,这与《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现状,让残疾人能够享受基本人权和自由。
(文章系作者2014年6月5日在世界语言大会上的主旨发言)
编辑 郭伟 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