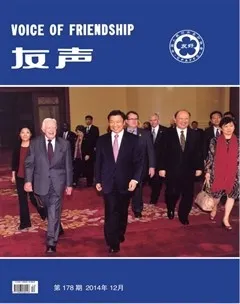“认得几个字”
编者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国文字博物馆精心策划制作了《汉字》展,以中国文字发展史为主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生动全面地展示汉字的起源、发展、演变历程和当代汉字使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字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伟大精神,浓缩了汉字对推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继2012年4月巡展预展在河南安阳开展后,2013年8月13日,《汉字》展首都首展暨国际巡展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作为全国友协推出的一项为期三年的大型对外文化交流项目,该展将陆续在加拿大、尼泊尔、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美国、斯里兰卡、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巡展。《汉字》展于2014年7月15 至25日在日本东京展出,本文作者随展赴日工作,此文为其所见所闻所感而作。
行走日本街头,街名,巷名,楼宇和路桥,民厝和店商,食肆和酒望,入眼的都是似是似懂的汉字。行人匆匆,衣着样貌也似与北京、上海乃至国内他地无甚差异。只是“河”变成了“川”,“舍”变成了“寮”,“慢”变成了“徐”,“停车”变成了“驻轮”,“气球”变成了“风船”,“护照”变成了“旅券”,“职务”变成了“役职”,“绿水青山”变成了“山紫水明”,到处好像有种陌生的雅致。
皇居一侧的街路唤“内堀通”。在大阪还有比肩接踵黼黻琳琅热闹得两只眼睛装不下的“道顿堀”。望着“通”能猜出是通达的街路,而把“堀”白念作“崛”时,却忘了古汉语里“堀”就有挖土成壑的意思,后来证实果然指的就是人工开凿的河渠。天气好时,沿着皇居护城河四方都是健步的市民;天色晚时,沿着道顿堀点起了素灯笼和霓虹灯,南岸的茶房酒肆、影院剧场热情招呼着越夜越热闹的大阪市民和慕名前来的观光客们。
毕竟是异邦,听得懂的没有,看得懂的零星,于是看得就格外认真。懂的不懂的,看得多了,看出三分古意:路旁的招牌多用书法笔体,行笔运墨或笔势奔放,或飞白苍劲,字里行间藏着一种轻松自然而简约淡雅的文人情调。
汉字源起黄河文明,随着使用它的人们一路迁徙,在地理上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渐渐成为包括长江、珠江的三江流域的通用文字。而后又在从东汉到唐的对外文化交往中南传越南,向东传至朝鲜和日本,作为国际通用语进入非汉语圈的周边各民族,百千年间,便有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概念。鹤间和幸教授把汉字、儒教、汉传佛教、律令制谓以东亚世界共通的四大文化要素。如是,则汉字作为四者其中的根基,意义尤为非凡。古代日本人,也用汉字书写情感,记录岁月,尽管后世的改革特别是假名字母的运用,使日文从汉字间夹少量假名,渐而发展为假名间夹少数汉字,但时至今日,日文中仍保留有上千个常用汉字。这也是《汉字》巡展在东亚首站东京的原因。
东西方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生产方式、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别,在思维方式上也有着显著差异。诸因素之中,文字作为思维的媒介,对人类思维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语形即文字的外形。方块汉字尽管历经书体演变,并未削减强烈的象形特征,这样的语形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字的本身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如果说方块汉字是自然万物物象的简化,那么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以直观、形象的符号来表达和理解抽象世界的思维方式。
相较于东西方方块汉字和拉丁字母的迥然差异,同处于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因为同样应用汉字,在社会和历史进程中,发展出许多相似之处。“汉字使我们相互理解、相互接受,并最终使我们心灵相通。”先人们的创造和传承使汉字始终具有这样的潜能,诚如日本外务省中国蒙古课调整官川田勉在开幕祝辞中所言,现代社会瞬息万变,使我们时常忽视了语言背后的含义,且抛开汉字对中国、日本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不表,在目前中日两国关系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借汉字之题展开两国国民相通的文化交流意义十分重大。
展览开幕当日几百市民观众前来观展更加印证了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位置,更不必说在日本随处可见的大量运用了汉字的标识招贴、幡旗暖簾和报章杂志。
1994年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过一套《现代设计》丛书,第18分册《连字设计》搬家来去一直带着,摆在书架上时常当画册来翻。通本书只有一篇桑山弥三郎的同题文章,此外就是大量的设计作品图片。细枝末节总会感到日本人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再改造创新的本事很强。日本的当代美术设计水平发展飞速,不乏杉浦康平、田中一光等国际级巨匠。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本人就是汉字学乃至汉学专家。在对中国汉字书法艺术深入领悟之上,通过“形”与“意”的创新而形成自己的书法形式乃至艺术风格,并运用到平面设计之中,是诸多日本名家的普遍路数。于是,传统的中国水墨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为日本平面设计的一种风格体现。
在日本,识得汉字之美。暗中感叹,中国汉字的发展源远流长,内蕴深厚,但到了近现代,汉字的美感在日与日键盘的敲击声中消磨。特别是这几年开始的城区改造,街面店铺整齐划一,极幸运,在一圈老住区里才能发现那种小时候刚识字时会指着一个个念出来的手写招牌,“修表”,“理发”,“自行车配”,陪上一个带着玳瑁花镜和蓝布袖套的大爷,丝毫不谈美感。然而坐在空调办公室对着一堆有机塑料强言情得久了,偶尔也需要在这所谓的质朴中寻回一点温度。然后会顺便试图想起上次用钢笔认真写字是什么时候,可是还是忘了“堀”本来作汉字的字意。
提笔忘掉的字越来越多,张大春写给儿子女儿的《认得几个字》成了时下最大小通吃的热卖识字书,读得多了,脸红书题一针见血——真是才“认得几个”“只知其然”而不至于是个白丁而已,所认得的寥寥汉字背后的精深又是学海无边的事了。乍到日本,看到什么也总是容易冒出“认得几个”的盲目乐观,幸而前辈早有“学日语就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好言为劝,决心还是回来用这《汉字》巡展的三年认认真真地认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