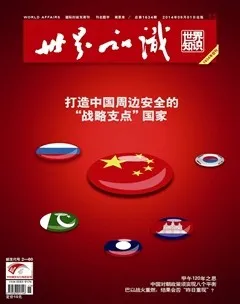中韩政治安全合作:乘势而上,顺势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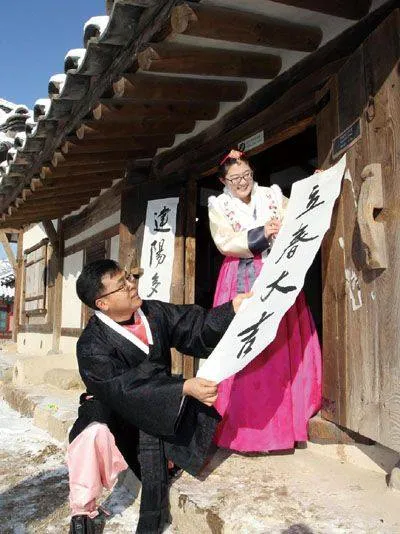

7月3日至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韩关系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注入的“正资产”、产出的“正能量”,进一步深化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赋予之新内涵。中韩两国历经建交以来20多年的双向互动交流,相互了解程度逐步加深,双方愈加懂得如何顾及对方的重大关切与舒适度,在很多地区性议题乃至全球性重大问题上,中韩两国也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或相似的主张。这是两国在政治安全合作层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也给国际社会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众所周知,政治安全合作是国家间合作的高级阶段,彰显国家之间彼此互信程度的深化,也是两国关系日趋成熟与稳定的根本标志。当然,国家间累积信任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冷战时期:政治安全上相互防范对峙
就中韩关系而言,可以将冷战时期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冷战大幕开启至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朝鲜半岛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前沿阵地,整个东北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美日韩与苏中朝(尽管这一阶段后期中苏关系破裂)两大集团兵戈对峙的局面。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与韩国互不承认对方政权的合法性。中国认为朝鲜是朝鲜半岛惟一合法政权,而韩国则承认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韩国出于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考虑,完全倒向美国一边,在外交上完全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美韩关系演变成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施惠与被施惠的关系。这一阶段中韩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相互敌对,彼此隔绝。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冷战结束。这一时期,整个国际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中美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东北亚地区原有的两方六国对峙的结构出现了明显松动,尤其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韩关系获得了难得的发展契机。但中韩两国囿于意识形态、客观现实条件、国家外交战略定位等多种因素,在外交相互承认上依旧止步不前。尽管如此,两国都不再将外交承认与开展经济交流相挂钩,两国民间经济交流因而得以开启。当然,这一时期中韩之所以迟迟没有建交,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一方面不希望因为中韩发展政治关系影响到中朝传统友谊与战略合作;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因为外交上承认韩国导致潜在鼓励台湾谋求国际社会的外交承认。这一阶段中韩关系也可以概括为:政治外交上继续相互不承认,但经济交流已把彼此隔绝的坚冰融化。
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其共同点在于彼此“相互否认”。这一时期,作为西方阵营与社会主义国家对垒的“桥头堡”之一,韩国理所应当地成为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重点拉拢的对象,而韩国出于自身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诉求也选择了与美国为伍,积极配合美国的亚洲政策。
后冷战时期:韩美同盟及零和思维影响仍在
按一般逻辑推理,随着冷战的结束,冷战时期基于共同安全威胁而形成的两方六国对峙的格局理应寿终正寝。但事实上,虽然作为东北亚对峙一方的苏中朝的战略合作不复存在,但作为对峙另一方的美日韩同盟却继续保留下来,并且长期持续左右韩国历届政府的地区政治安全战略。多年来,韩国实际上形成了经济上依赖中国与政治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平行结构。冷战结束后不久,中韩于1992年8月实现了建交。中国经济增长给周边国家与地区提供了难得的经济发展机遇,“搭便车”心态成为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务实选择。中韩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发展潜力巨大,韩国正是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在经济上不断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资料,2013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2742亿美元,是建交之初的55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等。但在政治安全层面,由于冷战思维的惯性和韩美同盟关系的稳定持续,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届韩国政府依旧固守韩美同盟及零和博弈思维,寄希望于通过韩美同盟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实现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事实已经反复证明,这一同盟理念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事与愿违,收效不佳。它不仅没能够破解朝鲜半岛安全困局,还影响了南北关系统一进程,并束缚了韩国的地区政治安全战略空间的拓展深化。
现实要求:东北亚安全困境助推中韩
政治安全合作
东北亚地区是全球范围少有的国际热点问题高度集中的区域,热点问题的聚集严重威胁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长期以来,韩国一直寄希望于通过韩美同盟解决朝核问题,但这种努力不仅没有收到其希望的成效,反而给问题的解决增添更大的变数。实际上,朝核问题的本质是朝鲜国家安全保障资源稀缺的外在表现。如果美国继续长期驻军韩国,韩美联合军演持续上演,朝鲜很难消除对外部安全威胁的感知,那么,敦促其弃核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反之,若国家安全得以保障,朝鲜很可能会采取新的战略选择,研发实验核武器也将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和经济压力。这反而为推进朝鲜半岛南北交流提供可能。另外,日本政府近些年来动作频频,与中、韩的领土争端不断升级,甚至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危险局面,但作为韩国盟友的美国,在韩日领土争端上却三缄其口。而且近些年来,日本国内一批极右翼势力,试图掩盖二战时期犯下的战争罪行,严重伤害了东北亚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很难期待在韩美同盟的框架下得以解决。因此,地区安全环境恶化与中韩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逐步促成了中韩两国的政治安全合作。
1998年,中韩两国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0年,中韩两国宣布将中韩友好合作关系推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03年7月,中韩两国同意将中韩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5月,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韩国总统李明博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但中韩政治安全合作真正步入快车道始于朴槿惠就任韩国总统以后。2013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中国,将其访问定位为“心信之旅”,并明确传达一个信号,即未来将平衡发展与中国的政治安全关系与经济、社会、文化关系。2013年11月,双方成功启动了中国主管外交的国务院负责人和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的对话。2013年双方还成功启动了外交安全对话、国家政策研究机构联合战略对话等《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中商定的战略对话机制,举行了两国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和第三次国防战略对话,构筑起多层次的战略沟通体系。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韩使中韩政治安全合作进入新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两国元首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联合声明》明确了中韩政治安全合作的基本内容:首先,实现两国领导人互访机制化、中国主管外交的国务院负责人和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对话渠道机制化,两国外长每年例行互访,建立两国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的1.5轨对话机制,定期举办由引领两国未来的青年精英参与的“中韩青年领导者论坛”等。其次,保持两国防务和军事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不断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再次,中韩两国将于2015年启动海域划界谈判。这些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内容务实且推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标志着中韩政治安全发展将进入实质化及可操作性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未来趋向:不断迈上新台阶
相较中韩经济合作,两国间的政治安全合作可谓姗姗来迟。建交以来的22年间,中韩两国之间尽管在政治安全领域存在零星的沟通行为,但两国在政治安全沟通与合作协商的制度建设上缺乏建树。这与中韩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当前,中韩之间经济领域的合作到了深水区,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韩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在所难免。加之冷战思维作祟,中韩之间关于一些高新技术的交流障碍依然存在,传统的单纯囿于经济层面的合作已经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尤其是在固有的地区安全结构的背景下,朝核危机持续存在,朝鲜半岛南北摩擦断断续续,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美化战争历史,韩日领土争端持续升温,这些都是韩国不得不面对的地缘政治现实。
历史经验和严峻现实再次警示人们: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单纯依赖于韩美同盟的架构,因为美日同盟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对外战略的基石,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友。东北亚国家应更多地基于东北亚地区自身的力量,充分体察地区相关国家的利益关切与舒适度。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不仅仅是半岛南北双方的问题,也关乎东北亚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安全命运。中韩作为重要的地区政治安全利益攸关者,理应顺应地区形势与时代潮流,不失时机地促成两国间深层次合作。这不仅契合双方的共同战略目标,也有利于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当然,鉴于目前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中韩之间的政治安全战略合作在较短时期内很难看到根本性的改观,但两国深化政治安全合作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地区内利益攸关方抛弃冷战思维,打破固有视野,彼此坦诚相见,真正从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大局出发,积极、务实地推进政治安全合作,才是民众真正之福祉。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韩国首尔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所说,“在新形势下,中韩两国应以面向未来的眼光解决现实问题,这是国家实现和睦相处、化解矛盾分歧、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的有效途径和可靠保障。”而且“要创新安全理念,朝着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方向,通过深入开展政治安全对话和合作,使地区国家成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伙伴,共同维护亚洲和平与发展。”这番讲话既是中国声音的一种传递,更是对中韩未来深化政治安全合作的深切期许。有理由相信,在两国政府的“顶层设计”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支持下,中韩政治安全合作必将乘势而上、顺势而为,不断迈上新台阶、跨越新阶段。
(作者麻陆东为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博士后,作者杨鲁慧为山东大学亚太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