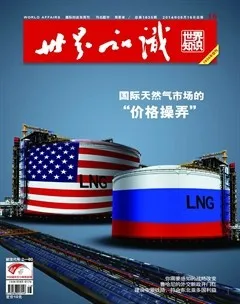TPP谈判为国有企业立规则:一把双刃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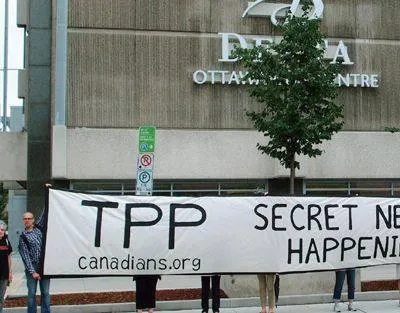
2014年7月12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落下帷幕。在此次会议中,TPP谈判成员国重新启动了国有企业议题的磋商,并推动谈判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尽管各成员国在一些具体领域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其总体原则和框架已日渐清晰。随着谈判日益接近尾声,TPP各成员国商定的国有企业规则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TPP的竞争中立原则剑指国有企业
2011年5月,在美国的倡导与推动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题为《竞争中立与国有企业:挑战与政策选择》的报告,较为全面地提出了“竞争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原则。报告认为,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补贴;二是政府及其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融资与担保;三是放松监管等其他降低运营成本的政府优惠待遇;四是垄断以及国有企业任职人员优势;五是政府锁定股权(captive equity);六是不受破产规则约束以及拥有信息优势。OECD提出的所谓“竞争中立”原则,简单而言,就是要打破国有企业的这些“不中立”的优势。
2011年11月,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能源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在纽约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发布会上,代表美国官方正式对外提出“竞争中立”概念。根据霍马茨的解释,“竞争中立”意即不受外来因素干扰的市场竞争,旨在重新规划现存国际经济规则或制度,从而保证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实现公平竞争。霍马茨的公开言论为竞争中立原则纳入TPP谈判做了铺垫。其后,在以美国为主的多个国家的推动下,竞争中立概念被纳入到TPP谈判中,并明确以竞争中立规则规范和约束在TPP框架内国有企业竞争行为。
2012年5月,TPP第十二轮谈判在美国达拉斯举行。在此轮谈判中,美国正式向其他谈判成员提出在TPP协定中增加有关国有企业的条款。与此前OECD和霍马茨的阐述一致,美国认为,由于政府给国有企业提供了各种便利,使私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违背了维护公平竞争的竞争中立原则。因此,TPP协定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为私营企业和外国国有企业营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在此后的TPP谈判中,竞争中立原则被逐步细化为税收中立、债务中立、规则中立,在内容上涵盖反垄断法律与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也包括对国有企业的竞争规范。它要求各谈判成员国制订反垄断的法律和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国有企业在获得信贷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资助上不存在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由此可见,TPP的竞争中立原则主要针对边境内的国有企业政策。
TPP的国有企业规则将产生示范效应
众所周知,TPP只是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其所包括的各种规则只适用于协定成员国。即是说,只有成员国对协定内容负有责任并承担相应义务;而对非成员国,协定条款没有任何约束力。但事实上,TPP谈判从一开始就为国际社会所关注,TPP中包括国有企业规则在内的所有新规则,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未来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TPP达成协定后,其国有企业规则很可能成为未来全球贸易与投资协定的模板,具有不可忽视的示范效应。究其原因,以下几个因素使TPP协定相比现有多数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更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TPP谈判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目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与对外投资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这赋予美国无与匹敌的主导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制订的能力。在TPP谈判确立国有企业规则后,美国可利用自身影响力将这些协定条款作为与其他经济体谈判贸易协定的模板,从而逐步演变为国际通行的规则。在当前进行的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以及中美投资协定等谈判中,美国正是利用其优势推动更多的国际社会成员接受反映美国诉求的美式规则。
其次,TPP谈判成员的多样性使其规则具有全球推广意义。在目前参与TPP谈判的12个国家中,既包括美国和日本等经济实力雄厚的发达经济体,也包括马来西亚、越南等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既包括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谈判成员的多样性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但相比其他双边和多边协定,TPP协定文本一旦达成,其确立的新规则将具有更加广泛的适用性,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效仿。
最后,TPP确立的规则符合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利益。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仍然是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世界,当一项规则有利于发达经济体时,更有可能成为国际经贸谈判中的主导规则。反之亦然。新世纪以来,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规模与实力迅速提升,无论是在资源能源产业、制造业,还是在主权财富基金领域,都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并对发达经济体的相关产业构成挑战。TPP的国有企业规则意在维护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优势,并平衡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压力,这与多数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经济政策是一致的。
总之,TPP的国有企业规则的示范效应,使TPP的影响远远超出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范畴,规范国有企业市场竞争行为的竞争中立原则纳入TPP谈判议题并逐步演变成国际规范,其背后隐含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应对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重新构建国际贸易规则等深层次动机。正如2014年3月美国副总统拜登所言,“美国现在做出的选择,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美国在全球的角色”。
理性看待TPP的国有企业规则
在TPP谈判中,国有企业议题涉及多个成员国的利益,因此成为TPP谈判的难点之一。目前,多数成员国拥有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国有企业。例如,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智利最大的铜企业智利国家铜业公司也是国有企业。此外,在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中,一些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亦不可轻视。这一方面增加了TPP的国有企业规则谈判的难度,另一方面也预示多数TPP成员国的国有企业将不得不按照新的规则进行新一轮改革,并可能因此对其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尽管国有企业规则正式被全球性多边规则谈判所采纳尚需时日,但对于非TPP成员国尤其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TPP的国有企业规则同样会带来新的挑战。在TPP谈判结束并达成协定后,对拥有国有企业的非成员国的潜在影响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了相关国家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的门槛。要参与到以高标准规则为特征的新一轮自由贸易谈判并分享由此带来的收益,这些国家必须提高自身的谈判门槛,以适应这种新的规则。二是减少了相关国家参与多边经贸谈判的筹码。由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约束国有企业时打着所谓“公平竞争”的旗号,因而可以光明正大地利用这些规则在多边场合对这些相关国家加以指责,从而使这些国家在多边舞台上陷入被动境地。
但辩证地看,对于拥有国有企业的国家来说,基于竞争中立原则的国有企业规则并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而是一柄“双刃剑”。应该充分认识到,它在给国有企业带来改革压力与挑战的同时,也会成为推动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动力。例如,TPP的国有企业规则所倡导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享受平等待遇,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危机意识,“倒逼”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参照,推动市场成为国有企业最强有力的约束条件,从而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最主要的方式。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