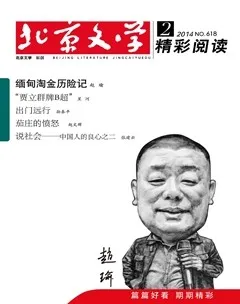消失的城堡
一、三十里铺,一封来自清代的邮件
生活在固原三十里铺大道边的张树仁老先生,现在居住的古堡,原本是一座急递铺。
《宣统固原州志》记载:固原州除设“驿站”永宁驿、瓦亭驿、三营驿、郑旗驿、李旺驿、蒿店驿等驿外,“固原额设铺司(急递铺)共一十二处。曰在城铺、曰十里铺、曰二十里铺,曰三十里铺……”三十里铺的地名,由此而来。
清代,这座“铺司”是朝廷邮驿网络中的一个点。它和其他急递铺一起传递着朝廷发往边地的各项要文,呈送着边官递往朝中的各种奏折,同时也经营着一些民间信函。
张树仁老先生陪我走到古堡的北墙下,指着墙上残留的柱槽说,那就是当年马厩倒塌后墙柱留下的痕迹。
清代集历代邮驿之大成,从康熙、雍正到乾隆,邮驿管理制度渐次完善,信息传递网络也随之基本形成。尤其在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邮驿成了朝廷要求地方官员务须办好的一项要务。《光绪会典》准确地登录了有关邮驿方面的数据:全国有驿站1970处,急递铺约14000处。同时也诠释了一应事宜的权属:由兵部车驾司掌管全国邮驿。车驾司下设驿传、脚力、马政、马档、递送等科,分办各项司务。驿站差事主要有四种:大差,接待公出的要员和使臣;紧差,传递加急的重要文报;小差,传送一般驿递的奏章及表册;散差,接待悯劳恤死特许驰驿者。可见这些专设的邮驿组织规模庞大,可谓星罗棋布,网络纵横。
试想,缺少了这些驿站和“铺司”,鸦片战争的爆发和道光皇帝签署《南京条约》的消息,何时才能为西北民众通晓?左宗棠围剿叛乱的捷报,以及固原地区深受蝗虫侵害的灾情,何年何月才能为朝廷知道?
当然,这些驿站和“铺司”的脉络,是随着清政府的鼎盛而畅通,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败而走向没落和消亡的。
我是2009年初冬的一个雪天再次来这里造访的。这天又是个大雪纷飞天。奇怪,我每次选中要来三十里铺这座“铺司”的时候,天上都飘着鹅毛大雪。更奇怪的是,我每次到来时,张树仁老先生都在清扫堡门前的积雪。
白雪皑皑,这座曾经作为“铺司”的古堡,和周围其他农庄院落一样,承接着缓缓而下的大雪,接受着雪花的抚慰,聆听着上苍发往人间的信息。古堡身边有笔杆似的新疆杨,有团坐着的草垛。古堡前的大道上驶过一辆辆南来北往、小心翼翼的车辆,给雪白的马路留下一道道辙痕。而已经把雪花归拢成堆,给自家门前扫出一条小道的张树仁老先生,拄着扫帚,口里哈着热气,看着漫天飘落的雪花发呆。
他耳朵没挂听诊器,面前没有病人,但他能听到自己嗵嗵作响的脉搏。一辆蹦蹦车蹑手蹑脚地去了,这脉搏还在跳;邻居家的鞭炮声停了,这嗵嗵嗵的声息还在响。他怀疑自己刚刚扫雪的时候,扫帚触摸到了大地的心跳。
跟着张老先生走进堡内新建的瓦房,坐近火炉,接过他递来的热茶,我慢慢呷了一口。他压在鸭舌帽下的目光,不炙热,也不冷。他没有因我这个陌生人的跟入而心生疑虑。他以多年做赤脚医生养成的习惯,观察病人一样的眼神打量着我,说:“你没有大病。”
是的,我没有大病。可我不敢说大年三十,人人都在准备迎接新春,大雪笼罩整个世界的时候,我却贸然造访,很随便地放下背包,毫不客套地坐在火炉边伸手烤火,毫不谦让地接过他递来的热茶,是不是一种病。他儿子、儿媳和三个孙子,在他身后用好奇的目光瞅着我,像瞅着一位过往的邮差。我取出介绍信。他们围了上来,当他们弄明白我是为探明这座古堡历史而来的采访者时,大失所望地散了。孩子们爬上炕头看连环画去了,儿子和儿媳忙着贴春联去了。
张老先生带我在堡内转了一圈,又回到屋里坐下。他看了一眼我放在桌上的相机,见我已取出笔和笔记本,便直截了当地说起来。
他今年七十多岁,住进这座堡子也已十多年了。但要说清这座堡子的来历,他确实无能为力。他曾经为此走访过许多老人,但谁也说不准确。他说了一些自己对堡子的看法和感想,意思是:“人在世上的时间必定有限,堡子如果没有人为地破坏,就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存在下去。”刚才他指给我看的那些柱槽,木头朽了,可痕迹还在。而一个行走在世上的人,一张薄皮包着骨头和肉,说化就化成水了。地下刨出来的白骨,谁也不知道它原来长在哪个人的身上。他当大队赤脚医生走乡串户几十年,救死扶伤的事干了大半辈子,老死病伤见过不少,可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死,死了哪根骨头先腐烂。
他曾问过有关他的寿辰。算卦先生说他为人祛病疗伤积下不少阴德,定能长寿。但说到最后,还是说不准他睡土的时间。
他说,听老人讲过冯玉祥在这座堡子里枪毙人的事情。民国十五年(1926年)冬月,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的部队从五原撤下来,到这儿基本上散架了。冯玉祥为了收拢部队,整顿军纪,枪毙了躲在马槽里睡觉的两名士官,枪声震动了三十里铺,震慑住了松垮的士兵,可叱咤风云的冯将军后来还是给人戕害了。说到这里,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蜷进手心,拇指挺着,小拇指和无名指翘着,又伸出右手逐个捋了捋拇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他想说什么,思量了很久,没说出来。
他挪了挪屁股,耸耸右肩,仿佛背着医疗包,骑着自行车,行走在乡间小路上。他说,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属于自己的生命信息,带着属于自己的病。每个人都像一个邮包,像一封循着收件地址赴向终点的信。
他的目光在自己的手心里徘徊。他再次捋了捋指头,讲了些有关他走乡串户的往事:
他先讲的是一位高烧不退、四肢抽搐、人事不省的青年,叫任天禄。那时,他刚从民兵连长转成生产大队的保健员,既不懂医病的常识,又没有医疗经验。眼看一个活脱脱的生命躺在自己面前,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心里“一昏儿”(茫然又忽然)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信息,眼前出现了“急性脑膜炎”几个字眼。于是疾速打开医疗包,取出阿司匹林碾碎了让任天禄服下。又用银针刺患者的阿是穴。终于,救活了年轻人的命。
继而是附近新龙沟四队出麻疹的娃娃。这娃娃在他出诊时已经叫不应声了。在孩子父母的哭泣和哀求中,他不知哪来的胆量,竟把两枚银针刺入了孩子前胸的膻中穴和后背的肺俞穴。当他用火罐从针眼里拔出浓黑的血水,孩子开始平稳地呼吸,孩子父母露出笑容时,他却头冒虚汗,全身瘫软了,差点昏死过去。他不知道给他勇气的信息来自何处,只知道这是一次天大的冒险。
再是小岔沟一位姓李的人,“心口子痛得要命”。那时,他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医疗知识,也知道他患的是急性胃炎。可当时只是赶集路过,没带医疗包。仓皇中,他被脚下的一块石头绊了一下。他眼前一亮,顺手捡起这颗石头,用布带把这颗石头绑在患者的“懒弯子”( 胳肢窝)上,让石头的尖端顶住患者的委中穴,然后令他运动。这办法竟然奇异地治住了患者哭爹叫娘的疼痛。
说到这,他坦白地告诉我,一个赤脚医生,要干好医疗行当,不能单凭外在的病理信息,还得有一颗善良的心。听到这儿,我已把这座“铺司”和他的繁杂信息汇集在一起了。
这座“铺司”,是清代庞大邮驿网络上不可或缺的点,当年自然会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有过不寻常的繁华。据他讲,自从董福祥带着清兵把回民起义队伍从这里撵走以后,堡子里就再也没人住了。后来,冯玉祥又在堡子里枪毙了人,堡子就更成了一个阴森的话题。孩子要哭,大人吓唬:“再哭,就把你扔到堡子里。”某人鬼迷心窍学坏了,人们会说他是“从堡子里出来的”。殊不知,张老先生自言自语地说,“堡子,只是一个传递过信息的站点,一个不会说话的土圈圈。”
十几年前,中宝铁路正好要从他家的老宅子经过,老宅子拆迁,没处住,他毫不犹豫,用几亩川地置换来这座堡子。他没有在意什么妖魔鬼怪的说法。他带着几个儿子住进来,平平顺顺地过到了今天。
他说,任何地方都有各自的信息场,任何人都有他的信息网。这座“铺司”仅有二亩三分地,却面朝四海,通达八方。也许正因它狭小,才聚得住气,才没有在“破四旧”时被拆毁。他说,信息是不固定的,是在不断地变化中。信息通过旷野、农田、电线、铁路、公路,也通过风雨雷电传输给人,使人一点一点领悟着天地自然的秘密。每个人也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感应,收集和疏散着各自的信息。
末了,张树仁老先生幽默地说,他只是一个邮件,他所居住的这座老堡子也是一个邮件。他说,老邮件了,还压着,不明收件地址,也不知收件人姓甚名谁呢。
天空苍茫,谁能知晓这一切?
二、追寻笼竿城
1
笼竿城无踪可寻。
一座古城无踪可寻,是否像一艘木船顺流而去,一只凤凰飞进烈火,一场大雪融入深谷那样没了呢?
是的,土筑的笼竿城,回归了土。
这座风云一时,又多舛多难的古城没了,在它的遗迹上冒出了许多树。也许这些新栽的松柏,会借着这块肥沃的土地成长起来,形成一片新的森林。如果这样,鲁迅先生所说的“万不料人的思想,是死掉之后也还会变化的”,就在黄土高原上、六盘山下得到了物质性的对应。
对于死亡,人们的看法从来都不统一,有时是痰喘之后的沉默,有时却是别种物象的新生。我很赞同周作人先生在《死之默想》中所说的那句话:“仙人活了二百万岁也只抵得人间的四十个春秋。”
笼竿城是没了,在劫难中死死生生而后终于融为了土。可曾经的一场场劫难和即将出生的生命,还在演绎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2
笼竿城的遗迹在宁夏隆德县县城的东边,在六盘山西麓。当年秦始皇巡边出鸡头山(六盘山),唐太宗越陇山去西吉将台堡观马政,都途经这里。只是那时没有笼竿城,只有笼竿川。秦皇唐王虽然没有在此驻跸,但他们一定昂首阔步在这里指点过。与秦皇唐王一样,司马迁、王维等人在这块土地上谈笑风生过,且留下了不朽的文字。
从1011年(宋大中祥符四年)宋渭州知州曹玮久居笼竿川募兵伊始,笼竿城就有了崛地而起的可能。至1013年,曹玮终于修筑了笼竿城,并把这座城定为泾源路第七将城。30年后,也就是到了1043年,泾源经略使韩琦来了。他以为这里近临西夏,地势险要,需要持重把守,于是改设笼竿城为德顺军。又因为他手下大将任福在离此不远的好水川与夏军作战,数万军马全军覆没,他为了防止夏军趁势以此为突破口杀进中原,为了把这座城建成坚不可摧的边防重镇,在加固此城时耗费了不少的人力和物力。正因为耗资巨大,疏于管理,1044年,宋军内部产生了矛盾,筑城督役刘泸被押进了德顺军监狱。直到泾源路副使范仲淹来此就任,出面说情,刘泸才幸免一死。
刘泸上演的这一出戏很能令人“扑哧”一笑。这位筑城督役,为加固城池的同时能在军城内增筑一座疏而不漏的监狱,煞费了苦心。可万万没有料到,他钻进了自己力挺筑建的牢笼,险些一命呜呼。
从某种意义上讲,卖官鬻爵、贪污受贿的行径自古至今时有发生,这些人最终免不了自跳火坑。然而,自古至今哪一个囹圄建造者的初衷不是为了囚禁自己的敌人呢?1077年,这座关押过筑城督役的监狱,终于派上用场,押进了夏军的探子。这些探子伪装成马贩子,混进笼竿城,在他们还没摸清宋军虚实的时候,被宋军察觉,一举逮捕,关进了监牢。此事,泾源路统帅蔡延庆还是真动了些脑筋,经过三思,为了麻痹夏军,他故作镇定、大大咧咧地释放了这伙探子。
3
战马无疑是古代战争的利器。1060年,宋仁宗为弄清宋军究竟为何连连惨败的原因,便旨令翰林学士吴奎、度支判官王安石等人进行深入调查。当他知道如若再不重视马政,再不借助快马作战,大宋有倾国之危机后,即刻下旨在德顺军、平凉、原州等草场茂盛地区兴建马场,大量引进马种,繁殖和饲养起了战马。到1070年(熙宁三年),三个地区的战马已达到了每年上万匹的储备。
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人心,可战火的燃烧取决于贪欲。西夏军队的速战速胜,使西夏君王的欲火越烧越旺。西夏建国以后,不断向大宋寻衅,宋元丰七年,即1084年,西夏军队欲取兰州,未能如愿,又反身攻打德顺军。德顺军巡检王友战死,军城失陷,夏人入城劫掠一空而去。
德顺军名义上是一座集军事和牧马边城为一身的重镇,实则是一只软柿子。“靖康之耻”(1126年)那年十一月,夏人再次攻陷了德顺军,知军事刘铨,通判杜翌世战殁,德顺军再次落进了西夏人的手掌。西夏人倒是很能见风使舵,他们见金军日趋强盛,自己无力关顾,便拱手把顺德军送给了金国。金国坐享德顺军之后,于金皇统二年(1142年)改德顺军为德顺州。自此,宋金之间的战幕在这里拉了开来。
1161年10月,宋军中军军马主管吴挺突袭金军,防守德顺州的金兵在不明虚实的情况下慌乱无措,宋军算是在此打了个胜仗,捡了个便宜。但由于此城长期落入他人之手,孤守没什么意义,可能还会遭到防不胜防的打击,宋军只好胆战心惊地弃掉此城,班师回军,另作打算。
第二年二月,宋军再次挥军长围德顺州。久攻不下,宋将赵诠只好调集敢死队以硬弓掩护,呐喊声助威,强登城池。金主簿赵士持见势不妙,出城投降,宋军借机活捉了金军知军韩珏。然而,德顺州城池坚如铁桶,宋军还是一时奈何不了。直到四川宣抚使吴璘闻讯赶来,亲自督战,借天降大雪切断金军的援兵,城内的守军才不得不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乘夜弃城逃走。
长期受金军欺压的宋民见宋军再次拿下德顺州,总算心落到了实处,他们扬眉吐气,欢歌笑语地“父老拥马欢迎”,使得宋军队伍“几乎无法前进”。
狂欢永远是暂时的。这些你攻我守、你败我胜的历史,伴着来来往往的历史,霜叶一般落下来又被朔风卷走了。边外的列强,当年还不是秋天的枯树,他们像一只只远来的鹰鹞,知道德顺州是一片森林,不仅可以藏身,还有诸多可以饱腹的雀鸟。成吉思汗来了。1222年8月,金军为防卫成吉思汗,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到平凉府去应付蒙古大军。借此,西夏军见有机可乘,便偷偷出兵攻进了德顺州。他们又对德顺州进行了大肆掠夺,又扬长而去了。
1227年2月,成吉思汗的大军浩浩荡荡地越过了六盘山,他们无坚不摧,连攻十二昼夜后,破了德顺州。金军守将爱申及高参马肩龙自杀殉国。多年以后,也就是到了元大德八年(1304年)二月,笼竿城被废,德顺州迁到了葫芦河畔的羊牧隆城,取名隆德。自那时起,隆德县的名字沿用至今历经860多年。
4
明洪武二年(1369年),残破的隆德城又得到了修补。修补之后的隆德城到了1505年,又经历了一场大浩劫。那年蒙古鞑靼大元可汗(亦称小王子)率五万余人由葫芦峡口进入,攻陷了隆德城,秋风扫落叶一般,大肆掳掠之后又慌忙撤走。
明末,崇祯七年(1634年)闰八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的起义军攻陷了隆德城。之后,他们转战六盘山区和泾河流域,以隆德为后方,不断获胜,先后七次进占隆德,并攻陷了固原城和海原等地。
1635年(崇祯八年)隆德城有过修复的历史记录。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隆德城也有补修过的记载。隆德城真像一件穷人家的布衫,为了暂时取暖,穿穿补补,补补穿穿,总没舍得丢掉。然而,到了清代,由于边界外移,隆德城还是荒凉了下来。1842年,林则徐在被遣新疆伊犁途中写下的《荷戈纪程》里,记录了借住隆德城时的情景:“……至隆德城,入东门,城内住,行馆深而狭,城颇大而荒凉特甚。”可一座古城寥落无度,也还是一座城。同治初年,陕西关中回民赫明堂、白彦虎等人领导各地回民起义反清,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隆德县知县被回民军毙命三任(宋继昌、蒋柏林、周其俊),赶走一任(苏国泰),仅同治四年至五年不到一年时间,县城被攻破三次。此后,隆德城因空旷难守,空城无主先后长达五年之久。
到了民国17年(1928年)秋天,驻扎在隆德县山河乡一带的土匪头子王福德攻取隆德城,尽管隆德军民联合石堡马保元民团勇猛迎战,但还是被土匪战败。王福德杀了马保元,县城又一次遭到了洗劫。据记载,这位带着喽啰洗劫隆德城的土匪头子王福德,不久以后在甘肃通渭,死于手下人的屠刀,死得血肉模糊、其状难言。
5
寻找不到笼竿城,可我看见了几棵苍劲的柳树,它们挺立在销声匿迹的笼竿城边。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发现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长达600里的大道边少有树木,于是上奏朝廷,栽植了不少柳树。他就任的十二年中,率领军民栽植树木二十六万四千余株。栽下这些树木,为了严令管护,他说:“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因此就有了后来的“绿如帷幄”,“连绵数千里”。
清代诗人杨昌浚前往新疆途经这里,看到杨柳成阴,人烟繁茂的景致后,留下了一首七绝: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时至今日,人们每看到这几棵柳树,不由得会想起当年的左总督。这些树,已经没有了原有的名字,人们只叫它“左公柳”。
民国37年(1948年),固原县政府调查登记全县境内(包括隆德)时有“左公柳”2051株。“在以后的岁月里,‘左公柳’屡遭砍伐。1958年大炼钢铁时,所剩的‘左公柳’被砍伐殆尽。”“左公柳”现今被列为中国古代五大名柳之一,只剩下隆德城附近为数不多的几株。这为数不多的“左公柳”身挂金色的铭牌,兀立于新栽的松柏之间,用它们繁茂的树冠泼出一团团不死的阴凉。
我把车子靠在路边,蹲下身,掬起一捧黄土。我不知道这土是笼竿城的土,还是德顺军的土。我轻轻松手,它们在清风中飘舞起来。我想伸手抓住它们,却招来了一位从身边过路的农民的调侃:
“你能抓住这些灰尘吗?”
我不知如何作答。但他唤醒了我,我紧忙问:“看来你知道这些尘土就是当年隆德城墙上的土了?”
他被我问住了。但他停下脚步思量了一下,说:“我们脚下的土,那片新园林的土和学校操场上的土都是隆德的土。土不是人能改变的,地不是谁能搬走的。”
我恍然大悟。我知道所有农民都是哲人,所有尘土曾经都是净土,净土上弥漫着一层尘埃。
笼竿城没了,隆德城栽下许多新树苗……
三、地穴
那天,当我听着野鸭“哇哇”鸣叫,对天空抱有留恋,在远处喝斥那条狗的时候,华仔喊了一声:“喜鹊落在石碑上。”
沿着华仔的喊声望去,果真有只喜鹊站在一尊石碑上。我刚用相机瞄准,喜鹊就飞走了,镜头里留下一块黑乎乎的石碑。
石碑上,刻有“打石沟新石器遗址”几个字,刻有1988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落款。目光从石碑移开,石碑身后有不少黝黑的窑洞,像一双双骷髅眼睛。这些眼睛凝视着我们,与整个裸露的山坡构成了一幅颓唐的画面。
想起来了。在报纸上看到过,彭阳境内有许多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大部分分布在红河、茹河、安家川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台阶地上。这些遗址避风向阳,临近水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打石沟遗址。报纸上还说,由于水土流失和土地的开发利用,其中部分被破坏。已发掘的遗址中,石陶器并存。陶器以细泥、夹砂红陶为主,也有灰陶和少量彩陶,属齐家文化。
看来,这些陈旧的窑洞就是新石器古文化遗迹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向窑洞靠近,像走近一座荒漠中的废都。华仔像文物探察专家,从破损的窑壁上取下一块土坯,端详着,不时发出文绉绉的喟叹。
我凑近一看,他手心的土坯与西海固所有土坯没什么两样,粗糙、干裂、不成形状,饱含着疲惫与怆然。这土坯不仅早就发酵过,要再次发酵,必得有人力注入不可。否则,它们只能这样皲裂,或陪伴荒蒿,或风蚀雨淋,或裸露在野。这些土坯从蒙昧时期走来,千万年没有拒绝过人类的造作。它们风化了,可以是大好河山的细微成分,它们遇水可以成泥,有种子埋入可以生根发芽。
我们沿着坡坎,寻找着3000年以前人类生活的蛛丝马迹。那些暴露在外的地穴,地面上有草拌泥和白灰泥的旧痕,有灰坑和灶坑的残迹。这些遗物具有泥土的本质,也具有动物的本质。我俩默默无语,我听得见华仔的呼吸,他正盯着地穴的一条裂缝出神。这时,没有风,野鸭也鸦雀无声,仿佛一切都在回味之中。
华仔就地蹲下,手里还捏着那块土坯。他指着地穴中的一张土台,说:“这或许就是古人用过的餐桌。”
我点了点头。
他又发现了一块条状的石片,说:“这或许是一把锅铲。”
他又盯着地面上的一些划痕说:“这恐怕是古人玩‘狼吃娃娃’留下的棋盘。”
他无意间捏碎了的那块土坯,粉末慢慢落在地上。我有些心疼,可什么也没有说。我发现穴壁上有个窝台,上半部分烟熏黑了。我猜想这窝台是不是古人放过油灯的灯台。
突然,我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擦过。抬头一望,一大群野鸭盘旋在空中。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最后留下几声喑哑的鸣叫。
等它们飞成了黑点,华仔问我:“它们还会回来吗?”
是啊,它们还会回来吗?鸟儿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想着它们会回来;树木被砍掉的时候,我们想着它们还会长出来;错过了时间和机遇,我们还想着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