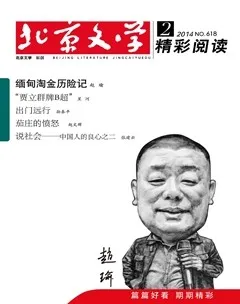雪之空白
1
到乌鲁木齐这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是个能记住的日子。此次来疆,非常偶然,要做一个典型人物的专刊,任务其实很重,我可以不来的,但我争取来了。因为我心里一直揣着一个巨大的愿望:去喀什的英吉沙县,看看老单位。离开那里已经24个年头了。
来机场接我的少卿是工作对口的副处长,从未谋过面,还没出机舱时只通过一次话,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看来我们有眼缘。
出了机场,深呼吸一口久违的熟悉空气,顿觉神清气爽。上车后少卿再一介绍,我才明白缘分就是这样产生的。十几年前,少卿在我服役的那个连队任过主官。我欣喜若狂,三个多小时的飞行疲劳一下子消失不见。我没催促,少卿自顾讲起老单位的情况。据少卿说,基层的营房设施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统一规划建成了新型的现代化营房。原来中队的营房全是土坯房,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拆除,这我是知道的。
少卿后面的话使我相当震惊,他在当主官时,把营院的白杨树砍伐一空。所有的!他还强调了一下。那可是近千棵高大挺拔的西北杨啊,大多是前辈们栽种下的,我刚去时,已经长到碗口粗了。当然,也有后来我们亲手种下的近百棵,这么多年过去,也长到有碗口粗了吧。无一幸免。那随着来自戈壁滩上的风,哗啦啦作响的挺拔的白杨,没了。
为什么?我瞪着两眼,没能控制住情绪,语气里有些愤慨了。
坐在前排的少卿在发动机的噪音里没听到我异常的语气,他轻描淡写地说,营院是四方的,木在里面,就是个困字,不伐不行。当然,这是上面的意思。
我无语,心里非常沉痛,无论基于什么目的,那齐整整的树木最后落得的下场却是悲哀的。我无意评判什么,只是因为内心对距离乌鲁木齐1500多公里的那个小地方依然保持着20多年前的记忆。记忆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无论你离开多久,走了多远,都会扯着你的心扯着你的梦,还要扯着你的——感觉。但我当真是个缺乏想象力的人,居然想象不出被砍伐掉白杨树的营院当下是什么面目。我闭上了眼睛,上飞机前,在西安就没停歇,又坐了三个多小时的飞机,早过了那种不知黑白昼夜的年龄,身心都很疲劳。
少卿还在介绍我当年养马时奋笔疾书的那个场所,那是个破败的饲料房,里面常年充斥着饲料混合着其他一些莫名的气味。只能说那时不光年轻,内心也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无视任何外部环境,仍然能够编织自己的梦。当然,那所房子亦不复存在。截至目前,我算得上是从老单位走得最远的一个吧。有关我的一些传说,被少卿他们演绎得面目全非,我却没有了一点矫正的心思。任它去吧。
早先在飞机上就想好了的,一出机场就吃盘拉条子的欲望显然受到情绪的影响,没那么强烈了。望着车外的积雪袒露在城市的边边角角,似被随意扔弃的抹布,那星星点点闪现出来的雪白一点也没有飘落时的那份纯粹与浪漫。我回到多年前对黑色积雪的厌恶,心里极不是滋味。他们问我最想吃点什么,我沉默着,在他们长时间的等待中,我首先说服了自己,不要刚回到新疆就不愉快,也确实抵抗不住拉条子的诱惑,依然说出“拉条子”三个字。
为什么不呢!世事总在变迁着,没有什么会一成不变地守候在原地,再美好的事物也经不住岁月风寒的侵蚀。
我心里并不释然,对乌鲁木齐的巨大变化惜字如金,少有赞美。这个曾经生活过7年之久的美丽城市,12年来一直占据着我心中的重要位置啊,我怎么能这样熟视无睹呢?
司机拉着我们去的第一家拉条子拌面馆太高档,根据我多年前的经验,这种地方很难吃到可口的饭菜,可我拗不过他们。到了那里,服务员说已过了饭点,没有拌面可吃了。我心欣喜,情绪陡然好转,已是下午4点,内地该准备晚饭了。新疆虽然还早着,但过了午饭时间有两个多小时吧。在我一再要求下,终于在一家小店里吃到了拌面,不是正宗的拉条子,而是手擀面,有些单薄的遗憾,好在手擀面也是我喜好的。我不吃肉,选择的是素菜拌面,觉得很可口,又没啥好客气的,一大盘面吃得很生动。少卿在旁边一再劝阻,再过两三小时就是晚饭,领导办宴接风,别吃得太饱,留点肚子给晚上吧。不是赌气,我平时最恨浪费,就算旁人看来小家子气也罢,在哪里吃饭,都很少剩余。这次也一样没听劝,将一盘拌面吃得一点不剩。
晚上的欢迎宴会,我几乎没吃食物,也没喝白酒。出于礼节,我用红酒与领导、老同事们走完这个流程。
当天晚上的失眠是注定了的。
2
先我一天到来的另三位同事还没展开工作,等我一起商谈采访计划。在我的房间里,与有关处长、干事拟定此行程序一直到晚上11点多才散。我开窗放了一些新鲜空气进屋,以冲淡屋里浓重的烟味。自戒了烟后,这几年我对烟味也敏感了起来,但这不是我失眠的主要原因。当然,少卿所说的老单位砍伐杨树也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像这次的任务,我就很有压力。十几万字,能不能写出新意,都是我所担心的。直到凌晨4点,才迷迷糊糊睡了。临近7点,一如既往地醒来,看窗外还在沉沉的夜色之中,才明白身在新疆,离天亮还早着呢。我曾经熟悉的那个时差毕竟离开我12年了。12年不是一眨眼的工夫,想要迅速地回到原来的状态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也试图使自己尽快适应,就算有那么多年打下的坚实底子,这个时候也派不上用场。时差不是随身的衣物,说换过来就换过来了。再睡是睡不着了,平时也有四五点早醒的时候,能看到窗外由片片的黑,变成浅浅的灰,再由浅灰染为淡淡的白,一切变化得那么宁静自然,于是早醒也就顺理成章。乌鲁木齐也是一个喧嚣的城市,但此刻静谧得毫无边际,若非心中有事,这种静谧绝对是一种享受。我不能坦然地享受这样的凌晨,便拿出任务规划,细细地想着,直到天色泛白。
按照计划,我们的美编老孟和另一个编辑跟着典型人物一整天,要拍出他真实的工作状态,按时间顺序刻画一个真实的普通人。把他们送到典型人物所在单位,我回来与另一编辑召集当地的写手,分配任务,把具体章节细化到每人头上,工作算是展开了,心里才觉得稍稍踏实一些。也可能是一天的忙碌使身体回归了以前的状态,毕竟对新疆的作息时间有过16年的切身体会,适应得也就不知不觉。这个夜晚睡眠恢复了正常。
第三天一大早,天空不似来时那般明媚欢畅,倒是一派阴沉压抑,似有雾霾。多年前的经验告诉我,乌鲁木齐一旦出现这种天气状况,地窝铺机场肯定会出现大雾。果然,刚吃过早饭不久,老孟就提着包从机场赶回来了。昨天拍了一天片子,老孟的任务基本完成,他要圆多年的梦想:去和田看看产玉的地方,或许还有别的想法。昨晚订好机票,凌晨6点就出发去了机场,按时间推算,该到和田的时间,他却返回了招待所。
老孟的返回也警告我,喀什暂时是去不了了。喀什与和田相邻,只是喀什偏北一点,在地理位置上,离乌鲁木齐近一点。但无论远近,于新疆这样宽阔的疆域而言,那都是不短的距离,就是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间,也比很多省与省之间的距离更遥远。这种天气飞机没法起飞和降落,从电视上也看到地窝铺机场延误的航班不少。工作还没头绪,我又不是那种可以为一己意愿便能扔得下所有的豁达之人,心中有事便一切难以实施,反倒成了不小的负担,所以也没打算这两天就去。况且,我对去老单位的欲望,已经没有开始那般强烈了。人就是这样充满了变数,不知道要鼓足了多少勇气才形成的一个念头,却总会因为一些称不上理由的理由,或者根本不需要理由就无端地消散。好在,这只是个人的一个想法,对旁人是构不成大碍的。
3
这天早上,也就是到乌鲁木齐的第四天,从熟睡中醒来,我没听到前几日窗外的喧闹,这个时间不应该有的安静,如海水温存地漫过海滩一般。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不会吧,难道我的预感还能这么准确吗?我起床轻手轻脚走到窗前,深吸了口气,猛地将窗帘拉开,果然,窗外大雪纷飞,整个世界已经银白一片,哪里还看得到其他颜色,那些堆积在路边、树根下的黑色积雪,好像破絮遭逢了新鲜软和的棉花,掩了那一份破败,又变得新鲜和洁净起来。
天若有情,是什么也阻止不了的。
雪下得酣畅淋漓,毫不顾忌季节的更替。这算是春雪了,乌鲁木齐特有的春天景象。离开新疆这么多年,再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我很幸运,没有错过。这天是3月8日,也是一个我们男人值得尊敬的节日。
祝愿天下的母亲、妻子、女儿节日快乐!
突如其来的这场大雪,使我们的情绪都平静了下来。老孟也不再张罗要去和田的事了。早饭时,他神态安然,也不见有多么失落,看来对老天的安排他还是能够接纳的。
这么好的雪天,不出去走走简直是犯罪。我想该去以前住过的地方看看,都在市区,路程也不远,即便天上纷飞着雪也不会有什么行程上的影响。其他两人有写作任务,当然也对我的故地没兴趣。我叫上得了闲的老孟一起出行。
雪下得飘飘扬扬,潇潇洒洒,一如当年。路上的积雪已经没过了鞋面,看这架势,一时半会儿没有止歇的意思。路上的行人车辆依旧,乌鲁木齐人对大雪司空见惯,只要天上不下刀子,就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出行。
我们在大雪纷飞中堵堵停停,走了近一个小时,才从城北赶到城南的家属院。
终于看到了熟悉的院落,尽管墙体刷成了粉红色,可面貌一点都没改变。进门的那一刻,我还是很激动的,要拉老孟下车一起去看我的老住处。他事不关己地缩在车里不下来,嫌雪大弄湿衣服。也是的,这里与他毫不相干,干吗在雪地里遭这份罪呢?我先到老门诊部后加的这个单元门前,抬头望着五楼那个窗口,百感交集。雪片情深意重地纷至沓来,扑进了双眼,但我确定,我眼里不是雪水,是泪,盈满了眼眶。那个窗口里面,曾经有过一间我的带阳台的屋子。我们一家三口与别人在一套三居室里合住了四年,而那个狭小的阳台,就充当了我书房的角色,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就在那里开始我的梦想之旅。我那会儿晚上抽烟是很厉害的,阳台没有暖气,又怕惊扰了熟睡的妻子和女儿,就靠着烟劲来驱逐睡意和寒意。那时候真是年轻,在冰冷的夜里居然也可以大半夜大半夜地熬,最后冷到手脚都麻木时躺进温暖被窝的那一瞬,感觉那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事了。在搬进这间屋之前,我们借住了干休所的一间屋住了几月,更早些时,是租住在城市边沿的土坯民房。民房没有暖气,但有火墙,我们都不会烧火墙,有时火灭了也不知道,就有半夜被冻醒的时候。所以,能拥有一间带暖气的楼房住着,即使是与人合住,我也非常知足了。
在楼下我留了张影,一点都不想上去看,再看也已是别人的居所,找不回原来的样子的。一切都过去了,属于我的,就只有记忆里那份绵延的满足感。
雪越下越大,整个大院似无人居住,在雪花的飞舞中静悄无声。我在院子东边的亭子前转了半圈,亭子的样貌自然也是不变的,连顶端那飘逸的壁画都是老旧的模样。再穿过原来的锅炉房——现在纯粹是垃圾集中点,来到三号楼前,这才是我此次来看的重点。这也是一幢旧式砖混结构的六层楼,南北走向,每个单元每层有三家住户,我住在四楼居中对着楼梯的那套两居室,大概40平方米大小吧。东边没有窗户,只有下午的时候才能看到阳光。这是我在乌鲁木齐时住的最好的居所。这套房子是1999年7月分给我的,粉刷后不到一个月就急匆匆地搬了进去,急于结束两家共用厨房、厕所的历史。只是,我在这套房子里住的时间并不长,外出学习一年,紧跟着就调走了,占用三年,我实际上只住了一年。但我还是爬到四楼,虽然住的年头不长,但总算是我们一家单独居住的处所,有着别样的感情。
没想到,12年过去了,402室的门居然还是我当年刷的那种蛋青色,这让我一下子有了认同感。恍惚12年的时光不在,我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还是每日的朝九晚五,每月总有那么几晚,整夜整夜坐在与厨房相邻的过道里,手边的浓茶依然温温地热着,夜起的女儿蒙眬着一双睡眼偶尔会来抿一口我那苦涩的茶水……我举手竟有敲门进去的冲动,好似这些年自己只不过是出了一趟长差罢了。可敲门进去,屋里还是我熟悉的布置,还是我温婉的妻子、欢跃的女儿吗?我打消了敲门的念头,听说房主已换过几茬,因为是公寓房,多是临时居住,都不屑大动干戈,眼下住的是谁,说不上来。再说了,里面还不一定有人,就别动心思了。我摸了摸门,仅仅是门而已,现在,它们都是别人的!旧有的时光真的不在那里,谁能找得回过去?能找到的,只能是一种缅怀罢了。依旧照相留影,悄然下楼,在大雪中默默离去。
4
雪后定是好天气。看到外面阳光明媚,从窗外飘入的空气清冷甘甜,顿觉神清气爽。饭后,大家一块儿说了说这几天的工作进展情况,心里有了底,商量下一步的计划。老孟坚持还去和田,对别的行动一概不感兴趣。这也是他的作风,执着于心。按原来的计划,该去喀什了,既然工作比较顺,还是大家一起去喀什比较合适。上网一查,全天没有了去喀什的机票,这也难怪,气候突变,积压下好多航班,只能等等再说了。去和田的机票却一点都不紧张,可这对我绝对构不成诱惑,没有诱惑,自然就没有动力。老孟当即订了下午7点去和田的航班,上午乐滋滋地要去玉石市场转转。我本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的,但玉本质温润,是可喜之物,去看看也无妨。谁知一看还真吓一跳,这价钱涨得也太离谱了。反正不是我喜欢的玩意儿,涨得再高与我关系不大。老孟却说,要是我离开新疆那年,买些玉石存放到现在,可就发大了。我对曾经的好多事都后悔过,唯独对金钱,除过工资、稿费,向来对其他来路的金钱不抱任何幻想,从不羡慕一夜暴富的那些人。钱多自然是好,可于我,有了这样的好,说不定就会有那样的不好,万事万物相辅相成,也有相克,物极必反的事例在我的周遭也不是没有见过。何况我这种性情的人,适合的就是平淡安宁的生活,活在太多的欲望里反而喘不过气来,何必呢!所以,我不认为自己错过了赚钱的机会,虽然未曾大富大贵,却对自己眼下的生活状态非常满足。有多少钱就过多少钱的日子,总不至于为赚一百块钱却非要一千块甚至一万块钱的奢华生活而兀自纠结,那太耗损人了。当然,我也见过蚊子身上都可以抠下几两肉,却绝不舍得花几毛钱买个馒头的人,这样的钱就算这雪一样伸手便可抱个满怀,却又如何?
晚饭时,才知道老孟半下午提着包又奔赴机场,实现他的和田之旅了。我说,不会再看到老孟提着包回来了吧。大家都说,今天肯定不会,天气这么好,这个时间段,老孟该在飞机上,过一会儿就到和田了。我们安下心来,为一个同事庆祝生日。可是,祝福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响了,是老孟。以为是他到了和田报平安的,正纳闷这不是他的风格,他是美编,总是一脸的清高样,瞧着我们都是凡人,逢年过节的他都不屑回一个我们这些凡人短信的,更别提他会给我们报平安了。可电话的确是他打来的。他的那个航班取消,他又一次提着包从机场往回赶来。
万事万物皆由缘而定,我只能说,老孟与和田的缘分没到。
我与喀什呢?却太有缘分了,从17岁到26岁,整整9年的时光,是在距乌鲁木齐1474公里的那个叫喀什和英吉沙的地方度过的。那时还没通火车,除过飞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得乘坐三天半的汽车。每次经过漫长的颠簸回趟老家,总觉得那里是天边边,实在是太遥远了,什么时候才能不那么遥远?可是只要返回那里,心里才能平静下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时,觉得我与那里脱不了干系的,那里才是我的根本所在。更不用说,那里是我的成长期、充实期、彷徨期,也是今天的——酝酿期。
可是,这次我怎么就没法去喀什?不是天气的原因,就是没有了机票。总之,一直没有顺着我的意愿实现。后来,我作出决定,此次不去喀什了。其实,我坚持要去,还是有办法的,可以等待别人的退票。就好像前几天在西安,不就是这样等到来乌鲁木齐的机票嘛。
是我与喀什的缘分已经没有了?还是19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我们的缘分就已经到头了?
不是。我与喀什永远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生命里注进了9年的历程,那9年如今依旧鲜明在我的心中。好像只要回首,也就只是寸步之遥。这种缘分,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断了呢?
送走客人,我来到户外,在凛冽的寒风中,踩着厚实的积雪,望着白茫茫的大地,脑子里盘旋着的全是1474公里之外的喀什下面,一个叫英吉沙的小县城。我于1985年1月21日中午到达县城北边的那个四方院子,直到1989年1月30日离开,什么时候我都清楚地记得,那四年零九天,我是在成排参天的白杨树环绕的那个院子里度过的。那些白杨,经常被来自戈壁滩上的风吹出一片哗啦啦的声音,那些骄傲的挺拔的白杨!
那种记忆是永远都抹不去的,无论怎样努力,它们都一直在,不曾消减,连模糊一下都不肯。
只是如今,我还有去的必要吗?没有了那些白杨树,可是,我现在绝对没有责怪少卿,还有其他人的意思。
可能上天也不想让我去吧。
没法找到答案。只有脚下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痛苦却有力量的叫声,充斥着我的耳膜,使我的大脑像这雪地一般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