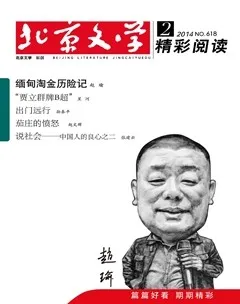液体的精灵与鬼魅
酒是液体,又不同于一般的水。就像文学不同于生活。酒应该是好东西,把日子浸熟了,酿出来醇厚的精华;将延续生命而进行的餐饮,变得充满了况味儿;把平淡的心绪撩拨得火烧火燎,并带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古往今来,酒与豪气,与爱情,与诗歌,与荡气回肠,与壮怀激烈,与视死如归,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酒也害了不少人,坏了许多事儿。酒乱性,与色捆在一起,有人借着酒劲儿出轨;酒迷心,有人在酒色中变节;酒壮怂人胆,有人酒后说些不该说的话,甚至做出不该做的事儿;酒驾约等于杀人,自不必说。这些年,酒桌上的故事和猫儿腻多了去了,酒早已成了腐败的媒介和帮凶。所以,酒这液体的鬼魅,到底是精灵,还是祸水,也就成了见仁见智的东西。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在村里当干部,驻村部队请吃饭,那天,我第一次见识了几位部队干部和村人用搪瓷缸子豪饮的阵势。心想,酒还可以这样喝。以后,我到公社当干部,又到政府部门工作。在工作生涯中,长了酒的见识,也积累了许多人与酒的故事。见证了酒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骤然兴起,并且久盛不衰。当然,这与改革开放本身没关系。刚到公社工作的时候,发现公社的老书记尹家信也爱喝酒,常和找他的几个老伙伴儿喝上几盅儿。来了客人,让食堂大师傅炒两个菜,划他的饭票,酒更是自己拿。那年夏天,公社机关每晚义务劳动,盖房子,干到很晚。大家伙儿都饿了,就让食堂加顿晚餐。为了解乏,还买了几瓶二锅头,都记了老书记的账。房子盖好了,老书记自己多付了几百元的饭费,还有酒钱。那时候,不要钱的饭只有每年的三级干部会议。一人两个馒头,一碗白菜粉条炖肉,不可能有酒。
1980年,我调到一家政府部门工作。部门的老主任李兆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平时也爱喝几盅儿。记得他不喝曲酒和低度酒,只喝高度的。老主任讲话时总这样调侃:“让我管建设,我是外行,我没有水平,只有酒瓶……”他还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年没去宝林寺酒厂当厂长。如果去了,整天泡在酒缸里,那该多带劲。可见他对酒的情感有多深。老主任爱喝酒,但酒风极正。都是自己掏腰包,与公家无关,与公款无关。那时候,建委的公用车是一辆绿色帆布棚的北京吉普。老主任每次到市里开会办事,只要是中午回不来,他就让司机灌好一暖壶开水,买上几个夹了肉的烧饼,中午蹲在路边树荫底下就吃了。后来,他带我们进城,就请我们到“东来顺”吃涮羊肉,或到“砂锅居”吃砂锅吊子和砂锅丸子。早晨,车子开到半路上,他就开始筹划午饭。“你们谁也别和我争,今天去砂锅居。谁让我是领导,我的工资高呢。下午还有事,酒就算了。”大家嘿嘿一笑,谁也不去和他争。只盼着中午的美餐。到了春节,机关会餐。他的方案是每人从家里带来一个菜,酒他自己包。白的红的啤的,管够。大家喝着老主任花钱买的酒,品尝着“百家菜”,畅谈一年的工作成果,其乐融融。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公款吃喝渐渐“放开”了,把离了休的老主任气得先是牢骚满腹,后来只剩摇头叹气的份儿了。
区建筑公司的经理叫李梦麒,是陕西人,酒量很大,酒瘾也不小。公司承建了许多大的工程:龙泉宾馆、高井电厂2号4号凉水塔、龙口灰库等等。工程干得很漂亮。当时的市领导都接见过李梦麒。工程干到哪里,他的办公室就搬到哪里。办公室里除了办公用品,还有一堆酒瓶子。但什么时间喝酒,什么时间不能喝,怎样喝酒,李梦麒心里非常有准儿。为了安全,他严格规定,不论是谁,中午一律不准喝酒。抢龙泉宾馆工期的时候,他还规定,工程不竣工,谁都不准喝酒。后来,看到工人们的出色表现,主管工程的副区长解除了李梦麒的禁酒令。并特意安排了一顿酒宴,犒劳施工的干部职工。李梦麒喝酒不仅都是自己花钱买,他还从不喝孤酒。平时,他总是把基层施工队的干部、工人师傅和机关骨干三三两两地叫到自己家里,让夫人老韩给做饭,大伙儿一块喝。有一次,在面粉厂施工,吃晚饭的时候,李梦麒把仅有的一碟咸菜丝摆好,把夫人给他带的一饭盒饺子放在火炉上熥热,再一个个夹到饭盒盖上,然后,从床底下抻出两瓶酒,叫过来几个人,有滋有味儿地喝上了。
那时,建筑公司是国家二级建筑企业,家底越来越厚,可李梦麒公私分明,还从不讲排场。出差坐飞机,他让别人吃机场的饭,自己从包里掏出烙饼,就着开水嚼上了。在外地吃饭馆,他舍不得花餐巾纸钱,掏出从宾馆带出的手纸,每人发一块儿。有一年,他请我随公司到海南考察工程。住公司在海口龙蛇坡买下的房子,每顿饭都是他亲自下厨给我们做。喝的酒都是两块多钱一瓶的二锅头。
在或高或低的度数里,这些人始终都很清醒。酒在这些人那里,永远都是好东西。喝酒,除了是他们的一种嗜好,还成为他们与群众交流沟通的融合剂。在普通人的眼里,因为酒,他们变得更有范儿,他们的人格更充满了魅力。由于他们品行和作风的清正,也没有坏了酒的名声。其实,人能否把持自己,关键是人,不能怨酒。也不能怪社会和工作的氛围。老主任李兆营常说一句话,八年抗战都过来了,如今,不能淹死在酒缸里。时至今日,两位老领导已经作古,那位经理也住进了敬老院。对他们当年酒风的颂扬,权当是对他们高尚人格和廉洁作风的追思与怀念。
如果总像这些老领导那样,掏自己腰包干公家的事儿,不仅需要楷模式的觉悟,也不公平。国家作出相应的工作用餐规定,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这些年,以酒风引领的公款吃喝愈演愈烈,哪儿还有什么标准可言,范围大得没了边儿。不论什么事都可以作为吃喝的由头儿。有理由时理直气壮地吃喝,没有理由找理由也心安理得地吃喝。餐饮业的收入与发展,许多来自单位的支票。多少美味佳肴倒进饭店的泔水桶。舌尖上的浪费是一回事儿,更大的问题是就像害虫啃树叶儿,党和国家的肌体与风气被啃得千疮百孔。还害了不少的干部。那些年,酒量几乎成了当干部,特别是当领导干部的一条不成文的标准。能在酒场上叱咤风云,就能在官场上称心得意。有人整天喝着公家的酒,多少干点公家的事儿,也有人用公家的酒为自己拉关系铺路,织成一张酒的关系网,用酒瓶子搭建了一个往上爬的阶梯。酒桌上推杯换盏的背后,上演了一幕幕相互利用,以权谋私的丑剧。
那时候起,区县纷纷办起了各种名目的什么“节”。这些节都为了给发展经济搭台,但也都是公款吃喝的高潮和“节点”。各区县各部门之间相互宴请,“节日”期间,几乎全地区的饭店爆满,真有些“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另一种韵味。甚至,有的部门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喝,顿顿喝,这种“酒精考验”还真得要点功夫。所以,有时候,没有酒量儿的人当不了领导,当不长领导,或者当不大领导。有人在酒场上失败,在官场上也失意。我曾遇到过一位刚上任就被酒撂倒的领导。一天,我值班,领导被司机搀扶着回来。先是吐得一塌糊涂,再往后就鼻孔冒血。我和司机立即送他到医院。一通洗胃,打点滴,才缓过劲儿来。没过几天,这位领导又因到外区参加一个什么“节”,喝成了中风,就再也没来上班。这只是身体受损,还有的因为喝酒要了命。我们的一位本是贫寒出身的大学生副主任,后来到一公司当经理。在酒桌上与财务科长暧昧了。后因相互勾结贪污挪用公款双双入狱。财务科长刑满释放,经理被判死缓,后在保外就医时病死。
酒在这时候,就成了毒品,受害者与害人者很难分清。喝坏了党风,带坏了民风,也败坏了酒风。党和国家在廉政建设中,一直重视惩治吃喝上的腐败。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下大力气遏制铺张浪费,狠刹公款吃喝风,符合党心民心。
其实,家人、好友之间偶尔聚在一起小酌,无可非议。那时喝的不是酒,是友情,是心绪。节日或喜庆的日子喝点酒也是很正常的事儿。酒是饮品,但品饮的是精神。像酒一样,任何事情也都有个度数儿,如果三天两头聚在一起喝,总是“拿酒说事儿”,永远走不出酒局,甚至继续着“公款消费”,酒就彻底变了味儿。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