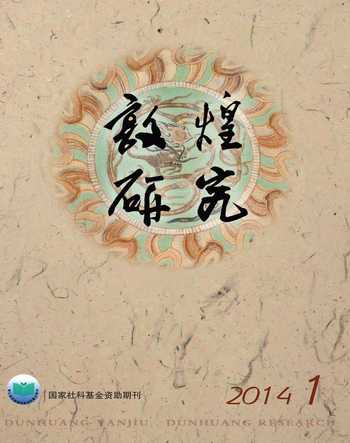隋唐宋初写经社邑考略
赵青山
内容摘要:写经社邑是一群为积累功德、获取福报的信徒组成的抄写佛经的团体。其规模视所抄写的佛经多寡和财力大小而定。写经社邑内部组织较为简单,所需财力由邑子承担,抄写的佛经送入寺院供养。佛经抄写完毕,写经邑随之解散。
关键词:社邑;写经;敦煌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087-07
社邑本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1],秦汉之际,民众出于经济互助、共同兴趣、宗教信仰等目的,自发结成社团,这便是在官方体系滋生出的社邑的新形式:民间私社。佛教东传后,借用中土民间私社组织形式,实践诸如造像、开窟、诵经、行斋等种种活动。至于佛教社邑内部组织情况、规模等问题,魏晋南北朝石刻造像题记有一定反映,但相对于历史久远、活动频繁的佛教社邑而言,造像题记还不足以体现其全貌。敦煌文献的发现为全面、深入了解佛教社邑提供了宝贵材料,中外学者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①。敦煌地区的佛教社邑种类非常多,可见者有行像社(P.2049V、P.3234V)、修佛堂社(P.496)、燃灯社(S.5828)、造窟社(S.3540)、写经社等。
其中,写经社邑是由一群为积累功德、获取福报的信徒组成的抄写佛经的团体。笔者共搜集到有关11个社邑的16条资料(见表1),本文拟围绕这几件材料,就写经社邑的规模、邑子成分、内部组成、运行情况等问题试做分析,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如表1所示,有关写经社邑的材料年代最早者为5—6世纪,最晚者为太平兴国三年,时间跨度近4个世纪。相对历史长河而言,相关材料较为稀少。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写经社邑若隐若现不绝于史,显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就材料反映的地域而言,涉及敦煌、吐鲁番及中原地区,具有广泛性。可以想象得到,隋唐宋初,写经社邑比我们搜集到的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更为普遍。
一 写经社邑的规模及其类型
现有材料表明,写经社邑规模大小不一,多者三十几人,小者四五人。写经社邑参与人数最多的是新疆吐峪沟出土的Ch.5509,该写卷残缺不全,高22.9cm,长89.2cm[4]。兹录文如下:
1.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2. 盖闻一乘妙理,法界传通,十二部经,金口所演。况复■
3. 岭真空之教,王□灭罪之文,火宅方便之言,险■
4. 善权之说,莫不受持顶戴,即福利无边,书■
5. 弘宣,还生万善。今有佛弟子比丘惠德、齐■
6. 欢德、赵永伯、范守□、赵众洛、范阿隆、赵愿洛、宋客■ ■
7. 洛、赵延洛、张君信、索绪子、张憧信、范历德、赵隆轨、王儁■
8. 刘常洛、范慈隆、赵武隆、张丰洛、张定绪、张君德、范■
9. 范进住、赵隆子、竹根至、刘明伯、赵恶仁、范黑眼等,敬人■
10. 往劫,重正法于此生,弃形命而不难,舍珍财而转■
11. 遂。即人人割宝□□□珍,敬写《法华》一部。其经■
12. 耳闻,消烦荡秽,心念口诵,证寂灭乐。用斯■
13. 愿合舍七祖魂灵,觐奉世雄,见在尊长■
14. 灭(?)儿,自身福备,家口善兹,小果悟大,真常■
15. 倍加福佑。外道归正,龙鬼兴慈,有识
16. □□含灵,俱沾圣道。
本件文书,池田温先生推测约为7世纪前半期[5]。陈国灿先生通过对比记录有赵延洛(第7行)、张定绪(第8行)、赵恶仁(第9行)等人信息的其他吐鲁番文献年代,认为Ch.5509《妙法莲华经》完成于“咸亨三年(672)前不久”[6]。文欣先生在探讨200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95号墓出土的一组文书时,也曾利用Ch.5509做过比对研究,指出Ch.5509中的范历德(第7行)、范慈隆(第8行)、张定绪(第8行)、赵隆子(第9行)四人又出现在阿斯塔那墓出土的2004TAM395《名籍》及61号墓十二件差科簿底稿中,得出与陈国灿先生大致相同的结论,认为Ch.5509年代大致在670年前后{1}。
此件文书,可识别的邑子共30人,从文书残损情况看,该社成员应在35人左右。与此规模相当的是P.2086,共有邑人32人,S.1415和BD14519大兴善寺写经邑的规模紧接其后,共31人,这三个写经社邑是规模最大者。中型规模的写经邑则在十几人左右,如Дх.1362志忍写经社邑共12人。最小者为P.3315开宝十一年王会长等四人组成的写经社邑。
至于写经邑人的成分,就所见材料看,一类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优婆夷社邑。BD00985《大方广佛华严经》由“优婆夷邑敬造”。此件写本没有明确纪年,池田温先生定为6世纪后期[5]157,《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认为属5—6世纪南北朝时期,笔者查阅该件文书图片,此卷隶书书写,南北朝书风浓厚[7],故笔者以为年代定为5—6世纪较为合适。此外,藤井有邻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7,是“开皇三年十月八日,优婆夷邑敬造”,此件文书是有确切纪年最早的优婆夷邑写经,也是“敦煌地区最早出现的由女性组成的佛教团体的记载”[8]。又津艺262《金刚般若经》是“天宝十二载五月廿三日优婆夷社写”[9]。这三条题记仅寥寥数语,我们无从考察优婆夷写经邑的规模、写经具体缘由、内部运作情况以及成员的社会背景等问题。
孟宪实先生曾指出,女人社中的成员具有一定的经济独立性和经济地位[10]。郝春文先生也认为女人社成员是由寡妇或单身女这几类在家中地位较高的女性组成[11]。如果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话,优婆夷写经邑的成员在家中也拥有较高的地位,并且有一定的经济支配能力。那么,由优婆夷组成的写经社邑与其他类写经社邑在社约、内部组织、选写的佛经等方面是否有不同之处,因材料有限,还不能做出具体回答。
第二类全部由男性组成,如Ch.5509,但无法确认该社邑子是否受过三皈五戒。第三类则邑子性别及身份不限,僧俗男女均可加入,如Дх.1362和上图088V。
社邑中一般有僧人参加,Ch.5509写经社邑中有比丘惠德,P.2086写经社邑中俗人有31人,僧人1人。如宁可先生所言:“(佛教社邑)与寺院和僧人有密切关系,多数是寺院和僧团的外围组织,僧人参加或领导的也不在少数。”[1]僧人在写经社邑中很有可能扮演指导和教化邑子的角色。
二 写经社邑内部组成
那么,写经社邑的内部组织如何?在诸多写经社邑题记中,S.1415和BD14519提到了写经社邑中职务设置情况:
大兴善寺邑长孙略。
王昶在《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认为,邑长是“邑中助缘者”,叙述较为笼统。按敦煌资料记载,社长通常为社的首领,是“三官”之一,由社人推举产生[1],负责社邑内部运作。而唐五代宋初,社又可称为社邑、邑、义邑等{1},所以邑长的职责如同社长。
S.1415和BD14519题记极为简略,仅书邑长之名。按常理,题记书写供养者姓名时,是遵循尊卑长幼顺序排列的,即先写地位显赫或在社邑中承担主要职责者,一般邑子胪列其后。若无足够的书写空间,出资少、地位低的邑子的姓名常略而不书。在S.1415和BD14519题记中,仅有邑长孙略之名,其余邑子则一概不提,表明在这个写经社邑中,邑长孙略是主要负责人,也是级别最高的邑子,而被省略姓名的诸位邑子,其身份应当较为普通。因此可以推断,组织书写S.1415和BD14519的社邑,其内部结构比较简单,只有邑长和诸邑子组成,而没有诸如三官之类的职务。
此外,依据题记,该写经社邑隶属于大兴善寺,故邑长称为“大兴善寺邑长”,这也表明,隋唐一些社邑依寺而设。大兴善寺为隋唐著名寺院,位于长安城内朱雀街东之靖善坊[12],是隋代的国寺和国立译经馆,对隋唐的佛教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等诸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13]。敦煌地区的寺院亦存在写经社邑。Дх.1362《大宝积经》题记:
1. 当寺僧上伴、志忍一人新戒,释门法律法寿、法律戒慈、
2. 法律戒昌、法律庆因、法律义勋、法律戒忍、法律戒论、
3. 法师戒护、律师保戒、[沙]弥道行、造食女人阿阴氏
4. 壹拾贰人等,同发无上胜心,敬写《大宝积经》壹部,施
5. 入永安寺者,国愿(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佛日重明,
6. 法轮常转。己躬清吉,保百载之延长,合寺康强,
7. 契迁年之快乐。永安塞表,八方伏叹,四野钦风
8. 而仰化。复愿先亡远代、七世灵魂,承斯功德之
9. 因,速遇龙华之会。然后十类四生之辈,含灵
10. 无蠢动之徒,赖此胜缘,咸登觉道。太平兴国
11. 三年(978)戊寅岁次三月十五日下手,比至六月
12. 十五日毕功断手题记。[14]
上图088《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纸背为Дх.1362的底稿,内容不完整,无Дх.1362第5行“国愿(愿国)安人泰”至第10行“咸登觉道”之间的发愿部分。此外,后又有杂写“清信弟子某乙发无上胜心敬写《大宝积经》一部施入永安寺”,僧法崇“又写《大悲经》三卷、《最胜王经》一部、《八阳经》一卷”施入“当界佛堂”,祈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
永安寺(第5行)于吐蕃统治初期辰年(788)初见其名(S.2729),至北宋天禧三年(1019)犹存(《天禧塔记》)[15]。Дх.1362中共有7位法律,那么这些法律是否全部来自永安寺?这涉及Дх.1362诸邑子来源问题。事实上,唐末宋初,敦煌僧职伪滥,十羊九牧。P.4981是某寺召集当寺徒众回寺修葺被“水漂破坏”寺舍的转帖,兹移录如下:
1. 当寺 转帖
2. 都僧录和尚 索僧正 解僧正 氾僧正 大刘法律 大
3. 罗法律 张法律 □法律 祥刘法律 马法律 平法律 曹法律
4. □法律 □法律 小吴法律 武法师 张法师 吴法师
5. □藏 法证 道宽 定□ 慈方 治力 大力 法胜
6. 福常 愿安 应林 宏志 承定 会集 弥保集 愿保
7. □真 理详 理□ 教兴 保达 子□ 定兴 □儿
8. 黑子 丑儿 理乘 再富 不勿 安通 臾儿 愿遂
9. 顺清 保兴 丑胡 苟奴 富盈
10. 右件徒众,今缘裴寺水漂破坏,切要众
11. 力修助。僧官各锕镢壹个,散众锹镢一事,又
12. 二人落辇一枚。帖至,限今月十四日卯时,
13. 依寺头取齐。捉二人后到,决丈(杖)七下,全不来
14. 罚酒一瓮,的无容舍(赦)。其帖速分付。帖周切
15. 付本司,用凭告罚。
16. 闰三月十三日蓝官僧正帖□。
此件文书,山本达郎先生等定为961年前后{1},即建隆二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执政时期。该寺全部僧人和依附人口共计55人,僧人约38人左右,法律11人,法律约占僧人总数的29%。此种现象并非孤立存在,后唐同光年间(923—926)P.2250《诸寺僧名录》显示,龙兴寺共有法律4人、金光明寺法律5人,均所见法律之职伪滥。
与S.5406相比,永安寺可谓小巫见大巫。所以,永安寺写经社邑中的7位法律应当皆为当寺僧职无疑。此外,题记言“当寺僧”、“合寺”等,是以本寺僧人口吻叙述的。因此,永安寺写经社邑中的12位邑子,也全部来自永安寺。与上述诸写经社邑不同的是,该社邑除造食女人(第3行)之外,全部为僧人。
那么这12位邑子是否就是当寺全部人口?从吐蕃时期到宋初,该寺僧人和依附人口数一直处于变化中。如辰年有僧11人(S.2729《吐蕃辰年(788?)三月五日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戌年(818)“主客僧总卅六人”(S.545《永安寺僧慧照上永安寺应管主客僧名牒》),寺户六户(S.542《吐蕃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仕车牛役簿》);后唐同光年间有僧(含沙弥)38人(P.2250《诸寺僧名录》)[13]630。那么50年后,亦即太平兴国时期,永安寺寺内人口数又有怎样的变化,由于缺乏材料,无从考证。
但笔者以为,Дх.1362《大宝积经》邑子并非永安寺全部人口。上图088V作为Дх.1362的底稿,多有修改,行间亦有杂写。在这份底稿中,写经社邑成员“计壹拾肆人”,较Дх.1362“壹拾贰人”多两人,仔细比对人名,可知多出“秀守”等二人,此二人为“当寺僧”。说明永安寺除Дх.1362写经社邑中的12人外,必定还有其他僧人或依附人口存在。
所以,一寺写经社邑并不涵盖寺内全部人口,只是寺内一部分人自愿组成的祈福团体,在邑子入社方面也没有严格的身份规定,无论是大德法律,还是新戒沙弥及地位卑微的依附人口均可以加入。邑子来自同一寺院,方便社邑事项的通知、邑子集合及各类活动的展开,显示了地域因素在社邑组织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仅体现在寺院社邑中,文欣先生指出,Ch.5509题记中所见人名,“其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在一个乡的范围之内”,而且大体主要为武城乡人{2},同样体现了地域因素的影响。
三 写经社邑的运行
写经社邑的费用一般来自社邑成员的捐赠,如Ch.5509:
舍珍财而转■,遂即人人割宝□□珍,敬写法华一部。[5]194
P.3351表述的更为清楚:
(前略)
1. 《多心经》一卷,开宝柒年戊寅正月廿八日,金光明寺僧
2. 王会长、张僧奴、令狐富通、阎延定四人等,舍《观音》、《多心经》一卷。
3. 后有人见莫怪者,及是人来莫怪者,及怪者亡性,莫见佛面。
4. 舍经师兄张僧奴记耳者(押)。王会长、巳延定麦一斗。
(后略)
延定在第2行中书写为“阎延定”,但在第4行中为“巳延定”,其中一处必为书写错误。如上所记,王会长和延定输入麦一斗作为写经的开销。
邑人是否直接参加书写佛经视情况而定。有的社邑成员不参与写经,而是雇人书写,如同造像社邑一样,邑人不直接雕刻佛像而是出资雇佣专门的匠人。如P.2056和书博藏《阿毗昙毗婆沙》写经邑中,佛经由雇佣来的经生沈弘书写,邑子道爽承担校对职责。除此之外,其他邑人好像并没有参加到写经队伍中。
在敦煌地区也存在社邑雇请专门人员抄写佛经的情况。BD05467《妙法莲华经》卷4题记:“社经。王瀚。”王瀚是人于BD00244《佛名经》卷12题记中亦有出现:“佛弟子僧裴法达、樊法琳、曹寺主等,奉为十方一切众生,愿见闻觉知,写记。经生王瀚。”又BD00018《维摩诘经》卷中题记:“奉为西州僧昔道萼写记。经生王瀚。”S.3909:“王瀚,龙兴。”BD00099《无量寿宗要经》题记:“已前六卷,纸卅张。王瀚写。眼暗书,不得不放,知之。”可见,王瀚是一位以抄经为生的书手。实际上,是人为吐蕃时期抄经生,在吐蕃官府组织抄写的《无量寿宗要经》题记中屡见其名,如S.1982、S.3036、S.3891、S.5314、S.3913、BD03398(雨98)、BD01072(辰72)、BD04891(巨91)、BD07771(始71)、BD08568(推68)[5]390,等等。“社经。王瀚”的题记说明,该社邑是雇佣专门的写经生抄写佛经的。
而P.3351V王会长四人写经邑中情况却相反,写经记录言:“戊寅年三月拾柒日金光明寺僧张僧奴写《观音经》一卷(押)”、“戊寅年贰月拾柒日金光明寺僧王会长自手。”这是邑子们自己抄写佛经的情况,或许这与他们抄写的佛经部头较小有关,抑或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雇佣抄经生,所以选择了诸如《观音经》篇幅短小的经文。
在各种佛教社邑中,有些是长期存在的,如行像社和燃灯社,这种时节性很强的社邑虽然一年可能只有一次集会,但是每年节庆到来之际,邑人都将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汇集并交纳物品、讨论社邑活动和社条等相关事宜。此类宗教社邑,因举办的活动有很强的周期性和稳定性,可一直持续下去。持续时间更为久远的是带有经济互助色彩的社邑,可延续几代不废,其社邑成员在一定时间内也基本固定不变。如S.6537(6V—7V)是净土寺僧慧信书写的《立社条样式》,其中社条云:“凡为立社,切要(久)居,本身若去(云)亡,便须子孙丞(承)受,不得妄说辞理。格(恪)例合追游,直至绝嗣无人,不许遣他枝眷。”[16]从条规看,邑人的责任子孙承袭,表明此类社邑可世代相传,不会因人而废。与上述这些社邑相比,写经邑可能是临时性的组织,当佛经抄写完毕后,写经邑也随之解散。孟宪实先生指出,敦煌结社的功能归纳为三种:一、生产互助型;二、生活互助型;三、精神方面的如宗教功德结社。“如果涉及具体的结社,这三种分类方式都不能保持纯粹,单一功能的结社是存在的,小型和限时的结社常常是单一功能的结社。而大型和长期的结社则多属于复合型功能结社。”[17]抄经结社的功能就在于通过抄写佛经获得福报,属于孟先生所言第三类,目的较为单纯,是短时性的。正因如此,写经社邑也并无如S.6537(6V—7V)那样严格的社条社规,邑子加入或退出社邑比较自由,如上图088V所示,打草稿时还有14人参加,正式书写时“秀守”等两人临时退出。
那么,写经社邑书写的佛经如何供养呢?从已掌握的材料看,大部分社邑是将书写好的佛经施入寺院,流通供养。如Дх.1362和上图003V写经邑将书写的一部《大宝积经》“施入永安寺”,P.3351金光明寺王会长四人写经邑亦是如此。《太平广记》引《冥报记》载:“有人偷窃社户所造藏经出货,(僧)义孚以廉价赎之,其羡财遂为所有。”[18]也表明寺院经藏中藏有社户书写的佛经。
四 余 论
宗教社邑是指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号召下,为达成某一事项,如雕刻佛像、开凿洞窟、行像浴佛等,但苦于经济能力所限,为实现资源和财力的集中而组成的社会团体。抄经社邑亦不例外,邑子们首先虔诚地相信,抄写佛经具有殊胜功德,如Ch.5509所言:“……耳闻,消烦荡秽,心念口诵,证寂灭乐。”又P.2086言:“求八字灭苦幽暗,四等出彼欲海者哉。略等希玄正路,为备三佛出世,桥梁度济。”此其一。其二,抄经社邑抄写的佛经卷数一般较大,如Дх.1362永安寺社邑发愿抄写《大宝积经》一部,抄写时间从“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次三月十五日下手,比至六月十五日毕功断手”,历时三月。P.2056以尉迟宝林为首的社邑则写“一切尊经”,规模更为宏大。如此浩大的工程凭一人之力难以完成。因此,整合大家财力显得尤为必要。当然,社邑所抄佛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邑规模大小和社内邑子人数。如果抄写的是小部头佛经,则微型社邑即可完成,如P.3351抄写的是《心经》和《观音经》,故而社邑仅四人,或者说,因只能召集到四人,故而选择抄写了小部头的佛经。
写经社邑作为宗教团体,在相同的信仰号召下,将来自不同背景、地位和身份的人整合在一起。如Дх.1362写经社邑中的造食女人,是敦煌寺院粟麦入破历中经常出现的人物{1}。造食女属于寺院依附人口,在寺院举行的各种活动,如行像、转经以及各种节日、筵席、丧事中,负责制造饮食。造食女在寺院中地位低下,分配到的食物往往只有“粗面”、“黑面”或“粟面”等,很少能吃到其他僧人食用的白面制成的食物[19]。而Дх.1362《大宝积经》显示,经济拮据、身份卑微的造食女人,却能够加入到由法律等地位尊贵的僧人组成的写经社邑中,可见写经社邑看重的是信仰的异同,体现了“贵贱一般”、“如兄如弟”的精神。在写经社邑这类空间内,身份卑微者或许暂时能够找到些许尊严和存在的价值,共同的宗教信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冲淡平日体现在身份上的森严的等级秩序,为卑微者获得身份认同提供了机会。
社邑虽为民间私人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社邑可以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首先,官府一直在引导民间社邑活动。其次,社邑活动威胁到国家权威时,国家完全可以用律令的形式将其取缔,如高宗咸亨五年(674)五月敕令禁断“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20]。最后,社邑本身也体现出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在社邑抄写的佛经题记发愿中,“国”、“君王”、“皇帝皇后”等屡屡成为邑子们祈愿对象,如Дх.1362《大宝积经》:“国愿(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P.2086:“君王诸邑,檀起(越)家国,含灵抱识,同归法界。”P.2056尉迟宝林社邑希冀写经功德“上资皇帝皇后”,并且在写到“皇帝皇后”时使用平抬格式。尉迟宝林身为朝廷官员,或许更能体会到朝廷对民间结社的芥蒂之心,因此在既想表达其奉佛之虔诚,同时又不愿背负“结构朋党,作排山社”(S.1344《开元户部格》)的罪名,或被指责为“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征求”,故而在以其为首的写经社邑发愿文中,处处体现出对以皇帝为象征的国家权力的认同。
参考文献:
[1]宁可.述“社邑”[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1):12.
[2]矶部彰.中村不折旧蔵禹域墨书集成: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蔵(中)[M].东京:二玄社,2005:20.
[3]王海萍.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残经书法艺术管窥[C]//第二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55-158.
[4]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21.
[5]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M].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194.
[6]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89-90.
[7]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4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307.
[8]郝春文.再论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结社[C]//郑炳林,主编.郝春文敦煌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74.
[9]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
[10]孟宪实.试论敦煌的妇女结社[J].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99.
[11]郝春文.再论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结社[J].敦煌研究,2006(6):105.
[12]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876.
[13]王亚荣.大兴善寺与隋代佛教[C]//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编.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6-29.
[14]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17.
[15]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30.
[16]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83.
[17]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1.
[18]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814.
[19]高启安.旨酒羔羊:敦煌的饮食文化[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119.
[20]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