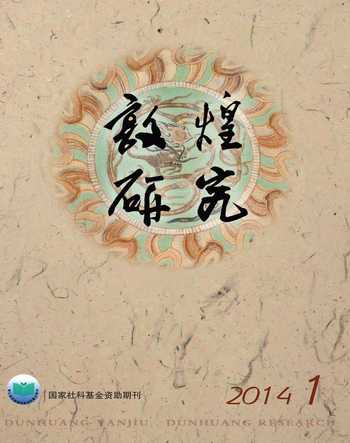燉煌的词源再探讨
谭世宝
内容摘要:有关燉(焞、敦)煌的词源问题,是伴随着敦煌学产生而一直吸引众多中外学者关注研究的跨世纪难题,迄今已经成为聚讼不决的百年历史悬案。有关燉煌等地名的族源及意义成为难以理解的历史问题,乃因时过境迁,使得原来完整的汉朝历史档案资料在两千多年来不断递减的过程中变成碎片流传于今世,而导致当代片面的历史研究者的困惑不断增加。特别是由于有关问题实际是由原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史记》、《汉书》缺乏全面深入研究理解的现代欧洲汉学家提出的伪问题,然后由他们及同样一知半解的日本汉学家对伪问题作出的种种错答案,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一些误论的影响,而导致了所谓燉煌为胡语的音译词之说在中国普遍流行,弄清这个百年悬案,必须源流都要厘清,既要把百多年来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史基本研究清楚,同时还要把《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的源流弄清楚。本文通过对有关传世文献源流的分析研究,再一次强调“燉煌”为汉语非胡语音译。
关键词:月氏;匈奴语;土著居民;名从主人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121-10
有关燉(焞、敦)煌的词源问题,是伴随着敦煌学产生而一直吸引众多中外学者关注研究的跨世纪难题,迄今已经成为聚讼不决的百年历史悬案。在此再作一些新探讨,就教于方家。拙文所论难免涉及一些前辈及时贤乃至新晋博士之论,均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论,唯愿能获得同仁理解,以促进对有关问题的研讨深入展开,尽快了结这个悬案。
一 以往的研究略述
笔者在二十年前发表的《燉(焞、敦)煌考释 》一文①,首先在其中的《燉煌、焞煌与敦煌的正俗源流质疑》至《“燉煌”与“敦煌”之正俗辨》等四节文章中,针对以往流行以敦为正字,燉为俗字之说,较为全面系统地收集了历代各种文献数据的有关记载和解释,从字的形音义的综合研究分析来证明燉(焞、敦)煌的各种写法中,应以“燉”为正体字,“焞”为其异体字,“敦” 为其俗体字②。其次,在第五节《燉煌之本义及族源》中,对前辈学者德国的李希吐芬与日本的白鸟库吉、藤田丰八、法国的伯希和以及中国的岑仲勉、冯承钧等人之说,还有当时所见时贤齐陈骏、刘光华、王宗维、施萍亭等人的各种说法提出商榷、着重否定了所谓燉煌为胡语音译之各说,力证被上述大多数中外学者所否定的东汉应劭“燉,大也;煌,盛也”的解释,其实是现存汉朝人最早也是唯一的“燉煌”正确释义,以后历代之史地及文字书籍多沿用此说。及至近现代学者,因不明“燉”与“敦”的正俗关系,又以应劭的解释不合燉煌当年实际既不大又不盛的规模,而又无法找到燉煌有其他含义,遂纷纷提出燉煌为胡语音译说。至于是何种胡语,则众说纷纭。其义是什么,就更无人能道。由此进一步证明“燉煌”完全是按照其汉文的两个字的本义组合而成的专有名词,绝非胡语音译。
如上所述,拙文发表于1993年的《文史》,而且后来又被收入了陈国灿、陆庆夫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历史卷(2),其应为有关研究者看到是理所当然的。加上在本世纪初,笔者在接受上海李伟国先生组织的“名家与名编”的对话中又进一步指出:
……“燉(敦)煌”在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已经是中国的一个军事屯田地区名……可见其出处年代早于前述任何一个胡语词,故充其量只能说那些胡语是燉煌的译音,而不能反过来说燉煌是它们的译音。伯希和修正胡语译音说而提出的土名说,也是主观的臆测。
应劭的解释既合乎中国乃至国际通行的传统命名原则,又合情理和实际。理由如下:
1. 因为孔子提倡“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见《春秋谷梁传》桓二年)。尊孔崇儒的汉武帝是不会违背这个原则的……更不可能采用在匈奴之前的族属和意义皆不知的“一种土名”的译音作为一个新开疆而设立的重要的军事行政地区的名称……
2. 虽然汉朝人在新开的政区地名上普遍实行了名从主人的原则,但是个别的小地名或山水等自然地理名称也有沿用异族旧名的译音……相反,汉代的文献从来没有说燉煌是来自胡语,已经可以反证其为纯粹的汉语地名。
3. ……燉煌之取义大盛,并非实指其时郡治之城市规模的大盛,而是用以象征汉朝的文明道德犹如日月之光辉一样大盛。故其首字应以从火的燉或焞为正,无火字旁的敦为俗写假借……故刘光华等对燉煌的大盛之质疑,也是不能成立的误解。[1]
可见拙见具有不容忽视的一定影响。但是,迄今不少有关论著在研究史的论述或介绍似乎都无视其存在,只是重复笔者提出过商榷的一些陈言旧论。例如,从1997年李正宇的《敦煌历史地理导论》[2],到2002年刘进宝的《敦煌学通论》都是如此[3]。影响所及,迄今仍然有同类问题存在。2010年郝春文的《敦煌学概论》虽然已经有比前两本书较为进步之点,但同时又有守旧之处[4]。这反映了当代燉煌学的某些专题研究中,一直存在对研究史的总结记述不够客观全面的缺陷,从而造成一些独到之新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故此笔者拙见所收之功效,就只是鲜有人再以否定应劭的解释作为胡语说立论的基点了。因此在下文的工作,就是继续质疑与否定胡语说的其余两点主据。
二 “燉(焞、敦)煌”为胡语说之理据再商榷
目前主张胡语说之主据如下:其一,是“燉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自西域归来后给汉武帝的报告;其二,是常与“燉煌”连称的“祁连”就是匈奴语的音译[4]。由于此说滥觞于刘光华,故就以刘光华之论为主,其他学者之论为副,再加探讨商榷。
1. 张骞有关月氏的报告涉及的“敦煌”年代与族源等问题
刘光华认为:“据《史记》、《汉书》的记载,‘敦煌一名在汉武帝于河西设置郡县以前很早就出现了。”其所引述有关月氏与“敦煌”的四条资料如下: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列传》)
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汉书·张骞传》)
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 (《汉书·西域传》)
接着,他就下结论说:“这四条资料都和张骞有直接关系……因为它反映的事实发生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这说明在汉朝建置敦煌县、敦煌郡以前,就已经有了‘敦煌一名。”[5]如此把“敦煌”一名的出现推定“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是相当主观片面的。因为即使是张骞的报告原话,距离“战国末至秦汉之际”也有很多年,更何况《史记》、《汉书》原稿出于司马迁、班固,其所记并非张骞原话实录,而且还有后来传抄、加工、刻印者再添加之手笔,他们都有可能用后出之郡县地名,插入其所间接转述之前人报告。故此,不可以根据这“四条资料”就判定在张骞报告之时或以前就已经有“敦煌”一名。例如,《史记·大宛列传》有关于元朔六年(前123)至元狩二年(前121)张骞从大将军击匈奴的结果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6]《汉书·张骞传》所载基本相同{1}。但是,“金城郡”乃“昭帝始元六年(前81)置。”{2}故不能认为在公元前121年或之前已经有“金城”了。正如《资治通鉴》胡注称此为“史追书也”[7]。且据当今专家考证,司马迁编写《史记》在公元前91年就基本完成了,并且是在“大概过一二年或者三四年,他死了” {3}。由此可见,有关“金城”的“追书”乃其死后他人所作。据此还可推断,现存《史记》有关张骞所述西域诸国之事,不可都信为太史公亲笔实录。再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击匈奴之结果如下:
……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6]
上文没有提及“金城”,原因就是金城郡之设立是在司马迁死后。值得注意的是,史、汉两书的匈奴传在元封六年(前105)的记载之下才提及“单于益西北,左方兵值云中,右方兵(案:《汉书》无“兵”字)值酒泉、燉煌郡(案:《汉书》“燉煌郡”作“敦煌”)。”{4}由此可见,史、汉两书的匈奴传所载燉煌的地名与年代较《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汉书·西域传》等为准确。但是,《史记·大宛列传》又于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记载:“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这固然如刘光华指出:“此乃李广利伐大宛后的天汉二、三年间事……证明天汉二、三年间敦煌尚未设郡。”[5]12对此有必要补充说明:这条资料至少还可以证明天汉二、三年间(前99、前98) 燉煌已经设县,因而可以作为重要的地理坐标之地名加载于军事行政的官僚组织系统的名称中。因此,《史记》此条的“燉煌郡”虽然也可能是后人之“追书”,但是更可能是后人传写误加了“郡” 字。笔者认为,删除了这误加的“郡” 字,则此“燉(敦)煌”就是指酒泉郡属下的“燉(敦)煌县”之简称,这样就不会与前述天汉二、三年间“敦煌置酒泉都尉”的记载抵牾。所以,笔者认为前引《史记》匈奴传所载之文应该删“郡”字及顿号为“右方兵值酒泉燉煌”,《汉书》标点本之文也应删顿号为“右方值酒泉敦煌”[8]。表明“燉煌”并非与酒泉平列的郡名,而是酒泉郡下的“燉煌”县。而李正宇曾据“东汉史学家李斐说:屯田犯人暴利长元鼎四年秋在渥洼水捉住‘天马,并说暴利长当时‘屯田敦煌界。元鼎六年才建立敦煌郡,那么元鼎四年的‘敦煌界只能是指敦煌县界,表明渥洼水属敦煌县地。”[2]36而其最近的论文则改为:“《汉书·武帝纪》……注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笔者案:此指敦煌县界)……”[9]这虽然较前书严谨,但是其引《汉书》之唐颜师古注文而不引较早的《史记·乐书》的南朝宋裴骃《集解》,则是因为误信《汉书·武帝纪》本文将“秋,马生渥洼水中”之事列入元鼎四年。而本人二十年前之文已经据《汉书·礼乐志》及《史记·乐书》的南朝宋裴骃《集解》的记载,将此事考定在元狩三年(前120)[10]。这里再补充说明,《资治通鉴》将此事记入元狩三年,胡注也将李斐所述暴利长捕捉天马的故事注于其下[7]636。故可以肯定在元狩三年(前120)或其之前,已经有燉煌县了。而李正宇之所以误信《汉书·武帝纪》有关此事之纪年,乃在于其在1990年之文已经对有关资料做了错误的取舍。认为元狩三年时“汉朝初有酒泉,驻军设政尚不能遽达酒泉以西千里之遥的渥洼水附近……看来,元狩三年之说当属误记”[11]。其实,如前所引《史记·大宛列传》已经明确记载元狩一至二年(前122—前121)“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域〕数万人,至祁连山……而金城、西河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 须知,这里提到的“盐泽”就是当今的罗布泊(lob Nur、Lopp或Lop Nur)[12,13]。因此,其时有随军西征之罪人留驻燉煌是完全必要而可行的。虽然,“金城”为后人“追书”,但是其地在当时与“西河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的情况,应是由于有人留驻燉煌一带已设的边镇据点作了原始的观察记录,曾被写进《史记》原稿,后来之传抄者才有可能在旧稿的基础上“追书”一些新名。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在元狩三年记载武帝为庆贺获得渥洼水天马与司马相如等文臣作歌配乐,即受到汲黯之直谏反对而“默然不悦”。而汲黯于次年就被免官。故获马作歌之事肯定不在元鼎四年而应在元狩三年。李正宇由于据不同的记载做了错误的选择和误解,就把敦煌县的设置年代推后至接近元鼎四年(前113)了。
其实,据前述笔者考订,《史记·匈奴列传》在元封六年(前105)的记载下提及“右方兵值酒泉燉煌”,《资治通鉴》也将此条记入本年[7]697。这就可以确定起码其时已经有酒泉郡属下的燉煌县了。
因此,确定酒泉郡开设的年代,有助于确定其下的燉煌县开设年代上限。李正宇又据《汉书·武帝纪》的记载,认为酒泉郡建于元狩二年冬[2]36,93,即公元前121年末至前120年初。而吴礽骧、余尧1982年之文则认为“酒泉郡应建于元鼎六年(前111)”[14]。虽然,最近贾文丽取用了2001年王宗维之说,主张“酒泉郡设于元封四年(前107)”,而其所引用《史记》、《汉书》之文多错乱误解[13]51,故难以取用。综合比较《史记》、《汉书》及《资治通鉴》的不同记载,以及当今学者的各种看法,笔者认为李正宇提出的元狩二年冬之说较为可信,可以据此推定其时已经有隶属酒泉郡的燉煌县。
现在再看前述《史记·大宛列传》等有关月氏与“敦煌”的四条资料,就清楚其为司马迁等人以“追书”之法将燉煌之名插入对张骞报告的转述中。同类之例除了前文提及有关金城的“追书”之外,还有《史记·大宛列传》开头转述匈奴降者所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之事,并无提及月氏之居处。至后文转述张骞有关匈奴与月氏等国的报告时,提及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之后,才加插倒叙补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而《汉书·张骞传》则在转述元狩四年(前119)之后,“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但是,《汉书》这段文字所据《史记·大宛列传》并没有提及“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其原文说:“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由此可见,《汉书》有关文字乃随意增改《史记》的文字,不足为据。至于《汉书·西域传》所载“大月氏国……本居敦煌、祁连间”,“乌孙国……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8],这两条资料有矛盾异词,其实也是将《史记·大宛列传》的有关文字增改而成。而且,《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载:“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而同书下文的《乌孙国》则载:“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可见,《汉书》有关记载多加入后出的异闻,不足为据。而《史记·匈奴列传》所载冒顿单于于汉文帝四年(前177)“遗汉书”已经提及其派右贤王“西求月氏击之……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又文帝于六年(前175)的回信亦对此事加以确认[6]。而《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单于的“遗汉书”与《史记》基本相同,但是却将汉文帝回信有关确认匈奴夷灭月氏的内容删略了[8]。由此可见《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较为原始准确,而《汉书》的两条记载都对《史记》的记载做了增删篡改,不足为据。近年已经有学者戴春阳指出这两条记载“得不到相关史料的支持和印证,同时与新疆地区及原苏联中亚地区考古发掘及研究所证实的乌孙活动的时限、区域不符,因而有理由认为班固上述记载是错误的”[15]。所以值得研究分析的,就只剩下《史记·大宛列传》倒叙记述的“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这一条。而此传既有前文所揭露的“追书”金城之例,故这一条的“敦煌”也可能是后人“追书”的结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前人完全信用四条资料,以此作为燉煌来源于所谓“土著居民”的胡语说之主证,是不能成立的。
2. “燉煌”与“祁连”连称不足为胡语说之据
如前所述,刘光华较早以“敦煌”与“祁连”连称作胡语说的第二主据。后来诸家之说,与其根据大同,而结论大异[3]。因此,必须再作商榷。现引其有关论证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四条资料中的三条都将敦煌与“祁连”连用。祁连就是祁连山,颜师古《汉书》注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这说明唐人认为“祁连”为少数民族语,并非汉语命名……它和“祁连”一样,应是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5]
这显然是对颜师古之注过度的解读。而且,刘先生最后还确定“原来乌孙是敦煌地区的主人”。但是,又说“乌孙是敦煌地区的土著居民,还是由他地迁去的客民,由于古文献资料缺乏,无法肯定回答”[5]8-9。如此片面而自相矛盾之论,有必要重新探讨。
首先,仅据颜注“匈奴呼天为祁连”这一点,既不能证“祁连”为匈奴语,更难证其为“少数民族语”,乃至希腊或东伊朗等异国之语。据《史记·匈奴列传》开头所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因而夏商周秦以来就有华夏汉族与匈奴等北方各少数族裔混居和对立交往的情况,故有关官名及物名等名词在两族或多族之间互相借来借去的情况甚多。但是,因为匈奴等少数族裔是没有本族文字的游牧民族或土著民族,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比汉族低很多,故其语言中的汉语借词显然远多于汉语中的匈奴语或其他少数族裔语的借词。例如,《史记》下文载汉初时期的匈奴国官制情况为“其世传国官号”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8]显而易见,这些王侯将尉等名称多数是匈奴译取自汉语,而汉人再杂用意译与音译的方法将其回译为汉文。故笔者认为,“天”与“祁连”就是一个汉语名词的变音被匈奴借用之后又回写为汉文的典型之例。这是因为汉字的单音节词自上古就有缓读而变成带有反切性的双音节词的情况。正如顾炎武指出:“……又迟则一字而为二字:茨为蒺藜,椎为终葵,是也。”“宋沈括谓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郑樵谓慢声为二,急声为一。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是也。愚尝考之经传,盖不止此。如《诗》:‘墙有茨。《传》:‘蒺藜也。 蒺藜正切茨字……《礼记·檀弓》:‘铭,明旌也。 明旌正切铭字。《玉藻》:‘终葵,椎也。《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 终葵正切椎字。《尔雅》:‘禘,大祭也。大祭正切禘字。‘不律谓之笔。 不律正切笔字。”[16]其例之多,不胜枚举。而“天”古时又音“乾”,且乾与天又有同义之点。例如,《易经》的《说卦传》第十章说:“乾,天也。”{1}因此,《史记》“身毒国”的《集解》引“徐广曰:‘身,或作乾。”《索隐》:“身音乾……”[6]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上·无雷国》的“捐毒”说:“捐毒即身毒、天笃也,本皆一名,语有轻重耳。”虽然王先谦的补注认为“捐毒即身毒、天笃”之说误{2}。但是,从古音来看,应该认同捐毒与身毒、天笃只是“语有轻重”的细微差别。因此,“天竺”又作“乾竺”{3}。而“祁连”正是“乾”的正切音。故此可以断定“祁连”为古时“天”及其又音“乾”的某种方言的缓读在匈奴等族的借用再回流给汉人通语的写音。而匈奴语的“天”字的另一汉人回译写音词为“撑犁”(谭案:《史记·匈奴列传》的《索隐》作“■黎”),实际就是“祁连”的同源词之异译,只是越往后之人就越不知其源最早为汉语的“天”。即使是博学的岑仲勉,也只证明“祁连”与“撑犁”或“■黎”及后世突厥语的“腾格里(t?覿ngri)”的源流关系:“大约汉人初译其全名曰‘天祁连山(今《史记》作祁连天山,乃其误倒)后知其义训天,又将天字截去,相沿省称为祁连山……故天祁连山之读法为t?覿n—grin。撑犁之读法为t?覿ng—ri。不过读法缓急略殊,祁连与撑犁实语原同一。”[12]525-526笔者认为,此说甚有理据,然尚有未达一间之憾。有关词的先后实在先有“祁连(grin)”,后有“祁连天山”,最后才有“撑犁”或“■黎”及后世突厥语的“腾格里(t?覿ngri)”。
以上的判定,是因为《史记·匈奴列传》本文不载“撑犁”或“■黎”此号,是今本《汉书·匈奴传上》的本文率先将匈奴语的“天子”称号写音为“撑犁孤涂单于”,并指出“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貌也。”{4}这表明“撑犁孤涂单于”的称号是在司马迁之后至班固之前才为匈奴译取自汉语。众所周知,将自然界的“天”宗教政治道德伦理化为神圣的“天”,且因此而用同一个具有“天人合一”的象形和取义的“天”字来表示,这在商代的甲骨文字已经有确证。而以“天子”作为世上最高的宗教政治道德伦理化身的王者之尊称,可以说是华夏族的祖先创立而历经商周秦汉承传确立的独特语言文字概念。匈奴原有的低级游牧文化,并没有产生出“天人合一”的“天”及“天子”的概念,其借用自然意义的“天”字的音译是较早进入匈奴的语言,故首先有匈奴语回译的祁连(天)山。至文帝时匈奴才开始学用神化的“天”,故在致文帝的两封信中先后自称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大匈奴单于”,可见其时尚未采用“天子”之称,但是它们已很接近“天子”了。匈奴是在司马迁之后译入“天子”之称,其方法是将以往汉语“天”的匈奴语音译,与其本民族的“子”字结合为一个匈奴语的新词。而这个新词中神化的“天”就是后来被《汉书》用汉字音译的“撑犁”或“■黎”。故也可推断“祁连”的辞源应非匈奴语或其他胡语。不然,何以史、汉多次记载“祁连”一词,但是其本文却从来没有对它的族属及音义加以解释。这应是由于其时人对此类单音节词缓读而产生的双音节词,是不言而喻的,故毋庸再加解说。
另外,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霍梅尔(Fritz Hommel)则认为该词源自苏美尔人的“Dingir”一词,意为“神”或者“明亮的”{5}。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苏美尔人的“Dingir”一词与汉语的上古“天”之音义皆有较大差异,且东西种族语言之源流关系更欠充足论证。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祁连”是匈奴语,也不能因为有三个“燉煌”与“祁连”连用之例,而实际只有《史记》一个是较为原始的,就证明“燉煌”也是“胡语”词。因为在《史记》、《汉书》中燉煌与酒泉、武威、张掖等纯汉语地名词连用之例更多,岂非也可用做其为汉语词之证?
更为重要的失误,是刘先生将大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说成是燉煌的“土著居民”。其实,最早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已区分“土著”与“移徙”两类民族说:“自筰以东北……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6]其后,《史记·大宛列传》明确记载大月氏、乌孙、匈奴等皆非土著的城郭之国,而是“随畜移徙”之“行国”,正如南朝刘宋裴骃《集解》释“行国”说:“徐广曰:‘不土著。”[6]《汉书·西域传上》对“土著”与“不土著”的居民也有明确区分说:“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其中夹有颜师古对“土著”一词的注释说:“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随畜牧而徙也。”{1}由此可见,由于大月氏等“行国”没有固定的城郭或乡镇之类的居民点,故不可能有相应的地名留下。假如在大月氏、乌孙、匈奴控制时期中,河西地区曾有零星而短暂的土著居民点,应该就是汉武开边驱逐匈奴以前的华夏族农耕之民流亡于该地区所建立。在缺乏强大的中原王朝的军事力量保护下,它们不可能有几年时间在游牧民族对土著居民的残酷打击抢掠下生存。因此,在汉武开边驱逐匈奴以后,才开始陆续在原来基本没有土著居民的河西走廊尤其是在燉煌地区,建立起以汉族兵农为主的一系列乡村城镇县郡等定居点,并开始有相应的地名。
三 再论“燉煌”为汉语词之理据
如前所述,《史记》明确记载大月氏、乌孙、匈奴等皆非土著的城郭之国。因此,他们不可能有由其建立和命名的城郭等,为后来的其他民族作为地标性名词所沿用,这本应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既然有不少学者皆误以他们为敦煌地区的土著居民,而且“燉煌”这一名词是由他们传给汉人,所以还要补论纠正。
1. 略论匈奴等“行国”无本族地名可作区域标界
由于匈奴既无文字,又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所以其“各有分地”的区域划分的地标名称,历来都是借用汉族与匈奴交界处的汉人所建城郭名称。而用这种方法记述匈奴等少数族裔居处区域变化范围的,乃滥觞自商周。《史记·匈奴列传》载:“(周)武王伐纣而营洛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暴中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胊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种以汉族地名标示胡族区域之古法,至秦汉不替。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述秦汉时期匈奴主要官名及其控制的区域划分如下:
……诸左方王将居东方,值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值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值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再看,唐司马贞《索引》对其中的“单于之庭”加按语说:“谓匈奴所都处为‘庭。乐产云:‘单于无城郭,不知何以国之。穹庐前地若庭,故云庭。”可见,一则由于匈奴的单于并无固定的驻地,二则其语言中原本就没有类似汉语城郭、宫殿之类的名词。故只能由汉人以汉语的“庭”译称之。既然其单于都无固定的驻地及其语名称之音译传世,那么其下的王侯官员皆无此类名称之音译传世,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双方都是没有固定的地标的游牧民族,就无法用汉族的地标名称为其划界了。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单于时匈奴与东胡两大国族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此文的“瓯脱”,《集解》注引韦昭曰:“界上屯守处。”而《索隐》引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汉人。”《正义》案:“境上斥候之室为瓯脱也。”可见匈奴等族边界只有统称“瓯脱”的细小的临时哨所,根本没有特别名称的固定边防城镇可资记载。《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所记匈奴控制区内的城镇,只有一处,这就是汉降匈奴的将领赵信于阗颜山所筑的“赵信城”。就连目前所知这唯一的匈奴区内之城,也是以汉化胡人之汉名“赵信”命名。其后《史记》所记有关匈奴边界的地标性地名,都是沿用前文的方式,采用汉族地名或汉族对其他民族的汉语名称,而无源于匈奴语的地名音译。例如,《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南……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又载:“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故此,如果要运用类推法来分析有关《史记》所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既可以推定其“敦煌”也可能是后人之追书,而且可以推定其与“祁连”皆为汉人命名的地标性名词,绝对不是匈奴、乌孙、月氏之类的“行国”民族的胡语名词。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史记》记载是写给中国皇帝及有关官员看的,有关国族区域和分界的地标名词不可能用一个古今人皆没有说明,其意义及族源皆无法考究的所谓“少数民族”的名词。
2. 从周秦汉对新设边镇关塞郡县之命名看燉(焞、敦)煌的族源
如前文所述,笔者二十年前之文已经认为,“因为孔子提倡‘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见《春秋谷梁传》桓二年)。尊孔崇儒的汉武帝是不会违背这个原则的,所以汉朝既不会沿用最近被其驱逐的敌国匈奴的地名,更不可能采用在匈奴之前的族属和意义皆不知的“一种土名”的译音,来作为一个新开疆而设立的重要的军事行政地区的名称。武威、酒泉、张掖、燉煌等四郡的命名,充分体现了对‘名从主人的原则的实行。”现在再补述《史记》所载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对匈奴等少数民族战争后的新设边镇关塞郡县等的一系列命名,就可以更加清楚“燉煌”绝对是出于汉人的汉语名词。
(一)周秦的新设边镇关塞的命名
(1)《史记·匈奴列传》载周代“诗人歌之诗曰:‘戎狄是膺,‘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对此唐张守节《正义》的注解说:“猃狁既去,北方安静,乃筑城守之。”
(2)其后文“义渠”的《索隐》引韦昭云:“义渠本西戎国,有王,秦灭之,今在北地郡。”“大荔”的“《索隐》案:‘《秦本纪》:厉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后更名临晋。”而本传下文更明确记载:“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3)其后文又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置云中、雁门、代郡。”
(4)其后文又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6]
(5)其后文又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因边山险壍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以上表明周朝至战国乃至秦朝的汉族诸国在占据胡族之地后皆以汉语词为新设之城镇及郡县命名。
(二)汉朝的新设边镇关塞郡县的命名
(1)《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
(2)《史记·匈奴列传》载:“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
(3)其后文又载:“呴犂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卢朐。”(谭按:此句“五原塞”的《正义》引《地理志》云:“五原郡茩阳县北出石门鄣,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軓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案:即筑城鄣列亭至卢朐也。服虔云:‘卢朐,匈奴地名也。张晏云:‘山名也。”)
有关例子不胜枚举,可以看出,汉朝对新设边镇关塞郡县的命名基本沿用周秦的惯例,绝大部分用具有明确意义的汉语名词来命名。正如笔者的旧作已经指出,《水经注》卷2引“黄义仲《十三州记》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言君者,至尊也。郡守专权,君臣之礼弥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为元首,邑以载民,故取名于君谓之郡。”可见,就连“郡”字本身都与中国的君主有关。又据《汉书·张骞传》载:“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此古图书,应指《尔雅·释丘》说:“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崘丘。”[17]可见,汉以前古籍之“昆崘(昆仑、昆仑)山(丘)”应为汉语词。有认其为外来语者,乃误以为“‘昆仑二字作何解,《(水)经》、《注》均未提及,仅言是山而已。”[18]其实,在“敦丘”、“陶丘”、“融丘”、“昆崘丘”等有关山丘的名词中,“敦”、“陶”、“融”、“昆崘”等都是没有独立词义的语素,它们都只是在与“丘(山、墟)组成的名词中才有“一成”至“三成”等意义。故《尔雅》以及《(水)经》及其《注》均不会离开有关山丘的名词或山丘的词义单独解释其敦”、“陶”、“融”、“昆崘”之义。例如,《水经注》卷一“昆仑(昆崘)墟在西北”句之《注》首引就是“三成为昆崘丘”之说。其后又引《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1}从汉武帝“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可见其对新拓展的西部疆域之地理及地名的高度重视,即使是自然的山川之名,也要由他亲自研究中国“古图书”的有关记载和定义来命名。再根据东汉应劭等古人的注解说明,可以知道汉代的一系列郡、县、亭、鄣等城镇命名取义的原因。诸如金城,因在城下得金,或指是用金来形容该城的坚固。酒泉,因为有泉水甘味如酒。张掖,其寓意为“张国臂掖,以威羌狄”。武威,其宣示汉朝强大的武装力量之意不言而喻,所以应劭及前人对此名不加注解。对于燉煌,应劭特别解释为“燉大也;煌,盛也;”其寓意汉朝的文德大盛。至于“县曰冥安,盖因冥水得名”。效谷,“本渔泽鄣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渔泽校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渊泉,“师古曰:阚骃云:地多泉水,故以为名”。 广至,其名见词明义,不用解释。原注只说:“宜禾都尉治昆仑鄣。”龙勒,其名也见词明义,不用解释。而李正宇认为,“‘龙谓骏马,‘勒即马笼头头……‘龙勒合言,若曰‘天马收勒之地。”[9]23当然,另有个别显然是出于其他原因的考虑而保留对被征服民族的个别词义不明的音译名词来命名一些地方,即使不能注明其义,也要注明其族源。例如卢朐,就只注明其族源为匈奴。至于“头曼城”是前述新设边镇关塞郡县名字中,唯一以匈奴单于名字的汉语音译“头曼”来命名而又不加注的特例,应是有当时人不言而喻的特别用意和原因。笔者认为,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载:当时汉朝所击破并要消灭的匈奴王国,乃是由冒顿单于才开始将它扩张至“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谭按:其时的“中国”就是汉朝)为敌国。”而冒顿则是靠搞阴谋射杀其亲生父亲头曼单于而夺取单于之位。汉朝特别将燉煌的一个城镇以“头曼”命名,这与清朝为被明朝子民造反逼得自杀的崇祯皇帝礼葬建陵相比,乃异曲同工,而且具有更加重大的政治道德文化的意义。其核心的意义,就是完成由汉文帝时派使节向匈奴发起的文明道德攻势,证明倡行儒家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汉朝文明远远高于匈奴的“贱老”、“父子兄弟死,娶其妻妻之”等野蛮落后的习俗。通过“燉煌县”及“头曼城”的命名,宣示汉朝战胜匈奴,不是单纯的武力胜利,更重要的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借此让匈奴的主动归降者或被动投降者永远记住,汉朝将靠弑父起家的冒顿单于王国消灭是正义合理的,汉朝将会在新设立的郡县继续推行文明道德以取代其野蛮习俗。冒顿弑父起家之事在当时的汉、匈两族是人所共知之事,故汉朝最早历史档案记录者无需对“燉煌县”及“头曼城”的名称意义预作解释说明。
四 结 语
自从东汉应劭等人略作解释之后,至清代两千年多间,从来没有学者注家对有关燉煌等地名的汉语意义产生过怀疑或提出过不同的看法。
有关燉煌等地名的族源及意义成为难以理解的历史问题,乃因时过境迁,使得原来完整的汉朝历史档案数据在两千多年来不断递减的过程中变成碎片流传于今世,而导致当代片面的历史研究者的困惑不断增加。特别是由于有关问题实际是由原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史记》、《汉书》缺乏全面深入研究理解的现代欧洲汉学家提出的伪问题,然后由他们及同样一知半解的日本汉学家对伪问题作出的种种错答案,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一些误论的影响,而导致了所谓燉煌为胡语的音译词之说在中国普遍流行。甚至还有学者仅据唐以后一度占领过河西走廊的藏族留下的“庄浪”一词在“今藏语义为野牛沟{1},因而得晤(谭按:晤应为悟之误)张掖的原意是野牛之乡”从而认定“张掖”与“敦煌”等都是羌语词:“敦煌之为羌语译音,盖与庄浪、张掖、删丹等相同。”“最终由索南杰同志提出‘朵航的对音来,这在现代的藏语中是‘颂经地或‘诵经处的含义。”[19]如此胡乱找来比“张掖”后出一千多年的“庄浪”,以及比“敦煌”后出两千多年的“朵航”作为“张掖”与“敦煌”的辞源,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欲要弄清这个百年悬案,必须源流都要厘清,既要把百多年来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史基本研究清楚,同时还要把《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的源流弄清楚。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分清是非真伪与正误,了结此案。
(本文原为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现作了一些删节修订)
参考文献:
[1]李伟国.敦煌话语(插图本)——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2]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M].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32.
[3]刘进宝.敦煌学通论[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3-8.
[4]郝春文.敦煌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3.
[5]陈国灿,陆庆夫.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历史卷(2)[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1-2.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634.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李正宇.敦煌郡各县建立的特殊过程[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1(6):23-29.
[10]谭世保(宝).燉(焞、敦)煌考释 [J].文史:第37辑,中华书局,1993:55-64.
[11]李正宇.渥洼水天马史事综理[M].敦煌研究,1990(3):16-23.
[12]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53,583.
[13]贾文丽.汉代河西军事地理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47.
[14]吴礽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M].西北师院学报,1982(2):27.
[15]戴春阳.乌孙故地及相关问题考略[M].敦煌研究,2009(1):38-47.
[16]顾炎武.音学五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41,50-51.
[17]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尔雅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01-201.
[18]陈桥驿.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
[19]李得贤.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杝[M].青海社会科学,1988(5):86-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