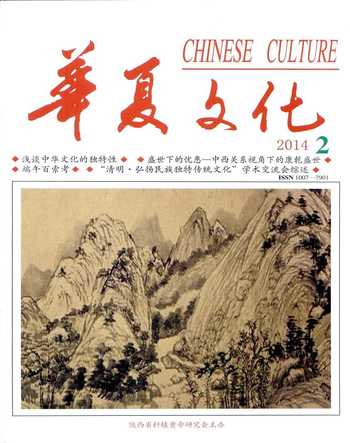盛世下的忧患
欧阳哲生
一
18世纪的中国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从传统的意义来看,所谓“盛世”,包括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权威秩序得以确认和强化,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吏治相对清明;通过对外用兵拓展疆域、巩固边疆,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对清朝的认同感、归附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士人在科举体制内获得对知识、权力的满足,异端情绪逐渐平息;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口增长,农民生活相对富足。这些条件到乾隆年间都已具备。好大喜功的康熙、乾隆两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远超历代君主,事实上他们在位的时间也最长,几乎跨越18世纪。中国历代的疆域版图之广以乾隆朝为最。毫无疑问,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此,戴逸先生中肯地指出:“直到18世纪,当时正处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如果只把它和汉、唐、元、明作纵向比较,而不进行世界的横向比较,中国封建社会看起来仍具有活力,仍在继续发展。18世纪的中国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与此相适应,18世纪的北京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国际性意义的都市。北京不仅是东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吕宋、暹罗、缅甸、汶莱等国,以及东南亚、中亚、西亚诸国保持着与清朝的传统往来关系,而且是与欧洲各国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都城。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三条途径与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据统计,18世纪耶稣会派往北京或游历过北京的传教士达到115名(参见拙作《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的“北京经验”》,载《中国文化》第三十四期,2011年秋季号);迄至1840年,遣使会派往北京的传教士至少有18名(迄今对遣使会研究的中文成果甚为缺乏,遣使会在耶稣会被解散后,取而代替耶稣会在北京的角色,同时大力发展华人主教、司铎,成为19世纪在北京传教举足轻重的势力);方济各会在北京设立了教区。从1716年到1860年,俄罗斯东正教向北京派出布道团十三届,约有130多名神职人员;这些传教士常驻北京,集传教、外交、研究与搜集情报于一身。平心而论,这些西来的传教士大力发展西方汉学,在世界范围内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了解中国、将中国文化带往西方的欲望,引发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潮”、“中国风”;同时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带到中国。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也是向东方殖民开拓的先行者。他们因长驻北京,有的甚至充当西方获取中国情报的“坐探”。在18世纪,欧洲各国派遣赴京的使团或使节,俄罗斯有伊兹玛依洛夫使团(1720—1721)、萨瓦使团(1726—1727),葡萄牙有裴拉理使团(1720—1721)、麦德乐使团(1727)、巴哲格使团(1753),英国有马戛尔尼使团(1793),荷兰有德胜、范罢览使团(1795),教廷有多罗使团(1705)、嘉乐使团(1720—1721),中欧外交继续保持往来。《皇清职贡图》卷一曾对来往的欧洲使节加以描绘,内中涉及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荷兰等国。在商贸方面,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商队在北京展开活动,北京成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场所;传教士、欧洲其他国家使节、使团随身携带的物品、礼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可以说,北京与欧洲的来往保持相当开放的局面。从整体来说,18世纪的中国仍然维持封闭的状态,但从局部诸如北京、广州这些城市来说,却与外部保持频繁的联系。北京是当时世界上与外部交往最为频繁的都城,北京有足够的渠道了解外部世界。
与18世纪欧洲的代表性城市巴黎、伦敦、莫斯科、罗马相比,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财富积聚、文化含量等方面,北京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明显优势。这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秩序给北京带来的丰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资源密切相关。
二
不过,中欧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信息交流)并不对称。在中西互相对望、互相对话、互相认识的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了解的程度,西方从中国获取的资讯和灵感远远超过中国从西方所得到的一切。中西之间的这一差距在19世纪得到应验。中国因对西方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而屡受战争挫辱,反过来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通过长达两三百年与中国的接触,特别是驻节北京的亲身经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外部到内部、从表层到深入、从地方到中央,有了极大的发展。西方对中国基本国情包括历史、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了解不能说已了如指掌,但大体不差,法国耶稣会士的三大汉学名著和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报告可谓明证。神秘的紫禁城对于那些频频出入宫廷的传教士来说其实已经熟悉,由于担任中欧交往之间的翻译,清廷的外交秘辛完全为传教士们所知晓。从利玛窦以来,北京作为帝都始终是耶稣会士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心所在,耶稣会士从适应策略——知识传教——上层传教,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这样一种传教策略对后来的西方对华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西方通过长期的、各种途径的接触,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是国家重心之所在,故其远征中国的战略,逐渐从沿海骚扰发展到打入京城,“擒贼先擒王”的“斩首”策略。面对辽阔的中华大地,西欧列强和俄罗斯采取的是不同殖民战略:俄罗斯寻求向东、向南扩张领土,对宗教传播兴趣不大;英、法、葡、意等国主要是在东南沿海骚扰和活动,对宗教远征和商贸往来怀抱浓厚的兴趣。“北京经验”在西人的“中国经验”中可谓重中之重,称得上是其精粹之所在。
来京的西方人士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进行评估。关于政治制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卷第6章《中国的政府机构》对明朝的政府机构及其职能加以介绍。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从第12章到第16章,用了五章的篇幅介绍清初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和京兆机构,基本上符合清廷实情。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第9封信为《致红衣主教德斯泰大人:论中国政治及政府》。杜赫德编辑《中华帝国志》第二卷大篇幅地评述了清朝的宫廷礼仪、政治制度。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第七章专门讨论了“政府一法律一地租和赋税一岁人一文官、武官,及文武机构”这些政治问题。《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则评述了清朝政府、司法、文武官员的等级和制度等问题。这些文献不断充实西方对中国政治内情的了解,更新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识。在西方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的文官制度以前,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和官僚制度所呈现的规范、有序和完备的体系给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庞大的帝国体系和精密的官僚制度是令西人着迷且精研的课题。
关于经济发展,将西人的中国观感按编年排列,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欧经济比较的大致把脉。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在第一卷第三、四章描述了“这个帝国的富饶,它生产的果实及其他东西”,表现了西人对中华帝国的富饶与繁荣之羡慕。《利玛窦中国札记》承认:
“作为中国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食用蔬菜的种类和质量和栽培植物的种植情况也差不多,所有这些中国人使用的数量都要远比欧洲人的通常数量多得多。”(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10—11页)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则声称:“航行和物产丰富即一个国家拥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是贸易的两个源头。中国具有这两大优势,没有别的国家能超过它。”“至于肉、鱼、水果及其他食物,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欧洲有的,他们都有,而且有许多是我们所没有的品种。”(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中国新史》,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8页)这是工业化之前,西人对比中西农业经济的真实感受。随着法国耶稣会士们的到来,情况发生微妙的变化,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宣称:“中国人在住房上远远不如我们,他们的房子不如我们的豪华美丽。”“在法国,无论个人的财富,还是个人的雄心都在奢侈豪华方面比欧洲任何一个王国走得更远,而中国人在一般活动和公共场合几乎都超过我们,看上去更为讲究排场,更加盛大隆重;但私下里居家过日子,我们的居室却是无比富丽堂皇,有钱人数目虽少,生活却过得更轻松,装束打扮更舒适,饮食起居伺候得更周到。一般说,费用支出更稳定平衡。”(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63页)虽然公共盛典的排场,法国远不如中国,但从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来看,法国人并不亚于中国人,在居室方面甚至优越。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志》一方面盛赞中国,“若说中国地大物博,风光秀丽,这一点都不夸张,单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就足以成就一个巨大的王国,以飨皇子的统治野心。其他国家的物产在中国几乎都能找到,而中国的很多东西却是独此一家。”“中国的物产如此丰富可以说归功于其土壤肥沃、人民勤劳和星罗棋布的湖泊溪流以及纵贯全国的运河。”一方面又指出,
“尽管这里物产富足,但是矛盾之处也确实存在。这个世界上最富强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非常贫乏。她虽然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也不过勉强可以维持居民的生计,大胆地说一句,他们需要再大一倍的国土才能安居乐业。”“极度贫困匮乏使很多中国人会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来。一个人如果在广州了解更深入一些就会发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父母遗弃几个亲生子女,父母卖女为奴,一己私利驱动了许多人。”(杜赫德编:《中华帝国通史》第二卷,收入周宁编注:《世纪中国潮》,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392页)18世纪中国极度的人口膨胀和土地使用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于外人面前,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中华帝国形象开始出现在欧人的文本中。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第九章《农村面貌》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他所见中国从北到南广大农村的面貌,留下了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有价值的材料。当时中国与英国的农业已呈现明显差距,表现在生产方式上,“英国大农场优于小农场。主要是大农场能够使用佃农更好地分工合作,因而能够把庄稼种得更好,这是小农场根本做不到的。”“在中国,90%的农民可以认为是个体农民,拥有的牲口极少(附加一句,数百万的农民根本没有牲口),因此人们根本不要期望整个国家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开垦和利用。就园艺而言,他们也许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在大规模发展农业方面,他们当然不能与欧洲许多国家相提并论”。(约翰·巴罗著,李国庆、欧阳少春译:《我看乾隆盛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22页)在人均耕地面积上,“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在长城以内中国的整面积为1 297 999平方英里,也即830 719 360英亩,而总人口多达333 000 000,那么我们会发现每平方英里将有256个人,每个人拥有土地2.5英亩。大不列颠平均每平方英里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亩土地,或者说每个家庭可获得12.5英亩地。因此,中国人口与英国人口比例为256比120人,稍大于二比一。英国每人可获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国每个人可获得的两倍。”(约翰·巴罗著,李国庆、欧阳少春译:《我看乾隆盛世》,第429—430页)实际上,当时中国人口的数量远超过英国人的估计,而可耕地面积则比其估算得还要少。在身体素质上,“在中国普通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的确,他们天生就身体瘦小,满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颊上显出健康的红润。”(约翰·巴罗著,李国庆、欧阳少春译:《我看乾隆盛世》,第411—412页)英国人从所见到的每一张中国人面孔,看出了普通中国民众生活的贫困和身体状况的不良。根据现场的观察,约翰·巴罗得出一个符合事实的结论:“总的来看,就中国在农业上值得称赞之处而言,如果要我斗胆说说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给一个中国农民足够的土地(足够到他和他的家人用锄头能够耕种得过来的土地),他会比任何欧洲的农民更好地利用那块土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但是,倘若在中国将50或100公顷最好的土地按平均地租交给一个农民种植(按一般计算,我们的农民创造的价值是租金的三倍),那么在支付种地需要的劳动力后,他几乎会无法养家糊口。”(约翰·巴罗著,李国庆、欧阳少春译:《我看乾隆盛世》,第424页)约翰·巴罗找出了问题的症结,中、英农业经济的差距和中国农民生活状况的低下,关键在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的不足。到18世纪末,英国农业经济发展已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关于科技水平,明末清初西学在士大夫中最受欢迎者为舆地、天文、数学,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士大夫认可自身的这些学科比较薄弱、急需弥补的缺陷。据统计,明清耶稣会士著译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除传教和汉学类的书籍外,天文、数学、地理、舆地方面的著译所占比重较大。其中在舆地学方面,“利玛窦之《万国舆图》、南怀仁之《坤舆全图》、白晋等所著之《皇舆全览图》,以及《乾坤体义》(利玛窦著)、《职方外纪》(艾儒略著)、《坤舆图说》(南怀仁著)等书,允为最著者也”(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页)。耶稣会士的这些著作在中土产生了积极影响,柳诒徵先生曾如是评价:“元、明间人犹未泯究心于地理,至利玛窦等来,而后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于天中之说。艾儒略著《职方外纪》,绘图立说,是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而清康熙中,各教士测绘全国舆图,尤有功于吾国焉。”(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679—680页)在天文方面,1600年前后,利玛窦将欧洲的天球仪、星盘和日晷等小型仪器介绍到中国来。从1629年起,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应徐光启之邀,供职皇家天文机构,在《崇祯历书》等书籍里描述了十几种欧洲式天文仪器,包括托勒密时代的仪器、第谷的仪器和伽利略的望远镜。清朝初年,汤若望开始执掌钦天监,并将《崇祯历书》修订为《西洋新法历书》。1669—1674年,南怀仁为北京观象台主持设计制造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刊刻了相关设计图纸和说明书。1713—1715年,纪理安为观象台添造了一架欧洲风格的地平经纬仪。1745—1754年,戴进贤、刘松龄等为观象台制造了一架玑衡抚辰仪。这些传教士所制造的天文仪器和传授的技术,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新知识,只是有些技术仅停留在文字介绍,有些仪器只是皇家御用品,未能广泛传播。在数学方面,明万历年问,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明末清初,为配合历法改革所编的《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里面收有若干种数学方面的著作,包括艾儒略的《几何要法》四卷、邓玉函的《大测》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测天约说》二卷、汤若望的《浑天仪说》五卷、《共译各图八线表》六卷、罗雅谷的《测量全义》十卷、《比例规解》一卷等。与此同时,中国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对传入的西方数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排和阐发,消化新传的西方数学。康熙帝向来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张诚、白晋学习西方的数学,此事经白晋的《康熙皇帝传》介绍,在欧洲传为佳话。康熙主持的《数理精蕴》既对传人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系统编排,又对西方数学与中国传统数学做了比较,是当时中西结合的一部数学百科全书。传教士并非专职的科技人员(法国耶稣会士的科学素养较高,可视例外),但他们传授的西方科技确给中国带来了一股新风,成为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最有价值的内容。在明末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从中国获取了大量信息、情报,在科技方面他们所获主要是传统工艺,如瓷器、纺织、人痘、植物、染色、漆器等技艺,他们开始形成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观点。“中国人擅长多种工艺,特别是丝绸和某类棉布的制作。他们擅长印染和定色之方,也优于处理颜料上色的研磨和调和,漆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利落的木匠手工活。但据说他们水平最高的是陶瓷技术,也就是将泥土尽可能做成各种用具,而且随意设计、上釉、着色和烘干。”“至于科学,中国肯定远远落后于欧洲。”(乔治·马戛尔尼著,何同济、何毓宁译:《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0—61页)这就是从中国考察归来的马戛尔尼使团的结论。由于拥有“绝技”的耶稣会士多被召往北京,故上述科技交流基本上是在京城进行,带有浓厚的“御用”性质,这可谓17~18世纪中西科技交流的一大局限。由于中西方之间的科技差距在当时尚未拉开,中国仍有能力消化来自传教士带来的信息,因此中国士人并不以之为差距,而是以差异来看待双方的落差。加上康熙极力倡导“西学中源”说,士人对中西学之间的裂缝以传统的方式轻轻地就抹平了,康熙和士大夫对西学的“受容”某种程度上似乎仍体现的是天朝的尊严。马戛尔尼、约翰·巴罗在他们的报告中对中国科技的评价和中西之间差距的看法,虽然带有一定偏见,但大体反映了走在欧洲前列的英国人的自信。
关于军事技术,国人最先认可西人武器,首推火炮。明末,辽东边境战事频繁,面对强悍的清军,明朝将目光投向火力较猛的西洋火炮,时人所称“红夷大炮”。《明史·徐光启传》谓:徐光启“从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神宗时辽东方急,光启“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黄伯禄《正教奉褒》又谓:“天启二年,上依部议敕罗加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炮,以资成行。”西洋火炮在明军抵抗清军的宁远之战中一度发挥作用。但是清军在围城之战中所缴获的“红夷大炮”,反过来为清军所仿造。清初命南怀仁制造大炮,“红夷大炮”改称“红衣大炮”,一字之改,表现了清军为这种武器的正名,西洋火炮成为清军南下攻城略池的利器,也成为清军平定三藩之乱使用的优势武器。西方军事上另一优势技术是造舰,在17~18世纪,中、西方之间虽未发生大规模海战,但对西方的造船技术,中国已有领教。当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船队出现在大沽口一带时,“三十多只中国驳船云集在使节船只周围。英国船只的高大桅杆和其复杂的构成,在一群简单、笨重、低矮但相当宽阔结实的中国船只中间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页)“英国在欧洲是第一海军强国,素被称为海上之王,英王陛下为了表示郑重其事,本来准备派遣最大的船只访问使节,但鉴于黄海水浅多沙,欧洲航海家们不熟悉这段航路,不得不改为派遣较小的船只前来。因此,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一百零十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50页)遗憾的是,这尊炮舰模型未能引起清朝足够的重视,至少事后没有仔细研究。否则,就不会遭遇后来鸦片战争的失败。“船坚炮利”是近人对西方军事技术优势的概括,实际上这一优势在17~18世纪已显露端倪。
有关18世纪中西方的实力对比,我们往往只能从西人当时的报道找寻中西之间差异的依据。这是因为国人当时基本上缺乏游历欧洲的经验,因而也就无法根据中方文献对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差距)进行真实对比。西人的记载当然带有成见、偏见、误会,甚至盲点,但西方当时与中国的接触毕竟已有相当的规模,故对他们留下的文献材料我们须加仔细甄别,但不可简单否定。在这场中西方对话中,西方是主动者,中国只是“受容”的掌控者。
三
戴逸先生在比较中西走向现代化的路程时深刻地指出:“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是由几个世纪的长期进程所准备起来的,是很多领域近代因素的汇聚、成长的结果。近代因素的积累和成长是一个静悄悄的、未被觉察的缓慢过程。”“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能够认识清楚这一历史真相,只有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疮才逐渐暴露。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久时间,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页)戴先生的这一看法值得我们深思。诚然,他视“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这一观点可以商榷,他可能将中西之间的差异提早了一个世纪。美国加州大学学者彭慕兰根据自己对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建构关系的研究,提出1800年以前并不存一个经济中心,仍是多元的世界。19世纪以后,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才脱颖而出,欧洲才真正领先于亚洲,世界才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大分流”或“大歧变”(The Great Divergence)。他的观点引起一些中、西方学者的呼应和争议。荷兰学者皮尔·弗里斯著《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Via Peking backfo Manchester Britai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China)和他即将出版的新著《一个有着惊人差异的世界:近代早期西欧和中国的国家与经济》(AWorld of Surprising Difference:State and Economy inEarly Modern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对彭慕兰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学者着力经济资源和生产关系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分析了中英两国基础结构的“硬件”设施,包括金融财政状况、政府机构的设置、军队组织以及政策方针,发现双方的差异是如此显著。“同清代中国相比,英国政府在基础结构上拥有更为庞大的权力。英国有着更多的收入、可以支付更多,拥有更为高效的税收和财政体系,更好的货币体系,以及债券体系,这是清政府所缺乏的。坦率地讲,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是根本没有这些的。英国拥有更为高效的政府机构和陆军,以及当时世界上最为高效的海军。英国中央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完全不同于当时清政府典型的农业家长式制度。”他强调,“国家政府可以被描述为一切制度背后的制度。”(参见皮尔·弗里斯著,苗婧译:《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中文版序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iv)在此之前,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表达了不能说是相反,但是相异的观点,他认为,从1400—1800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的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一统计还力图表明,这些白银是如何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缘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历史角度看,这仅仅是很近的事。”(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文版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0页)弗兰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围绕19世纪中国为什么衰落,西方为何胜出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涉及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评价中、西方在前近代的政治制度、生产关系、经济模式与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由于西方在19世纪崛起这一既定事实,讨论的歧异在于认可这是一种西方内在发展孕育的必然结果,还是偶然因素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在19世纪出现了落后于西方的情形,是否意味着中国内在没有向近代转型的动力。对于后一问题,毛泽东曾经论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新近李伯重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似为这一论断再次提供了新的证明。最近二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趋向是在世界视野下将中西方的历史独特性与近代工业化结合起来加以考量。这就要求我们对18世纪后中国何以未能自发地向近代转型的内在障碍,不是就是论事,而应放在世界环境中去做一考察。
18世纪的清朝统治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许最大的错误并不是不愿与外界接触,与西方打交道。事实上,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之密切可谓前所未有,清朝前期的开放度较明朝也有一定的拓展。问题在于清朝在与外国的接触中,力图建立自己的世界体系或者按照传统的朝贡体制建筑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他们都明确地向外部世界表现了这一意志。周围的弱小邻国纳入传统的朝贡体制自不待说,远道而来的欧洲各国使节,他们亦以此相待。除了俄罗斯、英国使团对这一做法表示异议,其他欧洲国家似乎没有反抗地就接受了清朝外交体制的规训。而俄罗斯、英国使团表示异议的潜台词,则实为表示英、俄君主拥有与清皇同等的地位,马戛尔尼则明确表示,英王乔治三世是与乾隆皇帝平起平坐的东西方两大君主。中英之间在外交场合的礼仪之争,实际上是英国扩张的殖民体系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之间的冲突。外交是政治的继续,是内政的延伸,是以实力为后盾的。所谓“礼仪”其实也是对自我认同的实力秩序的规范。
中国保持与西方的交往关系,这对中国了解正在崛起的西方会有一定助益。问题在于囿于传统的朝贡体制,清朝缺乏调整与西方关系的机制,也很难与西方建立起新的互动互惠关系。当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提出通商、传教等不当要求时,清朝如能以讨价还价的谈判策略加以应对,而不是断然拒绝,这显然是一种更为明智、更富柔性的外交选择,它对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许会预留更多想象的空间。清朝无意这样做,因为它不符合天朝的体制。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缺乏主动性,开拓性,处处表现被动、应付、自保的状态,从而失去了在对外交往中获取主动权的良机。强固的天朝帝国体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能使清朝循依“华夷之辨”的思维惯性制订对外政策,很难出现外交新思维。
当清朝感到西来的殖民者对自身的安全构成威胁时,其对外政策从嘉庆年间开始出现急转弯。“禁教”政策严格执行,天主教传教士大多被驱逐出境或被迫离华,教徒人数锐减。对外交往受到严格限制,俄罗斯派遣的戈罗夫金使团(1805—1806)在前往北京的路上,无功而返;英国派遣的阿美士德使团(1816)在北京只呆了不到一天,就被勒令出京。嘉庆皇帝关上了与欧洲交往的大门。航海贸易虽在嘉庆年间仍然维持正常发展,“中国在东南亚海域的航运实力,仍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在东南亚从事远洋航海贸易的商船总吨,超过英国来华船吨的四倍以上。但到道光年间,中西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到鸦片战争的前夕,来华的西方海船,1835年为199艘,总计78000吨,1837年为213艘,总计83000吨。这就是说,西方侵略者对华贸易所投入的船舶载重量,此时已与中国远洋商船总吨相等了。从1820年到1837年,中间不过十五六年时间,一方面是中国远洋商船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是进入中国海域的洋船日益增多,一消一长之间,表明了中国航海贸易的变化,也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对中国航海事业的排挤。”(参见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336页)与此同时,世界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英国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美国“新大陆”开始崛起,欧洲大陆发生剧烈变革。相形之下,中国却由于走向封闭,而陷入沉寂、保守的状态。面对神州大地的沉寂,龚自珍悲愤地哀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国缺乏制度革新的思想和动力。清朝在可比的世界竞争中,危机四伏。危机之一,内部民族矛盾严重。清朝统治集团在前期以满族为核心,满汉有别,北京内外城之分即是这一区别的一个象征。这一格局维持到19世纪中期没有根本改变。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地方割据势力悉数荡平。在传统秩序里,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国家机器之外,农村依靠宗法制维持乡间秩序。有清一代,由于满族对汉族实行严酷的统治,汉人只能通过建立秘密结社来反抗,以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为代表的秘密社会盛行成为18到19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实为当时满汉矛盾的一大反映。
危机之二,缺乏海上开拓的能力。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时,中国几无海上拓展的能力,“禁海”政策实际封闭了向海外开拓的可能。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防堵内地人民与台湾郑氏政权发生联系,清朝实行严格的“禁海闭关”。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到雍正五年(1727年)对南洋“禁海”,则主要是应对吕宋、噶喇巴两地的西班牙、荷兰西洋势力的渗透。乾隆六年(1741年)在福建实行“禁海”,禁止私人下南洋贸易,则是鉴于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当地华侨。在清朝前期,没有再像明朝郑和下西洋那样,举行大规模的出海活动。清朝的“海禁”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了军事上防止台湾郑氏政权和外来的西方殖民势力向内地渗透的需要,一方面是阻挠内地人民向外发展,在贸易方面控制军事武器和重要原料的出口。“禁海”政策在贸易上实际达到了闭关或限关(即限广州一关)的效果,而更大的危害则是放弃了向海洋拓展的努力,面对万里海疆,中国失去了可能成为海洋强国的资格。这与正在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形成强烈对比。
危机之三,士大夫普遍缺乏世界知识,缺乏向外探险的冲动。在18世纪,清朝除了于1729—1731年、1731—1733年两次派使团赴俄罗斯访问外,再没有派遣使团赴欧洲其他国家访问。除了随传教士和欧洲商人赴欧洲的个别教徒和平民百姓,一般士人囿于儒家“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和执迷于科举制试,普遍没有赴欧洲游历的兴趣,因而也缺乏切身体验的“西方经验”,士大夫对欧洲知识极为贫乏,他们只能从传教士撰写的一些介绍性小册子获取遥远的西方知识。
危机之四,实行文化专制,文网恢恢,大兴文字狱,窒息了革新的生机。惨酷严厉的文字狱几乎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始终,从康熙年间的明史狱,方天甫、朱方旦之狱,《南山集》案,到雍正年问的查嗣庭案,曾静、吕留良案,再到乾隆年间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王锡侯《字贯》案,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利用文字狱这种极端手段,钳制言论,禁锢思想,扼杀汉族士大夫的遗民情绪和反清思想。另一方面,又以开四库全书馆,修《四库全书》,搜集、整理、编纂历代典籍,网罗汉族知识精英,点缀其盛世的门面。在这种情势之下,汉学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考证之类学问得以助长,明末方兴未艾的启蒙思想火花渐趋泯灭。18世纪的中西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西方知识分子(以法国为代表)掀起启蒙运动,寻找向近代转型的突破口;中国士大夫囿于文化专制的牢笼,只能满足于做传统典籍的集大成工作为自娱。
总结中国未能自我成功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原因时,有一种普遍的价值预设,即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包括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科举制度)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视之为中国迈向早期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如果在经济领域,人们认可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或早期的工业化,在文化思想领域有着丰厚的历史遗产应当继承,那么,在政治领域就不免发生疑问,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或政治传统,是否就没有转化为现代化助力资源的可能。从近代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的例子来看,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完全有可能转化成为现代化的正能量,并不一定只有负面作用,至少在近代的早期是如此。世界上大部分近代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传统的政治资源,或在相当长的时间尽量保护自身传统的政治遗产。只有美国由于天生是一个新大陆国家,缺乏自身的政治传统,才产生一种崭新的政治建构。在发掘中国传统的政治资源时,孙中山在设计近代国家制度时,曾特别留意传统的监察制度和考试制度,将西方的三权分立扩大到五权宪法。胡适论及“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这个问题时,则特别指出“一个彻底民主化的社会结构”、“两千年客观的、竞争性的官吏考试甄选制度”、“政府创立其自身‘反对面的制度和监察制度”这些历史因素“可以解释辛亥革命,君主制的推翻,共和政府形式的确立,以及最近三十年与今后宪法的发展”(Hu Shih,HistoricalFound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In:Edmund J.James Lectures on Government:Second Serie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1.pp53-64)在一个革命话语占主流的年代,过分强调维护传统政治资源,会成为保守的代名;而彻底的推翻则可赢得革命的美名。孙、胡的努力表现出某种折衷的倾向。最后,我想以乔治·斯当东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18世纪末西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感受,它也许折射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伟大与局限:
如乔治·斯当东爵士所说:“这里出现一个罕见的宏伟景观:在人类的这个泱泱大国,人们都愿意结合在一个伟大的政治实体中,全国都安静地服从一个大帝王,而他们的法律、风俗、乃至他们的语言始终没有变化。在这些方面他们和其他的人类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他们既不想跟世上其他地方交往,也不企图去占领。”这个如实的观察,中国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和权力相比较,人类更容易受传统观念的统治(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著,何高济、何毓宁译:《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61页)。
(作者:北京市北京大学历史系,邮编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