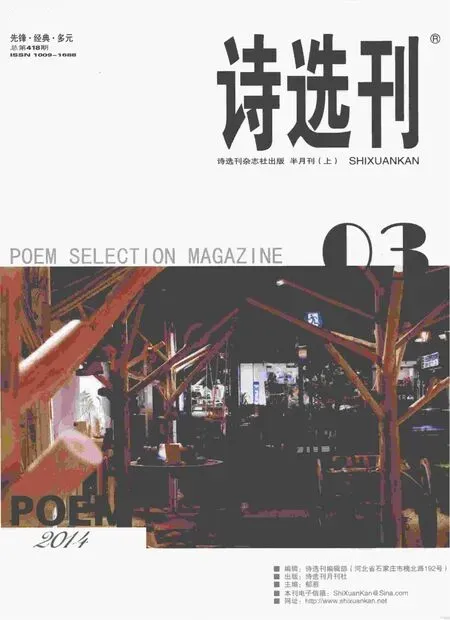以火妞妞的诗
以火妞妞

时光,和一个彝族女人的葬礼(组诗)
想永远住在六月
想永远住在六月
我尚不懂得死亡的日子里
六月里,还有我心爱的奶奶
——安慰过被信念灼伤,顶着浓妆夜半哭泣的我
还有泪眼婆娑下的最后一次目送
——您送我到我的梦里,我送您到您父母的襁褓中
最后一个心照不宣的善意谎言
——现实早已生了根,还被命运打了结,如同铁链
最后一片亲手拾起的您涅槃过的傲骨
——我便是这些骨灰的后代,只是现在,那把火和
您更亲些了
还有一个贵族最后的消息落在祭台上
——十三个兄妹已在那里团圆,您姐姐让您明年
秋收时带她走
亲爱的奶奶
也许七月时,我会好些
因为七月里,您的发不会再白些了
亲爱的奶奶
也许七月过去之后,我会好些
因为八月,并不住在六月的隔壁
亲爱的奶奶
也许下一个六月,我会好些
日子旧了一岁,忧伤也应该会旧一点
亲爱的奶奶
听说七月我最爱的雨要来为大地洗头
八月您喜欢的葡萄在阳光下迎风醒来
但我只想永远住在六月里
那时的我与死亡,不熟
她曾住在人间,被六月把脉
民国的女子
清朝的肺叶早已被鸦片熏得乌黑
被批斗的贵族在噩梦中打翻了黑锅
而您,将要去往哪个世纪
做哪国的公民,转世后
是否还要重走一遍
人间的婚丧嫁娶?
您没有牙齿时,还有爱情
您走后风雨同舟五十载的男子,夜夜为您掌灯
秒变成了分,月变成了岁
他仍担心您怕黑,记得您只喝很淡的茶,加几颗盐
您羞于说爱,但弥留之际对他说“快去找点东西吃”
您牵挂的事情芝麻大,您沉默的感情却擦亮时代的眼
爱情是您们的,不是我们的
生逢乱世,您一生未曾有过自己的婚礼
但婚礼是您们的,不是我们的
您一生只参加过自己的葬礼
但葬礼甚至也不是您的,而是我们的
民国的女子,其实是个头戴锣锅帽的彝家女子
一生不着红黄,不露肌肤半寸
不曾大悲大喜,不曾口出恶言
刺在手上的梅花纹,在南方干旱的大地上娇艳盛放
成年时父亲送的发簪,一直戴到和死亡重叠
断气的时候,有一口痰始终闷在胸口,带了点遗憾上路
彝族女人帽子上的礼节,压得一生都太重,却厚,且实
她年轻时,看着比她小十岁的丈夫日渐成熟,从他手里接过一张狼皮
她健在时,不肯向送来我作品的邮递员报上名姓,怕他是闹革命的红卫兵
她死前,梦见自己和逝去的亲人晴朗下重逢,认领一个未知的方向
她病时,只能说很少的话,不愿再提起母语里一切脱水的虚词
她死的时候发未白尽,身着自己亲手缝制的古早绿绸,静美极了
她在葬礼上,等到了生前久等不来的人,天下了刚刚好的雨
她死后不久,当年政府奖励的手表也停了,它只为她计时
她八十二岁
她完成了生
她从此不再被生活局限
她曾住在人间
被六月把脉
一个彝族女人的月亮
垂死的夕阳被风里的壮汉抬出窗户
吊瓶里未完的点滴仍等待一根虚弱的青筋
死亡的教科书用彝文写着——
女人须朝右而躺,仿死亡子宫里刚刚成形的婴儿
须梳两个辫子环头盘起,齐整如初似待嫁的新娘
拇指须握在手心里,庇佑后人殷实的福祉
让亲人去山野找骨灰里火炼过的首饰,死里播撒希望
葬礼外,有一只贪婪的眼睛斜穿过送丧的人群
黄昏时阴谋在他的心里顺产
我只相信,他不敢说出的话
是谁黑色的翅膀拍痛我的脸
左面右面,绕过赤道的中分
在迎亲的队伍里,咳血
患了风湿的膝盖跪了一宿
还没等来最后一道圣旨,那股冷便窜到了骨子里
——死神宣布鸣枪,留出一条道让灵魂通行
她信了一辈子的迷信
临终前,牛羊的腥味熏黑经文所有的章节
但她,只看得见死神挂在墙上的字母表
呵月亮本该是残的
十五那天那么圆
一定,很痛
众生问路,她不语
敲钟的人
怕自己猝死在错的时辰
在屈原投河的汨罗江打捞起一些水草
众生问路,她不语
再远一点,风景里
还有一个得肺炎的人,抓着上世纪的烟杆
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捂住胸膛咳嗽
生怕蹦出个心脏来,吓跑那个叫他爷爷的孩子
以及,东边的盆栽
和寸土结了一段寡淡的婚姻,在六月风暴里产籽
一生都裹着小脚,三百六十度咬住一个花盆的脸
西边的苍树,是一切风拉弓的方向
在悬崖边艰难翻身,返乡之路被荆棘爬满
偶尔踢翻几颗碎石,正对猎人的前方滑落
她们是一对,乱世里失散的姐妹花
她们,都嫁错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