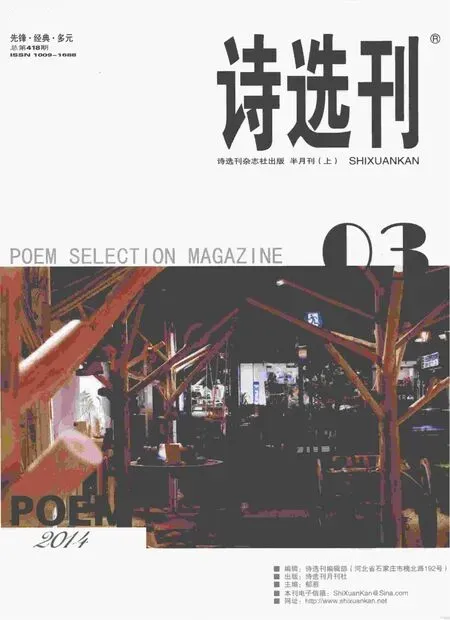林莉的诗
林莉

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
那里
……还是痛,洪水挟持泥沙涌进
你骄傲的产床,宫殿,那里,金色的黄昏
来到,你闭上眼,像一个
毫发未伤的小小蜗牛,卷缩
平静的天气,越来越苍凉,生命的红果子有了
腐烂的迹象
已经不能再后退了,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
那么多泥沙嵌进你坚硬的航道,那里——
蒙尘的珠贝已经远行,一只巨蟹举起闪亮的钳子
那里,你耐心等待被损伤和破坏
那里
枭雄般的蜗牛
并不能减弱持续的袭击、剥夺,时间的避雷针
逼退不了莫名的被炙烤的焦味
霞光
有时候它是无穷大,像宇宙满盈
所有鸟翅聚集到窗口。有时它是危险的消除
使我们盲从于冬天的旷野,抽走饱满鲜美的部分
提前只剩下骨架、轮廓
这些年
“褪色的天空里已经没有隐秘的花纹”
我们的房子、公交卡、对账单、香水瓶
凌乱的被褥,昨夜一个梦尚来不及完成、染色
呼呼的风声是无色的
身体里的潮汐是无色的
走过的每一步是无色的
眼泪、叹气、疲惫的奔波,都是无色的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为什么独有那一个傍晚
天空突然重新亮了,显现异象
仿佛一些被抢夺遮蔽的事物、道路
再一次被和盘托出
是啊,模糊变形的生活里一条花斑蛇
闪电般地来过,身怀冰凉的狂想
因绝望而燃烧,因一次痛苦的扭曲
而呼吸渐渐膨胀、窘迫
克鲁伦河
流水变得迟疑
从峡谷里涌出来,一些波纹重叠着
和我心里的皱褶等同
傍晚,有人
在岸边走动,那是一支弘吉拉部落
匆匆地赶着逝者之路
很久以后,我才听见那些踢踏的脚步声
与水的回响纠缠在一起,继而消失
我凝视河面,寻找一个倒影
又一个倒影,从那里可以看见斑驳的往事
以及近年来发生在我身上的遭遇和问题
是一场占卜玩牌,“把好手气都输光了”
是另一种游牧生活,“转场的途中数次撞上了暴风雪”
又是某一年,在大街上抵到腰部的匕首
此刻,克鲁伦河像静伺多年的一把快刀
霍霍出鞘,当我停息、观望,万物画出休止符号
用不了多久,在黝黯的水底
带电的皮毛,肉体上的破绽,就会露出迹象
所有星星的碎片
一段放浪形骸的生平有待销毁。
嘉峪关
谁是谁永远的关隘,谁又是谁不可攻破
的城堡,纵六百四十年的光阴切割,我仍要指给你
一轮李白的关山月横穿了祁连,昆仑、黑山口
王之涣的羌笛涌到博斯腾湖,艾比湖,塞里木湖
塔里木河,叶尔羌河,裴景福的雪中苜蓿
盘旋于安西、北庭、天山,林则徐的孤烟落日
带回了风雪散布出去的张骞、班超、霍去病、李广
牦牛般、老马般、残柳般,回到母亲身边
当我们在讨赖河墩上极目远眺,已不见旧时烽火
将士、战马,多少次寒光照铁衣,黄沙掩金甲都被
朔风吹散,唯有一只飞燕,在隘口上空啾啾哀鸣
一声一声,卡住我们的腔喉,更低处
是讨赖河带着冰渣在千里雄关迈开大步
走着走着,身子变得踉跄
严关百尺,残垣横连
箭楼、敌楼、角楼、阁楼、罗城、瓮城、内城
烽燧、墩台、古老的悬壁长城,如果
它们将自己举过头顶,它们就高于远远的
祁连雪峰,一旦它们匍匐
它们将低于大漠中的一截白骨、一粒
苜蓿的种子,茫茫流沙中的一声怨叹
四
有雪粒打在脸上的痛,有烽火的余灰迷茫
了双眼,有古戏文恰似走失的故交
瞬间带来惊秫,有征人胡不归的悲怆汹汹掩面
莫过一句“离合悲欢演往事,愚贤忠佞认当场”
终于挨到了这个分水岭,黑山峡口之南为断壁城墙
黑山峡口之北,为悬壁城墙
那是嘉峪关为我们从时光这个谜团里
扯出的两条线索,越抽越长,越长越没有尽头
五
更苍凉?更瑰丽?更悲壮?更安寂?
当我们经过魏晋墓墓葬群,古陶、石斧
壁画、色彩,那存在与消失,锋利与钝口
完整与破碎,流淌与凝固,都在证明
我们将在新旧交替中汇合
成为彼此的遗址和发现,成为
彼此的关隘和城堡,被大雪和流沙深埋。
河床
不再完整。所有的波浪都已撤退
所有的涌动在瞬间凝固,铅灰色的天空下
一段河床摊开枯竭多乱石的底牌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静,几支水蓼开始变红
几朵云被风吹散,越来越空茫
其实,我们都曾渴望过在一个蓄满涛声
的黎明醒来,一次次看见
昨夜似曾相识的梦境中,一条汪洋
肆意碾过了河床
席卷、冲击、撕咬,在无数次的磨损中
被耗空,是什么轻易取走了那些激荡着的水流、漩涡
“仿佛水消失在水中——”
多么疾速又多么缓慢,犹如短暂之于永恒
逝去对抗到来,无消灭了有
不再完整
一段河床躺在了流水的废墟下
我们在其上走动、思考、争吵,一点也没注意到
我们随手摸到的哪一个石头都布满了裂痕
我们随手摸到的每一个石头都在持久地沉默
当一轮上弦月把我们洗白,在时光的胶片上
我们,河床中一个坐满石头的遗址
因为
无法剔除的阴影而显得模糊、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