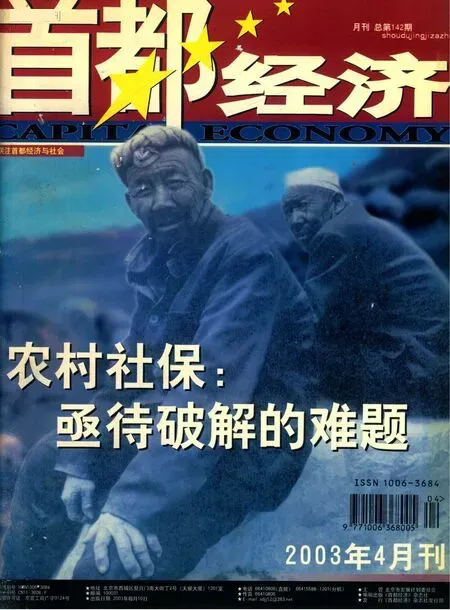重读门头沟
赵方忠
三年前,门头沟投入数十亿元整治河湖生态环境时,明确提出将打造成首都经济发展高地。当时,外界不少人对此评论的潜台词是“不可能”。
要知道,在此之前,门头沟多年的经济支柱资源开采业正全面退出,区域经济的转型才刚刚开始。
2014年1月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门头沟交出了全面转型后第三年的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约123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历史性地达到了20.7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8亿元,总量和增速连续三年居首都生态涵养发展区首位。
其实,对于门头沟来说,一两年经济数据的明显改善并不是很重要,依托数据背后逐步呈现的发展优势,门头沟正向外界勾勒一个“投资高地”的雏形。
如今,巨资打造出的生态景观,已成门头沟最为耀眼的名片。“一湖十园五水联动”的大尺度河湖治理,门头沟呈现给外界的是“一城山色半城湖”景观,并与临近的河北涿州、涞水、怀来、涿鹿等河北生态涵养区域,共同构成了京冀重要的经济缓冲地带,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并携手向绿色生态经济转型的稀缺空间。
而若从目前北京郊区县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络来看,阜石路、莲石路、长安街西延线、轨道交通S1线,以及正在论证中的109高速,不仅将门头沟和中心城区有机融合,而且彻底打开了首都向外拓展的京西门户,门头沟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与此同时,在文化上升为区域发展软实力的当下,门头沟沿袭千年的商旅古道、古村落,京郊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京郊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等红色旅游资源,以及古幡乐、太平鼓等民俗文化遗产,这些不可多得的文化优势也成为了门头沟优良投资环境的品牌背书。
事实上,作为区域经济全面转型的样本,门头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从某种意义上,以门头沟为代表的生态涵养发展区快速崛起,代表了北京投资理念的转变,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成熟。
“失宠”的幸运儿
伴随人口资源环境的日益突出,坚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成为了北京市2014年的首要任务,并被视为解决北京交通、环境等许多问题的关键。
资料显示,2011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018万人,比1990年增加87%。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北京市人口增加637万人,是前一个10年增加人口数量的两倍多。在全市2018万人口中,外来人口达742万人,比2000年的256万人增加了486万人,接近两倍。
而昔日经济发展不温不火的门头沟,却是近十年首都人口快速增长中的一个“另类”。统计数据显示,门头沟2013年的户籍人口为24.9万,常住人口29.7万,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数量,都是北京市人口最少的区县。
当然,“人口最少”并非是门头沟刻意为之,说到底,还是因为门头沟多年来经济欠发达,相应地对人口的吸引聚集能力较弱。
“过去,很多人抱怨门头沟没有物流园,没有大型的综合批发市场,没有专业的服装市场,甚至连像样的大型超市都没有,但以现在的眼光审视,门头沟到底需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却值得深思。”在门头沟发改委主任万钦看来,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必要容纳所有的经济要素,若一个城市容纳的要素越多,其整改的代价势必更大。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来一有风吹草动便见诸报端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大红门服装市场,被媒体不断爆出的艰难外迁就是明证。
事实上,此前因要素欠缺而经济不振的门头沟,却意外收获了当下产业结构调整的从容有度。相比其他区域,更容易低成本、快速地转移出不符合首都定位的低端产业。
人口少显然是门头沟的最大优势,但在现有城市规划体系下,由此带给门头沟最多的发展质疑是:人少意味着建设用地少,门头沟是否具有承载新兴产业发展的能力?
这在万钦眼里并不是问题:“门头沟面积为1455平方公里,20万户籍人口集中在55平方公里的平原棚户区,有巨大的土地整理空间,而1400平方公里的山区仅有4.9万人口,山区又分为建设区、部分可建设区、限制区、禁止区,由此形成了门头沟梯次鲜明的城乡体系。”
从某种程度上讲,门头沟的整个门城地区几乎全是建设用地,尽管总量不算太大,但却比较集中,足以承载一些重大项目落地发展,而山区的人口主要集中于小城镇,多因文化传承保留着一些古村落,既在城市周边保留了乡村风貌,又利于整个山区的生态涵养。
有投资者与记者谈到门头沟的投资环境时,也认可门头沟投资空间的不可多得。“过去投资项目选址一般注重三个方面: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生态环境。但近年来又增加了一个指标:休闲空间。前三个方面是宜业的需要,后者则是衡量宜居的标准,对北京而言,各区县均能满足前三个条件,但随着首都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大多数投资者希望宜业宜居的地方能够分开且距离不远,门头沟的建设用地主要集中于门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相对较好,近年来生态环境整治的成效也较为明显,是宜业的重点区域,再加上山区距离中心城区最近的广袤休闲空间优势,对投资者具有了独特的吸引力。”
重点机遇期的战略布局
不过,人口少只是门头沟有望实现经济跨越的先决条件。但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如何才能打造出区别于其他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竞争力?
其实,由于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被定位为生态涵养发展区,相比大多数区县,门头沟“黑、白、黄”为代表的资源型产业先行退出,虽在短期内让门头沟的经济增长备受挑战,但也让其经济转型能够先人一步。
一方面,贡献着区域财政收入近60%的石龙工业区,通过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业企业,置换科技研发、金融结算、互联网金融等占地少、污染小、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此前依赖资源开采业的山区,结合丰富的旅游人文资源和沟域经济的发展,旅游文化休闲产业正日益兴起。
但土地终究是门头沟产业升级转型绕不过去的一道坎,采访中,万钦用“拆”和“腾”两个字,向记者透露了门头沟建设用地“存量变增量”的两条途径。
比起一些区域针对单个项目的征地拆迁,门头沟的拆迁可谓大手笔,主要结合全区的棚户区改造而进行。据了解,门头沟近两年拆迁了500多万平米连片的棚户区,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新城,涉及十余万人口,也就是说门城一半的人口都与拆迁相关,由此腾退出了7平方公里的连片建设用地。
而门头沟的腾笼换鸟,从一开始便与众不同,石龙工业区管委会主任张丰收在此前记者的采访中曾谈到,腾笼换鸟主要集中于石龙工业区,其方式区别于简单地腾退低端产业置换高端项目,而是引导园区企业主动将生产制造环节外迁,保留企业的决策总部、研发结算、市场运营等高端环节,并通过工业区自建孵化中心招商引资的成功案例以身示范,鼓励园区企业自主投资建设总部大厦,以此吸引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驻。
如此“腾笼换鸟”的好处在于,政府不用付出高昂的腾退代价和巨额的建设资金,而是与所在企业联手向土地要效益和共同招商引资。
毫无疑问,棚户区集中连片的改造,带领门头沟步入了城市建设的高峰期,门头沟已经连续几年开复工面积保持在600万平米左右,在全市生态涵养发展区中遥遥领先。
但万钦一再强调,在城市形象快速升级的过程中,门头沟必须对今后的土地利用保持清醒。他认为,对于门头沟这个建设空间有限的“小区”而言,来之不易的建设用地必须以规划引领城市发展,力争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合理优化不留遗憾。
万钦告诉记者,作为长安街西延线最西端的空间节点,门头沟针对道路两侧近几百万平米建筑的风格、产业定位,制定了包含所有建筑体量的规划导则,并获得了市规委的批复。此外,棚户区改造拆迁出的7 平方公里的街区控规,日前也已经上报市规委等待批复。“要通过规划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为未来的发展留足空间。”万钦说。
除此之外,在万钦看来,伴随城市形态的改变和经济的转型,门头沟正快速步入城市管理变革的关键期,要突显城市的品位和价值,需要针对水电气热垃圾环卫等市政公用事业、河湖生态环境管理等,制定出精细化、智慧化的管理体系。
不仅是门城地区的建设创新,向旅游文化休闲产业转型的山区,门头沟也有着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搭建平台是门头沟推动山区经济转型的关键,近年来,门头沟相继成立了农村土地交易中心和农村产业发展基金两大平台,使农村的土地资源转变成为发展旅游文化休闲产业的资本,并引入了山区最缺乏的金融要素,使此前长年开采资源的农民成功吃上了旅游饭。
创新的政府行为
门头沟价值洼地效应已经显现,各路资本开始聚焦这片热土。“现在门头沟并不缺乏投资项目,但越是这样越需要冷静,我们宁可速度慢一点,也不会一哄而上。”万钦坦言,政府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好关、定好位。
相对而言,门头沟主要的招商引资仍然集中于石龙工业区。正因为此,石龙工业区新建的12个总部大厦,已经分别由12位区领导负责招商,严格按照区域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方向进行筛选。
但能否真正把好关其实还在于体制机制的创新,万钦向记者透露,门头沟将于近期组建成立招商引资评审委员会,由区发改委牵头,邀请产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专家,对拟进入的投资项目,根据占有的资源和创造的价值进行综合评审择优选商。
不过,要让投资项目在门头沟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价值,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万钦看来,政府的投资导向最为关键。“社会资本走到哪,政府投资就应该跟到哪。”他认为,政府投资一方面要对区域的产业发展发挥支撑作用,为重点产业项目投资发展做好相应的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另一方面要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将投资用于城市运营和民生改善。
正是政府投资的方向明确,近年来大量社会资本相继涌入门头沟的诸多建设领域。在北京市明确向社会投资开放的污水处理、自来水厂、交通设施建设、固废处理、养老等领域,门头沟均引入了社会投资,成为了全市社会公用事业市场化的成功典型。
其实,在万钦看来,区县的经济转型也就意味着二次创业,而政府在二次创业中定好位的最大价值在于,“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型不应该是政府的单方面意愿,应该是政府与市场共同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