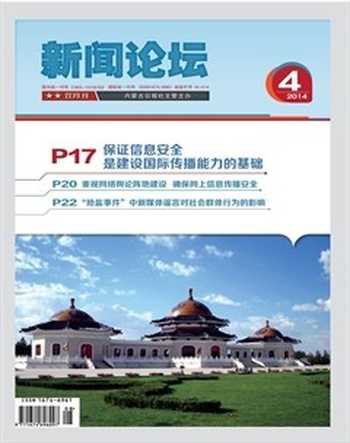开拓者的不休之路
2012年7月,我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这意味着我彻底离开了教室、告别了讲台,结束了我的教学生涯。庆幸的是,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我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2012年10月14日,大学同学在母校聚会,纪念毕业50年,畅谈人生感悟。我们虽然都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可以“在长烟大漠间远行千里”。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很多人仍不顾年高体弱,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那天,我对大家说:我这一生有许多的巧合与想不到,比如,小时候我随老人一同住在北京崇文门外一条胡同里,门牌27号;成家后,一家四口大约于1977年搬到前门地区一条胡同,还是27号;现在我住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院(在这个大院先后调整了4次住房,我都没跳出这个27号院),在北京我的住家都与“27号”结缘;我在北京上的第一所小学是穆德(回民)小学;六年中学都在北京十一中度过的,十一中校址原来是药王庙;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在校读书时放假回家,必须在马神庙上公交车;我退休于中央民族大学,家属宿舍原来也是一座寺庙,名曰法华寺,从小学到大学,乃至最后任教的学校和颐养天年的居所都跟宗教(寺庙)和民族有密切的联系。
提起“想不到”就更多:我没想到我能活过古稀,很多老同学都知道我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从中学就免修体育;上世纪70年代得过慢性肝炎,差点一命呜呼,当年谁要说你怎么也能活到60岁,我就会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我这个当年穿缅裆裤上大学的人,老实的近于窝囊,没想到我这个本科毕业生,还培养出了60名研究生,出版了十几本书,发表了一百七八十篇文章,有人把我捧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开拓者”,有人拿我当作偶像,自称是我的“粉丝”。2011年10月,“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在云南红河学院举行学术报告会,当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时,我这个忝列末位的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大串联”的年代我没出过北京城,没想到40岁后几乎跑遍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白山黑水、苗寨壮乡,进行调研考察、参加学术研讨,结识了海内外很多知名学者、专家教授。我第一次去台湾因有关部门工作失误,把途经澳门上报成了由香港转机。在别人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飞跃台湾海峡!谁承想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一波三折,竟准时抵达台湾政治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开幕式,与会同仁都说应当写篇《赴台历险记》。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书未必读过万卷,但‘行绝对超过万里。“我要把它记录下来!”这一想法刚一闪现,便有一慕名而来的年轻学子飞到我的身边,她紧紧握住我的手说,“由我来完成,书名《白话润生》,以飨读者。”这真是心想事成,哪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啊!
我的人生轨迹是多变曲折的,并非顺风顺水,一马平川。我的曾祖父虽是地主兼资本家,但到我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一贫如洗。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没有吃过早点,本想工作挣钱养家,也不知谁,别人帮我交上报名费,老师同学当时都对我说,你还不一定能考上呢?!因而高三停课后,我一页书也没翻过,整天帮家里干活。说来也巧,进入考场前,翻开笔记本正好看到一道大题,开考后发现竟是考题之一,此乃天意?!我在中学当了16年语文教师,教课、当班主任,给全区讲公开课,带学生野营拉练,“三夏”“三秋”,与学生摸爬滚打,要多积极有多积极,也不知写了多少份入党申请书,但总是达不到党章规定的入党条件。心想可能是有不能入党的硬杠杠卡住了我,正当我觉得这辈子入党无望的时候,时年61岁高龄的我以实际行动批判“入党做官论”,终于被党支部批准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大学毕业时,系主任通知我到门头沟教育局报到,但是当全班同学陆续到北京各区县报到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后,我又接到通知,改派崇文区一所新建校任教,教初一语文课,兼初一一班班主任。“文革”刚结束,我从中学一跃成为报社编辑,刚适应了报社的工作节奏,也就是一年光景我又到了大学任教,掐指算来正好三次工作变动。刚到高校,我就问在高校工作多年的老师:“我能当讲师吗?”因为我很有自知之明,大学里藏龙卧虎、学富五车的大有人在,著书立说谈何容易?学校第一次评定职称时,我不敢申报,等第一批副高名单公布后,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申请?你不是还出过书吗?我这才鼓起勇气申报。但并不顺利,我申报了三次,才当上副教授。申请副高三次,申请正高也是三次。我这一生还有许多值得纪念和令人振奋的想不到。比如,20世纪80年代,我与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代表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就餐,国宴前还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合影留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我和许多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代表一同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焰火晚会;中央民族大学建校50周年之际,朱镕基总理来校视察,我也作为师生代表之一与之合影留念。这些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至今想起来激动无比!
退休了,本应颐养天年,但真是退而不休,毫不夸张地说,比在职的还忙,忙上课,忙论文答辩,忙写论文,忙参加学术研讨会,忙培养研究生,忙为他人作嫁衣裳!难怪一位同学说我,“是‘院士!”意思是说,我退休后经常因参加学术活动而不能参加同学聚会。我虽不是“院士”,但我头上确有“虚衔”,什么“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理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中国报协民族地区分会顾问”等等。其实也有只尽义务的“实衔”,比如街道侨联的副主席,海淀区侨联参政议政专委会信息员,为什么说是“实衔”呢?“活儿”是必须干的,组织街道的归侨侨眷参观学习,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等等。只举一项任务——每到重大节日或纪念日上级侨联组织都举办征文活动,比如国庆6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年、党的统一战线确立90周年等,自己要带头写,还要组织辖区内的归侨侨眷写作,如不尽心尽力,哪次活动都完不成任务!现在想来也对,不管什么“虚衔”“实衔”也不管什么“长”,都不在国家的干部编制序列之内。
到目前为止,独著或以我为第一作者写作出版了14部书(不包括以他人为第一作者的合著成果),且有5次获省部级奖项,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但是这些成果多在退休之后完成的,换句话说,晋级(比如评二级教授)、评先进(模范)均无资格,连分母都不是,还能做分子吗!? 可能有人会说,你的名利思想严重!我不以为然。以书为伴以书为乐,读书教书写书,是我的乐趣与爱好,也是我的责任,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这恰恰说明我淡泊名利。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
从1995年《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我的专访到现在,有10余篇(不包括到外地开会、讲学接受学生的采访,和一般报道),其重要的有1995年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唐虞的《闹中取冷白润生》、1996年3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台播发的《杂家白润生》、1996年6月12日《人民日报》董宏君的《使历史成为“历史”——访韬奋园丁奖获得者白润生》、1997年《新闻三昧》第6期杨湛宁的《十年铸一剑——记民族新闻史专家白润生》、2002年6月23日《科技日报·中学生科技》施剑松的《穷困求学求穷尽》、2002年11月12日《中国民族报》蒋金龙的《薪火不断温自升——记少数民族新闻学学者白润生教授》、2003年《倾听传媒论语》(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傅宁的《白润生:手持木铎的采风者》、2011年12月22日《保定晚报》李丽敏的《白润生教授的故乡情怀》、2012年第5期《新闻论坛》傅宁的《民族化﹒现代化﹒全球化——白润生教授谈民族新闻学的现代化》、2013年9月24日《中国文化报》美文副刊陈莉娟的《润生老师》、2013年《新闻爱好者》第11期”封面人物·对话学者”栏,陈娜的《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新闻史——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白润生》等等,更令我想不到的是还有专门研究我的学术思想的论文——《论白润生少数民族新闻文化观》,论文的作者是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教授,最初发表在2011年第6期《当代传播》上,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简称“国研网”)和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我的字写得并不好,但也有人让我题字,有几次还发在了报上,最近的一次就是给《保定晚报》题写的“坚持新闻方向 坚持为人民为国家大局服务 提高公信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载《保定晚报》2012年1月18日A06版)。
有一位记者采访后写道“年逾古稀的白教授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中气十足。”问及养身之道,当时我顺口说了一句,“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我的身体的确与别人不一样,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老了却老当益壮!我愿献上一组“养”字歌与各位共享:“忍字养福,乐字养寿,动字养身,静字养心,学字养能,勤字养财,爱字养家,善字养德。”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文集《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对我从事写作的回顾与总结。
本人生性愚钝,但读中学时就喜欢舞文弄墨,办个黑板报,出个油印小报什么的。1957年高中毕业前夕,在《北京红十字》报上发表了一篇二三百字的短文,得了五毛钱的稿费。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铅字,高兴得忘乎所以。刚上大学时在校报上发了两篇总共五千多字的短文。其中《在红专道路上继续前进》是一篇书评,在同学中尚有一些影响。从那时算起,到现在大约写了大大小小三四百篇,而收入文集中的62篇(不含代序和后记与附录),是从一百来篇所谓“论文”(确切地说,就是字数比较多的长文章)中筛选出来的。已编入我的其他文集的,一般也就不再编入此集了。有全局宏观研究,也有微观个案研究;有学术会议的主题发言,也有分会场的研讨文字;62篇文章,分编为十辑,有对某一学术观点的陈述,也有就某一学术现象的碰撞;有作者学术研究的心得,也有对名家名著的评析。这一切都以我自己的思维方式,自我认知的深度,来诠释同一个理念,即发展与繁荣少数民族文化。
何谓文化?按着余秋雨的说法,“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①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一个文化过程。应当重视文化的外在形式,更应当重视它的精神价值;我们要重视文化的积累,更要重视文化的引导作用。重视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1954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8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就已规定,各民族均有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大力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事业。后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再次规定,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培养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干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把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区分开来,这是我们党的一大理论创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指明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特别是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其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论述,是指导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和工作指南。从众多的文章中筛选出关于少数民族文学、新闻、出版、教育的文章结集成册,并辅以标题《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白凯文少数民族文化文选》,意在对内呵护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外抵御外来不良文化的渗透,牢固树立“文化民生”理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中尽绵薄之力!
十八大胜利闭幕后,“树立文化民生理念,强化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认为,确立文化民生理念,这是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基础,一定要“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人人能够理解文化民生内涵,人人弘扬文化民生精神,人人都高举文化民生的旗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通过宣传和践行,以期形成我们共同的美好愿景。其实这才是我出版这部文集的真实意图。我们以及我们的前辈多少年来“黑夜寻火、鞭下搏斗”,不就是为了争取一种健康的“无伤害文化”吗?!
此次结集出版,除校改语言文字等技术性错误外,力求再现原文的本来面目,欢迎广大读者、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在拙作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领导和师生,尤其是赵丽芳(博士)副教授以及帮助我整理文稿、文字录入等几位年轻学子韦荣华(《森林与人类》编辑部副主任)、尹宏伟(2007级新闻学研究生)、陈莉娟(上海交通大学2012级新闻学研究生)、赵春风(2011级新闻学研究生)、李坤(2012级传播学研究生)、魏江楠(中央民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2012级本科生)、刘畅(2011级新闻学研究生)等,感谢他们对民族文化建设付出的努力和无私奉献!
拙作能够如期与读者见面,是与《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田玉香、梁雪云、宋辰辰等同志的辛勤付出分不开,借此亦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白润生
(本文转引自白润生的新作《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白凯文少数民族文化文选》后记,题目为编者所加)
注释:
① 引自余秋雨:《文化是一种集体人格》,载《北京晚报》2012年11月2日第4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