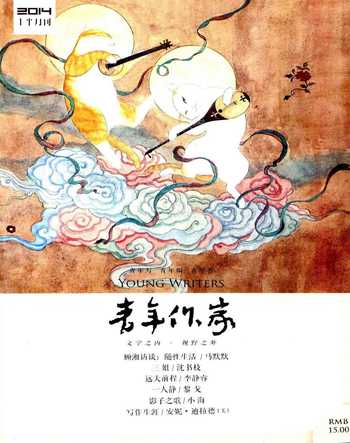第二人生
简安
【冷山】
上一次耳朵患疾,是四五年前。我那时候是个狂热的潜水爱好者,满世界找地方潜水。胆子又很大,不知道地有多厚,总是跟潜水长要求再深潜一些。回上海以后,有一阵也耳朵堵塞,没去看医生,过了几天就恢复了。后来,我开始写小说,把女主角也写成了听力有障碍的人。可是男主角的人生根本无法接受讲不通的逻辑,把她的话当成了吹牛皮,听力不好还当同声传译,你当我是傻子吧?耳朵有恙,也让我想起康涅狄格州。距离纽约一小时火车车程的寂静新英格兰,冬天冰天雪地,春天山里有鹿出没。那地方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山脉,属于丘陵,我总是习惯称康州为山里。我人生里,最不知日月的日子,不在瑞士,不在西藏,不在世界的尽头,而是在康涅狄格。这个世界的所有喧闹都因为我去到那里,暂时被阻隔,就好像是一段失聪的光阴。我记忆里的康州,是寂静无声的,连汽车的引擎声都没有,只有大片白茫茫的雪花从天空坠落。再冷的天气,路上总有人在跑步。
天气冷得刺骨,零下十几度是家常便饭。早晨的Stamford(桑德佛市)火车站总是很热闹,天蒙蒙亮就已经有很多人乘车去中央车站。天气很冷的时候,早晨头发要是没吹干,瞬间就结冰了。Stamford车站候车室里,Dunkin donuts(唐恩都乐,名列全美十大快餐连锁品牌)门前总是有人在排队买咖啡和甜甜圈。康涅狄格,到冬天就变成了冰天雪地的山林,可是那地方不萧索。康州人大多都是体面的,穿得保守又整洁。早晨有满满一火车的人去纽约上班,傍晚再回来。到了春天和夏天,汽车行驶在公路上,路就穿过山林,积雪化去之后,整个天地焕发出盎然的生机。越洋旅行的人,会去迈阿密,去纽约,很少人会去康州。康州夏天的海,总是有些冷清,没有比基尼的美女,也没有摩托艇。游轮和快艇安静地停泊在码头上。海边的餐厅,偶尔有海鸟盘旋而过,有钱人的太太们在那里喝气泡水吃午餐,她们打扮得优雅端庄,钻石很大颗,只是不知道她们绝不绝望。
从波士顿坐巴士去纽黑文,我遇见过一个耶鲁的学生,他对我说,“康州真是太闷了,太闷,太闷了,纽约多好啊,真羡慕你。”今年冬天Ellen陪我从纽约去过一次康州,我们坐在去往Danbury(丹伯里市)的火车上,望着窗外无边无际的冬夜,她对我说,这里真是乡下啊!温暖加州的大农村能接受,这样的冷酷仙境还真是受不了。可是我却喜欢康州,也许是我能够了解它的诗意,也许是别的原因。在我部分听力受损、对外界的感知能力退化的时候,便格外想念康州。那里冬天漫天风雪,是不言无语的静默天地。小镇Ridgefield(里奇菲尔德)走几步就逛完了,树上一直点缀着灯光,那点点的光,还有不远处的街灯,与渐渐暗下去的深蓝色的天空相配,好像繁星镶嵌,真是非常美。静谧的美,与欢腾的美比起来,总是在我心里更有地位。
世界忽然不够清晰的时候,竟也是一段清醒的时光。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声音排除在外,这个时候,我就格外思念康涅狄格,还有那个住在冷山里,读着《百年孤独》的人。
【夜空中最亮的星】
昨晚睡觉前,我在网上看到摄影师Alessandro Puccinelli(亚历山大·普西内里)拍摄的这组名为A Van in the Sea的照片,看得我睡意全无,立即爬起来找到Alessandro的官网,他说,这组2013年拍摄的照片,是他驾驶一台在2011年买的老旧但强劲的房车,沿着葡萄牙南岸行驶,在每天睡觉前拍下的。我之所以从床上跳起来,是因为那台停在星空下的Motor home(房车)太眼熟了,不就是那台在新西兰与我一起旅行了21天的Motor home吗?那片星空,不就是Nelson Lake National Park(尼尔森湖国家公园)那一夜的星空嘛?
一个摄影师的作品,让我曾经亲身经历却没能保存、无法分享的那个世界,以清晰感性的面目呈现——那是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南半球那台雪白孤独的Motor home。
对于Motor home,经过深入的胡思乱想,脑海中,是潇洒的人,四海为家,白天在风尘仆仆的旷野疾驰,夜晚静悄悄开进陌生的小镇,车窗里升起炊烟,穿着格子衬衣的开朗夫妇随手拧开无线电,“Country road,take mehome”混着车内昏黄光线,而他们的白天,永远属于路上。
所以,当我远在澳洲的旅伴Chris,他足一枚港男,SAP consultant(SAP实施顾问),我们具备天差地别的个性与风格,他能把旅行计划做成咨询报告;我可以开车开到油箱里几乎只剩一滴油,当然是在他睡着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这次驾驶的不是NormalVehicle(平常的车),而是Motor home时,我就把我们之间来往的邮件的标题从trip(旅游)改成了odyssey(冒险的长途旅行)。然后,我看着Chris与Matthew,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房车租赁公司——Maui雇员之间来来去去的邮件,有关汽车保险、有关促销套餐、有关怎么付预付款、有关车子万一抛锚在路上怎么办之类的问题,我已经开始在北半球自行联想怎么在车上睡觉?怎么在车上洗澡?怎么在车上做饭?怎么在车上如厕?
还未等到想明白一切,我已经站在奥克兰机场外,Maul公司的柜台前,领取了一包“厕所消味剂”。接着,我手里出现了一本字典厚度的Motor home使用手册,然后手捧一杯热巧克力看了一部历时十分钟浓缩版的电视教程,比如如何启动引擎、如何接通Main Power(总功率)、如何清洗马桶、如何点燃瓦斯。等到Maui员工将属于我们的那台雪白的房车交付并热情地祝我们好运时,我只知道这车子很高,不要随随便便开进停车场,其他的,我都打算依靠Chris。
随后踏进五脏齐全的Motor home,把背包甩到床上,Chris正式成为住在下铺的兄弟。可惜他对着一张竖在车子尾部的桌子一筹莫展,这玩意儿夜里怎么变成张床?接着我翻箱倒柜,发现车子里除了瓦斯炉,还有个烤箱,有个冰箱,锅碗瓢盆、砧板菜刀甚至洗涤剂都一应齐全。就是洗手间,袖珍了一点。
这个“有马达的家”,来自福特公司,手自排一体,对于开陨小车的我们,俨然是个庞然大物。Chris刚踩下油门,拖在车头后面的车箱,就不合作地跑偏,“真是个怪物。”我听到这个港仔在嘟囔。Motor home到底难不难开?它的体积是面包车,车上载有厨房、洗手间、床铺。视线也与普通车不同,你无法从后视镜以外的任何窗户看到车身外的情况。所以,一切得跟着感觉走。
属于Motor home的第一夜,多少有点陌生与期盼。我给自己的枕头套上枕套后,坐在上铺看Chris翻着使用手册,成功将桌子拆成了他的床铺,他有与我一样深蓝色的床单。然后他打开车体的那个匣子,拉出电线,车上的取暖器自动工作了起来,“我们有电了!”Chris终于感到踏实。
接着,他几乎把所有的锅碗瓢盆都端到了厨房里,我们其乐融融地煮了一顿晚餐,拿茄汁大虾出来跟隔壁只吃烤香肠的胖子显摆,把蔬菜炒得“刺溜”响。四下所有的房车都亮着暧色的灯,好似街区上的邻居,有人选择在车里煮饭,透过起雾的窗,牛肉粒的香味飘散出来。
饭饱洗净后,我爬上驾驶室上的床铺,取暖器吐着热气,那一夜的奥克兰,忽然下起雨来,雨点敲打着车顶,我躺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发现从来没离“屋顶”那么近过,也渐渐找到了一些感觉,我还发现,带着房车走,每天早晨都不用整理行李。真是一个“有马达的家”。
为了识别南十字星辰,我买了一本《通俗天文学》。我只是想开着车,在南半球那个岛上转悠转悠,看看南十字星,顺便跳个伞什么的。后来,我发现,新西兰有广阔蓝天、浩渺碧海、连绵雪山、葱郁绿地、自由生态,以及我所见过西藏之外夜空中最亮的星。上帝把最好的自然风光全部给了这片国土。
虽然家庭旅馆、汽车旅馆随处可见,但各种品牌,经过改装,独立驾驶或者由汽车牵引的各类房车依旧在南北岛的高等级公路上随处可见。新西兰的道路十分完美。路好认,如果你思路足够清楚,甚至不需要GPS。路好美,随随便便,都是一幅画铺在两侧。路好开,即便是山路,驾驶者也无需太多忧虑。如果你按照道路两侧的“建议时速”,完全不会有任何安全顾虑。无论深入到怎样偏僻的角落,道路的自身状况、指向标志、加油站的各项服务全部保持着相同的水准。倘若是在乡间行驶,会车的机会也不多,偶尔有车辆从身边驶过,对方也多半会与你打个友好的招呼。
Holiday Park全天开放,通常这样的营地,汽油、水、食品、旅行的各类信息、各种旅行生活设施都可以从此获得并补给。《魔戒》中,那个看似充满荒山野岭的新西兰实则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不过,21天的环岛游,总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途经Nelson LakeNational Park那晚,Motor home开进国家森林公园,Chris说,这个夜,就属于“随处停”之夜,因为这里不会有电。根据GPS的指示,车子已开到湖边,但过分黑灯瞎火,完全分不清道路与湖边。只见到远处有一辆亮着蓄电池的房车,我们摸索着往它靠拢。只是——轮胎陷了。那个GPS真精确,我们的确把车开到了湖边,再一脚油门,就直接开进湖了。因为太邪门了,附近房车里绑着辫子的英格兰小伙子跑下来,帮我们把陷在湖边石子路里的车子往外推。我想过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愣是没想过半夜车子陷进石子路是个什么情景。我几乎闻到了轮胎烧焦的味道,幸运的是,英格兰小伙力气了得,车子奇迹般地被推了出来。
我们谢过英格兰人,把车子停在安全静谧的森林里。那一夜,溪水流淌着,除此,万籁寂静。不过贴心的新西兰人,在国家森林公园里依旧建了厨房与洗手间,大冬天,厨房的水龙头里竟然流出了热水,我于是心满意足地洗了头。
后来这台Motor home,与我们就好像是过了磨合期的情侣,我们从北岛的奥克兰出发,途经陶波,在惠灵顿搭乘Inter IslanderFerry(国际米兰岛民渡轮)来到南岛,经过皮克顿、尼尔森,在凯库拉海钓,看成群海豚越过海面,在弗朗兹约瑟夫走了7小时冰川,接着在瓦纳卡跳了一万五千米的伞,在皇后镇蹦了极,经过米尔福德市,来到此行最南端的达尼丁,在库克山徒步,最后在基督城归还了它。
四年多过去,我一直记得那台雪白的Motor home。它在我记忆里,始终笨拙,始终沉默。它载着我,完成了一次环岛的旅行,而那一次旅行,才让我真正迷上世界的尽头。
【南非回响】
八岁时,我已向往着好望角。这梦想终于从趴在地图册上的神往变成可以许下新愿望的现实。旅行,让地图册上的那些奇幻角落一一变成了鲜活记忆。记忆,又在拼凑碎片时折射出最意想不到的光芒。
“无论对谁来说,离开自己温暖舒适的家,前往一片新奇而美妙(也许在最初时远称不上美妙)的土地,结识那里的人民,熟悉那里的文化,都将是个艰巨的过程。这种过程也许可以算是我们人生中经历的最难以应付的困境。”南非作家Dee Rissik(迪·里希克)在《南非文化震撼之旅》一书中这样开篇。对于好奇陌生的旅行者、独辟蹊径的移民,这种迷惑的状态,是一种文化的震撼,让南非,如磁铁般吸引着远方的人们。
“得再看一眼南非的晚霞。”临走前的那一天,我身旁的摄影师从克鲁格国家公园返回约翰内斯堡的高速公路上,看着落日以一种令人来不及捉捕的速度沉入宽广的地平线,他始终不肯放下手中的相机。第一缕南非的朝霞出现在我们到达那日的飞机机舱里。那时,他也一样兴奋地端着相机,不肯放过这同样异乎寻常的绛红色。谁说全世界的日升日落都一样?
这里可是南非!神奇的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国度。更何况,全世界的足球明星此刻都在这里,乌乌祖拉响彻云天。
岁月在两大洋的潮汐与海风中无声流淌而去,开普敦有一个全世界最著名的海角,还有一座桌山,有着绝不同于非洲大陆其他城市的优雅旖旎。她在这片大陆的顶端,面向浩瀚的汪洋——更深处已是南极大陆,背对广袤的非洲荒原,书上说,那是“钻石的棱角、舞者的足尖”。
开普敦是个花园城市,有山有海,特别是这里的空气,简直是太好了!”朋友驾驶簇新的七人座保姆车从开普敦机场直接开往桌山。南半球的冬季正午,阳光直射,人人都只身着单衣,鼻尖还渗出微汗。再也没有比在天气晴朗的桌山山顶发一整日的呆,更适合做南非游开篇了。整个开普敦城市与港口风光尽收眼底,如若换一个角度,在城区,随便一抬头,也可以望见独一无二的桌山。
每一个来南非旅行的人,倘若第一站是开普敦,一定会有一些质疑,这里难道真是非洲?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在非洲建立一个补给站,选择了南非开普敦省的桌湾作为据点,以服务往来于欧亚间的船只。从建城伊始,开普敦一直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与英国人争相做主的“客栈”。这座南非白人心中的“母亲城”,历经荷、英、德、法等欧洲诸国的统治及殖民,城市的模样,与人们印象中的非洲荒原大异其趣。
上帝长方形的餐桌安放在东大西洋海湾,远处大西洋里的椭圆形小岛是罗本岛,“Robben”在荷兰语中是海豹的意思,那里曾经关押过曼德拉等反对种族隔离的著名政治犯。约有3000名政治犯曾经在罗本岛上度过漫漫牢狱生涯,直到1991年最后一个政治犯被释放。
稍稍向东,便是更有姿色的印度洋了。大西洋,即便在夏天,海水依然偏冷,蓝色也偏淡。因这唯美海湾,可以在山顶做一日停留,即使什么都不做,只是享受开普敦的日光、空气、海风,也不会感到无味。
桌山虽然是沙岩叠片构造,植被却十分茂密,种类繁多,岩石的缝隙里都长满了灌木,山上的鸟类也多得出奇,保护区内有2000多种濒临绝种的原生花卉、植物,约150种鸟类。还有岩兔、蜥蜴在岩石上、小道旁,不避游人。上帝的餐桌,也是动植物们清新洁净的家园。
不得不再次提到开普敦的空气,开普半岛自东南方经常会有强风吹至,而当地人都将这股强风称为“开普医生”。这股风形成于开普敦西面的南大西洋高压脊,开普医生将清新的空气带来,把空气中的污染物吹走。
开普敦的白人区以爱德华式与维多利亚式的房舍最多。桌湾附近错落保存着18世纪的荷兰式建筑。去豪特湾的路上,会驱车经过坎普斯湾,开普敦的豪宅在此云集是有道理的——这里有迷人的沿海公路,十二门徒峰为背景,曼妙的白沙滩,天体浴场,澄蓝的大海……典型荷兰式的房子,以清一色的芦苇为顶,散落在海边或者山旁,如一场童话。
这一路,不断有豪华跑车驶过,真是拍汽车风光片的绝好地点。除了跑车,还有哈雷摩托呼啸而过。朋友说,有一年,某一个医疗组织来开普敦开会,组织者临时通知各位与会者:乘坐的大巴坏了。不过,为了到达目的地,组织方为每个人准备了一辆哈雷摩托,请各位撅起臀部,坐上哈雷,尽快赶到目的地。
标志牌上的经纬度这样标明:34°2125”S,18°2826”E。Cape of GoodHope——美好希望的海角。
在我8岁,也许更小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地理老师——父亲指着地图上一个遥远的角落对我说,“好望角,世界上最险要的航道,惊涛骇浪,在南非的最南端。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那些大大小小航船都必须经过这里,能不能顺利到达,要看运气……”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到好望角……”8岁的我,一定那样想过。
互联网上,有这样的航海日记:“乌云密蔽,连绵不断,很少见到蓝天和星月,终日西风劲吹,一个个涡旋状云系向东飞驰,海面上奔腾咆哮的巨浪不时与船舷碰撞,发出的阵阵吼声,震撼着每个海员的心灵……”在开普点不远处的洋面上,有一个白点,好像停在海上的帆船,又好像是跃出海面的鲸鱼,实则是耸起的礁石,而这片海域下,暗藏着无数的礁石,没有船只敢靠近这个海角。
一座1857年建造的古老灯塔默默耸立于开普点。一百多年来,正是它为来往的船只导航。后来人们发现这座灯塔建得太高,容易被云雾遮挡,便弃而不用,又在开普点下方重新修建了一座新的灯塔。开普点的观景台上还设立了指向全世界各大城市的路牌。从南非的好望角前往新加坡9667公里,新德里9296公里,里约热内卢6055公里,耶路撒冷7458公里……
摄影师用上了索尼微单相机的最新技术,转动上身,用镜头连扫好望角与东方的印度洋面,生成宽幅照片。海与海角,天空,白色巨浪,飞鸟,连风的速度都可以在宽幅照片中捕捉到。
航海者们千辛万苦经历了好望角的惊涛骇浪,进入平缓的流域,却发现,这眼前的一切,平淡无奇。还是一样的海面,还是一样的无边。只要往前,再往前,就豁然开朗。远方是如蓝宝石般的印度洋洋面以及通往神秘富蔗东方的航道。离开好望角,已是黄昏。整个好望角笼罩在暖黄的光线中,我依然回望,白色的海浪打在黄色礁石上,千年万年,不曾改变。
这个宁静的海角,寄托着无数人的向往,而我,自8岁起就惦记,终于来到。
【多住一个城市,总是好的】
去年深秋,有天夜里我和一个小有名气的摄影师朋友闲聊。他说,“特别想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明年5月去纽约大学进修。有时候,害怕改变,这样不好。”我说,“对啊,经常做些痴狂的梦,比如你,绑架林志玲,比如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个悲剧什么的。人生很短,要尽量干些不擅长的。我看了毛姆的《刀锋》,想要晃晃膀子,所以来了美国。”他说,“毛姆啊!毛姆不是凡人!其实,马尔克斯、亨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德、朱丽亚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哪一个是凡人?”我觉得他情绪高涨,就怂恿他,纽约此时此刻正在遭遇飓风,疾风骤雨,中、下城全部都没电了,等飓风过境,冬天一来就该暴风雪了,要争取“改变”,来体验体验纽约疯狂的生活,离开墨守成规(成规往往也不一定适合自己),才算是珍惜时光。他说好,还祝我变成疯子。
后来,他没有去纽约。至今还未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害怕改变。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害怕改变,再正常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惯常的路线,在哪儿加油、在哪儿吃饭、在哪儿逛街、在哪儿看戏、在哪儿喝酒、在哪儿消遣…一要在另一个地方,重新摸索出这一套来,大概也不太容易。如果没有去美国,我恐怕也不会来北京。
刚到波士顿那天,提着两个大箱子,打车打得心惊肉跳,大清早找到地方安顿下来,夏天房间里只有一个大风扇,简单的几样家具,去洗衣服要跑下5层楼,洗完要烘干还得再跑一次。真的不认识任何人。后来跑去日本火锅店吃了一顿好的,还魂过来。之后学会了坐公车、搭地铁,在陌生的城市寻找惯常的路线,与那里的人们培养感情。后来我又离开波士顿搬去了纽约,再一次找房子、搬家、寻找路线、培养感情。
纽约的过程比波士顿容易些,汽车到站,己经有朋友开着车来接,上西区比波士顿生活的街区便捷不少,生活越来越丰富。但还是只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夏天来的时候,我真担心没冷气会不会热死,好在纽约夏天二十几度的天,风扇足够了。要离开的时候,行李又重新打了包寄回国。过程真的是披头散发,我倒是没问过自己为什么要放弃上海安逸的生活跑到美国来吹电扇?
多住一个城市,总是好的。
变化的成本真的很高。房价太高了,连搬去另一个城区住都难以实现。可是,人怎么能够只住在一个地方。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颠沛流离”。经历了迁徙,再一次迁徙就不再如此难以说服。真是魔法的盒子。为什么旅居的人,不会觉得上路伟大而麻烦,时间久了就此加入了游牧民族,因为离开过一次,心态就轻便起来。任何身外物都无端端捆住自己,只有爱与梦、见与识,如轻风加冕。
于是,纽约回来,在炎热的上海呆了一个月,我又拖着两个行李箱,去了北京。开始在这里工作、生活,要搞清楚南北,获得新社交,还有必须适应北京的雾霾、交通、服务。最后的三点,基本是排斥的人们不愿意来这个城市的原因,可是,我总是想,都没来住过,就难以了解北京的好与坏。就好像纽约,让人又爱又恨,只有住过了,才能发现,那只109街的老公寓里的老鼠,能在余生获得回味。
其实,北京下过雨的夜晚,特别迷人。我还看见了真正多云的天气,北京城在浓厚的云层之下,不是雾霾,是真正的云,有种凝重祥和的美。望京有极好的美式brunch,东单破旧不堪的胡同深处,有特别正宗的越南小馆。超市里,营业员会豪爽地跟你调侃,甚至被出租车司机挤兑一番。这都是过往生活没有经历过的,没有经历过的一切,都吸引入。
我在北京的朋友,上周末对我说,真想要离开北京,放下工作,去德国的小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哪怕半年也好。我真想捏住她的肩膀对她说,“不要想一想就算了,要付诸行动!”
我跑步的时候,常常听Bob Dylan(鲍勃·迪伦),他摇头晃脑地唱道: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on your own
With no direction home
Lik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生活得好像一颗Rolling stone(滚石),不害怕改变,也许就拥有了第二个人生。“拥有第二个人生的方法很简单,放弃现有一切,包括你熟悉的语言,去完全陌生的地方住上一段时间,在那儿开始你的生活,所有事物将重新洗牌。不要害怕未知,因为人从来不是被恐惧养大的,理解这点,就能勇敢。”有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