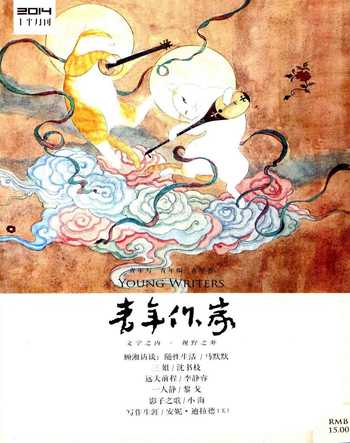魔王与男孩
纳兰妙殊
冬夜的森林黑得像浓浆一样黏稠。生铁气味的西风穿行在枝桠间,吁吁哀吟,犹如幽魂飘荡。一位父亲打马狂奔,穿过森林,怀中抱着不断战栗呻吟的男孩。
那男孩,该怎么形容他呢?他是人类能想象得到最美的孩子。一根根柔软金丝似的头发,每次要修剪时都让理发师舍不得动剪刀。带着精致褶皱的眼皮之下,眼珠蓝得犹如五月晴天。他的肌肤像积雪上照耀着玫瑰色的晨曦,嘴唇是浆果果肉似的柔软红润,牙齿闪动珍珠的光泽。而他又有着配得上那容貌的聪慧,虽然这小村缺乏智者贤人,但那好学的孩子已经依靠能读到的有限几本书,开始学习写诗、研究几何题了。在教堂唱诗班里,当他把金发梳理到脑后,穿上纯白的罩袍,用水晶似的声音唱出圣歌,聆听的人们总有一半要被那美景感动得落泪。
他像是奥林匹亚山上侍奉众神欢宴的仙童,不幸跌落云头,在人间迷了路。村里妇人在抚摸他头顶时,无不饱含复杂的情绪,暗暗叹气。她们对他父亲说:“这样的孩子注定养不大,万一……你可不要太难过了。”
父亲当然不会相信什么“注定”。就像这天村里的医生对着浑身滚烫、呼吸微弱的男孩缓缓摇头,告诉他孩子活不到天明了,他也不肯相信。他拒绝接受几个小时之后他的爱儿将像搁在火炉上的雪人偶一样,被无法排遣的高热烤融,而他将失去亡妻留给他唯一的珍宝。
年轻的诊所学徒忽然开口道,“也许……也许另一个村的诊所能救得了他,据说那儿的大夫曾治好过几例这种病。可惜路太远了,孩子坚持不了那么久。”
那父亲立即道,“告诉我诊所在哪,我一定能赶得到。”
人们找来地图,指给他看——那地方在地图边缘,得穿过一大片森林。
父亲向医生借了马厩里最快的马,一匹枣红色的西班牙马。他翻身上马,一手控缰,一手搂紧用毛毯裹住的男孩,双脚狠狠一磕马腹,似乎又焕发出当年当骑兵的威风。马长嘶一声,奋蹄奔去。
众人目送他的背影,面面相觑,没人提起——或者没人敢提起——那片森林的邪恶传说。据说在没有月亮的晚上,魔王会带着他的宠物双头蛇到林中散步,把他钟意的过路人带回他的洞窟。
可怜的父亲已经忘记,自己只是个十年前在逃兵役途中、爱上小村少女的外来人。他打马狂奔,穿过冬夜森林,怀中抱着失去知觉的爱子。
男孩蜷缩在他手臂里,像一只被猎人俘获的鸽子,肢体不时惊悸地抽搐一下。他只觉得那柔嫩的身体出奇地小,小得像是刚从亡妻身上摘下那天,湿漉漉、热腾腾的。那天风雪真大啊,清晨她还坐在窗边编织一双小毛线袜,雪光映在她双颊上,黄昏时婴儿出生,夜幕降临时她便咽气了。雪太大了,医生没来得及赶过来。婴孩的生日,即是她的死日。她用全部生命化成这一块崭新的血肉。在悲欢交织的莳育中,他瞧着亡妻的蓝眼睛和微笑在婴孩面庞上一日比一日更逼似、更鲜活。啊,只要儿子活着,她就还有一部分活在人间。
他那颗心脏在胸脯里焦灼狂跳,“砰砰”地撞击肋骨,仿佛要冲破皮肉的禁锢,扑到男孩身上去,用心头的血濡沃他、暖热他。
他反复念叨,“我的宝贝,我的珍珠,我的性命,这次我们一定赶得及,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你……”
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马蹄踏着满地潮湿腐烂的枯叶,声如急雨。父亲却仍嫌马速太慢,他真愿以十年寿命为租金,赁一匹带翅膀的飞马。
男孩咳嗽着,在父亲怀中不安地挣动,似乎清醒了一点。
“……父亲,我们在哪儿?为什么晃得这么厉害?”
“我们在海上。”父亲俯下头把嘴巴凑近他的耳朵。“亲爱的,你不是一直想要到海上去坐船吗?”
“哦,那真好……可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现在是晚上啊。”
“……给我讲讲,我们乘的船是什么样的?”
“是一艘漂亮的三桅船,桅杆高高耸立,主桅和前桅上悬挂洁白的横帆,后桅装着纵帆,它就像生着十对巨翅的神鸟在海上游动。啊,现在是个晴朗的夜晚,稍微有点风浪——所以船在颠簸。但星星们亮得像用丝绸手绢擦过一样。儿子,你可以沿着绳梯一直爬上桅顶,站进瞭望楼里,踮起脚尖,用手摸一摸星星,在上面留下几个指头印儿。”
男孩的眼睛半开半合。“明天我再去爬好吗?父亲,今天我累了。”
父亲柔声说,“再过几个小时,太阳就要出来,我们的船正驶过海峡,初升的太阳将给远方峭壁戴上光芒四射的王冠,大海将像煮沸的黄金汁液一样。答应我,明早跟我一起看日出,怎么样?”
男孩迷迷糊糊地答,“好的,父亲。”
夜枭的鸣叫如诡笑在树梢响起,忽东忽西,忽近忽远。他问道,“父亲,那是什么声音?”
“是海鸥,亲爱的,它们从一朵浪尖上跳到另一朵浪尖上,就像穿着白衣服的小孩子在草地上蹦跳嬉戏。”
狂风摇撼树枝,吹动树叶,头顶枯枝咯吱一声折断。他问道,“那又是什么声音?”
“是海豚,亲爱的,它们正跟着船向前游去,有时从水波里一个翻腾跃向半空,披着晶莹水沫,再落回海中。你若站在甲板上,就能看清它们丝绒一样的灰皮肤、小小的黑眼睛,以及总像快乐微笑着的嘴巴。”
男孩虚弱地说,“父亲,我冷,风太大啦,为什么还没日出……”然后他再次昏迷过去。
夜黑得透不过气,仿佛被遮盖在巨鸦的羽翼之下。树和树在濒死的气息中沉默站立,站成无数迷宫,小迷宫之外包围着大迷宫。那父亲打马狂奔,穿过深夜的森林,怀中抱着生命垂危的爱子。
……男孩听到有人轻声喊他的名字,他转过头,看到一个乘黑马的骑士出现在树枝和树叶的影子里。俊俏的小马,戴着银辔头,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
那骑士就是林中的魔王。
魔王跳下马,缓缓走过来,紫色长袍下摆在草叶上划过,簌簌有声。他的衣领和衣襟上装饰着黑得发亮的猫头鹰羽毛,领口扣眼里别着一朵风茄花,衣襟上以珍珠拼镶出奇异的图案。一条绿底黄花纹的双头蛇从他袖口里探出头来,嘶嘶吐信子,钻回去又从他领口中钻出,盘在他脖颈上,像一条活的领结。
男孩并不害怕,他只是好奇地盯着那条蛇,问,“为什么它有两个头?”
魔王笑了。他的手从袖口伸出来,像抚摸小猫一样轮流抚摸两个蛇头,答道,“一个头叫贪婪,一个头叫欲念。漂亮的孩子,别嫌它们丑恶,我实话告诉你,让人类进步的还就是这两样东西呢。”
他的声音是那么温柔,就像可供啜饮的丝绒,灌注进耳中有说不出的舒服。他的漆黑长发披散在肩头,包围着青白的脸庞,仿佛夜云环绕月亮。
男孩听见他说:“亲爱的孩子,跟我走吧,我会带你离开这里,到更好更美的地方去。”
男孩问:“更美更好的地方是哪儿?会比教堂后的花圃更美吗?老神父在那儿教我种植早金莲和黄水仙。会比春天时候的池塘和林子更美吗?我跟红头发的小蒂尔达在池塘里游泳,在林子里收集莓子和蘑菇。或者,能比我家的炉火边那张狼皮褥子更好吗?冬夜的时候我会暖暖和和地坐在那儿,靠在老狗阿莎身上读书,听父亲拉一段小提琴,有时他会允许我喝点他酿的苹果酒,给我讲母亲生前的事情……”
魔王笑得几乎呛住,说:“可怜的孩子!乡野之间这点小小乐子,比起我将给你的趣味,简直像用一根蜡烛的光去比正午的太阳光。”
他走过来,把男孩的手握在自己手心里,那手白得像象牙,是冷的,但又冷得并不令人讨厌。
男孩只眨了眨眼,面前的景象就变了。他发现自己身在一间宽敞的图书室里,四壁的书架从地面一直连接着天花板,空出的西面墙壁挂着有流苏的壁毯,以羊毛、真丝和金银线织成,织出阿波罗由林中众女神服侍洗浴的图案,地上铺着厚厚的象牙白地毯。房间角落的瓷瓶插着大朵茶花,几扇大窗旁边垂挂白纱里子的蓝缎子窗帘,窗边一个带靠枕的宽大扶手椅,让人一见便想坐下去,在柠檬色的阳光里读上几页书。
魔王伸开双臂,缓缓转圈,柔声说,“你喜爱阅读?这里有荷马、奥维德、塔西佗、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马基雅维利的全部著作,都是价值连城的珍本。这是棱纹纸,这是连史纸,这一套以丝绸装帧,这一套封面用了锻压的小山羊皮……一般读书人的书架上总会收藏尼禄那位好宰相裴特洛纽斯的《萨蒂利孔》,但这座藏书室里另有他已经失传的作品《尤思逊》和《阿尔布夏》。平凡人只能看得到李维一百四十二卷《罗马史》中的三十五卷,他们说其余的都散佚了,哈,可在这间屋子里,我们有完整的一百四十二卷《罗马史》。瞧,这儿还有几十卷中世纪基督诗人的寓言诗,几十卷文体家的论述,几十卷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凯尔特等民族的神话传说,几十卷绘制世界各地海洋山峰森林面貌的地理图册,上百卷由修士和僧侣撰写的历代帝王传记,甚至还有上百卷地中海巫术的文献研究……”
他在书架前滔滔不绝地讲解,回头发现男孩正呆立在房间中心的椴木桌子前面。桌上摊开着跟男孩身子差不多长的一本巨型书,那是《奥德修纪》,抛光牛皮封面,三面书口涂金,但更美的是书内装订的数十页镶嵌画插图。男孩一页一页翻动,花瓣样的嘴唇不自觉地微微张开,面孔上布满惊诧、虔诚和渴望。
魔王在一旁冷冷看着,轻笑一声,眸子闪烁绿幽幽的光,如深潭,如漩涡。双头蛇无声无息地从他手臂攀援下来,在手腕上邀宠似的昂起头,嘶嘶有声。他轻抚蛇头,像是在对蛇讲话又像自言自语:“我常常说,人们自以为能抗拒诱惑,只因为他们还未见识过足够美、足够诱惑的东西。”
父亲听到怀中的男孩轻声说,“书……”
一阵酸楚隗疚涌上喉头。他没钱,也舍不得离开儿子,所以始终没有送男孩到城里上学,只让他跟着神父读几本书。而他的儿子本配得上世上任何一所学府。
男孩又清醒了点,一阵痛苦的痉挛掠过他的面孔,就像乌云的阴影掠过草原。
“……父亲,我们为什么在赶路?要去什么地方?”
“去城里的学校,亲爱的,你不是一直想到繁华的大城市去上学吗?”
“哦,那真好……给我讲讲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吧。”
“是一所有几百年历史的著名学府,古老的青石砖墙上爬着藤萝,园丁精心修剪的草坪上,生有又粗又高的榕树,树荫下坐着背诵拉丁文诗篇的少年们。每个学科负责授业的都是鸿儒贤士,他们在课堂里讲述星辰、矿物、建筑的奥秘,讲解苏格拉底的学说,高声嘲笑当代欺世盗名的学人。午后他们就坐在自己的研究室里,你可以随时敲门进去,询问算术题目,或者让他们帮忙修理你诗歌作业中不和谐的韵脚……这些就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对不对?”
男孩应道,“是的,父亲。”
“学期末我会去接你回家,让你带我参观你那间小巧清洁的宿舍。明早,等太阳出来了,我就给你整理好书包,送你到教室去,好不好?”
男孩神志模糊地答道,“好的,父亲。”
他的声音犹如梦呓,“父亲,刚才我看到一个人,一个衣领上别着风茄花的人。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去游逛,他给我看了很多美丽的东西……”
父亲的心口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揪紧。他叫道,“亲爱的,不要理睬那个人,不要回答他,听我的声音,跟我说话……”
然而男孩的眼睛已经闭合起来,听不到他的呼叫了,他一分钟比一分钟急速地衰竭下去。父亲执起男孩的手放在唇边,深深地、忧急地吻着,仿佛想咬破那细嫩的指尖,把自己的生命力吹进那小身体里去。
夜黑得严严实实,宛如在深深海底。一切仿佛被一张密得没有孔洞的、绝大的绳罟网罗其中,万物在网底无声昏睡,不抵抗也不挣扎。那父亲打马狂奔,穿过深夜森林,怀中抱着生命垂危的男孩。
魔王笑吟吟地望着男孩,眸子闪烁绿幽幽的光,如深潭,如漩涡。“除了书,你还喜欢花是吗?那么来吧,好孩子,让我们到外面去看花。”
他们走出图书室,走过一个金碧辉煌的宽敞大厅,每一件陈设的器物都极尽奢华,那高高穹顶上绘着的诸神画像,要把脖子仰得贴到后背上才能看到。男孩问,“住在这里的是国王和王后吗?”魔王笑而不答,只携起他的手。
男孩眨了眨眼,面前的景象就又变了。他正身在一片望不到边际的花园里。七个水池里喷出七股喷泉水柱,每个池子里都有雪白大理石雕刻出的神话人物:宙斯和加尼米德,公牛与欧罗巴公主,欧律诺墨与美惠三女神……园中种着玉兰树和石榴树,树影下的小径边开着紫罗兰,蜂儿在花心里爬进爬出,嗡嗡有声。
他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叹道,这一定是御花园吧?魔王笑而不答,只携着他,慢慢向前走。
他们路过一块郁金香花圃。花茎纤细挺直,那线条简洁优美的花冠则像一对对虔诚合拢的手掌。男孩惊叹着,想驻足赏玩,魔王却不停下脚步。他说,“好看的还在后边呢。”
他们又路过一片山茶花花圃。有单瓣的,有复瓣的,红如玛瑙白如无瑕的玉,粉的如新娘羞赧的脸蛋。男孩摇头咋舌,想凑近些细看,魔王却拽着他的手,牵他继续前行。他说,“好看的还在后边呢。”
他们最后进入一个温室花房。魔王伸出戴着猫眼石戒指的手,一株一株为他指点,“种在这里的花才是这花园的精华呢,每一种花都特地配着一名园丁专门照料。看这种玫瑰,奶油一样的白花瓣边缘上带着少许粉红,它叫做“芭蕾舞伶”,就像身着白纱裙跳舞的伶人和着音乐、立在足尖上旋转时,听到观众的喝彩声,脸颊因兴奋得意而腾起红晕。再看这株珍品鹤望兰,它那橙红和蓝紫色的花瓣又尖又细长,正像是鸟的毛冠和喙,你远看时说不定会错认是一只鸟栖落在那儿了吧?等这一整丛都盛放的时节,把鸟舍里养的葵花风头鹦鹉和戴胜鸟放进来,混成一片,花儿像不会呜叫的鸟,鸟儿像少点香气的花,那才叫有趣!再看这株加尔西顿百合,它就是《圣经》里提到的、耶和华在高山布道时才出现的神秘花朵,这样颜色像春日晚霞一般的品种,是皇后的花园也孜孜渴求的……我的孩子,这儿的奇花异卉,你的老神父可培育得出来吗?”
男孩蹲下来,左瞧右瞧,每一枝花都令他不舍得挪开眼睛。
魔王又说,“瞧角落里这一丛!这枝黑色的鸢尾花可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一个珠宝店还值钱。它原本是奥斯曼帝国的御花园培育出来的,帝国覆灭后,一个花匠把球茎藏在帽子里逃出来,才令这花不至于绝种。”
这最珍奇的孤品,花瓣上闪烁妖异的紫黑光泽,像被墨汁浸泡过。男孩不由自主地伸手想抚摸,魔王却把他的手打掉了。“别碰,我的孩子。它叫“黑匕首”,每个花蕊都相当于一小撮砒霜的毒性,若是你看谁不顺眼,或是有人碍了你的事,只消请他到你的花园里来喝茶,趁他起身赏花的时候,把一个花蕊投进他的茶汁里……”
男孩惊骇地盯着那花,摇头说,“我不喜欢它,如果这花园是我的,我一定先把这花烧掉。”
魔王柔声道,“先别急下结论,也许以后你会改变主意……书房,花园,你想要么?”
男孩点点头。
魔王指一指花园中心的凉亭,“很简单,你只要娶她就行了。”
凉亭的象牙椅子上坐着一个身材枯瘦、表情矜傲的少女,两个黑人女仆立在她身后,一个捧着首饰匣,一个用玳瑁柄的梳子替她梳理栗色长发。她身穿绣着孔雀翎毛图案的绿裙子,像人鱼眼泪那么大颗的珍珠,在她干瘪的胸脯上发光。那瘠薄的嘴唇搽了过多胭脂,正跟那焦黄脸色成了对比。
男孩问,“那是谁?我本以为世间的女孩都跟小蒂尔达一样好看。”
魔王说,“她是权势和财富的女儿,她的父亲比所罗门王还有权势,她的母亲比示巴女王还富有。只要你娶了她,这一切就全都属于你。”
男孩问,“……我怎么才能娶她?”
魔王笑道,“以你这样的才貌,我的孩子,只要你听我的话,只要你不去想爱和尊严那种事,你可以娶到世上任何一个女子。你可以拥有世上任何好东西。”
男孩说,“爱是什么?我不太懂。可我确实想要这个花园。”
这时他隐隐听到父亲的声音:“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回来,我的宝贝,回到我身边来……”
幻象消散,男孩再次陷入一片漆黑。他喃喃道,“花……”
“花?”
父亲沉吟着,暂时松开缰绳,从衣服内袋里掏出一条项链。项链坠子是一朵玻璃做的玫瑰花。这本来是他赠给亡妻的结婚礼物,他买不起水晶或钻石首饰,只能在吉普赛人的摊子上买这么一条玻璃项链。
揿一下玫瑰花心,花瓣便弹开,里边镶嵌着他与亡妻的合影。她笑时那甜蜜羞涩的眼睛、嘴角抿住一点的样子,他看了无数次,每次都会看得呆住几秒。男孩笑起来就跟她一模一样。他在那小照上吻一下,将它塞进男孩的衬衣里,搁在最靠近心口的地方。
男孩哆嗦一下,醒了过来。他费力地干咳,又因为咳嗽引起疼痛,伸手死死按住胸口,像要把肺抓出来似的。
“……父亲,我们为什么一直赶路?要去见什么人吗?”
去见你祖父祖母,亲爱的。他说完又感到一阵愧疚,别家的孩子都能在夏夜听祖父讲睡前故事,或是夸耀祖母做的莓子馅饼。而自从逃兵役躲到这偏僻小村,他就再也不敢回故乡去。
男孩模模糊糊地应着,“那真好……能给我讲讲祖父母家是什么样的吗?”
“是城郊的一所老宅子,当年祖父的父亲拿二十个金币买下来的。我和你两个姑姑就出生在卧室那张松木大床上,祖母的猫‘雪铃铛最喜欢卧在床头的羽绒枕头上。你祖父会挨个给你讲:走廊里悬挂的画像哪幅是做过总督的曾祖父,哪幅是做过公主女侍的曾祖母,壁炉上那架古董镀金座钟有什么典故,墙上悬挂的公鹿头又是在怎样一次高地历险中打到的——他说不定还会带上你和他的老猎狗,去沼泽地划船猎鸭子呢。我们屋后的小菜园里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桑树,你祖母种了一畦辣椒,你祖父种了一畦葡萄,白天他们就在那儿晒太阳。等见至小你,他们肯定会给你雨点一样的亲吻,自豪地把你带至岭B居和亲戚家去,说,瞧吧,这就是我的孙子,漂亮得像天使一样的孙子。你也一直期盼见着他们,是不是?”
“是啊,父亲……”
“日出时,我们就会到你祖父母家啦。她会把餐桌铺好带花边的雪白台布,摆得满满当当的,然后笑眯眯地看着你吃——烘得热乎乎的黑麦面包,琥珀色的焦糖布丁,热可可,果酱,腌橄榄,刚摘下来的新鲜桑葚……坚持一下,宝贝,答应我,明早陪我吃早餐,好吗?”
男孩轻声说,“好的,父亲,我答应你。”
他吃力地喘息,胸腔随着呼吸剧烈起伏,喉咙里发出鸣哨似的声音。“父亲,刚才我看到一个人,一个衣领上别着风茄花的人。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去游逛,他给我看了很多美丽的东西……”
他嘴唇蠕动,声音越来越低,终至低不可闻,就像在半夜醒来,用半睡半醒的声音讲述梦中情景,又坠入梦乡。
父亲惊惶四顾,咆哮道,“不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滚开,离我儿子远点!”
然而回答他的只有凄厉的风声。
惨白的雾气席卷过来,犹如一块巨大的裹尸布。寒意中如黑森森的牙齿利爪。那父亲打马狂奔,穿过深夜森林,怀中抱着昏迷中不时谵妄的男孩。
“……当然,除了这张脸蛋之外,你还需要点别的东西。”魔王说。
男孩眼前出现一个会客室。一个干瘦、留着小胡子的人正坐在沙发上,等待主人接见,他焦灼得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用留着长指甲的手神经质地敲打扶手。
魔王悄声说,“瞧,那位满脸悖时相的倒霉鬼,他就是你在读书时结交的好友,他的才华胜过你,但他脾气太臭,写的戏没有一个剧团经理愿意接演,他家中的妻儿只能到面包铺去赊隔夜面包吃。而你则用很低廉的价格把他的手稿买下来,改一改细枝末节,拿去发表。虽然是同一个剧本,但作者不同,境遇可就大不一样啦。你相貌生得讨喜,娶了有钱的太太,手头阔绰,人缘又好,所有记者和剧评家都喜欢你,绝不吝啬他们的赞美。所以你每有一出新戏公映,谀辞都多得要用几辆马车来拉。人们称你有一个被缪斯吻过的脑袋……”
男孩听得目瞪口呆。他问道,“他不会生气吗?”
魔王笑道,“生气?他还唯恐你不跟他做生意呢。”
男孩看到客厅的门开了,一个青年走出来——那就是十年后的他。他的朋友赔出笑脸,把用布包着的一叠文稿递过去,低声道,“我又写了一部新剧,你有没有兴趣看看?”
魔王轻蔑地瞧着那人,又说道,“你将越来越出名,而越出名,你的作品也就越受欢迎,就像泼了油的火焰一样。你甚至不再需要你朋友提供的东西了,你自己的诗集和散文集都大受欢迎。自然你写得本来也不甚坏,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你的作品早就失去了审美,他们只会习惯性地喝彩叫好。当你结束这段供求关系,你那朋友也许会气急败坏地把你告上法庭,但没关系,官司只会让你收获更多的瞩目,是另一勺浇在火焰上的油脂。群众都是些笨蛋,他们只会盯着头顶最耀眼最亮的东西,不管那是太阳还是向太阳借了光芒的月亮。而只要你有名,万事都会像小刀切割奶油一样顺畅轻易。”
他口若悬河地说下去:“你具有所有粗鄙年轻人望尘莫及的、学者的优雅和见识——他们以为挥霍炫耀是一种值得矜夸的趣味,以及言语无味的学者们暗暗渴求的、社交场红人的美貌风度,还有交际手腕——他们以为博学多识就能弥补魅力的缺乏。人们将以与你交谈饮宴为乐,以能当面祝贺你的剧目演出成功为荣……”
男孩眼前像放幻灯片一样,飞快地闪过高朋满座、灯火荧荧的舞场、宴会厅,人头攒动的大剧院、音乐厅、画廊、沙龙。珠宝,绸缎,细瓷和银质瓷器,女士们带笑红唇下的皓齿,无一不在闪闪发光。魔王感叹道,在所有这些地方,你都将成为绝对的中心。人们等待聆听你发表高论,以便抢先附和;等待你讲一个笑话,以便及时哄堂大笑,他们拿你的话到别的场合复述,还得意地说,这是他跟我密谈时讲给我的。
男孩怔了很久,犹豫着说道,“这些都很美,很吸引人,但我跟父亲住在一起,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也有不逊色的乐趣,况且,我还有我的小蒂尔达……”
这时他隐隐听到父亲的声音:“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回来!我的宝贝,回到我身边来……”
但这一次他没有理睬父亲,而是紧盯着魔王绿幽幽的眸子。
魔王似乎早料到这种答话,他挥挥手,说,“那么你不妨看看这个。”
男孩眼前出现一个胖大妇人,褪色的头发在脑后挽一个潦草的髻,腰腹粗壮如男人,正岔开双腿坐在牛棚里为母牛挤奶。木桶挤满后,她站起来伸个懒腰,自己从桶中舀了一杯解渴。一口气喝下去,提起手背满意地抹掉嘴边乳沫,再将手蹭在围裙上,仰起脖子打了一个长长的、响亮的饱嗝。有三四个小孩子跑过来围住她,她蹲下来亲吻他们,大声说出带肮脏字眼的亲昵话。
男孩皱眉问道,“这妇人是谁?”
魔王冷笑,“这便是你钟意的小蒂尔达。三十年后,她就是这副样子。”
男孩愣住了。魔王轻声道,“花朵总会凋谢,美不是永恒的。但我却可以让你拥有四时不谢的、血肉的花朵……”
男孩眼前出现一个卧室,一个身材肥硕的中年人,身穿蚕丝的睡衣,倚在一张大床上,床前的地毯上站满头发眼睛颜色各异的女子。
那也是他。是三十年后的他。从挺直的鼻梁和眼睛轮廓,还能辨认出当年的俊秀,长年享乐则在那眼下画上了两团暗紫的阴影。魔王笑道,“亲爱的孩子,这时候你早已是个幸福的鳏夫了,婚后第三年,你那瘦伶伶的夫人陪你在花园凉亭里喝茶,不幸中风猝死,你获得了她名下所有财产。”
男孩身子起了一阵寒栗,像坠入湖中,猛吞了一口冬日的湖水。
那父亲感到怀中那身子在发抖,连忙再把毯子裹紧一些,试图与他说话:“别怕,很快就不冷了,太阳就要出来了。我们马上就到,马上就到了……”
魔王的左手扶在一位女子的肩膀上,那肩头圆润得像水蜜桃,他的右手则撩起另一个女子的漆黑长发,絮絮说道:
“啊,这是世间另一类珠宝,另一类珍禽异卉。这类美更加易逝,无法保存,因此依时令采撷就更像一种艺术。瞧这大溪地少女的皮肤,如同调了蜂蜜的巧克力,腻滑得像涂了油,当你伸手抚摸的时候,手指尖将尝到蜜甜的欢愉。日本女子善于低眉顺目,当她们匍匐在地时,你可尽情欣赏那天鹅一样的后颈曲线。印度姑娘的眼睛黑白分明,像是紫檀木和贝母镶嵌上去的,瑜伽术把她们的身体塑造得惊人柔软。锡兰美人犹如林野中的小鹿,充满弹性与活力。法国女子有苦艾酒一样醇香的风味。意大利女人的眸子像会发光的钻石……”
男孩摇摇头,“我对她们没什么兴趣。我并不觉得快乐寓于其中。”
魔王却胸有成竹地笑着,他的嗓音像泉水汩汩流过银瓶。“亲爱的孩子,我知道你自幼失掉母亲,村人视你为外来者,没人真正与你亲近。你从未真正拥有过一个女人,你岂不需要补偿吗?所有这些女子,她们温软的乳房,暖热的胸膛,柔滑的手臂,芬芳的体气,全都属于你,你难道不想没顶在乳香的海洋里、鲸吞那母性的柔情?”
男孩这才真正呆住了。钏镯丁当作响,那群女子缓缓围上来,像善魅的塞壬,用各自不同的语调呢喃道,“哦,我只爱你一人,我愿永远陪伴你,取悦你……”
黎明即将到来,森林也将到尽头。马的速度却无可奈何地慢了下来,鼻孔喷出的气息粗重,遍体大汗淋漓。
父亲不停亲吻男孩又湿又凉的额头,用脸颊蹭着他头顶,又声声呼唤亡妻的名字,求她保佑她的爱儿。
男孩的身子轻得像是不抓牢就会被风夺去。
他咕哝说,“父亲,那人说要我随他而去。那人,衣领上有一朵风茄花的人……”
父亲将男孩紧搂在胸口,用手掩住他另一边耳朵,叫道,“不要,不要听他的话!”他的声音忽然像被斧头砍断一样,他猛然一勒马缰,马儿痛嘶,人立而起。
他也看到了魔王。
魔王显身在几步远的夜雾中,脖颈上缠着双头蛇,唇角带笑,他只对那父亲说了一句话:“你可知道,我的爱好就是——把闭合得紧紧的蚌壳撬开,取出里面的珍珠,拿来装饰我的袍子……”
然后那身影便隐没了。
男孩像骑在云头俯瞰大地,他眼前出现森林和湖泊之畔那灰暗的小村,低矮破旧的房屋,昏暗室内简陋的器具。人们兴高采烈地准备节日的食物和服装,然而那顶好的也粗俗得可怜。魔王摇头道,“难道你真的宁愿把一辈子浪费在这汤盆大小的村子里,陪伴你那忧郁而口讷的父亲?你瞧那些头脑简单、毫无识见的乡邻,你真愿意一生与他们为伍?”
林梢的天空开始变色,墨汁像渗进水一样逐渐稀薄。拂晓的呼吸已经清晰可闻。
男孩的身子起了一阵猛烈的抽搐,他低声道,“父亲,让我去吧,他许诺给我一切最好的东西,最美的花园、书房、厅堂、最显赫的声名……我不想在这儿呆下去了……”
“不!”父亲绝望地叫道,不要相信他,“那不是花园,是吞噬青春和灵魂的魔窟。你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也不能再回来了……”
眼前的景象又变幻了。豪华的厅堂里,一位颀长的金发青年正站在人群中心,接受人们的祝贺。他身穿绣金线的黑天鹅绒外套,纽扣扣眼里别着一枝白玫瑰,俊美如年轻神祗。有人满面笑容地致辞,随后众人高举酒杯,向那青年祝酒。
那正是他自己。是十年后刚刚声名鹊起的他,世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就像种在花圃里的花朵,只等他弯下腰采摘。
室内管弦乐队奏起欢快的乐曲,人们纷纷走下舞池,翩翩起舞。一个少女走上前来,眼睛笑吟吟的,一只手持酒杯,一只手持一支红风茄花。她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问道,“喂,漂亮的孩子,我们成交吗?”
青年瞧着女子的衣领,在蕾丝的覆盖下,那里绣着一条两头蛇。她的眸子闪动绿幽幽的光,如深潭,如漩涡。他木立不动,任凭那少女伸手抽出白玫瑰丢在地上,再把红风茄插进扣洞,像一朵新染上的血渍。
……就像从山洞隧道里钻出,父亲终于冲出了森林。眼前倏地亮了起来,原来天空已这么明朗了。
噩梦般的夜晚和森林都被抛在身后,远山之间的天色呈出极浅淡的青蓝,太阳即将从那里升起。这景象是他整夜都在盼望的,然而当真正熬到这一刻,他却反而越来越恐惧,恐惧得再也不敢低头去看怀中忽然安静下来的男孩。
村庄在望。有烟囱冒出一道白烟,那是村里的面包铺。最早起身的牧牛人慢悠悠地走在道上,牛铃洒落一路清脆的丁丁声。
父亲在乡间诊所门前喝住马,他几乎是从马上跌下来的。
当身穿睡衣的医生跑出来,他的话因为激动断成一截一截:“求你,救,我的,儿子……”他颤抖得像要散落成一地粉末,低下头,解开包裹得紧紧的毛毯。
第一缕晨光照上男孩的脸,长长的睫毛在颧骨上投下浓重的阴影,那原本像百合花瓣一样的脸颊,现在变作了凄惨的尸青,他四肢软绵绵地垂着,阳光仿佛薄薄的金色纱布,温柔地蒙在他脸上、身上。
那孩子已经断气了。
父亲哀痛地低号一声,哆嗦着手徒劳地在那冰冷胸口上摸索心跳,手掌忽然被什么扎了一下。是那条玫瑰项链,玻璃花瓣不知何时碎成了渣子。
医生徐徐摇头,低声道,“抱歉,看来您到得有些晚了。”
“天哪,我的宝贝,我的珍珠,我的性命!天哪,我心爱的儿子……”那父亲死死抱住男孩的尸骸,恸倒在杏黄色的冬日晨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