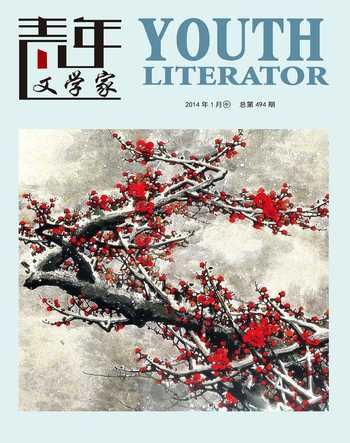薛昂夫《中吕?朝天曲》叛逆色彩微探
摘 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元朝社会经济活动中充斥着少数民族身影,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辉煌期。薛昂夫无疑是元朝少数民族文学家中的佼佼者,在薛昂夫传世68部元曲作品中,一组《中吕·朝天曲》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薛昂夫做平的典型代表,而这一组《中吕·朝天曲》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着叛逆色彩。
关键词:薛昂夫;《中吕·朝天曲》;叛逆色彩
作者简介:羊颂平,浙江师范大学 12级中国史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2-0-01
在中国元曲中,根据隋树森先生《全元散曲》的辑录,有名姓可考的作者达到二百余人。而薛昂夫无疑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位:原是“西戎贵种”却“尝执弟子礼于须溪先生之门”;“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却继承老庄思想追求“清逸”。
薛昂夫,名薛超吾,又称马昂夫,马九皋,为元代著名西域曲家和诗人,王德渊《薛昂夫诗集序》:“薛吾超,字昂夫。其民族为回鹘人,其名为蒙古人,其字为汉人”。薛昂夫和贯云石被称为元代维吾尔散曲家中的“双璧”,现在存世散曲小令65首,套取3首,共68首。而在这其中一组《中吕·朝天曲》22首就占据其存世作品的三分之一,在这一组《中吕·朝天曲》22首中体现了薛昂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对老庄思想的向往。
一、对帝王“文治武功”辛辣的讽刺
在薛昂夫这一组《中吕·朝天曲》22首中,提到帝王分别是刘邦、武则天,两位帝王是优是劣,史家没有定论。但是,两位帝王在任上可以称道的“文治武功”,都能够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中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薛昂夫在这一组《中吕·朝天曲》中,用近乎戏谑的口吻把这两位帝王描摹成一个活脱脱“小丑”形象,特别是对三位帝王“文治武功”的缩小化。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瑟.汤恩比评论说:“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刘邦推翻了秦朝暴政,结束了楚汉相争,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是广大的老百姓告别了暴政的奴隶,战争的奔波,有了安居乐业的期盼。而在薛昂夫词中刘邦成了深谙“御奴之道”“厚黑学”代表。首先,在《中吕·朝天曲(一)》开头一句就把刘邦贬成只知武力解决问题,不谙“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治国之策的匹夫形象:“沛公,大风,也得文章用。却教猛士叹良弓,多了游云梦”,其次,对于楚汉相争中刘邦的胜利归结于刘邦善于“权术”而不是其在军事政治上的天赋异禀,“驾驭英雄,能擒能纵,无人出彀中”。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帝王,《旧唐书》评价:“史臣曰:治乱,时也,存亡,势也。使桀、纣在上,虽十尧不能治;使尧、舜在上,虽十桀不能乱;使懦夫女子乘时得势,亦足坐制群生之命,肆行不义之威”,在史官眼里武则天是一个恰逢其时具有强硬政治手段的政治家。而在薛昂夫词中,用辛辣而又跃动的语言把武则天描摹成一个 “荡妇”形象,《中吕·朝天曲(十六)》:“四海淫风,满朝窑变,《关雎》无此篇。”把武则天描述成只知道享受淫乐的“淫娃荡妇”,而决口不提武则天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总的来说,薛昂夫对于帝王的态度是戏谑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叛逆心态使其在作品中充满着浓郁的逆反色彩:君主是人,在道德修养上也是有缺陷的,因而君主的不良表现都成了他最好的戏谑取笑对象。
二、对传统历史推崇的名臣贤士的批判
在咏史怀古中,薛昂夫真正用意不在于对诸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全面客观,而是对他们“未达‘自由的种种人生现象的‘刺和‘悟”,其词中最为重要的对比就是严光和杜甫、伍子胥和丙吉的对比。
1.严光“失足”折价和杜甫“穷酸”寻梅。
汉朝严光作为一代隐士高人,元曲家鲜于必仁的《双调·折桂令》《嚴客星》、马致远的《双调·拔不断》《失题》都认为他辞去富贵,甘做烟波钓徒最为高尚识趣,甚至江山清风,万古留名,遗产甚于光武帝。 但是,薛昂夫却用调侃的语调对严光的“高尚品德”做了另类的解释:
子陵,价轻,便入刘郎聘。等闲赢得一虚名,卖了先生姓。百尺丝纶,千年高兴,偶然一足横。帝星,客星,不料天文应。
薛昂夫对于严光“价轻”的评价是基于严光接受了光武帝的邀请,出去做官,而姑且不论严光三次拒绝和最好还是辞官归隐,而是仅仅抓住严光出去做官这一次,就批评其“等闲赢得一虚名,卖了先生姓”确实多多少少吹毛求疵,有失偏颇之嫌。而与此遥相呼应,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薛昂夫对杜甫的高度评价:
杜甫,自苦,踏雪寻梅去。吟肩高耸冻来驴,迷却村前路。暖阁红炉,党家门户,玉织捧绿胥。假如,变俗,也胜穷酸处。
杜甫一生做官,从没有归隐,甚至从没有归隐的想法。但是,薛昂夫给了杜甫很高的评价,认为杜甫有梅花的傲骨,不向权贵低头,始终保持自己高尚的人格追求,终其一生没有动摇过至死不渝。
2.伍子胥“鞭君忿”和丙吉“调阴阳”的对比
薛昂夫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伍子胥深深的同情:
伍员,报亲,多了鞭君忿。可怜悬首在东门,不见包胥恨。半夜潮声,千年孤愤,钱塘万马奔。骇人,怒魂,何似吹箫韵。
在曲中充满着对伍子胥的同情之心,对伍子胥为解心中不平而怒鞭君王尸体导致不为传统儒家所理解,只能化作“千年孤愤”的不平之情。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历来为传统儒家所推崇的,被誉为有先秦贤相“燮理阴阳”之风的丙吉却被薛昂夫狠狠的开了个玩笑:
丙吉,宰执,燮理阴阳气。有司不问尔相推,人命关天地。牛喘非时,何须留意,原来养得肥。早知,好吃,杀了供堂食。
伍子胥和丙吉的差别就在于其对待传统“礼”的不同观点。中国士大夫是一个“专事承担精神文化赓续发展责任的社会阶层”——他们多居官有职位,具有较高的思辨能力和文化修养。其中一大批名望又高、地位又显、影响又大,他们导引了中国文化的主流。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心理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文学中,人们透过文学便能感觉到时代的文化现象与心理的联系。 “丙吉问牛”的故事是丙吉成了历代贤相的代表,如明·程登吉《幼学琼林》第四卷:“楚王轼怒蛙,以昆虫之敢死;丙吉问牛,恐阴阳之失时。”然而,薛昂夫却并赞同不丙吉问牛不问人的行为,通过“人命关天地。牛喘非时,何须留意,原来养得肥。”批评丙吉身为宰辅本末倒置,不能够保民安天下而只是谨守追求儒家礼教“调剂阴阳”的虚妄教条。
参考文献:
[1]唐丽娟:《从唐宋文学看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差异》,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