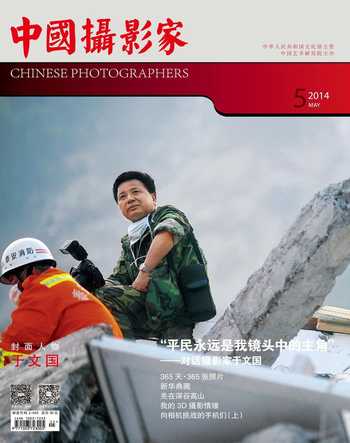羌在深谷高山
高屯子



自我放下手中的笔拿起照相机那一刻起,内心就渴望着能以一种新的语言,去述说那些文字未尽的冲动与感受,以图片去记述故乡平庸无奈的现实和苍凉悲壮的历史。西南汉藏之间“最后的羌人地带”上,那里有并不依着我们既有的知识、概念、映象所生活着的羌人。来到这里,是想体验一段与自然、与生命、与历史相关联,与“现代工业文明”有些区别的生活;是想以纪录片方式,去讲述那些代表羌人与祖先通灵、与鬼神对话的释比,讲述他们的心灵状态与现实处境。
在山野行走之余,我开始更系统地翻阅一些关于“羌”的文字。通过对甲骨文的辨析,我们发现:“羌”,是三千多年前,殷商人对其以西大约今天的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一带边缘人群的称谓;通过对《史记》《国语》等古籍的阅读,我们了解到:“羌”,是秦汉时期由秦陇向西大规模扇形迁徙的那些族群;通过对《华阳国志》《明史》,以及后来顾颉刚、费孝通等历代史家著作的浏览,我们又看到了两汉、魏晋之际,在整个华夏西部形成了广阔的“羌人地带”:从西北天山南路的婼羌;河湟流域的西羌;陇南蜀西一带的白狼羌、参狼羌、白马羌、白狗羌等八羌,再到川西滇北一带的青衣羌、牦牛羌。及至唐宋,吐蕃势力与藏传佛教由旧称发羌的地域迅速向东扩展,与中原势力与文化在这片广阔的“羌人地带”上,全面相遇。之后数百年间,甘、青、河湟与川西北广大区域的羌人,分别融入了汉、藏、蒙古等民族之中,到了明清,只剩下岷江上游和湔江上游一些高山深谷间有少量“羌民”了。这部分人,终于在1950年代民族识别区分之际,被认定为“羌族”。
我的拍摄,并非想要对“羌族历史”作出考证,但是,以汉字书写,或以羌语传说的种种“羌”或“尔玛”的历史,又是表现今天这些羌人,无法不去面对的苍茫背景。这段时间,我终日在历史文献记载的“羌”和岷江上游高山之上生活着的“羌”之间,来回穿行。
我拍摄了能寻访到的所有羌族释比。我的拍摄刚一开始,汶川县龙溪沟的余明海、萝卜寨的张福良、茂县永和沟的龙国治等几位老释比就已先后去世,我的拍摄还未结束,理县熊耳山的周润清等释比又随后离世。我不知道,再过几十年,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羌族释比,但我深信,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潜藏着与不同空间维度的生命交流,与天地万物感应的能力。即便是代表族人与天地鬼神沟通的释比,抑或萨满,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殆尽,但人类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对天地精神的追问,是与生俱来的,是不会被物欲和妄念长久蒙蔽的。“释比”,这一名称、人群、仪式终将消逝,但其敬畏天地、顺任自然的心性深藏于人的内心,总有一天会在人性温暖的光照下,再次萌生。
你也许会发现,中华民族的许多古风雅韵,往往靠着一群边远乡村的农民在保存和延续;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并不一定永远消失;那些正在流行和横行的,并不一定益于人类长久的福报。我所展现的,是苍茫历史时空背景下,“5·12”大地震之后,在那些尚存一丝历史余温和乡土气息的村寨里敬天法祖、耕种劳作的羌;是现实与理想在我心中叠化而成的影像。时间无终始,当我们遭受危机与困顿时,也许,我们可以在流淌的光阴里,寻到给予我们启示的远古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