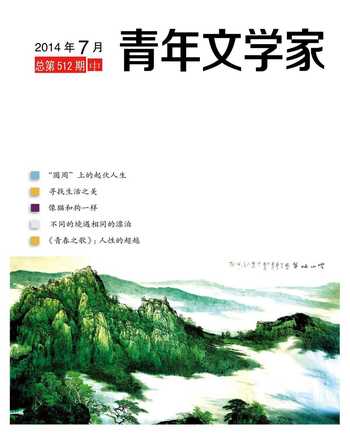月夜灯会下的生存雾霭
摘 要:尹雪艳是白先勇笔下一位极富神秘感与传奇色彩的女子。其独特的处事方式与深刻的象征寓意凝结成一代文化的缩影。而作为一个生存个体的尹雪艳,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派的自由主义伦理价值观与当今社会的背离。这种背离导致了她的个体价值被忽视,由此决定了命运的悲剧。
关键词:尹雪艳;自由伦理主义;个体价值;悲剧
作者简介:杨颖慧(1990-),女,汉族,山东烟台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0-0-01
《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先生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的开篇之作,女主人公尹雪艳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奇女子”,有的评论者认为尹雪艳是邪恶的化身,是幽灵,是死神;有的评论者则认为她是作者笔下的一个繁华富丽的旧梦。基于此,本文从叙事伦理学角度对《永远的尹雪艳》进行分析。
一、绝色的精灵
白先勇以其独特的人生阅历和精微的观察力在小说刻画了一系列的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都是身袭一身华美得惊艳明媚,在没落的年代里或是性格乖戾或是孤单无奈地存在着。尹雪艳就是这么一个女子。
“尹雪艳总也不老”1,这是一个对自己的容貌极为自负的女子—“尹雪艳从来不爱搽脂抹粉”。面容姣好,依旧有自己的个性—“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这样惊艳明媚的外表和百乐门舞女的身份注定了这个女子少不了“武陵年少争缠头”的纠葛,不论是财阀还是政客,总是有人愿意前仆后继的奔赴继而埋没在温柔乡。
这是一个十分让人觉得惊异的女子,带着灵气但又似乎亦正亦邪。这也似乎决定了尹雪艳不再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个体存在,她成为了一个符号甚至于一种象征。这个符号的价值出自于人们无意识的追捧,然而在这种被动赋予的过程中,她的象征意义就变得越来越丰富甚至于超越了她本身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价值。这种“超值”的赋予并不是美好的开始,负荷的加重及对个体无意识的忽视慢慢的使得她的灵魂与肉体脱离,自由享乐主义也就决定了个体对于社会责任与道德人性的藐视,继而冷漠地面对周围的人性悲剧。
二、浮华背后的轻盈与沉重
希腊智者普罗迪科曾经给苏格拉底讲过“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赫拉克勒斯在十字路口碰到两个女人:肌体丰盈柔润、脸上涂抹的光鲜亮丽的卡吉娅和生得质朴、恬美、气质剔透的阿蕾特。卡吉娅带来的是安逸和舒适,阿蕾特带来的是辛劳与获得。他感觉到这将是两条不同的生命道路,一条通向美好,一条通向邪恶。因为结尾是按照叙述人的道德指向发展的,苏格拉底让赫拉克勒斯选择了阿蕾特,而白先勇同样是以一种破碎的方式放弃了“卡吉娅”—尹雪艳。因为她同卡吉娅一样,自由伦理观念下的无知和无畏导致了没有道德的轻盈,由此必然走向毁灭。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提到:“丧失或者唾弃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力,不再觉得生命中有任何东西令人感动就是现代伦理自由的品质之一,至于这种品质是否高贵,另当别论。”2换言之,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导致了这种感受性和认知力的下降继而使人性慢慢的丧失,尹雪艳即是如此。她成为了别人的寄托,寄托着喬迁遗老们旧日的荣耀,寄托着新贵们名利的追求。她的肉身只求光鲜的存在或者是寄居着,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所谓的“美好的沉重”,各种各样的环境迫使灵魂背弃,它早已没有了栖身之所。
三、月夜灯会下的生存雾霭
昆德拉用生存迷雾比喻没有道德法庭和道德归罪的生存状态。置身于光明中,人们行为指端受制于各种约束;处在黑暗中,人们被黑暗牵制以至于陷入盲目。“只有在雾中,人是自由的——但这是在雾中人的自由。”3换言之,这种心安理得的自由伦理只是一种在有限的现在中享有的自适伦理,没有道德束缚,只讲求肉身闲适的存在而不追求生命的意义。
在这样的解释下用雾霭相容尹雪艳的生活环境似乎很合适。混沌的上流社会就如同一片雾霭,人物以各种各样的道德方式生存着。月夜灯会下极易与现实隔离,由此极易在雾中放纵自己而忘记了原有的生活轨迹和赖以生存的集体道德约束。一群被困或者说是被现实所遗忘的贵族们索性将过往幻化成尹雪艳,让她成为一个纪念抑或是假想成过往的继续,而尹雪艳在这片雾霭中生存,也无需沉重的道德枷锁,无需用灵魂追溯有意义的人生,只需轻盈的肉身存在去给予落魄者安慰,尽管这样的安慰带着煞气与厄运。也就是说在另一程度上,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一个冰冷的象征。
刘小枫曾经这样定义伦理与幸福:“伦理问题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偶然生命的幸福以及如何获得幸福,关键词是:个人命运、幸福、德行(如何获得幸福的生活实践)”4。或许像尹雪艳那样的生活只是一种在混沌中带有欺骗性的安逸,这种安逸的背后更多的是堕落,是被虚伪蒙蔽的心安理得。也许,自由主义的伦理观念也会使人走向美好,但这种美好并不代表幸福。雾霭并不恒久,也并不适合所有的存在。作为一个踏实存在的个体,我们应当在公有的伦理观念下选择自己的自由,不是一味的顺从亦不是一味的放纵,应适时负荷属于自己的“沉重”,去追求一种最为充实的象征。
注释:
[1]白先勇:《台北人》,2000年版,第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2012年第六版,第87页,华夏出版社。
[3]昆德拉:《遗嘱》,第238页。
[4]刘小枫:《沉重的肉身》,2012年第六版,第108页,华夏出版社。
参考文献:
[1]白先勇:《台北人》,2000年版,第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2012年第六版,第108页,华夏出版社。
[3]昆德拉:《遗嘱》。
[4]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大众文艺》2010年3期。
[5]罗刚:《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