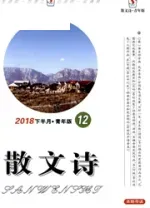诗意的纯美与精神的辽阔
周根红
在我们的诗歌写作中,我们生活或曾经生活的家园也许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它将响应我们内心的召唤。成为诗歌创作的灵光。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土情节。它不仅仅是一种记忆或现实的呈现,更是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回归。也是我们对写作的纯粹质地的抚摸。马亭华的散文诗正是固守着大风起兮的苏北世界,以体察入微、随处可感的灵性,歌唱了一个干净纯粹的“苏北”和一个历史沧桑的“大荒原”,形成了诗意的纯美和精神的辽阔特征。
一
马亭华的散文诗始终洋溢着唯美情怀,构筑出一个个唯美的意境,语言极富张力。诗人通过意象和句子,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苏北世界的精神转换和提升,独特而唯美地表达了诗人对乡村生活经验的美好怀想,不仅完成了乡村的诗意,也实现了精神的提纯。“从一粒麦穗里醒来的是子规的余韵,层层叠叠的叶子上住着神的花朵。”(《为苏北写诗》)“草色如火,大地包容了一条河流桀骜不驯的内心。”(《苦旅》)“冬日静止的河流,似阳光的刀刃,清霜一样碎了。”(《河流》)“风坐在风里,独饮霜粒,扶住月光,在茫茫归乡的途中。”(《归故里》)“风的翅膀和化蝶的神话,抵达春天的梦境,静静的月光渡平平仄仄的前生,这人生的晚秋,薄暮中的苍茫。”(《晚秋》)诸如此类富有文采、想象力和唯美意境的句子数不胜数。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说。马亭华的散文诗是一个语言的陈列室,他用诗意的组合将那些原本司空见惯的词语组合成句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诗歌境界。正是对这种唯美的诗意的追求,马亭华的散文诗特别注重语言的锤炼。如“家乡的门环,是一双患了乡愁病的耳朵。”(《落叶》)“风放牧着白云,塬上轮回的尘缘如雪绽放。”(《风放牧着白云》)“月亮出来了,我们可以趁着夜色拉满岁月的弓,将自己卑微的一生,射出去。”(《命运》)“白了头的芦苇望着星星的梯子”(《风放牧着白云》)正如诗人坦言:“我偏爱过华彩、纯粹、辽阔等等给读者以震惊的追求及梦想,从而创造出完美、自适、理性的境界。”然而。与纯粹追求语言的华丽相比,马亭华的散文诗写得洗练,没有拖泥带水的词句,在寥寥数语里饱含阔大,在词语组合中实现诗意,充分摆脱了纯粹词语堆积所形成的语言臃肿症状,显得“干净纯粹”:“干净纯粹,这是诗歌最美的一种品格。我权且把它称之谓‘风骨。我写每一首诗时都突感内心的洗礼,那是一种清澈之美。”(马亭华语)
马亭华散文诗的唯美意境和想象,其实更多来源于他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并将这种古典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营造了诗歌精神的复合体。他的散文诗有着非常深厚的古典诗歌传统,这在今天的诗歌不断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诗歌的古典传统不断失落的今天,马亭华“回归诗歌的民族性和传统,赋予诗歌新的元素、活力和辽阔的气质”有着非常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在这些优美的意境里,诗人骨子里流露出浪漫的情怀,形成了古典传统与浪漫情怀的交相辉映,成为马亭华散文诗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正如马亭华所表达的诗学观:“当下诗人们提及的传统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一类是欧美现代诗的传统。而我的传统则是追求从汉语诗歌的民族性出发抵达全人类文明的传统。”可以说,古典气质与浪漫情怀是马亭华散文诗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那梦中的马,还在花瓣的草地里驰骋,乡村正以铜的皮肤扬鞭。”(《泥土》)“玉米剥开红红的嫁衣,大豆开口向着秋阳说着心里话,番薯带着浑身的疼痛,以灯笼的意象,把黑夜的土壤彻底照亮,把难以回首的青春献给金色的秋天。”(《粮食的家谱》)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诗歌有着浓烈的古典传统、浪漫想象和独立的精神意境。马亭华的散文诗以其灵活、生动、深刻而叩击着读者的阅读神经,迸发出内心的记忆、想象和美好,直抵我们内心最柔软最温暖的部分。尤其是他直接写到古典的那些诗歌,更彰显了诗人对于古典传统的尊重和创造。如《端午诗章》《线装的江南》《茶经》《三国赤壁》《杜甫草堂》等都有着非常古典的美。正如耿林莽在对马亭华《杜甫草堂》的评价里所说的,它突出了“诗人与民间的血肉联系”,“风吹草堂,雨落民间”何其自然而又凝练地概括了这种关联:“一座草堂,要给整个民间疾苦押上韵脚”。语言被思想照亮,思想以诗语言的翅膀而飞翔并熠熠生辉(耿林莽评)。这正是马亭华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价值和发展所在。
二
马亭华的散文诗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他笃守着故土之源,运用经历、记忆和热情塑造了一个“大风”中的故土。他从体察到呈现,从关照到返回,由此构成了他诗歌中的一面镜子,歌唱着历史的沧桑与美好,写出了诗意的纯美与精神的辽阔。
马亭华的诗歌总是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唯美的诗意,他的散文诗完全是内生性的视角感受。那就是苏北土地、家园、亲情的眷念,表达他对苏北最纯粹的地方体验。他的关于苏北的散文诗,避免了我们固有的城乡文化模式和二元对立式的书写。而是把自己作为苏北精神的传承者和守望者,是苏北的守护精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歌里洋溢出来的感恩,温情,迷恋,而不是批判。他的这些诗歌的意义,在另一个维度上告诉我们,如何拓展情感体验,而不陷入抑郁和绝望。诗人的苏北故土写得沉静内敛。他的组诗《爱上缓慢的时光》(七章)其实就是他对苏北故土的主要情感定调。他对苏北故土的描写呈现出“缓慢”的内心情愫。“时光,有着缓慢的节奏,此地打开了村庄多少晨钟暮鼓。黄昏,镀亮了麦穗,牧童的竹笛把炊烟吹醒,沉默的老牛走在了回家的土路上。”(《农谚》)“在乡土中抬头,你的目光一定会撞上温顺的羔羊,羔羊后背手的老爷爷。他们都有柔弱和善良的呼吸。在苏北,我爱上了这些缓慢的气息。”(《气息》)诗人对苏北乡村的描绘始终克制着内在的冲动和情愫的倾斜,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用缓慢的语言叙述乡村里的日常场景。这些场景里,透露的是乡村的平静和日常,没有刻意的夸张,全是自然的体验。正如耿林莽先生所言:“他得心应手的诗情,却是苏北乡村,古黄河边,微山湖畔的清风明月,一种清新秀美的抒情格调和浓郁的乡情。”这种乡情始终给人温暖的感觉。“歌颂那晨光中的父辈和兄长,那馥郁的泥土里一定有他们最朴素的爱,和最朴素的思想。”(《春风》)马亭华的乡村其实正是这样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载体。
甚至这种唯美和宁静,使得马亭华的诗歌显示出一种禅意,一种乡村的禅意。他为此还特地写了一组题为《村庄内心的禅》的诗歌,凸显了诗歌和乡村的宁静所渗透其中的禅味。如:“不论走动,抑或静坐,每一个人的心头都应怀着一片清澈的星空。”(《在傍晚的时刻》)“我放弃了春天的修辞,我的春天,一再趋向淡泊,像梨花的胭脂,在雨中轻走。”(《时光漂洗的春天》)“春天的清音,是哭着长大的草,与露水结伴的稻草人,守望着黄金的麦田。”(《我爱我的乡村》)“我相信枯枝在梦中酣睡,梦见自己长出了时光的长发。”(《我相信枯枝在梦中酣睡》)……“把每一朵花拧亮一些,把鸟鸣的小鞭抽得再通俗一些,响亮一些。”(《把每一朵花拧亮一些》)马亭华的散文诗正是这样试图追求一个宁静的乡村景象,一个诗意栖居的地方,他用纯美的内心发现乡村的纯粹与干净,他用雨水、大风、月光、花朵、鸟鸣铺就了一条乡村的诗意大道。
马亭华苏北散文诗有着一种真正的植根环境里的身份认同:不是隔靴搔痒,不是故作高深,不是矫揉造作,而是置身其中的深切体悟。“村庄为我照耀,让我醒来,我埋进九月,感受五谷。”(《民谣》)马亭华就这样以深入泥土的姿态、埋进农历的深度,植根性地完成了乡村的吟咏。“现在,请允许我再为苏北写一组诗,用大风中的一杯浊酒,用泥土深处一粒最轻的词汇,用我这一世纪辽阔的爱,用漂泊的灵魂,用这村庄空洞眼神中最后的一盏烛火。”(《为苏北写诗》)这样的诗句,蕴含着诗人赤诚的乡村情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就可以理解诗人的“自言自语”:“乡愁可以决定人的两种命运,一种是自焚的,一种是自恋的。当然,乡愁也因每个诗人的境遇不同而在身体内部表现出迥乎不同的征兆。”马亭华对苏北村庄“慢”的描写,正揭示出村庄真实的生存境遇。在现代化时光急速流转时,村庄始终沉浸在过去的节奏里,甚至慢慢回到从前。“慢”实际上是村庄的品质。诗人马亭华牢牢抓住苏北“慢”的品质,以诗歌的方式,完成了握造:“那些把雷声背在身上的穷乡亲啊,能不能走得慢一些。再慢一些,好让这温润的土地能托起发芽的巢,托起心头小小的幸福。”(《祭祀》)因此,他的散文诗从纷乱喧嚣中呈现乡村的宁静与美。我想,作者的内心应该有着静水流深般的坚持和对乡村的坚定信仰。
三
马亭华在那些写苏北的诗歌里反复提到“大风”。并且也将他的新著命名为《大风》。可想,大风在他的诗歌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大风”实际上成了马亭华诗歌里的一根骨头。耿林莽先生曾用“荒原上的黑马”来评论马亭华的散文诗,荒原和黑马这两词语的组合,有着他诗歌一般的质地:空阔,辽远。诗人不断写到“大风”,这是诗人生活的徐州的历史品质——一个以“大风歌”传唱千古的帝王之乡的时光触须。他的一些描写“大风”的诗歌,就展现了苏北世界辽阔的意境,揭示了历史的沧桑感,反映了存在论的畏惧和孤独的主题。诗人反复地用语言描绘了一个外在的心灵世界,显示出人生的苍茫、漂浮和渺小等历史与现实的深度思考。如“一次次饮下大风,在泗水亭的秋天,古老的歌谣还在传唱火焰和美,传唱前世的马匹、灯盏和箭。”(《歌谣》)“在苏北,大风已成为一种高度,可与英雄比肩。酒和剑,也仅仅是殉葬品,被细小的沙粒一一掩埋。大风甚至吹过了乌江,吹透了一部文辞渊雅的《汉书》,吹透了猛士的骨骼。清澈的星辰,和族谱上的烈酒。”(《大风》)在大风的书写中,诗人还表现出在历史的微尘烛照中的孤独感:“从黄昏里掀起的大风,似一望无垠的天涯,和尘世之爱,这诗,这歌,这无限被镜头放大的孤独,和漫漫征途。”(《大风歌的苏北》)这是一种历史沧桑里人的渺小和无法对话的落寞。毫无疑问,“大风”是诗人对于历史的寄托,也是自己渴望达到的一种精神高度。
“大风”对诗人创作的重要影响,我想主要是,写出了诗歌精神的辽阔。如“汉画像石博大精深,寂寞中领受繁华。石壁传来了马嘶,敲打声越来越远,疾走的刀锋用一生放弃对世俗生活的敌意。时光倒流。飞溅的石屑化作繁星,溅湿的鸟鸣,似飞翔的铭文。大汉之光,一遍遍照亮苦涩的村庄和土地,一幅汉画像石里藏下我的今生前世。”(《题汉画像石》)尤其是他的《大荒原》,以极富有想象力的意境和语言驰骋在历史的天空下。因此,他的“大荒原”并非荒凉和贫瘠的,而是历史沧桑后的苍凉感,是“历史的符号”。“一个苍茫的漂泊者,裹紧内心的王,站在伤口的前沿,站在广袤的荒原之上,迎着风吹——”即便那些并非写苏北的诗歌,也难脱那种“大风起兮”的宏大气势,如“挤满天空的是染红了日月山的云裳,骏马和云鹰在晚霞中诞生了生命的渴望。”(《日月山》)“在青海遇到的每一尊菩萨都面带微笑,都把天空背在身上,心里装满了救赎的星空。”(《与一株菩提在黄昏相遇》)“长白山,让我抱一抱,我的心胸有了十万雪花。”(《寻梦长白山:热爱》)……这样的诗歌精神,我不敢断然说是因为地域的“大风歌”文化的影响,但是,我想,他一定与作者深深体悟到了“大风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