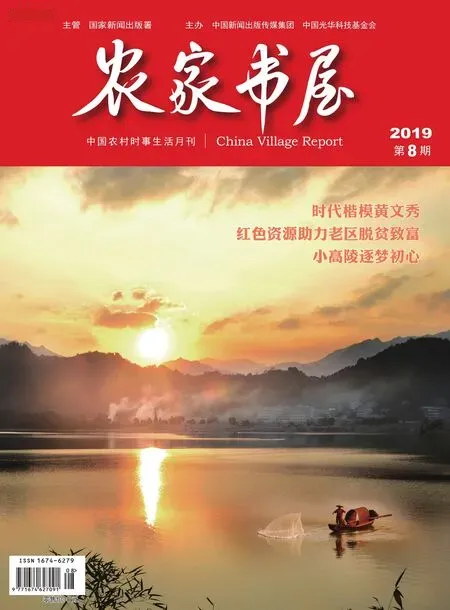李渔:在乡居与城居之间徬徨
沉钟
人生是一场奔波,马不停蹄,风尘仆仆,于是,对家居的忆念和眷恋也尤为真切。万千奔波的劳苦,其实只在于一个安宁而稳固的家——不仅仅是作为最终归宿的寄托,也往往着眼于短暂驻足的风景。
李渔的一生,几乎一直都在为安顿自己的“家”而筹画、而忙碌、而困惑。从出生地如皋到故乡兰溪夏李村,再到金华、杭州、南京乃至北京,最终回到杭州,其间,经历了“小城——乡村——中等城市——乡村——大城市”之间的多次辗转往复。古往今来,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比李渔先生在家居建设上投入更多精力的文人墨客了。
唯其如此,也当仁不让地成就了他作为有清一代无人可与比肩的造园大家的地位。
李渔对“家”的选择,起初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在他出生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而立之年,科场失利,遭遇时变,境况急转直下。据他后来回忆:“甲申乙酉之变,予虽避兵山中,然亦有时入郭,甚至幸者,才徏家而家焚,甫出城而城陷。其出生于死,皆在斯须倏忽之间”(《闲情偶寄·饮馔部》)。改朝换代之际,兵火连天,李渔在金华城里的家被毁,死里逃生,无处存身,只得回到兰溪夏李村的故居。此时家道破落,财产销尽,要修建几间可容一家人的茅屋都无能为力。他在《拟构伊山别业未遂》诗中写道:
拟向先人墟暮边,构间茅屋住苍烟。
门开绿水桥通野,灶近清流竹引泉。
糊口尚愁无宿粒,买山那得有余钱。
此身不作王摩诘,身后还须葬辋川。
幸而一批亲朋好友伸出援手,帮他了却一桩心愿。此后,他便绝意仕进,今生甘为“识字农”,一度把心思都花在了这“伊川别业”的布置和修饰上,种花莳草,引水灌园,经过一番精心打理,居然将几间草房及周边环境弄出了一派诗情画意。这一段乡居生活,成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回忆。他在《闲情偶寄.颐养部》中记述:
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夏不谒客,亦无客至(兵燹过后,自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匪止头巾不设,并衫履而废之(呵呵,完全不必顾忌斯文扫地!)。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此公实乃现代版“天浴”的第一著作权人。);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是人类退化为动物,抑是动物进化为人?)。洗砚石于飞泉,试茗奴以积雪。欲食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果落树头(简直有点孙猴子的味道!)。可谓极人世之奇闻,擅有生之至乐者矣。后此则徏居城市,酬应日纷,虽无利欲薰人,亦觉浮名致累。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今欲续之,求为闰余而不可得矣(笠翁一生阅历,堪称“曾经沧海难为水”,自认为得享仙福者“仅三年”。我等庸常之辈,细忖起来,一生中又能真正享有几年清福?)。
但李渔终究还是放弃了这种无心无事、闲云野鹤式的生活,将他精心营造的“伊川别业”连同所置的周边百亩山林全部转卖,携了这点资本,遂由宁静的乡居转向喧哗的城居,谋求另一种人的活法。
李渔注定不是一个湮没无闻的乡曲之士。他处在一个劫后余生的时代,黎民百姓需要抚平战争留下的心理创伤,个人亦急需在废墟上重建家业并重振家声,而清初相对松弛的文网也为他提供了发挥才情的独特空间,那个时代更需要借他的杰出天赋去开辟一块无人问津的新文化领域。他这一去,著述卖文、出版图书,度曲演戏、组建戏班,策划生活、设计造园,又是小说家、剧作家,又是戏班班主兼导演,更是身怀绝技的造园艺术大师,一时锋头凌厉,八面风光,名满宇内,宾朋天下。与此同时,他把家安在了杭州,安在了南京,甚至安到了北京。
李渔的城居,最有名的当数南京的“芥子园”,既是住宅,又是书局,还是戏院。“芥子”,极细微之物也,佛家曰“芥子纳须弥”,意谓一粒小小的芥子能够容纳广大、庄严的须弥山。李渔为南京的芥子园手书对联:“因有卓锥地,遂营兜率天。”这芥子园“过目之物尽是画图”,倾注的岂止是泛泛的匠心,更是主人巧夺天工的创意和灵感。也许是挥洒之余意犹未尽,李渔又把芥子园的“分店”开到了京城。可惜,如今这南北两京的芥子园都已付诸尘埃,无有觅处。
直到67岁那年(康熙十六年),李渔才从南京搬回杭州,最终定居并老死于云居山东麓的“层园”。
营造“层园”这个最后的家园,可谓李渔平生最后一搏,搞得心力交瘁,贫病交加,一次还失足滚下楼梯摔伤了筋骨,差点送掉老命。因资金链断裂,工程无以为续,不得不给京城友人写公开信求援,信中说:
我本是浙江人,虽然家于金陵,并非土著。狐死必首丘,此念蓄之已久,况且故乡还有祖宗的坟墓在。自从乙卯年两个儿子回浙江就读,便决定搬回杭城。幸蒙主政官员帮助,使我得遂买山建宅之愿。自夏至冬,不到一年,卜居择基之后,便投入土建;土木工程尚未完成,又遇婚娶之事;婚娶方毕,即着手搬家事宜。从金陵到杭州,有上千里之遥,四十口之家,非一舟一车可载;何况在金陵住了二十年,负债满身,在则可缓,去则不得不偿。所以临行所费金钱,十百倍于搬家之数。除去卖掉金陵别业(即芥子园),还有生平著述之版权、衣物乃至妻女的首饰等等,凡是值点钱的,无不变卖,还清债务,才得挈家启程。可怜彼一时也,只顾医疮,使尽难剜之肉,以致此一时也听其露肘,并无可捉之襟……
可见李渔最后一次对家的选择仍然相当被动,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也是幸得朋友资助,才使他得以圆满最后的归宿。
如果说李渔一生对家居有过主动的选择,唯有“芥子园”差可拟之。但自从他搬离南京后,芥子园继续作为书局的存在,已不得不改换门庭,花落别家。
李渔在小说《闻过楼》中有一段夫子自道,古语云:“小乱避城,大乱避乡。”予谓无论治乱,总是居乡的好;无论大乱小乱,总是避乡的好。……予生半百之年,也曾在深山之中做过十年宰相,所以极谙居乡之乐。如今被戎马盗贼赶入市中,为城狐社鼠所制,所以又极谙市廛之苦。
晚年的李渔思乡之心尤切,有一次乘船沿富春江回兰溪,经过严子陵钓台时写下一首词,词中道:“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
总结回顾自己的一生,在乡居与城居之间,李渔高度肯定了乡居的价值,而对曾经给他带来辉煌的城居却刻意加以贬薄。此种心态,看似与当今一些出自草根而借城市发迹却口口声声念叨着“乡愁”的成功人士如出一辙。
不过,李渔此处说的的确是真话。为了奢华的城市居住和生活,他的付出太多太多,不止是金钱和物质,更是精神上的透支。城居令他疲累不堪。
卖文为生,售艺养家,靠自己的才能吃饭,没什么可说的,“我以这才换那财,两厢情愿无不该”。尤为可贵的是,李渔作为中国第一位文化企业家和中国第一位专业戏剧导演的天赋,让他可以用自己赚的钱使一家四十余口活得相当滋润。只可惜李氏戏班的两个台柱子——乔王二姬过早离世,从事业巅峰骤然跌入谷底,迫使他不得不更多地借助于“打抽丰”这一当时文人惯常的谋生手段,由此而来,自我感觉中的人格自尊也不得不自贬三分。虽说李渔平常与那些贵人、富人打交道,交朋友,为他们赋诗撰联,谈文说艺,唱曲卖笑,筹画园林设计和营造,不但能“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五侯之鲭,夜宴公卿之府”,还不时获得丰厚的馈赠,但这种角色充其量不过是“高级文丐”而已,“人以俳优目之”,其内心的角色冲突无可避免。时人讥其“奔走势利之门”,其实,所谓“市廛之苦”,笠翁可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那么怀念当初的“居乡之乐”,良有以也。
平心而论,不论是当今社会还是李渔那个时代,乡居与城居于人生都是各有利弊。乡居生活成本低,轻松怡养,悠游自在,益寿延年;城居生存压力大,环境嘈杂,尤多外在和内心的雾霾。——不过,惮于生计,竞争驱使,城居转而有助于成就一番事业,也合乎逻辑。
设想李渔当年不走出兰溪夏李村,何以成就他历史上的李渔?
据说李渔回到兰溪故里,已是物是人非,不禁感慨万千,赋诗道(《二十年不返故乡重归志感》):“不到故乡久,归来乔木删。故人多白冢,后辈也苍颜。俗以贫归朴,农由荒得闲。喜听惟涧水,仍是旧潺湲。”
从古到今,失去了的乡居不可复得,消散了的乡愁不可追寻。盖因一切随时间空间条件转移,乡愁所附着的乡居、乡居所附着的土地,皆如暗逝的流水吞声而去,让人再也无法踏入同一条河。
这也是当今许多年轻人宁愿漂在城市而不肯回到小地方的原因。
至于某些成功人士一边享受着城市的盛宴,一边又在渴望乡野的风味,所表现的除了物欲之贪婪,就只剩了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