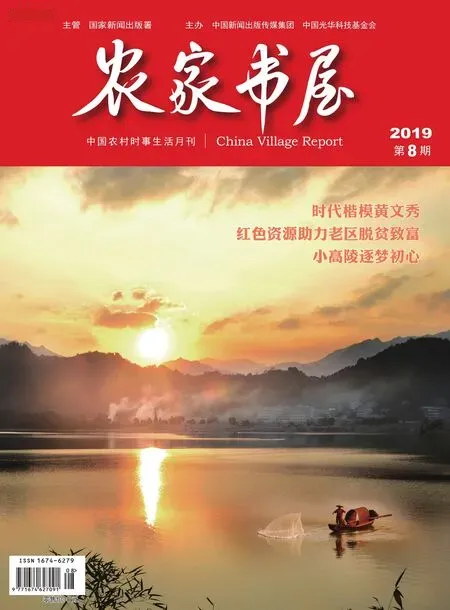云南马关:花米饭节说村事
盛湘颍
每逢六月初一,云南马关县壮族有一个独特的花米饭节。这一天,壮家人不用外出干农活,家家户户忙着泡染五颜六色的花米饭,共庆花米饭节。你随便走进一家,簸箕里、木甑里都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花米饭,黑的、红的、黄的、紫的、白的,绚烂的米粒或一色归一色并排放着,或各色混合,真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待你坐定,好客的壮家妇女会抬着装满花米饭的木甑到你面前,刚蒸出来的花米饭颜色鲜亮,用手抓一把,或摊在掌心吃,或捏成团吃,米饭清香袭人,且有微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米饭的颜色均用植物染成——用植物给食物上色是一种古老的智慧,它既满足了一个封闭而艰苦的民族对色彩的渴望,又在客观上保护了食物天然的品质。你或许会惊叹:他们何以发现那么多的植物染料?
花米饭由来已久
五色花米饭,由来已久。清代诗人沈自修在《西粤记俗》中说:“宣化(今邕宁)武缘(今武鸣)之俗,三月三日,各村以乌米饭把真武。”清代《武缘县志》一书记载:“武俗作黄赤色饭,随时染之,惟三月三日取枫叶泡饭为黑色,即青精饭也,枫叶老而红,故昔人谓之‘南天烛。”《西珥事》一节中载:“青精饭,用南天烛染饭作黑色,谓之乌饭……今粤人以社日相馈送,然又有染作青黄赤以相杂,谓之五色饭者。”
1888年编的《归顺直隶州志》也说:“清明前后,拜扫故墓,染糯米五色煮熟,供散光彩异常,取小精邪崇不能夺吃之义;祭毕席地团坐,复焚香椿拜跪,依恋不舍,斜日在山始归。”又“每年五月十四日雨耕耘已毕,选取吉日共作牛魂节。假如一家有四人,即杀四鸡鸭蒸糯米,糯米仍染五色,蒸熟合鸡用大叶包,各人自带到平日看牛处,至午刻各人相食,另以糯米饭包一大包灌牛食,以酬其耕耘之劳。”
因语言差异,不同地域的壮族人对五色糯米饭有不同称法,如糇能、乌米饭、青精饭、五色饭、花饭等;至于其来历,各地更有不同的传说,其中最富生活气息的版本,是说与古时壮家村寨一个叫特侬的青年有关。因父亲早逝,特侬与瘫痪在床的母亲相依为命。每次上山砍柴或下田插秧,特侬都为要母亲准备一包糯米饭,但总有一只猴子会把米饭抢走。
有一回,特侬在山上砍柴掐到枫叶,手指染了黑色。他灵机一动,把枫叶割回家捣烂,和糯米一起浸泡蒸煮。次日,那猴子看见黑乎乎的一团,居然不敢碰了。后来,壮家人都学做黑色糯米饭,还用黄栀子、红兰草做成更多颜色的米饭,逐步演变成五色花米饭。
如今,每到三月三,壮族村寨到处可闻到五色糯米饭的芳香。屋前房后,孩子们手拿五色糯米饭,边吃边玩;村头树下,妇女们互相品尝“杰作”,交流蒸饭经验;年轻男女,则揣着用荷叶包着五色糯米饭去赶歌圩,送给心上人品尝……
在广西武鸣壮族乡,妇女们提前十天就开始忙了,她们拿出细心贮藏的糯米谷子,磨米、椿米;到三月三前一天,村村寨寨就已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这一天,武鸣伊岭村的几口泉水旁,总是围满了洗米、刷木蒸桶的妇女,大家一边淘米一边交流蒸五色花米饭的经验。
据广西作家苏贤庆撰文回忆,他那已过百岁的祖母,曾是伊岭村全村公认的蒸五色糯米饭的高手。头一天晚上11时前,祖母就把木蒸桶架到放有半锅水的大锅中,用几米长的湿布条塞入锅与木蒸桶的接合处,以防水蒸气挥发,然后把已浸软和染好植物汁色的糯米放入木蒸桶中。当次日零点到来,守在灶旁的一群小孩既兴奋又犯困时,穿着新衣的祖母准时往灶中点火,嘴中念念有词:“求灶王爷保佑五色糯米饭能既靓又香。”
当大锅内的水开始沸腾,发出咕咕的声音,厨房内顿时飘满了诱人的香味。从这时起,到天将亮的这几个钟头,祖母都不会离开灶台。她要不断地给大锅加水。五色糯米饭蒸的时间足够,才会又软又香。苏贤庆说:“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三月三那天,我们起床后把手洗干净,就可以用手抓着香喷喷的五色糯米饭团来吃了。”
寓意五彩生活
“灵巧不灵巧,就看她家花糯米饭做得好不好。”制作五色糯米饭的过程有些繁琐,需要诸多细心和耐心。壮族各个村寨的妇女,多以能制作颜色鲜艳纯正的五色饭为傲。在广西田东县人谢佩霞的记忆中,小时候,每到三月三,她就会早早起床,和母亲一起守在火炉旁,等着那透着诱人清香的五色糯米饭。通常,天翻出鱼肚白时,糯米饭就蒸好了。
“母亲做的五色糯米饭非常特别,尤其是那黑色,乌黑发亮。”谢佩霞回忆说:“我最喜欢那黑色,也只想要那黑色的,可母亲不让,她说,五种颜色都要一点,这样,你以后的生活就会像这五色糯米饭一样,五彩斑斓。”
壮族人一直认为五彩缤纷、鲜艳诱人的五色糯米饭是吉祥幸福的饭,因而常用于祭祀或重大节日。到了四月初八,早稻已插完返青,壮族人用五色糯米饭揉成小团团,黏附在竹枝上,插于祖宗神龛,又从田中取回一蔸生长旺盛的禾苗,以南瓜叶包根,放在碗里,一并祭祀祖宗,祈求五谷丰登。
那些用天然植物染成的五色糯米饭,不仅美观美味,而且有一定药用价值。清代《侣山堂类辩》记载:“红花色赤多汁,生血行血之品。”壮族人深信,用来染红色的“红兰草”有生血作用,染黄颜色的“黄花饭”或栀子具有清热凉血等作用。
染黑色用枫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枫叶“止泄益睡,强筋益气力,久服轻身长年”,用枫叶煮成的青精饭,人食之能“坚筋骨、益肠胃、能行、补髓”。据说杜甫也曾写下“岂无青精饭,使我颜面好”的佳句。
最讲究制作技巧的是黑色糯米饭,做得好,糯米饭乌黑发亮,带有一股淡淡的枫叶味;如不成功,米饭颜色偏灰。每年,年长的壮族女人会在村头枫树下,向年轻人传授经验:取三叶枫叶及其嫩茎之皮,放在臼中捣烂,稍微风干后浸入水中,一天一夜后捞出叶渣滤净,取得染料液,还要放入锅中煮至五六十度,浸入糯米,染出来的颜色才够纯正。
至于黄染料,则用黄花汁或黄栀子、黄羌等植物的果实、块茎提取。将黄花汁煮沸,或将栀子捣碎放入水中浸泡,即得到黄橙色的染料液;也可用黄羌捣烂后与糯米拌均用力搓,可得黄色的糯米,就可以直接蒸,不用浸泡。
红紫糯米饭则是用同一品种而叶状不同的红兰草经水煮而成。叶长为紫,叶圆为红,此中奥妙,也只有寨子里资深的老妪弄得清楚。据说,这种染紫色的红兰草,在布依族民间疗法中,单方熬汤服用,能治疗糖尿病、高血压、头晕等症。
在云南曲靖罗平县城东南40公里处,有一条美丽动人的多依河,住在河两岸的布依族人也爱做五色糯米饭。有人说,花米饭是布依族的特产,它在布依族中流传已有近900年历史。将泡好的糯米分装在五个小瓦盆中,把五种色汁分别掺进去搅拌,将糯米浸透后,拿到小河边淘洗——多依河畔淘花米饭的布依少女是这条女儿河上最美的风景。
常年吃着母亲做的五色糯米饭,谢佩霞的生活也像母亲预言的那样充满色彩。她说:“直到我做了母亲,我仍然每年带着儿子和母亲一起守候在火炉旁,等着吃那五彩的糯米饭,儿子也在等待中编织他自己五彩的梦。”
饭香,情更重
“三月三,到壮乡,五色饭,真是香;吃一口,再一口,意未尽,永难忘。” 亘古亘今,无论地域和民族,最打动人心的,仍是食物背后脉脉的亲情。五色花饭色彩缤纷,清香可口,尤其那绚烂的色彩,既是生活的色彩,也代表着人生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
在农家生活艰苦的年头,只有在节日,大人们才会杀鸡杀鸭买猪肉敬神,并自制五色糯米饭。因着五色糯米饭,很多人都曾从小期待农历的四月八。这一天,俗称“牛王诞”,农村的养牛人家很早就习惯在这一天用各种方式,庆贺牛王始祖的诞生。
这一天,亲戚朋友们也会互相走动。“四月八,杀鸡又宰鸭。外婆来了,大姑小姑回娘家,敬天敬地敬牛王爷爷啊,家家吃饭花。”这歌谣中的“饭花”,正是指五色糯米饭。“这刚刚蒸熟出锅香喷喷的五色饭,五彩缤纷犹如初春的鲜花。”苗族人春晓记录说:“这首当年儿童时代的歌谣,我至今记忆犹新,它伴随我走过了许多沟沟坎坎。”
对很多壮族人、苗族人而言,五色糯米饭中凝聚着母亲的身影,他们对五色糯米饭的思念,同时沾染了对母亲的想念。“母亲做的五色饭很香,香得能把本来还想赖被窝的我熏起来。”壮族人闭剑东对于五色饭的美好记忆,源于其苦涩的童年。
闭剑东小时候,家境困难,虽不至于断粮,但因母亲时常一病数月,干不了农活,家中的重担全都压在父亲一人身上,经济状况可想而知。但就算家中再困难,每到三月三前后,母亲依然硬撑着,把五色饭做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母亲弄的五色饭好吃,可能吧,她是在努力弥补家庭贫困对我带来的冲击。”闭剑东解释说:“用母亲的话说,用来祭祀神灵的五色饭不能马虎,所以童年的我就常能在三月三前后吃到了母亲做的美味可口的五色饭了。”
母亲做五色糯米饭时,很有讲究,将染成各色的糯米,用筲箕滤干,接着,先将黑色糯米沿着甑子平铺底层,然后再在上面放上另一颜色的糯米,依次类推直至把五种色彩的糯米放完为止。等到香喷喷的五色糯米饭出炉时,母亲就开始唤儿来吃五色饭了。
“那唤儿声忒有味,就像她做的五色饭一般。”闭剑东说:“我深深眷着母亲做的五色饭,因为它陪伴着我走过艰辛的农家岁月,直至我大学毕业离开那个小山村,我离开了那个山村而母亲也离开了我。”
母亲离开后,闭剑东很难吃到地道的五色饭了,即使偶尔回老家扫墓,吃上几口别家做的五色饭,他都失落极了,“那往日里熟悉的味道荡然无存,逃逸得无影无踪。”如今,每到三月三,他就感念母亲蒸煮的五色饭,想念母亲淘洗糯米的场景,以及蒸好米饭后,母亲那悠然响起的唤儿声……
谁能想象得到,看似简单的五色米饭,藏匿着那么多诀窍与母亲的心思呢?不曾在此长大的外乡人,又岂能知道,制作风味绝佳的花米饭,当选用生长在较通风的黄土坡上不老不嫩的枫香叶,和花蕊带点黄色的染饭花?
当制作花米饭的村妇代代老去、更替,那些枫树叶、黄栀子、红兰草始终开得鲜艳。物是人非,山岚静无言。或许,真正不变的,仍是五色糯米饭那绚烂的颜色和温存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