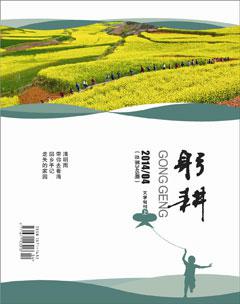农事三题
◆ 王振东
农事三题
◆ 王振东
打粉
“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这个中国农民多年的梦想,早已变为现实。想想,工业化的步伐真快,转眼几十年功夫,农民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正从传统的纯手工生产方式向工业化生产方式转变,大到耕种收打、磨面运输,小到打铁打绳、制秤做鞋,无一不是这样。老家的手工打粉也受到了冲击,昔日家家户户的手工作坊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
打粉,是老家人把红薯粉碎过滤制成粉面的过程。打粉并不是像“打人”、“打鼓”那样有“打”的动作,而是“制做”的意思。老家人的日子好像是打出来的,生活中许多劳动的动作常常被运用“打”这个动词,如:打场、打夯、打水、打草鞋、打烧饼、打豆腐等等。很难说“打粉”是指这个劳作过程中的哪个具体环节。
“想喝浆汤儿,前后宁洼儿(老家的名字)”。这句顺口溜足以证明老家是名副其实的“粉乡”。每年红薯收获季节,家家户户都打粉,不说院子里摆的粉缸,光村头的小河边,成排的粉缸就有上百口之多,场面颇为壮观。
最古老最原始的打粉完全是人工生产的。做一个长宽高各一米的木制斗子,把洗净的红薯倒进去,用铁铲剁。只见一名壮汉手持铁铲朝下剁,“咔嚓”一声,几个红薯即被剁成两半,同时,另一名壮汉也手持铁铲剁下去,又是“咔嚓”一声,又有几个红薯被剁成两半。两人的动作交替进行,颇似柴油机汽缸里的活塞运动。这样你一下我一下,直到把红薯剁成拇指肚大小的块儿,倒在水磨(磨面用的磨叫旱磨,磨较薄,每扇只有一厚。打粉用的磨叫水磨,磨扇较厚,是旱磨的一倍。)上磨,把红薯块儿磨成糊儿,然后过罗沉淀。
把一斗子红薯剁碎可不是一件轻松活儿,力气大的壮汉才能胜任,所以剁红薯的人都是每天能抓十分的壮劳力。他们胳膊粗壮,肌肉发达,赤膊上阵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阳刚的体魄。就是这样的壮汉,一套粉打下来,都会累得背酸臂疼,有时双手都磨出了血泡。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恐怕没有人知道雪白的粉面在制作过程中,打粉人流出的血汗。
在年复一年的剁红薯打粉中,最初级的机械加工的触角伸入到红薯粉碎环节,一种笨拙的、用生铁铸成的红薯粉碎机应运而生,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机器,无疑是红薯粉碎的一场革命,使农人打粉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机器构造十分简单:一个生铁铸的支架,顶端焊一个倒放的漏斗状铁斗,下边焊一个像抽屉一样的“U”型铁槽。把一块长方形薄铁皮用铳子顺一个面倾斜铳开无数个米粒大小的小洞,被铳开的铁皮翘起来就形成了一根根小刺,把带刺的薄铁皮钉在圆柱型辊子上,然后装到漏斗下面,机器就做成了。粉碎红薯时,用电动机或柴油机驱动粉碎机,把洗净的红薯倒进铁斗里,下面的铁槽里就流出了糊状的红薯渣。
无论是原始的粉碎方法,还是用机器粉碎红薯,只是完成了打粉的第一道工序。接下来就是“过罗”了。先过大罗。大罗是用木板或铁皮制成的圆柱状罗圈装上罗底后的一个器物。之所以说大,是指罗圈大(直径一米),罗底(网状尼龙制品)眼儿粗。过罗时,把大罗放在支好的大瓦缸上,把红薯糊倒入罗内,倒上清水,用“捺子”(形状像搋子,木制,柄上端横向安一个把)在水糊中摇动,差不多把水挤干时,再倒入一圈清水,再摇捺子。这样连过三遍,这罗红薯糊中的淀粉就基本过滤净了。然后再过第二罗,直到把所打的红薯糊全部过滤完,让浆汁沉淀一晚上,等着次日过“二罗”。过完大罗剩下的粉渣,当天就喂牲口了,喂不完的,捏成窝头状,晒干,放到来年春上喂牲口。
过二罗是打粉的第三道工序。二罗的形状和大罗一样,只是直径小多了(约一尺半),罗底眼儿也变小了。过罗前,先将“大浆水”轻轻舀出,把缸底的淀粉掀起,添清水不停地搅动,使淀粉完全溶入水中,然后起出倒入罗圈里,用和大捺子形状一样的小捺子摇动,把浆水过滤完使其再次沉淀。滤下来的细渣掺点儿面和盐、葱花炕馍,这也算改善生活了。让过滤后的浆水沉淀一晚上,第二天舀出浆水,又白又细的淀粉便露了出来,把淀粉扒出,装入粉包(两根绳在四角的方白布)里,控干水分,就成了一个个“面蛋儿”。
晒粉面是打粉的最后一道工序。选个晴天,把“面蛋儿”用刀砍开,掰成小块儿,晾晒到苇席、床单或塑料单上,两、三天后,块状的粉面就粉化成黄豆籽大的粒了。晒干的粉面可打凉粉、下粉条、旋粉皮,这些我将在其它篇什中写到。
打粉,不但要有体力、技术,还要有责任心。好粉匠从不惜力,过罗遍数多,淀粉过滤得净,出粉率高;过罗时加水多,淀粉沉淀得好,出的粉面更白,下出的粉条、旋出的粉皮色泽好,筋道。他们这样上心地打粉,不只是为了名声,更是为了良心。
打夯
打夯,老家人叫“抬硪子”,是过去盖房时,为了防止地基沉降,将地基夯实的一种劳作过程。
盖房一般选在冬春季节,一是农闲,有充足的时间,二是雨水较少,有利于施工。
盖房日期选定后,首先要找人打夯。夯有两种,一种是一块正方形石头,中间凿一个洞,洞中插一根木棍。石头的四角也各凿一个洞,用来穿麻绳。打夯时,领夯人手握木棍,掌握平衡,其余四人每人攥一根麻绳,一齐用力,夯就起来了。另一种是用石磙做成的,这在老家最为常见。在农闲时用石磙做夯,也算闲物利用了。打夯前,把石磙立在地上,在靠上边的位置,把四根胳膊粗的槐木椽子像“井”字样夹住石磙,再用铁丝捆紧,椽子和石磙接触的地方各垫上一只旧布鞋,这样石磙就不会脱落了。就这简单的一垫足以体现出老家人的聪明与智慧。为掌握夯的平衡,夯的上边还固定了一个手柄。
用石磙打夯,至少需要九个人,除领夯人外,抬夯的八个人都是一天抓十分的棒劳力。领夯人边掌握平衡边喊“夯歌”,老家人叫他“夯头”,相当于乐队的指挥。只见夯头握着手柄,就像乐队指挥手握指挥棒一样,一道无声的命令便下达了,八个汉子同时弯腰,分别紧握椽子的八个头儿。只听夯头咳嗽一声清清嗓子,吼道:大伙抬起来呀——此句尽管尾音拖得很长,但仿佛从胸中迸发,声音震天,气势磅礴。夯歌一起,八个汉子一齐发力,齐声应道:嗨哟!然后把夯重重砸在地上,“咚”地一声,震得大地一颤,地基一下子陷进去半尺来深,接着再打第二夯。这样一夯压一夯地往前砸,砸够一遍,再砸第二遍、第三遍,直到夯落地时,跳起来老高,不再有坑时,说明地基瓷实了,地基才算打好了。
打夯是团队协作很强的劳动,必须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夯头的指挥显得尤为重要了。若有人用劲小了,夯就会侧棱,夯头就喊:某某别偷懒呀!这人立时就用劲了;若夯需拐弯时,夯头就喊:大伙往东拐呀!八个汉子就转弯九十度;若夯行走路线偏了,夯头就喊:往南压半夯呀!大家就把夯往南拉……此时此刻,最能体现“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纪律性。
看打夯、听夯歌是儿时最好的精神享受。因为那时老家文化娱乐节目很少,所以无论谁家盖房,我们都像燕子一样围在一起观看。广爷家盖房时,付叔是夯头,别看付叔个头不高,却很壮实,浑身都是肌肉疙瘩,嗓音特别洪亮,喊起夯歌来能听半拉庄子。付叔的脑瓜还很灵活,能即兴现编歌词,编的歌词知识丰富,引人向善,诙谐幽默,既能鼓动打夯人的卖力打夯,又活跃现场气氛,从而提高劳动效率。所以,村里谁家打夯都请他当夯头。只听付叔一声:大伙抬起来呀!八个汉子齐声吼道:
嗨哟!
这个地方高呀!
嗨哟!
使劲往下敲呀!
嗨哟!
这个地方凹呀!
嗨哟!
咱们少砸下呀!
嗨哟!
劲要使一停呀!
嗨哟!
才能砸得平呀!
嗨哟!
嘹亮的夯歌在村子上空回荡,既感染着打夯人,也感染着观众,现场的人越聚越多,欢呼声也越来越高。一曲终了,打夯人停下来歇一下发酸的胳膊,喝半碗主人送上来的柳叶茶,就又上阵了。
三月好风光呀!
嗨哟!
大伙栽树忙呀!
嗨哟!
屋旁栽桃树呀!
嗨哟!
路旁栽白杨呀!
嗨哟!
院里葡萄架呀!
嗨哟!
河边柳成行呀!
嗨哟!
三年五载后呀!
嗨哟!
绿荫满村庄呀!
嗨哟!
黑馍变白馍呀!
嗨哟!
草房变瓦房呀!
嗨哟!
光棍娶老婆呀!
嗨哟!
农村大变样呀!
嗨哟!
这是借打夯说通过辛勤的劳动,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最终走上致富路的。
连成你小两口呀!
嗨哟!
你们别吵架呀!
嗨哟!
连中你娶了妻呀!
嗨哟!
千万别忘了娘呀!
嗨哟!
这是教育夫妻互敬互爱、孝敬爹娘的。
过了春分种谷子呀!
嗨哟!
清明前后种棉花呀!
嗨哟!
种得稀了耽搁地呀!
嗨哟!
种得稠了要抓瞎呀!
嗨哟!
不稀不稠才得法呀!
嗨哟!
这是教人们科学种田的。
抬起来呀!
嗨哟!
用劲干呀!
嗨哟!
再来几下!
嗨哟!
快吃饭了!
嗨哟!
吃他三碗!
嗨哟!
再来打呀!
嗨哟!
这是说停夯该吃饭了。
在无数次的夯起夯落中,地基被夯实了,尽管十分疲惫,可八个汉子满脸喜悦,以胜利者的姿态把石磙高高举起,就像演员演完一场戏一样做了个谢幕动作。
这天,付叔唱了许多夯歌,在那时看来,仿佛是天簌之音,让我们大饱耳福。我就想,付叔也没文化,咋就会恁多夯歌?
尽管这次打夯结束了,可那粗犷、朴实、启人心智的夯歌仍在人们心中回荡。如今,夯实地基都用电夯,不但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还提高了劳动效率,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打夯的时代早已随着岁月远去,夯歌也随之消失了。这一消失,不仅是一种乡间劳作,更是一种朴实的乡村文化。
打场
《现代汉语词典》里给“打场”的注解是:麦子、高粱、豆子等农作物收割后在场上脱粒。但老家所说的打场,是特指打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场南风刮过,滚滚热浪把一望无际的麦子沐浴得金黄金黄,农人们挥起镰刀,开始了人和麦子之间硬碰硬的对话。
麦子收割后,被牛车一车一车送到场里,一场打场的战役即将打响了。
过去,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块打麦场,根据土地多少,辟出十几、二十亩不等。场在麦收前就已轧好,往往是一场小雨过后(没下雨就泼水,叫泼场),用牛拉盘空耙,把场面浅浅地耙起一层,然后将耙退去耙齿,人拽着没有耙齿的耙,一遭一遭地拉,老家人叫“抹场”,直到把场地抹平,再泼一遍水,用牛拉着石磙反复地轧,直到场面平整、瓷实、无缝,场才算轧成了。
麦子送到场里后,选个睛天,就开始打场了。
碾场是打场的开始。先把麦子用桑杈抖散、摊平,晒上两个小时就可以碾了。碾场用的是石磙,长约三尺,直径一尺多,两头中间位置各凿一个圆窑,那是安放磙脐的位置。石磙上安有框,框后面拖着一块半圆型的薄石板,叫“磱石”,它的作用是增加摩擦力,缩短碾场时间。一个牛把式一手牵牛子,一手扬鞭催牛,牛拉着石磙转圈儿,一磙挨一磙地碾。有时一场麦有三、四犋牛参与碾场,好似现在的机收会战,场面颇为壮观。一遍过后,刚才还趾高气扬的麦秆被碾得匍匐在地,只剩尺把厚了。这时要把麦秆一杈一杈地翻过来,然后再碾,一般要碾三、四遍,这场麦子就碾成了。
接下来是挑场。先用桑杈把长麦秸抖擞几下,让混在麦秸里的麦籽掉下去,然后挑起麦秸堆在场边,再用四齿筋杈(用牛筋缠的杈)把碎麦秸挑一遍,只剩下麦籽和麦糠。别看那薄薄的一层带糠的麦籽,那可是农人收获的希望。
拢场是把夹杂有麦糠的麦籽拢在一起,然后借助风力,把麦糠扬出去。拢场用的工具是一个像推土机铲子的木制推板。一个人手握推板在后面推,另一个人把一根绳子拴在推板上向前拉,把麦粒麦糠推到场中央,形成一个长堆。拢场是有讲究的,必须看风向拢,使长堆的侧面与刮来的风垂直,这样才有利于扬场。
扬场是个技术活。扬场人手持木锨,铲起夹杂着麦糠的麦粒迎风抛出一个优美的弧线,随着“刷”的落地声,麦粒和麦糠就分开了。扬场需要风,风不能大,也不能小。风太大,就把麦粒刮跑了;风太小,糠扬不出去,麦子就混到麦糠里了。这样的风力,最能体现扬场人的技术,技术好的,既不会刮跑麦粒,也不会让麦粒混进麦糠里。扬场过程中,一旁的助手平端一把扫帚,站成马步,在麦粒落下来的瞬间,用扫帚把风刮不跑的碎麦秆、大坷垃掠出来,老家人叫“打掠”。打掠也是个技术活,好的打掠者不会把麦粒扫一边去,却能把杂质扫净。随着扬场人抛出一条又一条弧线,金黄金黄的麦粒便像小山似的堆了起来。
把扬净的麦子起到仓库存放,叫起场。这时的农人是最高兴的。把麦子装入布袋(由棉线织成,一布袋装一百五十斤麦子),由棒劳力往生产队的仓库扛,并顺手拿一小截木棍儿,叫“数袋棍儿”。倒完麦子,把数袋棍儿交给保管员,最后把棍儿一数,就大体上知道这场麦子的数量了。至此,这场麦子才真正算打完,人们这才坐下喘口气,尽管十分劳累,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
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我正上初中,帮家里打场时,听到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十二队的张忠有,成天神神道道的,人称张半仙,他说打场时,妇女小孩不准进场,若进场,就冒犯了场里的神仙,麦子就打得少。这天打场时,刘嫂到张忠有的场里借扫帚。刘嫂是个寡妇,孩子又小,种地打场的活得自己干。张忠有见刘嫂要进场,赶忙阻拦,可已经晚了,刘嫂的一只脚已跨进场里。张忠有脸一寒,使劲朝地上吐唾沫,不情愿地把扫帚给了刘嫂。刘嫂刚出场,张忠有赶紧跪到地上,给场里看不见的神仙磕头,祈祷神仙保佑他家别少打粮食。那天打完场天已很晚了,张忠有没往家起麦子,第二天起麦时,二亩麦子只起了九袋,每亩只合四百来斤,和预估产量相差很多。张忠有很生气,就骂刘嫂不该到他场里,让他少打了麦子。
不久,乡派出所破获了一个盗窃团伙,盗窃分子在供词中说曾偷过张忠有五袋麦子。办案民警找到张忠有取证时,张忠有却说没丢,只说是刘嫂进场让他家少打了麦子。民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让他按指印。他念叨着“咋会这样呢?”才迟疑地按了指印。过后想想,张忠有的做法真的很可笑。
日月轮换,斗转星移。随着脱粒机、联合收割机的兴起,打麦场不见了,石磙更是没了踪影,古老传统的打场场面已渐行渐远,一项劳作被机械化取代后,随之而消失的还有我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