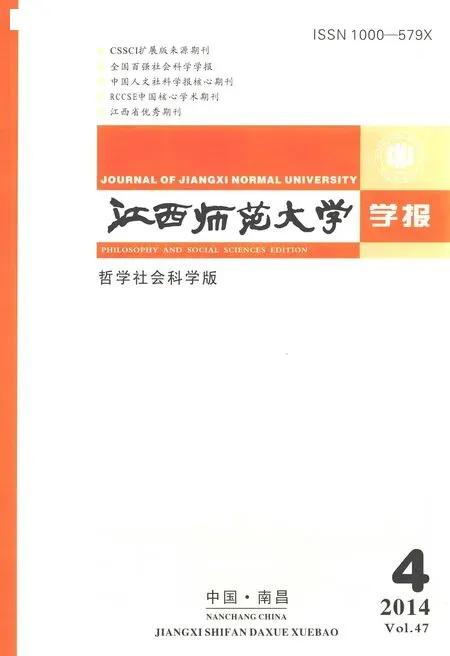从符号域到生命符号学:塔尔图对符号界域的推展
代玮炜, 蒋诗萍
(1.湖南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2.西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3.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从符号域到生命符号学:塔尔图对符号界域的推展
代玮炜1,2, 蒋诗萍3
(1.湖南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2.西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3.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符号域(semiosphere)作为文化符号学的重要理论,是塔尔图学派的领军人物尤里·洛特曼留给其继承者们的宝贵学术遗产。在新一代塔尔图符号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符号域理论得以和塔尔图的另一宝贵学术资源——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Umwelt)理论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新塔尔图学派的理论基石。在此基础上,塔尔图的符号学者们将符号学研究推进至生命符号学的领域,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符号学的疆界,为当代的符号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符号域;塔尔图;生命符号学;符号界域
在当代符号学研究中,塔尔图-莫斯科学派(Tartu -Moscow School)可谓盛名远播。塔尔图大学建立于1632年,是北欧历史第二长的大学,历史传统十分悠久。塔尔图处于几个文化、历史、政治、语言、生物地理和生态边界的交叉中心,这些边界或许支持了广义上的文化创造性。塔尔图的整个传统氛围具有文化多元性,支持跨学科的研究,且对异见者相当包容,这或许是为什么该学派的领军人物洛特曼(Juri Lotman)声称,塔尔图或许是他的学派可以形成的唯一一个地方的原因。①彼得·特洛普写道:“多亏了塔尔图这个地方,这里的符号学家们有幸继续两大传统观,将乌克斯库尔的传统和洛特曼的传统相叠加。”(Semiotica Tartuensis:Jakob von Uexküll ja Juri Lotman Kalevi Kull & Mihhail Lotman,Chinese Semiotic Studies[J],2011,6:312)。本文从塔尔图的理论基石、两位时代的异见者——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 (Jakob von Uexküll)的重要概念切入,试图勾勒出塔尔图符号学从文化研究到生命符号学的重大转向,借此说明塔尔图符号学派对当代符号学做出的重大贡献。
一、符号域与环境界:两位异见者的宝贵理论遗产
当今塔尔图符号学是建立在两大符号学传统——始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和始于乌克斯库尔的生物符号学之上的;具体而言,就是符号域和环境界的理论。“符号域”一词是洛特曼受到维尔纳茨基(Vladimir Ivanovich Vernadsky)“生物域”(biosphere)的启发而创造的,这个奇妙的巧合似乎从一开始就暗示着它和生物符号学的基本概念“环境界”具有某种天然的相同之处。根据洛特曼给出的定义,符号域指的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和机制,它既是文化存在的条件,也是文化发展的结果。[1](p69)洛特曼认为,符号域的边界在于各文化的自然语,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洛特曼符号学的研究领域是以语言为界的,即语言是最基本的符号,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是符号域的基本组成单位。
符号域理论非常强调语言符号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作用:语言是符号域的边界,是文化核心的直接体现,它就像是起到过滤作用的细胞膜一样,使外来文本必须经过翻译、改写、变形,才能进入到符号域之中;而在这种语言符码的转换过程中,意义的嬗变得以发生。洛特曼认为,在文本意义的多次转换和激活中,语言边界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他的这种看法影响了整个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学者们,后来,他们将自然语言定义成为首度模塑系统(First Modeling System),认为它是现实世界的一般模塑化;而建立在自然语言之上的符号系统(如文学艺术文本)被他们定义成为二度模塑系统(Secondary Modeling System),是对世界的二次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描述不是单向度的机械再现,模塑的不同方式会影响到文本化的过程,甚至改变文本的结构。
正是洛特曼的语言模塑系统理论启发了著名的美国生物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他将模塑系统作为遍及所有符号系统的概念来使用——这些符号系统既包括了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系统,也包括了前语言的动物系统。*“西比奥克……在洛特曼语言观的给定感知作用中看到了索绪尔或一般的符号学家所不具有的对生物学的敞开。他因此得以将德国的爱沙尼亚裔生物学家乌克斯库尔的内在世界(Innewelt)和俄国爱沙尼亚裔的符号学家洛特曼的模塑系统熔铸为一体,组合为一个三层的模塑系统。”Cobley,Paul;Deely,John;Kull,Kalevi;Petrilli,Susan (eds.).Semiotics Continues to Astonish:Thomas A.Sebeok and the Doctrine of Signs.(Semiotics,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7.)Berlin:De Gruyter Mouton.2011,8-9西比奥克认为,首度模塑系统是所有生命体的感知系统,它们根据自己的功能圈(functional cycle)对这个世界进行感知、辨认和意义生成,从而模塑出每个物种所特有的环境界。西比奥克由此指出,语言只能够是在此基础上的二度模塑系统,而语言之上的文本,则是进一步的、三度的模塑系统。[2]“模塑”的概念无疑为“符号域”和“环境界”的内在贯通提供了融合的渠道:西比奥克自己就指出“英语中与(环境界)最贴切的对应词显然是‘模塑’”。[3](p46)而洛特曼的传记作者,美国的符号学家爱德娜·安德鲁斯(Edna Andrews)提到,洛特曼的系统无疑是和西比奥克、雅各布森和乌克斯库尔提出的模式是一致的。[4](p24)
乌克斯库尔和洛特曼具有某种相似的身份:两人都是学术上的异见者,和他们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在达尔文进化论占据生物学界主流的时候,乌克斯库尔却提出了“环境界”的概念,以此描述生物体和环境的共构(而非单方面的适应)关系,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学术自信的。
“环境界”是指作为主体的生命体所建构和适应的世界,它是生命体从现实世界中辨认、反应、建立的意义世界。由于不同生命体的感知器官和方式相异,在同一环境中生活的不同生命建构出了不同的环境界。比如,同一个环境在鱼鹰和鱼的主体意义建构中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它们所辨认出的对象不同,同一对象对它们而言也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这些千差万别的环境界中,由于只有人类具有二度和三度模塑体系,也就是说,由于只有人类具有符形能力(syntactical capabilities),因此,他们是唯一可以构想出无数环境界的动物,并且可以对自己建构的环境界进行反思。有学者由此认为,这是人类对其他物种负有伦理符号责任的根本原因。[5](p535)
除了“模塑系统”这一理念上的内在联接以外,塔尔图的学者们对“符号域”和“环境界”这两个概念的互通性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就指出,这两者都为我们提供了系统研究的内在和外在双重视角;[6](p144)而洛特曼的儿子米哈依·洛特曼(Mihail Lotman)则指出,两者在共时哲学范式上具有一致性。[7](p155)正是这两者的融合,使得塔尔图的符号学研究突破了文化研究的局限,进入了更深广的生命符号学领域;而该领域由两部分所构成:生物符号学(bisosemiotics)和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
二、生物符号学:卡莱维·库尔的重要贡献
生物符号学的先驱,是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乌克斯库尔,而奠基者则是西比奥克,自他的动物符号学系列著作发表以来,生物符号学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而库尔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库尔本人是生物符号学历史的主要记载之一,马塞洛 (Barbieri Marcello)评价说,他努力“把生物符号学转变成为一个完全跨学科的事业,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关注”。[8](p226)
库尔在生物符号学领域最重大的贡献,就是他整合了国际生物符号学界的资源,积极地推动了整个学科的发展。法瓦鲁(Donald Favareau)在《生物符号学演化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库尔于1992年开始推动的生物符号学界年会,认为这是当代生物符号学历史性的事件,并且把库尔看做是“实际上同时掌握生物符号学传统,和东欧一般理论生物学传统的历史学家”。[9](p55)他高度赞扬了库尔的组织活动,并且指出正是“库尔在多方面的背景,包括生物学方面的实地考察、基于实验的生物学、生态学、动物行为学、理论生物学与生物符号学,他才能独一无二地把当代生物符号学的研究计划置于更大的理论生物学的历史潮流之中”。[10](p420)国际符号学界对于库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符号过程和生命过程一致性的讨论上,他的研究证明了洛特曼所定义的“符号域”可以向前推进,从而变成“符号生物域”(semiobiosphere);在人类的符号活动和生命体的生命过程之间可以找到相同的意义模式,从而使原本繁复而不可解的意义过程变得半透明化,使其中深藏的意义结构得以显形。这也意味着对符号意义的探索进入了一个人文与自然学科高度交织的领域,符号学的疆界得以大幅拓展。
发展生物符号学,就是试图在符号学方法和概念的运用和帮助下,为复杂的现象找到更为简单的解释,找到有机符号系统的入口,使我们了解符号在自然中是如何被创造和翻译的。对这种更为广义的一般意义模式的寻求,使得库尔将许多符号学描述意义生产机制的概念巧妙地加以挪用,融入到生物学的意义研究中去,比如说,他和特洛普(Peteer Torop)一起,提出了生物翻译(biotranslation)的概念。库尔和特洛普将翻译分为前翻译(protranslation)和真正的翻译(eutranslation),或者说,生物翻译(biotranslation)和语言翻译(logotranslation)。他们从环境界的理论出发,提出了种际符号系统(interspecific sign system)的概念,从而进一步指出:尽管他们承认只有人类才具有语言的能力,但在没有句法的符号系统中,翻译仍然是可能的。他们认为,既然翻译是意义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传播,那么,拥有不同表意系统的物种,就有可能(部分地)对其他物种的符号使用进行理解。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共生物种之间的意义互动关系,以及不同物种之间的觅食、警告、领地等表意系统的相互转换,这为生物符号意义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的研究还进一步指出,翻译可以作为对遗传现象的解释,即不同的代际之间存在着在其他的模式序列上产生的模式序列,而且这种生产需要符码:基因符码,它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不是可以通过物理化学法则可以推断出来的,因此,它是一个符号学范畴内的问题。[11](p33-43)翻译,它本来是符号域理论中描述文本符码转换的一个专有术语,在这里得到了更为广义的延伸:它被用于描述不同符号系统中的符码转换过程。文化符号学的经典概念被运用于生物学的研究范畴,这不能不说是符号学疆界上的一大突破;而这种探索所具有的开放性,也为符号学在本世纪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助力。
三、文化生态符号学:基本框架的形成
除了在生物符号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之外,塔尔图的符号学研究为生命符号学的另一分支生态符号学也奠定了理论基础。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是诺特(Winfred Noth)于1996年在《生态符号学》一文中提出的,诺特将其定义为:生态符号学是对生命体及其环境的相互符号关系的研究。1998年诺特和库尔在著名符号学期刊《符号系统研究》(Sign Systems Studies)同一期分别发表题为《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和《符号生态学》(“Semiotic Ecology”),库尔在该文中将“符号生态学”定义为人与生态系统的符号关系研究,后统一改称生态符号学。生态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分支就此正式出现。从它被命名的时期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偏向生物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和偏向人类生态学的方向,后者主要讨论的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经过符号调节的关系。在《符号系统研究》2001年第1期的专题号《自然符号学》(由库尔和诺特共同主持)中,所收录的二十三篇论文中,也可以大致遵循这个方向进行分类。塔尔图现有的生态符号学研究,明显延续了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研究的传统,是遵循文化生态符号学的道路进行的。
库尔认为,对所有生命及其环境的生态符号学研究无法真正和生物符号学进行区分,在研究区域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在他的影响下,塔尔图的生态符号学家蒂莫·马伦(Timo Maran)以“环境界”为基本研究模式,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生态符号学概念:自然文本(nature-text)和地方性(locality),并认为生态符号学研究的目标应当是双重的:除了讲述自然、指向自然的书面文本之外,它还包括描述自然环境本身的部分,为了功能关系,自然环境肯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性,或者可以被文本化的;这两个相对物之间的意义关系中形成的单元称之为自然文本。而对自然文本的分析应当包括书面文本的作者和读者,从而是四重的:一、文本化的自然环境;二、书面文本;三、文本作者;四、读者。[12](p269-294)这个概念使得自然可以被“文本化”,从而获得了文本性,成为了符号域研究的分析对象,从而使生态符号学研究具有了很强的可操作性。而在《地方性:生态符号学的一个基础概念》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地方性具有很强的生命体特征,它与语境性(contextuality)概念的并陈和相融,是和强调自然与文化的二元主义截然对立的,而这可以是研究地方性生态文化的适合起点。[13](p79-90)这对于塔尔图提出的,微观的、强调文化个体性的生态符号学研究是高度贴合的,在这个初步形成的理论框架之下,可以展开许多精彩而有趣的文化个案研究。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以“符号域”和“环境界”理论为基石的塔尔图符号学研究,将符号学界域推进到了生命研究的领域,并且始终和文化研究紧紧扣合,显示出了符号学天然的跨学科性特点,但又并未背离符号学对自身成为“人文学科最大公分母”的追求。塔尔图的符号学研究为当今的符号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求和学习。
[1]胡易容,赵毅衡.符号学-传媒学词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彭 佳,汤 黎.与生命科学的交光互影:论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J].俄罗斯文艺,2012,(3).
[3]〔英〕保罗·科布利.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M].周劲松,赵毅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美〕Andrews Edna.Conversations with Lotman:Cultural semiotics in language,literature,and cognition[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3.
[5]〔意〕Susan Petrilli,Augusto Ponzio,Semiotics Unbounded: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5.
[6]〔爱沙尼亚〕卡莱维·库尔,彭佳.新塔尔图研究:继承、融合与推进——卡莱维·库尔教授访谈[A].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6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7]〔爱沙尼亚〕米哈依·洛特曼.主体世界与符号域[A].汤黎译,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6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8]〔意〕Barbieri Marcello.A short history of biosemiotics[J].Biosemiotics,2009,(2).
[9]〔新加坡〕Favareau,Donald.Introduction:An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biosemiotics[A].In:Favareau,Donald (ed.),Essential Readings in Biosemiotics:Anthology and Commentary.(Biosemiotics 3.)[C].Dordrecht:Springer,2010.
[10]〔新加坡〕Favareau Donald.Theoretical biology on its way to biosemiotics[A].In:Favareau,Donald (ed.),Essential Readings in Biosemiotics:Anthology and Commentary.(Biosemiotics 3.)[C].Dordrecht:Springer,2010.
[11]〔爱沙尼亚〕Kull Kalevi,Torop Peeter.2000.Biotranslation:Translation between umwelten.In:Petrilli,Susan (ed.),Tra Segni[M].Roma:Meltemi editore.
[12]〔爱沙尼亚〕Maran,Timo 2007.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J].Sign Systems Studies 2007,35(1/2).
[13]〔爱沙尼亚〕Maran,Timo.Locality as a Foundation Concept for Ecosemiotics[A].In Siewers Alfred K.(ed.),Re-imagining Nature: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nd Ecosemiotics[C].Lewisbu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
(责任编辑:张立荣)
FromSemiospheretoBiosemioticstheSemioticBoundaryPromotedbyTartu
DAI Weiwei1,2, JIANG Shiping3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2;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u,Sichuan 610041;3.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
Semiosphere,one important theory in the cultural semiotics,is the valuable heritage left by Juri Lotman,the leading figure of the Tartu School.With the efforts and collaboration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semioticians of Tartu School,semiosphere has been merged with another precious theoretical legacy,the theory of umwelt of Jakob von Uexküll,and form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the new Tartu School.Based on this theory,the semioticians of Tartu School pushed the semiotic studies to the realm of biosemiotics,greatly expanded the boundary of semiotics,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semiotics.
semiosphere;Tartu;biosemiotics;semiotic boundary
2014-04-2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新塔尔图学派符号学研究”(编号:13YJC720029);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卡莱维.库尔的符号学前沿研究”(编号:13SZYQN01)
代玮炜(1975-),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蒋诗萍(1988-),女,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
I0-03
A
1000-579(2014)04-008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