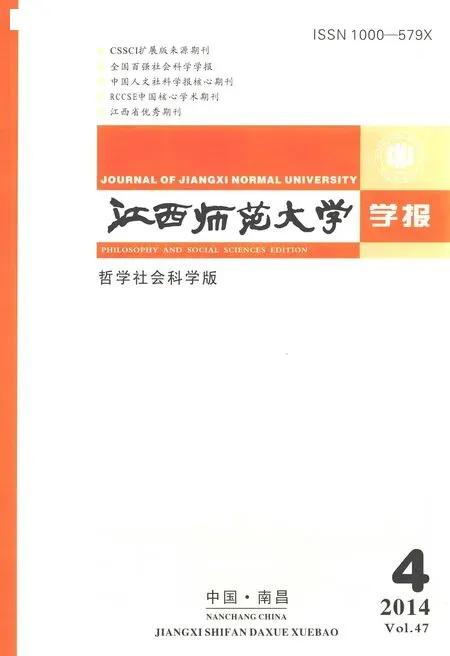论二我差:“自我叙述”的共同特征
赵毅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论二我差:“自我叙述”的共同特征
赵毅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二我差”是所有的第一人称叙述不可避免的现象,不同的“我”既合一又分裂,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纪实的体裁,始终贯穿着这种分裂造成的张力。叙述者“此我”与人物“昔我”的分裂,既可以是时间上先后造成的,也可以是自我意识分裂形成的。有时候这种差别表现在语言风格上,有时候表现在意识上,是两种主体意识对话语权的争夺。“二我差”甚至可以构成戏剧化的情节结构,此时二我的分裂成为叙述推进的根本动力所在。
二我差;自我叙述;叙述者;人物;叙述现在
笔者称为“二我差”的现象,发生在所有的“自我叙述”(homodiegesis)中。自我叙述,即我讲我的事,就是一般所谓第一人称叙述,在所有的叙述体裁中都极其常见。在小说之外的叙述体裁中,自我叙述更多,例如检讨、忏悔、日记、自传、表白等等,凡是自我叙述,就必然有这个“二我差”问题。“二我差”问题,在一百年的叙述学史上没有人讨论过,也不见于任何中外叙述学词典,自从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这个概念后,[1]中国学界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渐渐多了起来。
一、二我差的产生
凡是叙述者显身,叙述中又讲到自己的过去,就必然产生二我差,有时这种差别表现在语言风格上,有时表现在意识上。不管是在虚构的小说中,还是在自传中,还是在口述中,一个叙述者“此我”,讲述自己作为人物的往昔,既可以用“昔我”的语言,也可以用“此我”的语言;既可以表现“昔我”的意识、经验、判断,也可以用“此我”的意识、经验、判断,这种语言或意识的差别,就是“二我差”。
在不同叙述中,“二我差”会有很大变异,有时“二我差”细微到可以忽视,有时表现强烈,有时甚至是强制性地成为叙述的基本构成要素。例如写检讨,说忏悔,表坦白,必须用“此我”的意识来否定“昔我”的“当时的意识”。在所有的自我叙述中,叙述者与人物只是在“累积身份”上是同一个人,叙述言语主体与经验主体只是可以追认地合一,例如在坦白书中,两个我是法定上合一,“此我”必须为“昔我”做的事负法律责任,承担惩罚。但是在叙述中,“昔我”并不具有充分主体性,因为不是此刻的讲述行为者,不是叙述意识的源头。法律无法惩罚“昔我”,而必须依照“此我”主体的状况进行判决。这就是“坦白从宽”“将功抵罪”的叙述学基础:在主体的充分性上,“此我”已经替代“昔我”。
在隐身叙述者的叙述(即所谓“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主体与人物的被叙述主体,本来就是分割的,不会出现不同的“我”既合一又分离的张力。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我”与人物“我”是同一个人,又不是同一个人。叙述者“我”出现在后,在“叙述现在”,人物“我”出现在前,在“被叙述往日”,此刻的我是叙述者,讲述过去的我的故事。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我”为叙述者讲述爷爷奶奶那一辈发生的故事,彼时有无“我”这个人物,并不是小说叙述的必须条件:“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写作时间与阅读时间处于经验世界时间轴上,与纪实型叙述事件有关,与虚构叙述时间无关。写作时间与接收时间,处于作者读者的世界中,它们也都是文本之外的,这点不难理解。对于文字图画等记录类叙述而言,写作时间必定后于被叙述的时间。
由此,在所有的自我讲述中,赫然出现了两个甚至一连串完全不同的“我”。似乎叙述者“我”在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几个不同的叫做“我”的别人的故事。有时,甚至叙述的语言都不再是叙述者的语言,而是人物的语言,这是有可能出现人物“我”抢叙述者“我”的话。这两个“我”的间距,笔者称之为“二我差”。
二、“此我”与“昔我”争夺话语权
“二我差”不是一个稀罕物,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著作经常是“二我差”的最好例子。鲁迅《伤逝》中有一段两种声音的混杂:
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冰的针刺着我的灵魂,使我永远苦于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还有很多,我也还没有忘却翅子的扇动,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
第一句是人物涓生的语言,当时他跟子君提出分手的时候是带有一点开拓新生活的勇气的。第二句是叙述者“此我”对“昔我”的感受和评价,叙述者“我”知道后来子君自杀了,所以“我”“自责,忏悔了”。
“此我”的忏悔心理,也出现在朱自清的自传散文《背影》中,朱自清《背影》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点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太不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文中用两个表示时间的词语“那时”,分开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使得叙述与故事本身有了一种间距。所有的“自我叙述”的结构通则是,一个成熟的“我”,回忆少不更事的“我”如何在人世的风雨中经受磨炼,最后认识到人生真谛。成熟的我作为叙述者当然有权力也有必要对这成长过程作评论、干预和控制;作为人物的“我”,渐渐成长,要去掉身上许多缺点,免不了要被成熟的“我”评论并且嘲弄。
鲁迅的名著《故乡》中大家熟悉的段落:“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这是小时候的“昔我”)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这是叙述者“此我”的回忆解释,是昔日的我并不太理解的家庭亲情。)”
再例如《简·爱》里写简·爱小时候被罚禁闭,独自待在死去的里德先生当时咽气的那个房间,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返回原地时,我必须经过大镜子跟前。我的目光被吸引住了,禁不住探究起镜中的世界来。在虚幻的映像中,一切都显得比现实中更冷落、更阴沉。那个陌生的小家伙瞅着我,白白的脸上和胳膊上都蒙上了斑驳的阴影,在—切都凝滞时,唯有那双明亮恐惧的眼睛在闪动,看上去真像是一个幽灵。”这一段是成年人叙述者简·爱对童年面对恐怖场景和畏惧心理的一个回溯。
从《简·爱》的例子,可以看到:各种“我”实际上是不同主体:叙述者“我”成熟,饱经风霜,愤世嫉俗,认清这世界;人物“我”是个在渐渐长大的女孩子,“虚幻”、“冷落”、“阴沉”这样的字眼是小孩子能感受得到但是用不起来的。写照镜子看到了“陌生的小家伙”,这也是从大人视角回忆的证据:“二我”在这面镜子前后都得到了映照。前者的语言犀利尖刻,后者的心理生动。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中有例:“一系列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就开始了,直至柯希莫拒绝吃蜗牛并决定把他的命运同我们断开的那天为止。……这种家人之间的怨恨的积累我后来才明白。当时我八岁,觉得全都是在做一场游戏,顶撞大人是所有孩子的脾性,我不明白我的哥哥为表现出的知道劲头中蕴藏着更深的东西。”叙述者“我”回忆当年的“我”,当年的“我”当时只是一个八岁的懵懂无知的孩子,以为一切都是游戏,但“此我”已经长大成人,明白了哥哥反叛的原因。
大部分二我差例子,“此我”总是比“昔我”高明,但是这并不是规律。埃德加.艾伦.坡的名著《黑猫》,“我”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如何喜欢小动物时,一方面说“抚摸它们一下,我都快乐得要死”,这显然是当时童年时的“我”的语气。但是又说“父母对此(喜欢小动物)也百般纵容”,“纵容”一词应不是儿童之语,而是长大后的回忆口吻。回忆第一只黑猫时,叙述者说它“是我最心爱的宠物和玩伴”,但在说道第二只黑猫时,则说“毫无疑问,这畜生招致我厌恶的原因,就是在我带它回家的第二天早晨,看到它和普路托一样,眼珠也被剜掉了一个”。《黑猫》的叙述经常出现两个叙述主体“我”:一个是在回忆中具有某种忏悔和自责意识的“我”;另一个则是暴虐、善变、乖戾的“我”,在叙述的某些片段出现。显然“此我”的思想已经相当混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叙述者“我”是个彼得堡九等文官,坦白地说他自己“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但10多年前对妓女丽莎的鼓励又显然是另外一个人,“还有一句话,丽莎:一个人只爱计算自己的不幸,而不会计算自己的幸福。你好好算一下,就会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当年的乐观亲和,体谅别人的我已经不见了,叙述者“此我”自卑软弱悲观,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人。
三、非时间性的“二我差”
除了年龄的成长外,二我差还发生在叙述者与人物的其他品格变化之间,例如一个清醒的叙述者,回忆的“我”当时愚笨。阿来《尘埃落定》:“那个麦其家的仇人,曾在边界上想对我下手的仇人又从墙角探出头来,那一脸诡秘神情对我清醒脑子没有一点好处。”“我”作为人物,是一名傻子,本该一无所知。然而作为叙述者,却能辨别周围的是是非非,因此叙述者能说此时仇人的神情是“诡秘”的。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梦叙述也是一种“自我叙述”,梦者看到自己在梦境中的种种经历,但是梦中的我,既是我,又不是我。梦者是主体分裂后的产物:在梦中,梦者并不认为自己在做梦,在梦的世界中,“我”实际上并不在做梦。而在幻想中,主体也是分裂的:“现实世界的我”并不进入幻想,在幻想的我,无法进入幻想。分裂出来的“第一人称我”,在幻想中,不可能意识到“我”是在一个被上层主体“我”创造出来的世界中经历幻想。
如果说,对于幻想,这一点还比较难于理解的话,对于梦这一点就是常识:梦中的“我”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做梦,而做梦的“我”实际上没有看到梦,因此,“我”被“我”自己的分裂隔成两半。我做我的梦,导致“我”是梦世界中分裂的存在。在此可以用上一个全世界知道的中国典故:“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实际上,在任何梦中,都“必有分矣”,二我必然差别。
甚至可以说,任何“心像叙述”(错觉,白日梦),都是在人格分裂式的“二我差”中展开的:此我非彼我。彼我是另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中的我,在那个世界中,只存在彼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个荒唐人的梦》,主人公想自杀,但是没有勇气,在梦中,他自杀成功,体验了死亡及入土安葬的全过程。清醒的叙述者,与不由自主的梦者,形成了“二我差”。
四、“二我差”情节的追赶格局
自我叙述的“二我差”,形成一个特殊的“追赶”情节结构:被叙述时段的延展,不断在迫近叙述时刻点,二者的距离不断在缩短。被叙述时间在延伸,而叙述行为时刻,从定义上说无法移动,如果被叙述时间一直延伸,到最后两者会重叠合一。这是记录类叙述的普遍局面,叙述者“我”出现在后,在“叙述时刻”;人物“我”出现在前,在“被叙述时段”,此刻的我是叙述者,讲述过去的我的故事。叙述的过程,也就是人物“昔我”赶上叙述者“此我”的过程。
虽然故事的发展越来越迫近叙述时刻,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追赶”不显著,对叙述活动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某些叙述中,“我追我”成了情节的基本结构。
英国作家斯蒂文森(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Dr Jekyll & Mr Hyde)对此种“昔我”追赶“此我”的情景,给了一个最戏剧化的说明。这本幻想小说写的是同一人格被药物分裂为二,性格不同,长相不同,最要命的是道德感不同。因此海德作恶杀人,杰基尔博士不得不为此负责。但是“从恶如崩”,杰基尔随时可能控制不住自己变回海德。杰基尔写忏悔书,坦白一生的秘密,也就等于揭发杀人犯海德,而道德责任感不同的海德,肯定撕毁此忏悔书。两个自我必须异时存在,叙述本身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叙述者自我分裂。被叙述的人物海德,不断在追赶写忏悔的杰基尔博士,尽管这两个人物是一个主体分裂的产物。只有阻断被叙述时段,让它追不上叙述行为时刻,才能让叙述存在下去,成为记录式叙述。因此杰基尔在最后一刹那自杀,以躲避变成海德的结果,让这份叙述文本逃离被撕毁的命运。
德国电影《门》中,主人公原是一位成功的画家,七岁的女儿因为自己的疏忽(与邻妇偷情),不幸淹死于家中的泳池中,深深的自责让主人公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后来他偶然发现了一扇神奇的“重生之门”,走进去一切回到五年前的那一刻。他进入那扇门,救回了自己的孩子,也见到了五年前的自己。在本片中,同一个叙述主体,却有两个人格:年轻的自己无法忍受此后的自己的态度与人生观。但是他再也走不出来:只有亲手杀死自己,避免“今日的”自己犯错误。因此,叙述学家柯里说:“只有当叙述在进行时,人物身份才成为人物的身份……故事最大的神秘之处是这个时间段(“被叙述时段”结束,“叙述时刻”尚未到来),因为它未知,未决,未述。”
同一个原因,“精神分裂”也是造成“二我差”的重要手段,因为两个我在争夺对主人公的控制权。A.希区柯克《精神病患者》男主人公严重的恋母情结导致其人格二分(分裂为“我”和“母亲”),最终结局以“母亲”人格为自己罪行辩解,“二我差”始终存在;B.马丁·斯科西斯《禁闭岛》因战争的余毒过度的人格二差,杀死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而自己又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导致精神分裂。在正常人格和变态人格中间徘徊,一边寻找“杀妻”真凶,渐渐发现自己的真实人格,无比痛苦,最终致使医生不得不对其进行手术,“二我差”消失,叙述结束。此外,大量的精神分裂电影如大卫芬奇《搏击俱乐部》,朗·霍华德《美丽心灵》《飞跃疯人院》等等,在进行不可靠叙述中展现人物“二我差”。
电影《环形使者(Looper)》,老年的主人公为了避免死亡,穿越到自己年轻的时代企图改变过去,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年轻的主人公并不认同老年的自己的看法,于是二人互殴,叙述主体既应该是一个人,又是两个人,形成了奇特的“二我差”。这种“二我差”变成“二我斗”的桥段,在《回到未来》三部曲中已经使用。人物与叙述者的最后相遇,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叙述行为本身,会阻断有关自身的叙述。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Agatha Christie)《罗杰杀人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中的“我”罗杰是本地医生,帮助大侦探波罗破案,但是最后“我”被发现正是谋杀犯,是叙述者在帮助人物试图蒙混过关。小说最后一节《自白书》中,“此我”写到最后时刻的“昔我”写坦白书给波罗:“已经是清晨五点,我感到精疲力竭——但我完成了任务。写了这么长时间,我的手臂都麻木了。这份手稿的结尾出人意料,我原打算在将来的某一天把这份手稿作为波洛破案失败的例子而出版!唉,结果是多么的荒唐。……把手稿全部写完后,我将把它装进信封寄给波洛。”因此,寄出信这个叙述行为的完成环节,即次叙述框架的设立,依然阙如,“昔我”与“此我”的合一,依然被死亡所隔断。
五、如何擦除“二我差”?
二我差给自我叙述以张力,但是每篇叙述要求不同,有时候必须擦抹掉这种差别。无论作何种处理,“二我差”总有自我叙述在语言和意识上需要弥合的鸿沟。为了避开这个困难,某些小说有意把叙述时间与被叙述时间的间隔缩小。例如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把叙述时间安排在少年主人公结束冒险经历之后不久,而不是在他长大之后若干年。这样,全文的戏谑性街头少年的语言,就同时属于两个“我”,不会发生“二我差”。
消除“二我差”的另一个办法,是用成熟的“我”来纠正过去的“我”,把过去的“我”的人物视角说成不可靠。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就是这类典型。成年马小军在影片大部分是以画外音的方式出现,两个人格经常是冲突的。这位叙述者一方面诚诚恳恳讲述那年夏天与梦中情人米兰发生的故事,一方面又不断在叙述中承认“我的”记忆是多么不可靠。当电影讲叙马小军借生日兴头挥拳狠揍刘忆苦时,叙述者立即插话,“千万别相信这个,我从来就没有这样勇敢过,这样壮烈过……我悲哀地发现,根本无法还原事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这样就否定了前一个“我”作为叙述主体的存在价值,此时“二我差”实际上被擦除了。主角马小军和伙伴们与米兰在北京的“老莫”餐厅聚餐,忽然马小军和刘忆苦为了米兰打起架来,几分钟后画面停滞,传来马小军的画外音,“千万别相信这个,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勇敢过,这样壮烈过”,这是成年后的马小军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自我”批评。直到影片结尾,成年马小军出场,“二我差”才得以弥合。
在成长小说式的格局中,“二我差”最终会渐渐合拢、消失,因为人物渐渐成熟,在经验上渐渐接近叙述者“我”。《月牙儿》的最后,人物“我”的身份已经变成关入监狱的暗娼,她仇恨冷酷世界的态度,与叙述者“我”一致了。
最极端的一种消除“二我差”的方法,是干脆把“我”在名称上分裂成两个人格,甚至转用另一种人称,把“昔我”称作“他”,甚至给一个不同的名字。王朔《看上去很美》用第一人称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但是称呼幼年的“我”用名字“方枪枪”,叙述就是“我”与“他”混合。用“我”的回忆者意识,比较客观地说“他”的故事。“我没有发现他当时有什么思想活动”,这个“他”,是过去的“我”,不是现在的“我”。这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叙述方式。
消除“二我差”,有时候可以变成一种自我幽默打趣。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
这整个一段是人物的语言,似乎准备讲一段“昔我”观察到的猪的浪漫史。但此时叙述者突然话锋一转:“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叙述者干脆用“此我”之无能来放弃责任,自我取消。用这种反讽式的自我检讨,“此我”面对“二我差”的责任,被叙述者郑重其事的歉意擦抹去。所有第一人称叙述不可避免的“二我差”现象,终于在“此我”叙述能力的自我消解中,归于无形。
有时候,“二我差”会不小心地暴露出作品的意识形态差距。郁达夫的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
我囊里正是将空的时候,有了这五元钱,非但月底要预付的来月的房金可以无忧,并且付过房金之后,还可以维持几天食料。当时这五元钱对我的效用的广大,是谁也不能推想得出来的。
全文都在讲“昔我”的苦事,此话是“此我”唯一的自我泄露。我们突然意识到叙述者“此我”在讲述自己过去这段经历时,“此我”与“昔我”突然分裂:那个穷愁潦倒、贫困不堪,在上海贫民窟与卷烟女工二妹同病相怜几乎互相爱上的 “昔我”,现在可能阔多了,不再在乎那五元钱的意外收入。《春风沉醉的晚上》之所以能打动人,在于其弥漫一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伤感,尤其是其结尾之无出路,之绝望。上引这段中暴露出的“二我差”,可能是个疏忽,却差点毁了整个小说,也几乎翻开了整篇小说的意识形态“盲区”:被抛出权力结构的现代知识分子,与被抛出土地的农民,在游离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上海贫民窟中,有结合的可能吗?
最后一种排除“二我差”的办法,是把人物的语言置入“直接引语”之中:“此我”所模拟的“昔我”的语言,不一定是客观上必须具有“昔我”说话的品格。所有被文本叙述出来人物的语言,都只是一种比拟,不可能绝对“如其人之言”。
引发争论的还是最常见的一段,即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一段,有些论者讨论两种主体对比,总喜欢以此为例: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叙述学者们解释说:Ade是德语,此时的迅哥儿还是学前儿童,显然不懂德语,因此是“二我差”。视角人物是小时候的鲁迅,而叙述者是多年以后学贯中西的鲁迅,想是鲁迅回忆起童年时的自己,不自觉的用了德语,成年后的“我”抢了小时候的“我”的话。[1]
这个看法似是而非,完全弄错了“二我差”的叙述学构成。叙述学上说得直接引语,就是人物说的话。这是以引语方式(引号,或其他标记,例如上引这一段是“自由直接式”引语)为准的,而不是语言本身的质地来决定的。一旦人物的话语用直接引语表现出来,人物就对自己的话语有全部控制权,也就是负全部责任,叙述者只能尽转述的义务,而无法加以干预。童年鲁迅能否说出德语,完全是作者安排问题:他让人物说,人物就有权说。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更戏剧化的例子。二十世纪之前,中国文学中第一人称叙述比较少见。文学史上公认最杰出的“自我叙述”恐怕是沈复的《浮生六记》。其卷二《闲情记趣》有一段:余问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见市中卖馄饨者,其担锅、灶无不备,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调端整,到彼处再一下锅,茶酒两便。”
我们不禁要问:这对夫妻之间,生活再有雅趣,需要这样文绉绉地讨论吃馄饨吗?当然不是。看一下为时先一个半世纪的《红楼梦》,看一下社会等级高得多的人物如何说话。《红楼梦》第46回说吃肉:“一时只见凤姐也披了斗篷走来笑道:‘吃这样好东西也不告诉我!’说着也凑着一处吃起来。黛玉笑道:‘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哪怕贵族人家,生活中也不用如此子乎者也的文言。《浮生六记》是十九世纪中叶所作,已经接近现代,商人家里说吃喝之类闲事,绝对不会如此说话。那么这是不是沈复写作时形成的“二我差”?当然也不是,原因不是由于《浮生六记》叙述者“此我”与“彼我”没有太大不同,而是因为沈复夫妻的话用引语隔断,不同主体,就不可能冲突。一旦叙述者的人格被挡在引语之外,这引语再文言腔,再外语腔,都只是“记言”的方式问题,不存在“二我差”。
[1]赵毅衡.二我差与叙述主体的分裂[J].上海文学,1987,(6).
[2]张雨林,张 烜.回忆性散文中的“二我差”及其表现[J].现代语文,2006,(2).
(责任编辑:张立荣)
OnSelf-differentiationCommonCharacteristicofSelf-narrative
ZHAO Yi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
The self-differentiat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of all of the first person narratives.The different first person narrator includes both unity and division,the tension caused by this kind of fission is through to the end,whether the genre is fiction or documentary.The reason for the fission between present narrator and past narrator are as follows:time order and self-awareness fission.Sometimes this kind of difference displays in the language style,sometimes displays in consciousness,and two kinds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es are in the fight for the right to speak.The self-differentiation can even form a dramatic plot structure,then the self-differentiation become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narrative.
self-differentiation;self-narrative;narrators;characters;narrating present matters
2014-04-1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编号:13&ZD123)
赵毅衡(1943-),男,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符号学。
I01
A
1000-579(2014)04-006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