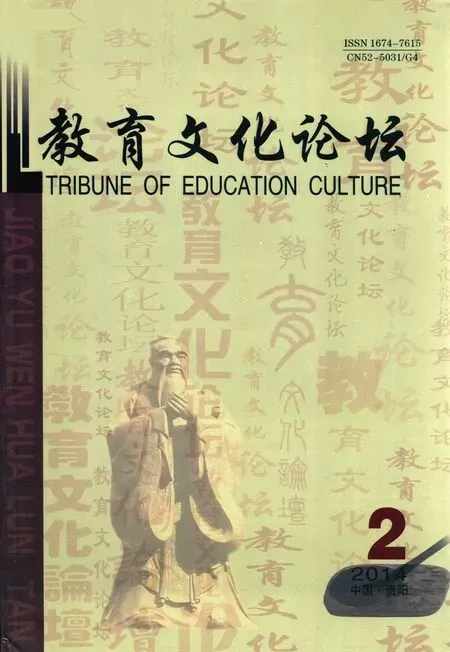贵州军屯制度与屯堡族群建构
吴 羽 孟凡松
(安顺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政权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军屯作为重要的经国措施。它涉及军事、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明代贵州军屯更是对贵州的开发与建省、贵州的民族关系与社会经济结构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贵州的军屯制度对安顺独特的地域文化——“屯堡文化”的产生与传承、屯堡族群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贵州军屯历史的宏观背景下,考察了屯堡人生存的制度背景,进而从发生学意义上对屯堡族群的建构传承机制进行制度层面的解读。
一、田制、里甲与赋役体系:明代贵州军屯的制度遗产
户以籍定,籍以役分。军户、民户,军籍、民籍,军役与民役,明代的军民之分,不仅是户口与身份的差别,更表征着针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异同。不仅在户口上有军民之分,整个国家的疆土管理体制,也由军民两大系统组成,所谓“军民分际”,在明代包含着最为丰富的内涵。
明代贵州军屯依托卫所制度而展开,同时也是卫所制度存在和维持的经济基础。卫所与军屯互为表里。在贵州,卫所的设置与实践,既是王朝体制与观念内外之别的展现,也是一种汉与非汉、教化与文明的族群标识,卫所是设省置府建立流官统治的先声,是中央政权在贵州实现流官政治的坚强后盾。军屯的实践则为贵州建省提供了经济基础(主要是土地)、社会基层组织体系(屯田的组织与管理体系)与赋役制度(军役与屯田子粒)。清政府改卫归流,将明初贵州所建立的地方管理中的军民两大系统转变为单一的行政系统(即民系统),促进了贵州建省的最后完成。
明清贵州军屯经历了兴起、衰弊与变异的过程。卫所“有土有民”,具有构成行政单位的最为基本的要素,这使得具有很大强制性特征的卫所军屯在洪武、永乐期间短暂兴起之后即迅速走向衰弊。宣德以后,贵州卫所衰而不亡,军屯弊而不废,卫所的行政化特征日趋明显,军屯管理的民田化趋向也日益加深。清承明制,在经过改朝换代、改卫归流以后,卫所军屯虽不复存在,但基层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屯田承载的各种赋役规定仍然相沿不改,它以一种变异的形式继续发挥影响。
通过卫所军屯的展开,贵州赋役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其中,卫所屯田在贵州赋役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卫所科田的发展则代表了贵州土地管理与赋役改革的趋向。同时,明代贵州卫所军屯的基层组织体系与州县里甲体系一样,具有类似管理户口、征收赋税的功能。明代中后期所设的卫所相对明初有了很多变化,如规模变小、赋役规定简化等,这种趋势到了清代继续发展,就是将卫所彻底转变为一个管理户口与征收田赋的单位,直至最后改卫归流,因军屯而建立起来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被吸收入州县里甲系统。然而,改卫归流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明代卫所影响的彻底消解,因为在相当的程度上,清政府仍然保留了卫所时期的基层社会组织系统与赋役制度。安顺屯堡的长期存在,在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甚至还被主流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族群事项加以记载、描述,从里甲体系、赋役制度及其所积淀的族群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理解,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思路。
二、军屯制度与屯堡族群建构
黔中屯堡族群的出现,是明清时期朝廷军事移民和后续汉族移民的结果,自落土贵州并不断繁衍后代起,就具有“卫所屯田”的制度性安排。由于黔中地区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及其由此产生的特殊的制度设计,黔中屯堡族群自落土当地以来,始终自觉地通过国家符号的利用与国家意识的强化来强化族群意识、建构族群身份,保持着国家权力和族群意识强化共融互嵌的状态。在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屯堡族群体现出不同于其他明清军屯地区(如贵州其他地区,我国东南、东北地区)的农村社会结构和地域文化。在考察贵州军屯历史尤其是对明代卫所制度背景下贵州屯田历史作出比较系统的考察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军屯制度对于屯堡族群的意义。概括地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明代军屯实践存留于屯堡社区的制度遗产是屯堡文化得以持续的历史基础
明初贵州卫所在川滇驿道、滇黔驿道沿线密集设置,与卫所开设相应的就是卫所屯田的开展与大量屯堡社区的形成。但是,屯堡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社会文化,却仅在黔中安顺一带得以保存至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虽然经历清代、民国长时间的历史变迁,但明代军屯实践存留于屯堡社区的制度遗产却一直持续存在。这种制度遗产就是明代卫所军屯所形成的赋役制度与基层社会的组织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安顺是贵州军屯制度实际消解最晚的地方,清代改卫归流以后仍然延续的赋役制度以及由卫所屯田组织转化而来的村社里甲组织体系,为屯堡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
具体地说,在平坝一带,卫所裁撤以后,其基层社会组织体系与赋役制度并没有消解。相反,相对于明政府对贵州卫所或县级政区的基层社会控制能力而言,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整顿和强化①改土归流与改卫归流后的清代贵州县级政区大体都依托里甲制度建立赋役征发体系。改卫归流之后,安平、清镇、普定等县级政区,大都直接接管了卫所遗下的土地和户口,将之纳入州县赋役管理体系。但是,对于卫所军屯实践造成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与赋役则例却没有作出根本调整,这恰恰为屯堡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虽然清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批准“黔省军田许照民田一体买卖”、“每亩上税银五钱,给契为业”②《清世宗实录》卷83,雍正七年七月戊申。。但是,截至光绪十年(1885)仍记录在汪公会中的“屯田”,作为“集体”的、汪公会会产的一部分,它们不可买卖的特性仍然被特别强调,并且“绝军”户与耕种者形成佃耕关系,说明明代的屯军户与清代改卫归流后的里甲户一旦登载于田赋册籍就具有不可更革的法律效力。同时,“屯田”所承担的田赋仍按“分”统计,每分纳粮四石,也可视为明代“卫制”的继续。这意味着,在户籍与赋役的意义上,直至清末,卫所军屯制度所消解得仅仅是政治、军事功能,而赋役制度规定下的民间运作机制远未瓦解。与之相适应的是,家庭作为屯堡族群最普遍和最基本的结构细胞,经历了朝代更替和社会变迁的冲击,仍然稳定地支撑起屯堡族群的生存繁衍。
(二)军屯制度预设了屯堡人的社会结构
军屯制度预设了屯堡人以家庭为主的非宗族的社会结构。学术界一般将血缘和地缘视为中国传统社会两种最为主要的社会关系,并将血缘的作用置于地缘之上,以此来解释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以及生存于其间的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特征。但是,屯堡族群却采取了非宗族血缘关系的另一套建构方式。弗里德曼认为,在“边陲地区”,由于政府社会控制力的软弱,宗族组织得以发展。安顺屯堡族群的例子表明,“边陲地区”未必一定有发达的宗族组织,这就可能对弗里德曼的命题提出修正,乃至是对其命题的证伪。
在屯堡地区,非宗族组织发展,宗族的发展却受到限制,仍要需要从军屯制度本身来理解:首先,以军户家庭为基本应役单位,军役负担沉重,缺乏宗族发展的经济条件;其次,屯军比较分散地来自南直隶、湖广等省区,在严密的军屯组织下,屯田官、旗、军对祖先的强调,是要表明世袭的身份在军役权利与义务上的差别,而不是要通过宗族的形式争取地域社会的领导权——这种权力已经通过世袭的户籍身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因此也就不再强调通过共同祖先记忆构建宗族;再次,包括屯军在内的,从各地移民而来的卫所旗军,与当地原住民相比,他们已有汉族群的认同、强调与凝聚,在村社范围内继续强调自身宗族的结群要求也就变得相对次要。不强调宗族形式的结群,并不意味着不发展其他形式的结群。在屯堡社区,核心家庭居于主导地位而宗族势力较弱,但核心家庭结构又难以满足屯堡人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要求,需要屯堡社区和屯堡族群加以补充。正因为家庭在社会性需求上对社区和族群有较大要求,导致了家庭、社区、族群相勾连的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中,屯堡人互为团结、内聚力的依持源于共同的生存困境,屯堡村寨之间团结的依恃也同样源于互为呼应认同的族群生存需要。
军屯制度限定了屯堡人的通婚圈。在明代数百年间,包括正军、军余及其家庭在内的卫所旗军一直代表国家守御着“一线之外,四面皆夷”的黔中民族地区,在自身来自内地、代表国家与正统的身份意识主导下,与当地的原住民保持一种隔离关系,这使得他们只能在族群内通婚而不可能与当地原住民或非屯堡族群通婚。后来,虽然经历了改朝换代等社会变迁,但长期积淀的身份意识与婚姻观念却一直延续,族群内通婚成了屯堡人婚姻形态的核心内容。这种婚姻形态可追溯到屯堡人的起源上。当初,调北征南先是军士,紧跟着带家属随军,落土之后,是以军户、贴户为细胞,而非军士、余丁为细胞。根据户籍管理制度,卫所官兵一律入军籍,称为“军户”。每军户由一名男子服军役,史称“正军”,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正军死亡或老病,便由余丁替代,如全家死亡,就必须到原籍勾取族人顶补——原籍勾补当然在执行上存在很大的难度。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卫所制度所限定的军役制度,使得婚姻可能成为承担军役的依据,这也限制了非屯堡族群与屯堡族群的婚姻关系。总之,从屯堡族群的身份及身份意识、军役制度等方面,屯堡族群与非屯堡族群之间的婚姻都较难发生,这是双方面的,而不能仅仅强调屯堡族群的因素。不管怎样,相对狭隘的婚姻圈,使村庄之间的关系在世代承传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屯堡人常说,“一人亲亲一家,一家亲亲一村”。族群内通婚的直接结果,是以婚姻这一最基本的也最牢固的社会关系,泛化到对整个族群的社会基础的建构上。
(三)军屯制度强化了屯堡人的政治意识与族群意识
作为明初政府政治军事行为执行者,屯堡人是强势的军事移民,肩负着国家的使命,普遍有一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优越感。随着朝代更替,当国家的光环在他们身后消失的时候,屯堡人经历了从国家武士向乡村农民的转化。要在西南边陲这样一个陌生而又充满族群冲突的环境中生存与繁衍,屯堡人必须充分利用国家符号,进行族群的身份建构。这使得屯堡人能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通过对国家使命与国家意识的记录和确认来表达国家使命感和政治优越感,以此强化屯堡人的身份认同。
三、军屯历史背景下地方族群与国家政权的互动
在我国历史上,军屯作为解决军队粮秣供给的重要方式,被历代政府所重视。但是,作为一种将土地与劳动者结合起来的强制性的国家行为,军屯的意义又不止于此。在割据时期,军屯是分裂政权之间角力的重要工具;在民生凋敝的战乱时期,军屯是恢复社会生产的重要举措;对于一个统一的政权而言,它是解决军饷的有效途径,它贯彻着国家意志,在地方族群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互动中改变了军屯区原有的社会经济与人口族群结构,更是经营边疆的基础性措施。通过对贵州军屯历史与屯堡族群的研究,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的国家政权向西南边陲拓展的进程中显示出地方族群建构与中央政权的一种互动形式。
贵州在明清时期“军屯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下延与地方族群意识建构成为了一对明显的矛盾,并导致了少数民族政权与国家政权的冲突对抗。而屯堡族群的身份建构与国家权力的下延却处于一种相互共融的互嵌状态中。屯堡族群一直自觉地、自组织地、自下而上地通过国家符号的利用与国家意识的强化,来进行族群与身份的建构。
正如高丙中所指出的:“民间社会在已经与国家疏离的场景中又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而国家也在征用自己曾经完全否定的民间仪式。民间社会复兴自己的仪式,总是要强调自己的民间特色和身份,但同时又要利用国家符号。越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其仪式就越容易获得发展。”[1]当然,对国家符号的利用最终还是要为屯堡族群身份的建构服务的。“在地方各种力量运用国家符号象征来宣示自己权势和特征的同时,地方社会也构建了一个由支配力量和依附力量共同创造的地方认同空间,不同的力量可以在比国家认同更为宽松的环境下找到自己的生存支点和文化定位。”[2]在屯堡族群的建构中,国家符号与族群利益之间构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屯堡族群和其他的族群一样,“常常去寻找各自祖先遗留下来的入住证据,他们懂得如何尊重和巩固自己祖先对环境的改造成果,并懂得如何制造出一个理想的祖先形象,对祖先的崇拜是为了与今人的竞争。”[2]而军屯制度规定的历史使命,使屯堡人的祖先与国家的军事举措有更高的关联,“汪公”、“顾成”等国家使命的执行者更成为了屯堡人的民间权威,被赋予中国传统忠义勇武精神的民间权威被镌刻到屯堡人的历史记忆中,深入屯堡族群的建构中;深入到每一个屯堡家庭,成为屯堡家庭与国家符号之间的鲜活介质。万明认为:通过这些民间权威,保家卫乡与忠君爱国联系在一起成就了家国一体的观念,从而在屯堡地区形成一种融合性和凝聚力极强的本土文化。汪公、顾成等民间传统权威在屯堡族群的建构中成为屯堡族群象征意义的祖先,在族群建构过程中勾连了屯堡族群与国家符号,使屯堡族群的建构能以广范的家庭作为其坚实的基础与支撑。[3]
贵州军屯的制度背景使屯堡族群主动将国家意识与符号运用于族群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打破了国家符号与族群建构的对立冲突模式,实现了代表国家主流文化的“大传统”与代表地方(族群)文化的“小传统”之间的有机结合,最终使国家的权威得以在地方族社会中“驻扎”,充分利用对国家符号更有效地支撑了屯堡族群的身份建构。
[1]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
[2]罗一星.资源控制与地方认同——明以来芦苞宗族组织的构建与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J].2007,(01):48.
[3]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J].中国史研究[J].2005,(0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