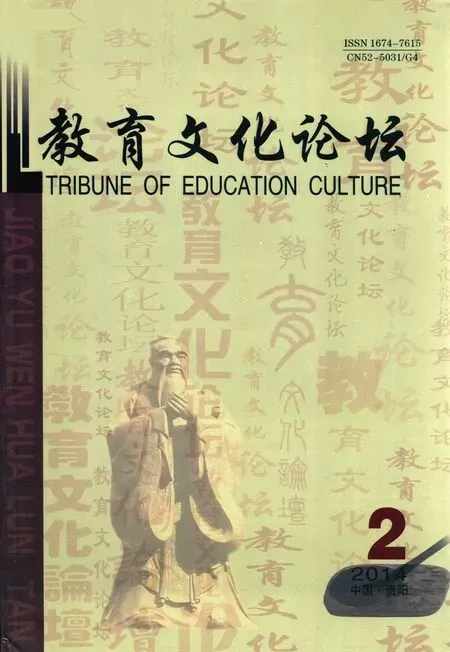龙图腾:基于多元一体语境的中华民族认同
马 昀 徐则平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大学人民武装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华民族不分地域和族群,历来都以“龙的传人”自称。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5000多年中,东方文明里唯一一个无可取代的特殊符号便是龙图腾,倘若抹去龙图腾符号,东方文明可谓不甚完整。论其地位和影响力,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华传统文化到民族心理再到每一个中华民族个体的内心深处,龙图腾符号无所不在,可见一斑。现实中的龙并不存在,而龙图腾符号本身只是上古先人的观念意识物质化。摩尔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中表明,图腾是氏族社会的“徽志”,它就好比是一个商标或品牌,通过它来分晓自身族群与他者,使族群内部达成互相认同的状态。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更深层的指出,图腾所被赋予的神性和主宰力量,即是源于对氏族社会本身的维系。可见,图腾对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非凡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使用蛇、鹿、兔、牛、鹰、虎等九种动物的多元部分,拼凑汇合一体,形成独一无二的龙的形象,其多元一体的深刻意蕴,是上古先人留给我们打造民族认同,构建民族国家不可多得的契机。[1]
一、龙图腾符号的多元与一体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龙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在此,我们把龙图腾符号分为龙的造型、龙的本质、龙图腾所蕴涵的文化三个层次进行剖析。
从造型上来说,早期中国的原龙是以动物为想象蓝本的,形象接近蛇、鳄鱼等动物,在原始社会中还有近10余种形象接近其他动物的龙的原型,氏族社会时期的龙的形象是现实中存在的单一的某种生物。[1]而到了文明社会初期,人类把蜥蜴类和鳄类等爬行动物统称为龙,并创造出杂糅多种动物造型的龙的造型,也是对龙图腾符号的一种创新解读。
从本质上来说,龙是一种神灵动物,同时亦是古代氏族社会的图腾。龙是“九似之兽”,在中国的图腾中象征着神灵,是有神性的,而这种特殊的图腾本质上是中华民族的标志,从一个侧面表征着中华文明。
从龙图腾符号所蕴涵的文化来看,龙还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中华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龙的神话传说,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龙。龙是一种综合了牛头、羊须、鹿角、马鬃、蛇身、蜃腹、鱼鳞、鹰爪、虎掌一体多元的图腾符号,这反映出中华民族形成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包容力。}多元的动物造型、丰富的文化内涵,幻化于“龙”这一体,深刻阐释了多元与一体的融合。
多元的动物造型意味着多元的文化,正是由于多元的文化交融、汇总于华夏之地,造就了龙图腾符号的“多元”特征。而论其本质属性,归根结底,当属“一体”。龙图腾是一个整体符号,它不仅体现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成长史,更体现出历经五千多年而经久不衰的民族哲学思想和民族文化精髓。当然,不可否认我们敬畏龙图腾符号所包含的每一种动物图腾的形象,但它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表征出中华民族的身份,不能勾连起子子孙孙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龙图腾符号的多元孕育于一体之中,倘若割裂开一体,便不能传递出龙文化的精髓,自然也就不再具有图腾符号所共有的号召作用、凝聚作用、和认同作用。鉴于此,民族理论学界应格外关注龙图腾符号的“一体”属性所传递出的对于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不竭动力。
二、崇拜龙图腾的中华民族研究
自从中华大地上出现龙图腾符号后,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就一直崇拜“龙”,几千年来始终如一。因此,龙图腾文化伴随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人类文明史中为数不多没有中断的图腾文化之一。龙图腾崇拜的演化,可以笼统分为蒙昧野蛮时代的龙图腾崇拜和文明时代的龙图腾崇拜,具体的说,进入文明社会后的龙图腾崇拜,随着朝代的更迭,大致以夏朝、秦汉、宋朝、清朝等为重要的发展节点。
原始社会的龙图腾崇拜主要发祥于距今8000-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1935年在内蒙古赤峰的红山遗址中出土的玉器龙被考古学界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龙图腾器物。这则玉器龙猪首龙身,出土时处在棺椁中尸体的胸前,在表现出墓主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也说明了龙图腾的崇拜在当时就已盛行。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脊椎动物的脊椎胚胎演化都是从弯月形态开始的,无论是较为低等的水生脊椎动物的早期脊椎胚胎还是人类的早期脊椎胚胎。这则世界上最早的龙图腾器物也是呈现出几乎首尾相连的弯月形态,而当时的医学远不足以探知动物的脊椎胚胎演化过程,所以,这则神秘的玉器龙饱含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孕育天然的领悟力和对生命创造天然的敬畏感。[3]
龙图腾符号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中大多是以凶神形象出现的,其在夏朝仅出现在祭祀专用的青铜礼器上,当时的龙图腾符号常伴随着螺旋纹样,且使用频率远不及后世,说明龙图腾符号在当时尚处在发育期。进入周朝后,龙图腾符号和凤图腾符号在使用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使用范围局限在祭祀礼器上没有扩大趋势,而且凤图腾的出现频率一度超过了龙图腾,尤其引人深思的是个别地方的龙图腾符号被移植进了凤冠,呈现凤冠龙头状。这大大弱化龙图腾符号作为凶神的狰狞和威严,平添了一丝柔婉感和艺术感。到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的社会状态使得严谨的宗教秩序和祭祀礼仪出现了松动的迹象,龙图腾符号的使用范围随之出现了漫延趋势,从之前作为凶神出现在祭祀用品,发展到使用在林林总总的青铜器具上,镜台、酒樽、门环等等。
百家争鸣的社会状态发展到秦汉时,儒学和道教已经被广为接纳,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结之中,这使得龙图腾符号也随之广为盛行,发展空前成熟。其具体表现为不同于先前的符号变体化、多体化,龙图腾符号大多呈现出统一的造型,有了公式化、固定化的趋向。秦始皇划时代的开辟出皇帝乃是真龙天子的先河,随后在中华民族的民族观念里龙图腾符号多包含的寓意不仅仅是凶神和瑞兽,更是神灵下到凡间化身成一国之君。
宋代是龙图腾符号演进中又一座里程碑。此时,龙图腾符号已从秦汉之际的统一刻板、简单粗略,越来越呈现出栩栩如生,繁复逼真的特征。例如,在细节处理上,龙图腾符号开始以有龙鳞的形象居多;在呈现方式上,龙图腾符号开始成对出现在廊柱、成组出现在画卷中;在使用意义上,龙图腾符号开始剥离图腾的精神内涵,仅仅以装饰物品的形式大范围频繁出现。此时民间兴起了“九似三停”的画龙技艺,可以说,龙图腾符号已然从宗教象征进入世俗生活,从祭祀神坛走向民间日常。这套民间画龙技艺的广泛认同,为元明清时期画龙风尚确立了标准,同时又推波助澜增强了龙图腾符号的审美旨趣,推动了其在纯美术领域的深化发展。
明清时代,龙图腾符号成为皇权的象征和标志,地位达到空前的制高点。而实际上,物盛极则衰,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即便以真龙天子为诏谕,封建首领集团终究逃脱不了从盛极一时走向衰败没落的命运。明清之际龙图腾崇拜作为皇家崇拜,其老态龙钟气象已经显露端倪了,}时间进入20世纪,龙图腾符号作为皇室符号的表征意义也进入了历史博物馆。现代社会的龙图腾符号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寓意着祥和的好兆头,出现在民生百态之中。中华民族作为“龙的传人”,龙图腾符号表达为每一位中华后人对祖国深沉的认同身份。世界各地的华人以“龙的传人”为图腾的火把,无论置身何处总会把中华民族同宗同源的图腾认同之火熊熊燃烧于内心,龙图腾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写照。
三、以龙图腾符号为契机,巩固中华民族认同
中国民族学界巨擘费孝通先生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针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进行了深入探究。他指出,通常我们在提及“长期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五十六个民族”、“香港、澳门、台湾同胞”、“海外华人”这几大群体时,运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介于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语境中的民族认同体系应当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微观上主要针对的是五十六个下位民族之间的认同问题,以族群属性作为划分标准,中观上主要针对的是香港、澳门、台湾华人与本土华人之间的认同问题,以社会制度作为划分标准,而宏观上主要针对的是海外华人群体与本土华人群体间的认同关系问题,以国界、国籍作为划分标准。既然同属中华民族,同为“龙的传人”,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应以龙图腾符号为契机,以巩固中华民族认同为己任。
(一)巩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
狭义的中华民族是对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所有下位民族的统称,[5]而民族认同关系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认同语境中的焦点。从微观上讲,民族认同包括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心理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两个层次。对于本民族的认同心理是下位民族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是上位民族认同,两者之间并不矛盾。[6]龙图腾符号作为饱含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积淀的文化精髓,无论对于汉族还是对于少数民族同胞来说,都具有强大的感召作用、凝聚作用和认同作用。而其所蕴涵的九种动物于一体的特征,又恰如今日的中华民族包含着五十六个下位民族于一体。因此,龙图腾符号理应成为维系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心理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的桥梁,成为巩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认同的基石。
(二)巩固本土华人与港、澳、台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
本土华人与港、澳、台华人之间的认同关系问题,实质上,是基于多元一体语境的中华民族认同问题。随着上个世纪末中国陆续收回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当地华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问题已然不复存在。然而,鉴于台湾地区的特殊性,仍有部分华人,尤其是出生在和平和繁荣发展一代的年轻人,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疑问。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认同语境下分析认同问题,具有其独特的优势,[6]完全可以运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认同,尤其是龙图腾符号的认同,来研究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同胞之间的认同关系。
中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语境中的“一体”,注重的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虽然由于历史原因具有特殊性,还无法实现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完全统一,[6]但必须承认,香港、澳门的华人都已纳入中国国籍,脚下的土地也属于中国领土范围。中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语境中的“多元”,注重的是社会制度的多元化选择。事实上,多元的社会制度与中华民族认同并行于不同的时空领域,可以相互协调、相互兼顾。一体与多元,分属思想认同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语境应用于大陆与港、澳、台同胞之间的认同关系研究中,是统筹兼顾中华民族认同与社会制度差异的必然选择。[6]而龙图腾文化,作为得到大陆与港、澳、台同胞普遍信仰、共同崇拜的文化符号,理应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语境、两岸三地一盘棋中最有力度的一颗棋子,为巩固大陆与港、澳、台同胞之间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铺路,为构建民族国家奠基。
(三)巩固本土华人与海外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
中国与海外华人同为“龙的传人”,两方之间的认同关系问题,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认同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值得说明的是,我们不能将海外华人单纯的理解为海外汉族。五十六个民族中,苗族、满族、黎族、京族、维吾尔族等众多下位民族都有旅居世界各地的海外成员,这些跨境民族的同胞都属于海外华人。作为世界移民的一部分,这些海外华人群体的认同心理相比港、澳、台华人群体更加具双层性:一方面产生了目前居住国的认同心理,另一方面也有认祖归宗的中华民族认同心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主要源于血缘和文化的传承,而对居住国的认同心理,则主要源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交际网络,两种认同心理可以并行不悖。[6]民族认同心理是联络本土华人与海外华人之间的心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语境,尤其是龙图腾符号的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完全能够适用于海外华人研究,并为处理中国与海外华人的认同关系提供一种思路。
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语境中的“一体”,侧重于民族认同情感的角度。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很多出生在当地的华裔对中华文化,特别是龙图腾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以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为荣。民族认同情感是将海外华人维系在一起的基本要素,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一体”。[6]本国华人与海外华人之间的认同关系,必须得到审慎地处理,尤其是在中国国际影响不断扩大的今天,应该用全局性的眼光看待海外华人的积极作用。[6]多元一体语境下的中华民族认同,特别是得到所有华人心心念念向往和崇拜的龙图腾文化,无疑适用于中国与海外华人的认同关系研究,在此框架下,更加便于海外华人恰当地处理其中华民族认同情感与所在国家认同情感之间的关系。
[1]曹薿丹.浅谈龙图腾的含义与民族性[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10):62-65.
[2]段宝林.中华龙图腾浅说[J].文化学刊,2012(5):102-112.
[3]李玉山.走向世界的中国龙文化[J].学理论,2008(2):131-137.
[4]李玉山.中华龙文化的演化内涵和意义[N].今日信息报,2008-05-26.
[5]周文.佤族心理认同的代际差异研究[D].云南大学,2012.
[6]郭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三个层次[J].东方论坛,2011(5):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