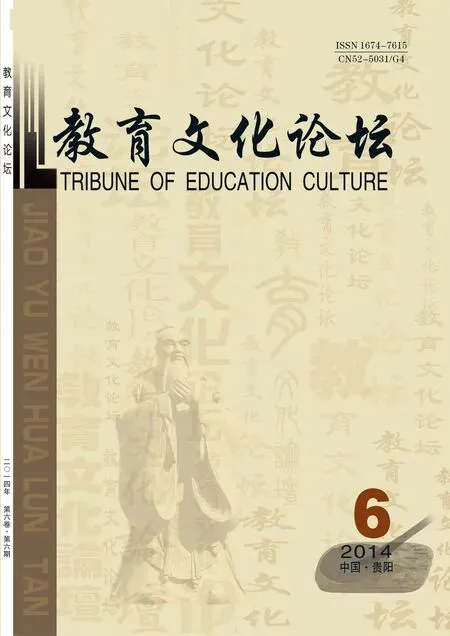从儒学的现代性发展看知识与价值的良性互动
——成中英教授访谈录
引 言
西历2012年11月8日至12日,假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之机,学界共商隆重举行庆典活动,拟回顾过去,面向未来,从而推动中国文化之创造性发展。遂经反复协商,乃以 “中国文化之继承、发展与开新”为题,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四方朋友响应者甚多,皆无不热情与会,诚可谓盛况空前也。成中英先生虽远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亦跨洋度海莅会,先后发表两场演讲,均引起巨大反响。惟稍感遗憾者,余以为当今汉语世界,若论思想理论之系统完整,并世学人少有出其右者,然因主持会议,无暇畅谈请益,乃嘱弟子王晨光、朱俊二人,事前拟出采访提纲,于花溪河畔专程拜谒,成此访谈稿长文一篇。而今会议结束已近两年,成先生返美也亦两年,乃稍得闲暇,遂通阅润色一过,以为读后必甚有启迪,乃公诸世人,以飨学界焉。
黔中张新民西历2014年10月6日谨识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一、人性具有神圣的创造力量
王晨光(以下简称“王”):成先生您好!采访之前,我曾看到一篇文章,是贵大学报13年前所刊登的您与蒋庆先生的一次谈话,当时成先生谈及中国问题的根源时提到,中国的问题在于缺少理性结构的思维方式,中国想要现代化,必须解决中国文化内耗太大这个问题,中国问题在于法律还没有建立起来伦理就已丧失掉了。因此如何透过德性伦理建立责任伦理,如果不参考西方,从自己文化开出的话,也许需要需要几万年来走。然而,如今学界对于新儒学的指责则在于其纯粹以科学和民主作为“新外王”的标准,此不免有变相西化之嫌,政治儒学与保守主义认为民主所代表的多元化的趋势是一个世俗化的倾向,从人的角度来确定政治秩序,始终是从形而下的角度来确立,最终仍不能解决整个政治秩序的正当性。蒋庆先生也认为多元可能会导致分裂,自由可能会变成任意妄为,民主也可能会变成暴民统治。新民师也经常提及人的生命中存在的终极关怀不能消失,必须从传统吸取经验资源以重建现代制度。而更关键的质疑则在于,道德心性一旦处于统摄地位,其最终是不能实现理性的架构。所以想请问先生,13年后的今天,对于当时的观点还是否需要补充说明?
成中英(以下简称“成”):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表述蒋庆政治儒学的立场,你能不能再描述一下。
王:我认为蒋先生主要讲社会秩序的建构不能纯粹依托于形而下的个体理念,它需要立本于一个形而上的宗教,或者说必须寻找儒家哲学的正当性依据,将秩序跟天道运行结合起来。
成:我不知道当初是否谈到对儒学的基本了解的问题,因为他(蒋庆)对儒学了解跟我对儒学的了解可能有点不同,认为形而上和形而下是分离的,那就是说我们要把形而上的天道世俗化成为人道,好像就是要放弃天道,可是天道和人道不应该分开,人道里本来就有天道,天命之谓性,所以人性当然是天道不可脱离的一个基础,形而上是看不见的一种存在,但并非就意味着可以脱离中国的现实或人类发展的过程,形而上和形而下虽然是两个层面,但却是不能分开的,形而上理念要落实为气,气也可以上升为道,气又能够转化为人的生命的意义。道并不能离开人的行为,道要表示为道德的行动,从这一意义看,我认为形上形下从未分开,我觉得反而是他将此分开了。
道也可以是形而下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群体的组织方式。实现政治的方式有很多种,不能说自由民主一定是世俗化,自由民主有两个意义,一个从自由的角度讲是使人们更有能力来面对道,每个人可以选择他自己的信仰,我们信仰需要保护即政治制度上必须受到尊重,而从政治制度看,则须保护人的自由,但是制度应该能够开发人的能力,形成人的主体性,成就至善的目标。至善的目标一定要合乎人心中的天道,当然民主是否为最好的方式,我始终认为,在中国的制度层面上,民主就是实现民本的一种方式,民本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从这里也可看到,道是天命;而就人的行为而言,则是民命。所以天命即是民命,民命离不开天命,任何人的感情都是跟他的天性有关联的,都是人的行为的基础,所以天道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道,把神圣化和世俗化分开正是西方人的问题,我认为蒋庆正好自己不自觉的融入神圣化和世俗化问题当中,希望将两者结合起来,甚至希望用神圣化来主宰世俗化,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容易导向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当然,在儒学里面,孔孟是把天道和人道结合在一起的,孔子讲人能弘道,道不离人,只有到了董仲舒,为了要控制当时的局面,因为秦火之后,人民需要休息,国家需要整顿,那时才产生所谓的政治儒学,所以依经学言政治,我也不反对,目的即在于实现人之为人的所谓五伦,并不是将三纲归入永恒。这是一种内在的关系。父子也是一样,并不是子必须听从父,而是一种协商,君臣也是一样,是一种协商,以大局为重,以共同目标为重,从这一层面来讲,是不是要走西方的民主道路,我以为其实不然,应该是磋商式,达成相互间的了解,形成共同的目标,是一种民本为主的民主。
我认为蒋庆的政治儒学是对儒学的误解,可能会导向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尤其把世俗化和神圣化分开来谈,仍然没有掌握中国儒学的基本价值。从西方来讲,我们不需要向西方自由主义的道路走,自由的含义即不受权威的压迫,宗教的权威也是一样,即谁有权威就必须听从谁。而只有透过理性说服和教化——我觉得从来就不需要信仰权威——经过理性思考的过程,共同来沟通或解决信仰问题,西方就较为接近我的说法,即每个人都可以谈宗教,宗教教义可以集体发挥,但是宗教不要跟政治结合,如果跟权力架构结合儿,即可能绑住人的生命,拘束了人的潜能,限制人的价值的发展,这点我觉得不是儒家的理路,也不是仁爱的。
王: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儒学复兴与现代国家建设》中认为儒家思想能够建构一种相对温和的“儒家民族主义”,所以中国的基本问题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文化融合的问题。而关于如何建立的问题,先生认为仅仅通过理性是不够的,只有通过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才能出现国家建设的真正目的,这是把普遍的道德修养看作国内和国际间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谐化的基础。同时,在先生的其他谈话中,先生明确反对把儒家“天”的概念超验化,也不赞成内圣外王把某些人神圣化。然而这样似乎有一种趋势,即儒家的道德理念在坊间被演化成类似八荣八耻、以人为本这类口号。因此,如果革除传统儒家立本的宗教化因素,儒家思想是否能真正建立社会秩序?而正视民国以来经学史学化浪潮下的祛魅事实,先生所说的儒家民族主义有无可能建立?
成:我认为神圣性其实并没有在现实社会中真正消失,儒学讲天道,天地人三才之道,便是从源反本。中国文化有一源头活水,便是融合人的认识和天的地位,天是一种创造力,拥有弥久弥新,日新又新的能力,这就是天道。当然,也可形象化称其为天,天不是人格化的上帝,我不知道宗教化是否一定要有对象化的上帝。上帝毕竟跟天不完全一样,天没有人格化的对象在里面,是一个形象化的存在,事实上天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力,地变成权力的象征,一种主宰性的对象,一种独立的位格或是人格。天之所以为天,是由于天本来就高,能做应该做的事情,代表一个基本的方式,所以能转化为一个对象,我说的就是一个统治者,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而不是把他的存在作为价值标准,是以他的存在带领价值,而不是他的存在就是价值。祛魅是西方术语,过分强调上帝的权威,如同霍布斯所说的神权,一切来自上帝,上帝是绝对权威,上帝可以不理性,可以随意。现的在大家喜欢谈论天道,然而天道在儒家看来,不完全是理性的存在,而是人性的基础,是人性善的根源,所以它不一定表现为理性,而是意识性的存在,怎么能否定其没有神性魅力呢?一般人没办法去思考,他就相信天道或上帝,以此作为行为的标准或感情依托的载体,那当然可以理解。然而作为知识分子或建构政治制度,却不能视其为真正实际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虚构的说辞。为什么道教要祛魅呢,就是因为神道设教太强烈了,人可以用神道设教来掩盖自己不透明的目标,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但我们不否定大众需要某种神道设教的权威,需要道德的权威,需要历史的权威,需要他们可以信赖的权威,需要各种基于亲情的权威等,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这一切变成教条——机械的、逻辑的、法律的、道德规则的教条——它背后仍有一种人性的力量,所以人性里面能够透露出一种神圣的创造力,能够使人感受到自己就在其中,最后目标则是使自己成为的道德存在或道德的主宰,因而不需要再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控制和统治这一切。所以我不太赞成回到神学统治,拿宗教来作为说辞,这是对宗教本身也不理解,宗教是一种信仰,信仰是从人性深处发出的道德感和生命感。
二、哲学必须关注生活的需要
王:政治秩序的重建——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始终都是儒家特别是新儒家关心的命题,按照牟宗三先生等新儒学大师的理论,儒家对于现代政治秩序的重构,依托于上智者对儒学心性、天道的把握,再经由“道德坎陷”来实现上学的下达。然而,即使搁置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间的对立,随着公民思维的逐渐觉醒,一方面知识分子对于春秋制合法性产生质疑,不会接受“以元统天、立元正始”的儒家春秋大一统传统政治理念。一方面下层民众的政治心态又尚未从圣王天子心态转换出来,新儒家如果要参与今日的政治秩序建构,那么要如何应对这种断裂的困局?
成:我是最早反对牟宗三这一说法的,人应该追求德性,人之为人,他要有仁道,要知仁、讲义、重理。重要的是成就理之后,则要重建仁义社会,当然从论语到孟子这条路,行仁道来感通人心之后才能王天下,所以仁政和王天下是从道的基础去发展出的政治含义,建立国家与建立政治是个人修身与治国平天合为一体的,并不是说治国平天下每一步骤都有向外推广的过程,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王者,只是说有能力去作为王者。所以内圣的内德是基于对外在的了解,是以知识作基础的德,而知识是以德作基础的知识,道德和知识是相互依存发展出来。能不能够成为王者,则是要不断推广外显而感动人心。以孟子来说,是要说服一些当权者,孔子也是一样,他要说服诸侯,但是都不成功,所以需要继续努力。从荀子来看,圣人治理卓越,他就是王者了,王者能够行王道,他便是王者,而若不能行王道,治理不卓越,便不是王者。可见这里得不出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道理,内圣不能保证外王,二者之间不一定必然关联。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一定就有事实上足可统治他人的能力。统治和治理要考虑到各种外在的因素,如经济的发展使人向心,或者说能提供发展的机会。除非他已经有王道,不然他就是平民,他就是内圣,怎样才能开出外王?他是个平民,他要外王,他只能有两种方式,他只能打天下或建立政党,政治是一种权力,是要在现实当中实现的,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内圣开不出新外王。
作为一个圣人,如宋明诸儒所强调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当然有可能感动王者,自己则不一定能成为王者。他提供了治国之道,而知识也好,道德也好,他们之间是有相互依存的关系的,但与权力相联则是另外一层关系。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只能说每个人都能做到内圣。内圣还有一个意义,即每个人都能够自我管理,天下不需要王,大家都是君子,君子意思就是能够自我管理的人,君子都能自我管理,何须别人管理,政治的最大目标就是管理他人,使他人能够管理自己——庶之、富之、教之。我完全不同意牟宗三的说法,但却是新新儒家的思考。所以我反对坎陷的看法,有了良知,再去坎陷,坎陷以后怎么办,他可能去学习科学知识,但事实上人的发展是内外并进的,一方面人要学习做人,一方面人要学习知识,两者是相容的。并不是学了以后再坎陷,那坎陷就成为霸道了。这个说法排除了二元论的论调。当然,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内圣,内圣之后再将其放在一边,再学知识而成为统治者,第三步又回归内圣。但现在的管理并不是直接运用德性,而是以自己的德性作为标准,作为行为的模范,用感动的方式而非统治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是治理的问题,不能不依靠外在的知识。从人跟就人的需要来讲,要懂得别人需要什么,懂得民间需要什么,为政必须以民为本,不能不有实际的观察,为民着想,身先士卒,德性必然会支持这种行为,这就是我的看法。
中国人从夏、商、周以来便有重视百姓的传统,重视民心怎么表达,一方面自己考察他们如何表达,一方面透过形式逻辑来表达,过去讲要听人说话,经过长期教化之后,民众也可以表达他们诉求,进而参与政治活动,即从民本到参与再到民主,就是孔子说的庶之、富之、教之,教之之后让他们来参与,这也是一套治理的学问。我们参照西方的经验,西方从专制走向民主开放,也是因为认识到普遍民众的诉求,看到他们管理能力的增强,让他们参加政治而成为议会,所以政治是为了生活的需要,并不是彰显宗教的权威。由于生活总会有个体难以预料应对的行为,如集体防卫,灾难救护,大型工程等,所以必须靠政府的管理。可见政治不是维护宗教的权威,也不需要宗教的权威来实现政治的力量。就在于如何实现以民为本的天命,而民命即是天命,所以我们可以呼吁神圣的意义,但按照这种说法,人作为君子,应该是独立思考的人,独立思考的人则应免于恐惧,免于他人的胁迫,独立思考能帮助人更好地处理或管理。虽然这是启蒙时代的思考,但启蒙又将理性放大为一切,忽视人们独立思考,所以要考虑人民的需要,重视生活的需要,并不是一切都理性化,而是理性只是工具,帮助人实现人的生存价值、生活价值、情感价值等。这就是我的政治哲学,不能套用到其他理论之中。
王:您曾经提到中国文化的世界定位问题,认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定位在显示其对整体性的尊崇,对直接经验的信赖和对关系与过程的依持,以及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但无论是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面对中国文化,都存在一个自我与他者应对、接洽的问题。请问您以为具体应当以何种方式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全球承受的价值?
成:我想只能透过现代语言的论述来说明或沟通,我称为对话的逻辑,或对话的文明。因为相互之间不能了解的话,对话的方式,至少现代经过人类长时间的冲击和矛盾,产生了互不了解的隔阂,我们会由于误解和自大,加上科技的发展,不少国家拥有了核子武器,一旦对地球进行毁灭式破坏——科技文明的破坏力大于创造力,创造需要很大的力量投入,毁灭则十分快速——后果就不堪设想。而人类今天已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大家应该理性地思考和对话。
合理的认识逐渐显现,理性实际就是沟通的基本条件。语言可以通过翻译,形成共同所指,达致共同意义的了解。在这两大前提下,我们知道自己的意愿是什么,想法是什么,对象是什么,通过长期的磨合,进入到沟通的模拟状态。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沟通还来自历史所积累和释放出来的感情素,来自历史的主张及其与之相应的深层意义和繁荣,所以问题必须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中国首先要有自信,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有没有普世价值,今天讲普世价值有主观的两个基础,并不是说普世价值就是普世价值,首先自己要能够认为它是普世价值,要有普世性,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客观的说,它能运用到人的行为之中并产生具体的作用,有了这个主观的基础,则通过沟通使其成为普世价值,所以普世价值是现象的问题,是构建的过程,是求证的问题。我不认为有天生的先验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必须产生实际的作用,如普世到什么程度,特殊情况下是否存在不可用的成分,必须客观地、逻辑地、分析地来探讨,而不能空洞地讲,只有透过长期的沟通、发展、教化的实践过程,才能达成与普世价值有关的共识。
三、研习哲学必须关注价值感的获得
王:中国哲学的重建和重新诠释一直是您关心的问题,而一方面,中国哲学与文化重建显然有待遇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另一方面,哲学需要关心活生生的人与现实,如您所说的“对生活本身发生作用。”面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经典的诠释应当指向何方,关注和解决哪些现实问题?比如价值的崩塌、意义的虚无、人的孤独无依等问题,中国哲学与文化有何种资源来应对,或者说应该如何应对?
成:中国哲学当然需要重新建构和重新诠释,我不是提出本体诠释吗,现代诠释是进行经典诠释,现代诠释透过历史寻找训诂的根据和传统的说法,来将其整合为一套说明,重新发挥经典的新义,彰显经典做时代意义,包括其当代价值,我觉得不是最深刻的,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了解历史,不止是透过历史去了解经典,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了解来解决生活问题,必须对经典有更深层的全面的认识,这叫做本体诠释。只有了解其深层意义及根本体系及所指的方向,才能对实际的生活产生作用,才能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这就在于我们自己作为人不断反省,不断学习,主要的仍是免于无知和愚昧。过去赞同有他的需要,现在赞同则只能成为概念游戏,所以除了依据过去的活动方式作为参考外,必须要以科学知识作为基础才能解决问题——不管是经济问题还是生态问题,知识系统的问题、伦理问题、艺术创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站在已有的知识上,来进行本体诠释,解决意义何在的问题,要抓住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做些什么,了解问题的所以然,了解其产生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我们必须掌握自己,但首先要肯定自己的价值目标。中国文化是有他的价值目标和意义的。我们要有内在的思考,内在的信念,我们的知识和信念融合在一起,就不单纯是信念,而更是一种内在精神,是活生生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诠释或注解而已。这就不会产生价值崩溃的问题,而是价值的建立;也不会产生所谓虚无和失落,内心很充实,怎会有孤独无依的问题。孤独无依是内在的空虚,而只有历史的爬梳才是空虚化。存在是活生生的,对未来和历史不断探寻意义,不断建立信心,如果仅将其视为历史上的依托,没有自己的存在感,没有自己存在的方向,那你当然是空虚的,所以中国哲学始终在建立内在的价值标准,我想孔子一生也是不断思考人道是如何表现在人的生活中的,教导子弟应该做什么,无论堕三都,或作中都宰、大司马,都是要发展社会生活,推进此儒家的精神,儒家并不是让你苟且度日,或爬梳历史,或是找一个上帝的权威来依托,或利用什么权威来忽悠他人,所以孔子才讲知人知彼知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王:心性儒学是儒学的重心所在,然而心性体认是一种高度内省的道德实践,难以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因此在儒学传统中一直存在汉、宋儒学的虚实之辩。关于生命实践的学问,是道德的形上学,然而学术史中一直都存在着虚、实的争辩,其实对于我们学生也长期有这样的困扰,便是如今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应广博闻见之知,还是应直接契入精神之大体培养德性。所以想借这个机会请教成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希望依据您早年进学的经历,给我们谈谈读书治学的方法与次第。
成:我说的心性儒学,都是我独立思考的,不能认为我在附和哪一家.,我是一个独立的哲学家,是把心性儒学融化在我心中来发言的。心、性、意志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人是跟外在的世界和人的交往中来对自己认知的,所谓知己知彼很重要,能够使自己有目的感,有自己的信念,有价值感,然后在行为上有所依持,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当然,所谓行为规范,从学问方面讲,便是古代的经典经过我的生命体验,已燃烧成为一种活动的能量,成为我的思想的一部分,达到这一层次,就是六经注我了,就是一个独立的顶天立地的人了。在这一意义上,所谓汉儒、宋儒之争,其实不是根本问题。不过,宋儒显然是要找寻这宇宙与生命共有的精神的,从张载、周敦颐、二程到阳明,都在找寻人的立身之道,寻找本体精神和主宰自己生命的主体意识。朱子讲尊德性与道问学,阳明谈良知,良知是基于知识而产生的内在价值观,否则便是空洞的良知,所以阳明学仍以致知作为良知说的基础,没有知识则开不出自己的内在标准。而汉儒去古未远,本体精神还在,通过董仲舒、郑康成,他们是抓住了根本的精神的。也就是说,凭借前人的注疏,学者们更容易把握经义,我並没有否定他们。但是到了清代,依附汉儒来做训诂考释,实际他们并非真正的汉儒,所以我认为要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建立饱含创造性的德性。
说到治学,我还是用中庸里那句话,必须博学之,书是要多读的。例如搞历史,哲学也要读一点,至少得读一本好的哲学导论。
王:先生有没有专门推荐的著述?
成:非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比较中立,不要马上切入意识形态,现在因为慢慢解冻开放,主要在于能不能深刻思考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功用,而本体的东西,还是必须通过中国哲学来体认。知识不能不有论证的形式,不能不有理性的分析,所以一定要选读现在的哲学概论。我认为最好找一本翻译著述,当然随便找一本也不行,比如卢梭的已经过时,它只代表一门一派,现在要开放一点,比如政治哲学,伦理哲学,知识哲学都要有跟上时代的论述,跟现在哲学家的思考联系起来,要找这样一本书来认真研读。伦理学方面的书,我想一定要看。伦理学的概念要加深,因为伦理学是关系人类的。从历史了解西方,一定要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以后反观孔孟,则会有新的思维方式。而现代伦理学,一些经典型的典籍,比如论自由,论功利主义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定要读。正义问题是根本问题,我认为都可以看看。
王:请问先生经学方面的读书门径,比如清儒和汉儒的注疏该如何抉择,而您当年学习时是如何入手的?
成:四书五经当然都要看,我一开始是学《易》学和《尚书》《诗经》我是慢慢阅读,然后对诗教或诗学有一种特殊的感受.从哲学思考来看,我觉得还是《易》学与《尚书》最重要,尽管二者都很难。能把四书融会贯通就不错了。从方法工具看,容易了解的就选。有的版本同时包含了朱注和汉儒的注,从经学或理学的观点说明道理,汉宋儒都说得很清楚,所以朱注并非太重要性。《周易本义》也是朱注,五经都必须重视。《左传》和《公羊传》都要参考。《左传》《国语》都隐藏着一些孔子的基本看法,可以从中平章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而《公羊》则超越历史,将历史推向美好的境地,所以有三世之说。当然,将其视为历史,也不太完整,它更是历史哲学,需要我们很好地发挥出来。历史的功能和目标究竟何在?我们并没有认真探讨,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经典的深切体会与认识,否则就走到西学去了,我觉得这一点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四、严肃的哲学思考有裨于社会的进步
王: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有所谓思想淡出,学术繁荣的提法,王元化会担忧文化的崩溃,包括新民师也是这样。他们都担忧学术越来越走向专门化、技术化。学术仅仅关心知识,而不再关心价值。我们年轻人进入学术生活,也常常会遇到知识与德性之间张力难以调和、平衡的问题。学问的目的何在,价值何在,究竟什么样的学术才是好的?
成:这个话题很重要,我们可以引用戴东原的说法来回答。戴东原是训诂家,很重视历史文献考据弄。考据是很有意思的,必须说明真相。例如天文方面的知识,测量太阳的历法,都可借用现代科学知识,对古人的文本进行考据。可见考据的作用在于增加知识,或摸清历史的真想。当然,传统的历史学家,都偏向史的陈述,引经据典说明历史事实,弄清文字的解释意义,可能也会涉及科学方面的问题。运用考据法还原历史真想,如顾颉刚的古史即派,就做了大量的考据工作。历史需要考证,收集资料,但即使事情都考证清楚了,对人的生命又有什么帮助呢?所以戴东原说知识之最终结果是要了解道理,他晚年写《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即通过知识的考证和文本的考证,最终明白到底什么是道,什么是人生追寻的目标和价值,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所在,所以从戴东原的观点看,他既重视考证的学术,也重视思想的学问,是较能说明问题的典型。
现代人如何呢?现代人只谈学术不谈道,是想逃避到学术中去,过平稳安定的生活,无非是找到一个研究项目,保证客观的知识的追求,容易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从西方的视野来看,自然科学不能不作为独立的领域来展开研究,而人文学科科学化以后,便完全成为学术,尤其是文史哲,都变成了史,将史当成史料来考证陈述,所以今天的时代不是哲学的时代,不是哲学家思考的时代,是需要安全稳定生活的时代。至于哲学的信条,因为生活环境可以使人们不需要去直接面对问题,大家也都不愿意去面对问题。但这不是问题不重要,而是自己不敢面对,甚至以为不应该面对。也就是说,学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出严重的病态。而思想之所以淡出,是因为思想受到了钳制和压迫,思想得不到任何的真理,思想必须围绕意识形态,思想没有火花,也没能够启蒙的思想家,没有真正的儒道者。
思想问题太复杂了,思想问题也太严重了,疲于思考,思考的结果,人们居然认为它没有用,得不到必要的尊重,也无法检验是否为真,种种社会因素导致了时代的变乱。这其实是一个如何辨认哲学的问题。社会认为哲学不务实际,不是当急之务,因为已经有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指导了。哲学的思考其实也要还原真实,找到真实的性命来作为行为的依托,来作为启明人心的智慧。而回避了这些问题,所谓哲学思想就淡化了。这是从社会原因来讲,并非否定思想的重要性。进一步再分析,假如思想完全淡化,从事学术必然涉及一大堆客观事实,而到底为什么要研究,甚至基本的价值标准都没有,便难免不会盲从。何况即便是大时代——各种文化传统彼此互尊的时代——别人有他行动的追求和哲学的思考,而我们却没有,只是一个被动者,犹如奴性的生活者,没有思想便等于没有灵魂,一派苍白,虽然拥有一大堆故纸堆,但不能做出是非善恶的选择,问题就很严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个人都如此,则国家和民族便缺乏文化生命,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开拓,没有独立生活的开创,没有自己的价值,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去依托别人吗?完全不要生活,不要思想,只是遵从习惯,这是极大的遗憾,也是为中国文化失落的一大原因。
中国近年来大讲国学,即便官员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如果你跟西方人交往,面对
全球化的背景,对方会有一种宗教主张,会有个人的伦理主张,需要回答什么才是是与非,然而中国人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有没有自己的立场来谈论是非,有没有道德的观点来解决行为的方向,能不能展示社会的守衡发展之道,能不能参与国际立法,都值得我们深思或考虑。如果别人讲世界伦理应该是什么,环境应该如何保护,就像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不能说明为什么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就应该彻底反思失语的历史原因。这涉及历史正义、战争正义,因此应该让我们的外交官来接受培训,让其对中西哲学思想有所认识,他们在外交上就能发挥道德力量,不仅认识到思想的力量,而且认识到宇宙的真理,就能更好地解决纷争或主权问题。
学术繁荣而思想淡出,是一种悲叹,是一种描述,正好到出问题之所在,而不是对思想的贬低。别人以为思想没有意义了,不如去做纯粹的历史家吧。这是不对的。兴趣所在并不能决定基本问题之所在,一定要关注基本的问题,学术本来就是高处不胜寒的,它高高在上,不应落到下面,关键时候才能有用。我们需要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思维能力、更多的知识背景,才能充分地思考重大问题,并让人感到震动,然后才能引领下一代。这需要培植,不能因为艰难就放弃哲学思辨。哲学的真正意义是将入引入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哲学思考对我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