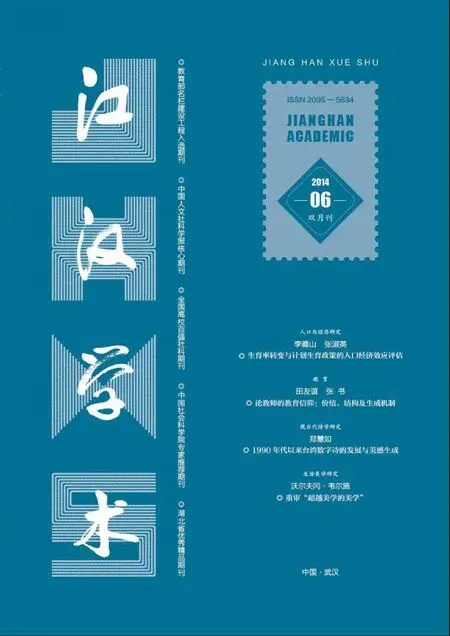用方言朝圣
——刘醒龙创作的语言维度
但红光
(江汉大学 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武汉 430056)
用方言朝圣
——刘醒龙创作的语言维度
但红光
(江汉大学 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武汉 430056)
刘醒龙创作有着浓烈的“圣地”情结,在其不同阶段的创作中,“圣地”所对应的空间并不完全相同。方言,作为“圣地”空间的言说方式被一同“圣化”,贯串了其创作的各个阶段,且因“圣”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初期作家用古奥、生僻的名词性方言指称大别山区古老神秘的风物,深具楚文化神奇、怪诞的巫风特色;第二阶段,作家用明白晓畅的方言书写民间圣贤和底层日常生活;第三阶段,作家通过方言与韵文结合来凸显仁善的圣贤文化空间。在方言“圣化”之外,作家对乡村风物和艺术种类也一并作出了高下区分,突出了民间和本土的清雅与脱俗,并将其“方言化”。从本质上讲,刘醒龙的“圣”实为对普通话所代表的流行文化霸权的挑战,是他力图纠正社会浮华,试图回归高贵、优雅、经典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努力。
刘醒龙;方言;朝圣;本土主义
刘醒龙的创作有着浓烈的“圣地”情结。他说:“一个‘圣’字,解开了我心中郁积了八百年的情结。”[1]鄂 东罗田 的胜利 小镇[2]、黄梅 的香炉山[3]、安徽霍山 的 漫 水 河 镇[4]等,都 是 刘 醒 龙 生 命 中 的“圣地”。《威风凛凛》中的西河镇,《凤凰琴》和《天行者》中的界岭,《圣天门口》中的天门口小镇等都是刘醒龙所着力营造的神圣、高贵、优雅的精神家园。他的“圣地”虽无明确所指,但显然不是作家久居的武汉等现代城市场域,而是大体位于作家早年的家园所在地——鄂东大别山区。
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思想是同构的,海德格尔进一步将其阐发为“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刘醒龙在圣地营造中,语言始终是重要的维度,而其中特色鲜明的鄂东方言更被刘醒龙称为“母语”[5],在对抗城市文明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刘醒龙的圣地空间
刘醒龙说:“只有相信文学是神圣的作家才能成为好作家。”[6]他不仅相信文学神圣,还通过文学来书写神圣、指证神圣。在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中,刘醒龙叙述了艺术家陈桦从大城市回归曾插队的大别山区寻求精神安慰的故事。在曾经憎恶的贫穷落后山区,女主人公被奉献山村的邱光点亮灵魂后,才找到了情感归依和艺术源泉,真正意识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实现地不在繁华、冷漠的城市,而在贫穷、神秘的山村。这实际是一个找寻精神栖居空间的故事,极具隐喻意义地奠定了刘醒龙此后的创作主题——边缘人(外来者)的故事、个体与环境的冲突,也即精神家园的寻找与营造。在这一系列充满冲突和对峙的故事中,有悲剧意味的大别山乡村始终是最后的归宿。
刘醒龙及其评论者们都倾向于将其作品以《威风凛凛》和《致雪弗兰》为 界分成 三个阶 段[7]:第一阶段代表作品为“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第二阶段代表作为《凤凰琴》《分享艰难》和《秋风醉了》等,第三阶段代表作为《圣天门口》《天行者》。这三个阶段的作品都是关于空间及营造圣地空间的故事。
在“大别山之谜”系列作品中,作者展示了大别山区景物的神奇和神秘。古老大别山的神秘森林、河流、山寨都是传奇,是上天所赐的地域瑰宝。在《雪婆婆的黑森林》中,向往了神秘黑森林 17年的阿波罗在入伍前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了森林深处。《灵狄》中的灵兽、《牛背脊骨》中的老树、《两河口》中的铁砂堤岸、《大水西河》中的花桥、西河岸边的石牛、《鸡笼》中的鸡笼都是让刘醒龙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敬畏了一辈子并为之殉葬的大别山圣物。这种对大别山器物的圣化,既是对大别山空间的神圣化,也是对古老文化传承的神圣化。其时,适逢“寻根文学”盛行,敬畏和梳理“文化的根”的必要使刘醒龙和许多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景、物的古老化、神秘化和怪诞化书写来营造文化圣地。
对于自己第一阶段作品,刘醒龙并不满意,在其后也很少提及。在其创作的第二阶段,刘醒龙变造境为平实写人,写人在险恶环境中的坚贞与高洁,境退居到了幕后。《威风凛凛》中的西河镇、《凤凰琴》中的界岭、《村支书》中的望天畈村、《大树还小》中的垸、《暮时课诵》中的灵山寺都平淡无奇,奇的是主人公的坚贞与高洁。赵长子在举世皆浊的西河镇听任肉体遭受种种折磨和欺侮,坚持着精神的引导,保有了灵魂的洁净,成为镇上的“圣人”;《凤凰琴》中的界岭小学教师们、《村支书》中望天畈的方建国、《大树还小》中的秦老四、《暮时课诵》中笃信菩萨的村妇等,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窘迫的人际圈层中坚持奉献、坚持自我操守。在这些作品中,恶劣环境因这些“圣人”的存在而圣化,成为了凸显“圣人”的神圣空间。
第三阶段,刘醒龙直接以“圣”为题,以小山村来指代政治社会,通过小山村的“圣化”故事表达了使政治社会空间纯净、和谐的理想。这一理想,在《圣天门口》中是通过优雅、高贵的爱和宽容来化解家族矛盾、党派纷争和情欲纠葛;在《弥天》中,通过女性温馨的爱来化解政治的残酷,温暖成长的心灵;在《天行者》中,通过奉献和感动来实现对环境和他人的感化。
刘醒龙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自己对故乡、对故乡历史、对曾经的生活和对小人物的“敬畏感”①。也许正是这种广泛的敬畏感使他写出了一个个以大别山故乡为原型的“圣地故事”,表达了作家对高贵的精神、优雅的行为、坚贞高洁的圣贤的呼唤,对和谐温馨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的渴盼,对深邃的古典文化回归的渴盼和朝拜。
二、被“圣化”的鄂东方言
和大多数 1980年代中后期走上文坛的作家一样,刘醒龙对作品语言有着清醒的自觉②,在写作的不同阶段,其作品的语言风格大为不同。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新批评学派也认为,语言作为作家思想的传达形式,并非死的工具,而是作品“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也多次谈到“道”与“言”的对应关系。尽管在不同阶段,刘醒龙的语言风格变化明显,但大量使用方言始终是其作品的语言特色。在刘醒龙有关鄂东大别山故乡的“圣地”书写中,鄂东方言作为重要的符号被“圣化”。
在《晓得中原雅音》中,刘醒龙称湖北方言为“母语”[5]、“艺术品”。这种对“母语”的独特定位,表明方言在其心中的地位,能带给人“高贵、神奇、美丽的愉悦”。而与方言相对的主流用语,刘醒龙认为:“写小说时,我有一道心理防线,从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语为主要因素的各种粗鄙的流行用语。无论它如何甚嚣尘上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亲近感和时髦相。我还会喋喋不休地诘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升华既有的民间人文精髓本来就是大错,那些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制造文化垃圾的行为,就应该挨天堂里老祖宗的鞭挞了。不记得是谁写的,只记得那本书名《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义吧,起码对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8]与通 常 所 认 为 的方言粗 鄙、浅 白、不 便 沟通,书面普通话典雅、有内涵、便于交流不同,刘醒龙从文化角度将二者的地位彻底颠覆。他通过对粗鄙文化垃圾的贬斥,来凸显方言的地位,表达了对现代浅薄的流行文化的拒斥,如其推崇的书名“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彰显了他渴盼文化经典的赤子之心。
刘醒龙说:“一滴唾沫,哪怕它来自上帝的舌尖,也还是一滴唾沫,不能当成是普降天下的甘霖。砰然倒地的修女,正如那些深藏于民间的珠玑般的方言。在现代信息狂潮肆无忌惮地泛滥之际,那些曾经不被注意的方言,反而显著地提高了自身的重要性。绵绵不绝的方言是一种经典。稍加整理,就能透出神采飞扬的韵律。又因为基因遗传及文化熏陶等要素,精彩方言和方言精华,会使我们随着潜意识沉入博 大 的 民间叙事和 深 远 的 人 文 理 想 中。”[9]在与上帝、修女的类比中,方言虽然是“砰然倒地的修女”,但无损其神圣,它是高贵、经典、博大、民间、深远的象征。王鸿生认为,好的小说语言并不需要眼花缭乱地展示丰富、博杂与时髦的语词,“这样的语言是瘫痪的语言,无根的语言,没有故乡的语言。”好的语言应该有“生命的质感和自然的气息”,“焕发出某种经由地域文化长期浸润而形成的韵致和自然的气息”[10]。刘醒龙正是通过方言来表达了“好语言”的构想,他将方言提到神圣的地位,以拒斥文学中的语言炫技、信息比拼及不关痛痒的浅层书写,使语言配合作品中的神圣指称,一起抵达其心目中的“圣”。
三、刘醒龙作品中的方言使用
刘醒龙作品的语言在不同阶段风格迥异,虽然风格不同,但对方言的重视是始终如一的。他说“我写作的时候,用武汉话讲还是‘弯管子’(不标准)普通话,不是标准的,但写作的时候想到的话都是方言”[11],“从一九九 九 年 至 今,我用 六 年 时 间 来写作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每天都用母语与上个世纪的一群人物进行交流”[5]。他在写作中惯于使用典型方言词语,且始终如一地服务于作家“朝圣”的目的,虽然其不同时期的“圣”并不相同。
在第一阶段,刘醒龙通过对大别山古老山寨的描写,意图表现山寨神秘、古老、神奇的文化之根的意境和传统文化的“优根性”。在使用方言词汇时,他多选用古奥、怪诞的方言名词,如称老鼠为“高客”,称獐子为“灵狄”,称银杏为“鸭掌树”,称山为“老祖母山”“牛背脊骨”“倒挂金钩”,其他如“山魈”“黑蟒”“瘸子猫”“撞山”“招魂”“阴阳大师”……这些词语充满怪诞、神秘、浪漫的色彩,再现了楚文化神奇、瑰丽和天人合一的巫风神韵。这种“选择性”的方言罗列喧宾夺主地成了文章的主要关注点,如在《鸭掌树》《灵狄》《倒挂金钩》《牛背脊骨》中,作家甚至直接以这种怪诞的方言作为作品标题,并将文章的重心放在对怪诞景物的烘托上,以至于忽略了对故事情节的经营和对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但不可否认,作家在“文化寻根”和地域“圣化”方面表现得十分出色。
王先霈认为刘醒龙第一阶段的作品“强调文学作品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的区别,有时几乎是‘能指自炫’——把选词、造词、词语排列秩序错动的效果看得比词句的含意更加重要”[12]。而第二阶段语言“日见其平畅,文学圈内的人可以读,圈外的人也可以读,文化水平高的人可以读,文化水平偏低的人也可以读。……他一门心思想描述生活的真实状况,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语言,不过是表达的工具罢了,作者无意让语言离开生活内容与作者情感表达,独自向读者暗送秋波”[12]。 这精当地指 出 了刘醒龙作品两个阶段的语言风格和作家的用心之处。在使用方言词汇方面,如果说前一阶段作家是刻意为之、苦心经营,第二阶段则不露痕迹,顺势而为。在这一阶段,作家主要着眼社会现实问题,通过具体事件表现底层社会中不顾个人得失,不随流俗转向,为民请命的脊梁式人物,展示其坚持不屈及卑微的高贵。这些圣雄一样的英雄人物有村支书方建国(《村支书》)、界岭上的教师(《凤凰琴》)、陈老小和高天白(《生命是劳动与仁慈》)、荒村劳模胡长升(《黄昏放牛》)等。在这一阶段,作家使用的方言词汇也回归到现实与日常,如称呼父亲为“父”,称田里粪肥为“火粪”(《火粪飘香》),称牛为“触人佬”(《黄昏放牛》)及“苕”“屙尿”等,极显底层与民间。如果说前一阶段的方言作家有意于古奥与怪诞,此一阶段作家则着力用方言凸显卑微背景下主人公的高洁品格。如映山红的鄂东方言“燕子红”是《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的核心词汇,以最常见的山野植物来指称作者崇敬的翠、陈老小等底层社会支柱。如作者用称呼傻子的“苕”,来称呼那些坚定的、不会随风转舵的“傻子式”人物。在新出版的文集中,刘醒龙干脆将其作品《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更名为《燕子红》[13],他 也 坚 称 《天 行 者》中 自 己 最 喜 爱 并尊敬的人物是“苕妈”,而“苕”是其方言中的对人物的一种敬畏称呼。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作品,刘醒龙使用方言有炫技或刻意的成分,第二阶段他的方言使用则温暖得多,回归到质朴和明朗,立场鲜明地将自己的关怀投向最令他崇敬的底层英雄们。在《关于〈大树还小〉的对话》中,刘醒龙说:“我曾以为中国的农民没有大家所云的话语权利。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他们只是无意于纸上谈兵。所谓大辩不语、大辩无言,用沧海桑田来作表述和表达,应该是大智慧与大哲学。”他此期对平实方言的使用,也出于为底层百姓代言的目的。
对于自己第三阶段使用方言的情况,刘醒龙认为“有人评价说,我在《圣天门口》起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其实不然,常用的方言词汇也就二十来个:汰衣服/掇东西/啸水/阊风/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后日/嘎白/晓得/吊诡/嗍几口,如此等等。这些较为典型的鄂东方言,与当下常用的同义语对比,明显具备高出一筹的优雅。这种特质犹如定海神针,一旦出现,就会让人觉得无所不在。仰仗民间人文底蕴的长篇小说,不可以视流行俗语为至宝”[8],充 分 体 现出此期 使 用 方 言 的 目 的——突出“优雅”和“人文底蕴”。这种“优雅”和“人文底蕴”正是作者从书写底层英雄的坚韧,升华到通过民间社会关系的维持,进而探讨社会和谐的普世课题。在此一阶段,方言更多地和日常生活相关(如“汰衣服”“打野”“肉尕尕”等),代表作者价值观的核心人物也大多为女性,如金子荷、梅外婆、雪柠、蓝小梅等,显示出作者对现实的温柔转向和对民间优雅与高贵的强调。刘醒龙多次谈起童年时期,忘不了受人唾弃的“地主婆”在艰苦环境中的优雅与高贵,而这些,就是他心中的“圣”;《圣天门口》之所以得名,则出自于他对于女儿舞蹈老师日常谢幕礼的感动。[1]这些平和、地域特色鲜明的方言词汇,展示出了作家对普通话社会的文本式改造与融合。何平在《革命地方志·日常性宗教·语言——关于〈圣天门口〉的几个问题》中说:“刘醒龙夹带着韵文的私货,擦亮了方言的蒙垢,回到语言的‘外省’,看来他是准备书写一部和自己心灵相关的小说了。它关于革命的‘地方’,关于俗世的富有宗教渴望的日常生活。”[14]刘醒龙正是通过方言的运用,使读者于俗世日常中感受到高贵圣洁的宗教情怀。
四、方言语境下的“返乡”精神向度
方言属于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方言,并无高下之别。但方言出现在作品中,必定蕴含着作家独特的“意味”。囿于接受范围,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无法普泛化,因此所选方言必定具有典型性。这些精选的方言词汇,在韩少功那里是文化寻根与反思;在张炜那里是回归自然,重拾生命的活力与野性;于范小青是再现苏州风貌;在许多英美文学中是粗俗的象征;对刘醒龙而言,方言的文化符号相对稀薄,它更是文化精神与价值的象征,是精神家园的所指,是脱离低俗与庸常、走入高雅仁善与坚贞的必需品。对刘醒龙而言,方言所对的是普通话所代表的现代城市的低俗,而不是真正的家乡风物,因此,作品中使用哪种方言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他之所以使用鄂东方言只是因为他是鄂东人而已,他在《楚汉思想散》等多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方言,所指也只是普泛的方言。因此,刘醒龙的方言使用意识形态意味明显,化为了乡村对城市的“复仇”——他认为乡村始终处于城市的压制与歧视中,且“复仇”工具不仅限于纯粹的语言,刘醒龙作品中的许多风土、人物和艺术种类也被“方言化”,变得特色鲜明。
在这一方面,他的作品《冒牌城市》最有代表性。在这部作品中,胡家大垸所在镇变成了县级市,胡家大垸村成了城市一部分。为脱去土气,“村”要改为“居委会”,“胡家大垸”要改成“青春大道”,领导也要从外派驻,但村民认为“只有不要祖宗的人才去改地名”,“小庙只供土地神(本姓人)”。相持不下,上级只得让步,“青春大道”改为“古月大道”,上级派了个姓胡的领导,居委会领导也被习惯称作“居(猪)长”。镇改市之后,城市需要树立现代化的雕塑,竞选的结果是农民艺术家捏的“圣女”最为百姓喜欢,领导称之为“神女”,百姓称之为“观音娘娘”,雕像边的意见箱被百姓当作功德箱,纷纷往里捐钱。改市之后,胡家大垸修建了宽敞的公路,但交警与胡姓族人之间不断争夺对道路的控制权,最后公路成了打谷场和放牛场,交通岗成了庙和杂货铺。在这极有喜剧色彩的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中,作者颇有讽刺意味地刻画了城市和现代文明的矫揉造作、故弄玄虚。与此类似的是,在《民歌与狼》中,城 里的洋 派女孩 被称作 “假模假样”[15],乡村女人却自然清新,辫子像山涧的藤条一样荡来荡去;《民歌小屋》中,象征乡村的笛子是天籁之音,所谓高雅的钢琴一点也不文明,学琴的小孩总是挨打;在《天行者》中,乡村的雪是纯洁的,而城市的雪则是肮脏的。
在艺术种类的优劣方面,刘醒龙的“方言化”意识同样突出。在《农民作家》中,刘醒龙谈到民间通俗文学与专业作家的雅文学的分野,作品通过孙仲望戏剧《偷儿记》的曲折修改经历,讽刺了雅文学的做作与脱离群众;在《民歌与狼》中,作家通过民歌的“清雅”来对比流行歌曲的“淫艳”;《冒牌城市》则将高高在上的现代雕塑与民间泥捏菩萨进行对比,讽刺了现代雕塑的自命清高,实为民间泥菩萨的改头换面和故作深沉;在《音乐小屋》中,作家进一步将钢琴与口琴进行类比……无一例外,城市的、现代的艺术形式一律为可笑的,来自民间的艺术形式才是真正自然、有生命力、值得尊重的。毋庸置疑,艺术的高下并不以地域或雅俗区分,刘醒龙的艺术优劣分类理论虽然颇可质疑,但其正是作家“方言朝圣”狂热之下不惜做出的偏激之举——正如鲁迅当年奉告青年不读中国书的行为,也是作家在乡村式微、文坛和社会大众态度模糊氛围中的一种表态。何言宏认为“刘醒龙的本土主义文化认同由于其过分的执拗和偏狭,容易走向一种本土主义的形而上学”[16],这种形而上学也即 本 文 所言的“圣 化”。 对乡村空间、风土人情和艺术种类的圣化,体现了刘醒龙偏执狂般的本土主义情怀,这种对传统文化根系的强力维护举动令人肃然起敬,但传统并非永远正确,我们在打捞民间、维护传统的同时,也必须懂得突破,不要让传统和本土成为前进的绊脚石。
五、结论
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主体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是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映射。刘醒龙创作中的方言取向,并非对鄂东方言的自我吹捧,更不是坐井观天式的一叶障目,其作品存在一种不为大众所注意的隐性对话关系,方言始终有一个潜在的对立面——普通话,世俗空间之外始终存在着作家勾画出的圣地空间。“方言”和“圣地”并无特定所指,“方言”可以指普通话(刘醒龙所言的北京俚语)之外的一切方言,“圣地”可以是一切在价值取向上符合作家个人理念的角落,并不必然是乡村。只是对于深具文化保守主义情怀的刘醒龙而言,甚少被外来快餐文化和现代流俗所浸染的乡村更适于表达其悲悯情怀和古典文化理想。方言也即世代承传的民间的、本土的文化精萃和民族优良精神的代指,而普通话实为流行的垃圾文化的代指。这种处理包含着作者对现代文化的抗争和对文化殖民的恐惧,他寄希望于儒家圣贤文化的回归,挽救正在沦陷的社会关系,回归曾有的脉脉温情。但作者对此并不自信,其作品总免不了蒙上悲情的色彩。在通过方言书写圣贤理想的同时,作者也经历了一个空间神化、个人圣化和社会关系圣化的渐进过程。在新近出版的《蟠虺》中,刘醒龙更是让楚学界泰斗曾本之反复吟咏“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抨击了学术圈的造假和逢迎,表明了他塑造圣贤的主旨并提示了成为圣贤的途径。文中大量出现的楚简成语(如“楚弓楚得”、“楚乙越凫”、“楚璧隋珍”)重申了刘醒龙回归传统和本土、以“方言”朝圣并成圣的主张,只是这一次他走得更远,直接回到了楚文化的源头,并将其上升到了民族兴亡的高度。
注释:
① 在《钢构的故乡》和《一滴水有多深》中,他一再提到对故乡及故乡历史、风物的敬畏;在《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 1期)中,他一再提到自己对人物与命运的敬畏;《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真理不是用鼠标点击出来的》中谈到 “内 心 要 有 一 些 敬 畏 ”:http://www.ccnu.edu.cn/show.php?contentid=2732;《刘 醒 龙:我 对 小 人 物 充 满敬畏》中刘醒龙谈到他对小人物的敬畏感,见《楚天金报》2013年 1月 26日 A26版;《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真理不是用鼠标点击出来的》中谈到“内心要有一些敬畏”。
② 其时正值现代派文学和先锋艺术兴盛的时期,对语言和形式的追求,对许多作家而言,甚至超出作品主题的传达。
[1]王久辛.刘醒龙的“圣”[J].时代文学,2011(7):52.
[2]刘醒龙.后记:失落的小镇[M]//威风凛凛.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3]刘醒龙.乡村弹唱:序[M]//刘醒龙文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4]刘醒龙.无树菩提:序[M]//刘醒龙文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5]刘醒龙.晓得中原雅音[M]//寂寞如重金属.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72.
[6]刘醒龙.生命之上,诗意漫天[J].扬子江评论,2011(6):1.
[7]周新民,刘醒龙.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7(1):62.
[8]周毅,刘醒龙.觉悟——关于《圣天门口》的通信[J].上海文学,2006(8):70.
[9]刘醒龙.小说是什么[J].小说评论,2007(1):72.
[10]刘醒龙.无神的庙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19-120.
[11]新浪读书.实录:刘醒龙称文学还是要靠文学来说话[EB/OL].(2011-09-18).http://book.sina.com.cn/news/a/2011-09-18/2251291053.shtm l.
[12]王先 霈.你 的 位 置 在 哪 里?——致 刘 醒 龙、何 存 中[J].长江文艺,1995(4):64.
[13]刘醒龙.燕子红[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14]何平.革命地方志·日常性宗教·语言——关于《圣天门口》的几个问题[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2).
[15]刘 醒 龙.大 树 还 小[M].北京: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2013:194.
[16]刘醒龙.荆山楚水的本土话语[M]//黄昏放牛.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6.
责任编辑:夏 莹
(E-mail:silvermania@qq.com)
I206.6
A
:1006-6152(2014)06-0100-05
2014-10-20
本 刊 网 址·在 线 期 刊 :http://qks.jhun.edu.cn/jhxs
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重点项目“汉派文学武汉方言运用研究”(2013A01)
但红光,男,湖北赤壁人,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