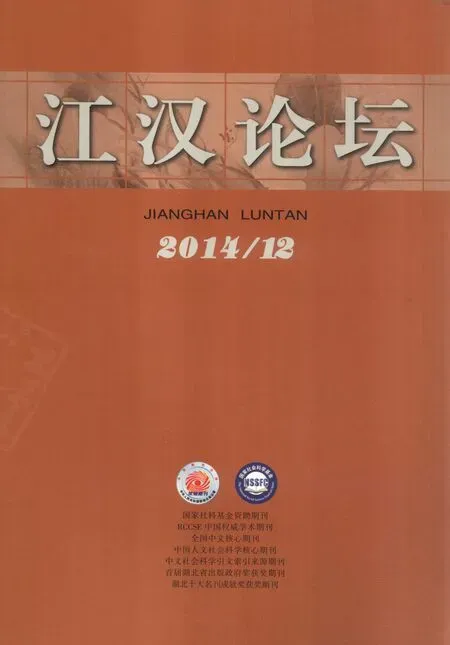儒学与人权:一个建设性的架构
[美]萨姆纳·突维斯文 顾家宁、梁涛译
人权观念,究竟仅仅关联于某种特定的宗教—哲学传统,还是一种跨文化的普适性构想?对此,笔者着重关注以下三个议题:(1)国际人权理念及其正当性如何能在跨文化的道德对话中得到阐释?(2)普适人权理念是否与特殊文化传统必然无法共存?(3)如何回应人权对话中那些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原则碰撞而导致的困难?本文尝试为不同文化间的人权对话发展出一套建设性构架,并以儒家传统为例来证明此种架构的实用价值。
这里,我把人权主要理解为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于1970年代中期生效的两个相关条约(1976年生效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译者注)中得到清晰表述的一系列权利,此外也包含此后签署的相关条约、协议①。
通常认为,这些协议规划了一整套对人权概念特征的典型理解,这种理解的引入起初是极富价值的。人权被理解为一种在道德上(也包括法律上)具有极高优先性的主张与要求,它被理解为对某种境况或财产的要求,这种要求应当为社会所保障,而且为全人类共有,尤其是弱势人群可以利用它来正当地对抗那些特权群体——这些特权群体具有满足人们权利要求的相应责任。借用罗纳德·德沃金(RonaldDworkin)的妙喻,人权好比一张全世界公认的人们借以抗衡特权群体的“王牌”。此外被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人权若要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实用性的优先性要求,那么它就必须被作为一种权利而得到宣示与承认。
在这些人权概念特征的典型性描述之外,我也引入了一些例外情形。下面就让我来举例说明。首先,我们将会看到,存在着一种以发展权与集体性权利为主旨的新一代人权,它强调所有民族与共同体的优先需求,而这些内容为人权的典型描述所排斥。其次,上述典型的人权的描述认定,为了保证权利的有效性,人权的优先性要求必须被视为一种权利。但如此则不免忽略了一些例外情形:在某些特定的传统或社会中,权利并未得到明确宣示,但由于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政府与政治体制本身的系统性需求,人权所指向的生存境况与财产要求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其他方式得到了保障。令我惊讶的是,一些制度与传统虽然缺乏甚至抵制那种作为概念而被明确提出的权利观念,但由人权主题所确认的权利优先性却仍然可以受到保障。
一、经过修正的人权观念及其正当性论证:一个基于历史与实践的进路
为了回应上述问题并发展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架构,我们有必要密切留意那些不同文化传统的代表及其研究者们思考国际人权问题时遇到的关键问题。在很多人眼里,作为西方道德意识象征的人权观念极有可能威胁其它不同文化、宗教与哲学传统中的道德观念并取而代之。这一理解,在跨文化对话与比较伦理学双重意义上都对人权思考的进展构成了严重障碍。回应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消除跨文化交流与研究中的障碍,也使建立一种经过修正的人权理念成为可能。
由此引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作为一种“底线道德”而获得普适性的人权,与根植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那些更具特殊性,同时也更为广泛、丰富的道德观念之间,究竟是何关系?令许多非西方文化背景学者倍感担忧的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人权观往往被当作一种用以衡量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行为合乎道德与否的核心尺度,这就意味着人权理念将毫无疑义地成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他们担心,将核心道德建立在个体权利之上的人权观将会取代那些(比如)更加侧重于群体指向的道德传统,这将意味着那些曾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共存的道德传统的衰亡。由此而产生一个尖锐诘问:这样的替代是否真的意味着全人类的道德进步?抑或毋宁是一种社会原子论主义者画地为牢的短视?
除却这种对以“薄”的权利道德主导并取代丰厚的道德传统的反思,人们也开始质疑那些将人权抬升为一种普适性道德判断标准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假设。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对那些已经过时的道德知识理论(即基础主义foundaionalism)的质疑。这些质疑包括:过于狭隘的人性理解(如利己主义),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片面化理解(原子化个体、商业社会中互不相关的陌生人),剥离了彼此互助、联系、同情之后的冷漠世界。正如很多人断言的那样,人权观念本身或许就建立在对人之本性、群己关系、道德感受等问题的一系列值得怀疑的信念之上。既然如此,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接受这样一种缺乏合理依据、甚至已经不再为很多西方人所接受的的人权观?
然而,这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人权之本质、渊源与功能的误解。尽管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人权只不过是西方特殊的人性论与道德理性假设下的产物,然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世界人权宣言》已在1948年经由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代表们正式协商通过②。显而易见,在人权问题上不同意见的实践性磋商仅仅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而不是道德知识、政治哲学,甚至法理学意义上的理论建构。我们不禁要问:这一进程对人权的本质、地位与合理性问题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人权观念中某些占主导地位的特殊思想的疑虑。
不论效果如何,各种人权宣言、协定、公约的创制者都试图在普遍人权准则与特殊文化传统之间建立联系。此种尝试基于这样的事实:虽然道德具有多样性,文化具有特殊性,然而人们发现,危急情形下,来自不同传统的人们往往会诉诸某些体现人类根本价值的共同信仰。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例,它是二战的历史性产物,这场战争中的种族屠杀等暴行给人类带来了深刻危机。面对这一危机,来自众多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最终断定,那些残暴行为乃为他们各自的传统所共同抵制。经过一系列实践性磋商,他们同意通过人权话语将这种道德判断合为一种统一表达。这里,权利话语的使用诚然是西方法律传统在现代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然而对非人道行为的抵制绝不是西方道德判断下的专利。
类似地,随后在1970年代陆续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同样产生于人类的某种共识,即人们遭受的政治压迫与物质贫瘠,是与诸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道德敏感性不相容的。类似的进程也发生在1979年签署的有关保护妇女权利的公约以及联合国1993年拟定的《保护原住民权利宣言》中。这些人权表达,绝不是要抢占并取代那些不同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丰富的道德教化,相反,它们本身就产生于这些传统的信仰者们所达成的共识,这些共识正是对不同道德传统所共享的那些特定价值的宣示与捍卫。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尽管存在着区别,但它们仍能共享很多真实而重要的道德价值。
在实践道德的基础上,不同文化传统和人权团体的代表或许可以将人权的特殊表达形式视为持有不同价值观的民族之间不断寻求共识的产物,这些价值观被其各自独特的文化—道德传统所拥有。没有哪一种道德传统可以单独构成人权的唯一来源,人权乃是由为不同文化传统所共同珍视的一系列重要的道德期待构成的③。再者,将苦难强加于他人的行为在当前人类生活中并未绝迹,因此我们期待更多的道德共识之达成,期待更多新的人权内容之实现。
以上对人权磋商与共识所做的回溯,意义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一系列人权准则的形成过程。人权问题跨文化共识的形成有其历史,正如BurnsWeston提出的,人权的历史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每一阶段的人权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不断补充与细化④。第一代人权的发端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主要包含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权,同时也涉及某些社会经济权利。1970年代诸多人权公约的签署标志着第二代人权的明确形成,它加入了对社会经济权利的强调,如对财产、服务所享有的权利以及它们的公正分配。第三代人权的主要诉求在于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权力、财富以及那些事关人类命运的共同财产(如生态、和平)。对集体发展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以及在地区与全球范围内更加公平地分配物质与非物质财富的要求与强调,也被加入到民族自决权与发展权中。国际人权界一致认为,这三代人权是同样重要而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值得人们去努力追求。概言之,以上三代人权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其中的某一点可能会因时代需要而受到着重强调。
需指出的是,有一种做法,倾向于将三代人权分别明确对应于特定的人性与群己关系预设,由此,三代人权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观念似乎受到了削弱⑤。Weston将公民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与集体发展权分别与自由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整体性社群哲学相联系⑥。由于不同文化传统都对国际人权观念的形成做出过贡献,这种理解也有一定合理之处,但同样可能导致一些错误认识。事实上,后续出现的人权观不仅为前代人权观补充了新的内容与侧重点,更重要的是,它修正了我们先前对于人权之本质与重要性的一些理解。换言之,国际人权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传统,有助于消解由于吸收不同文化所导致的人权观念之内在非一致性(incoherence)。
举例而言,倘若按照自由个人主义的理解而将公民政治权利明确描述为一种旨在摆脱政治权威压迫的“消极自由”,他们就很可能偏离这样一个事实:自由同样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能力”或“天赋”,它使得人们能够成为政治共同体或社群中活跃而卓越的一员——他们对如何以一种最好的方式在社会中共同生活抱有自己的想法,并试图以之影响他人。公民政治自由与其说指那些消极的“摆脱压迫”的自由——这种消极自由通常与个人主义标榜的那种对彻底自主、离群索居、自私自利、非历史非文化的个体之私人空间的保护相联系——毋宁是指那种社会成员对繁荣社群的积极参与能力,它正与社群主义传统中的道德、政治思想相协调。基于对受剥削阶级与殖民地人民的关注,以社会经济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代人权通过阐明以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为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强调了公民政治权利的积极功能。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一观点背后蕴含的洞见,即公民政治自由对于促进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关键意义。比如,公民政治权利的实践可能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状况改善的动力。由此,超越了以往与第一、二代人权相挂钩的种种哲学传统与理论预设,我们对这两代人权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某种质变,它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理解这两代人权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影响。
在笔者看来,全部三代人权事实上确认并促进了对于个体与群体之较为广泛的赋权,这种赋权对于个体和群体在本地和更大区域的繁荣都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基于这种理解,人权观念在原则上既可与那些强调个人重要性而较为排斥集体的文化传统相协调;同时,也能与那些主张群体优先、强调个体应对群体作出贡献的文化传统相协调。它既吸收了自由个人主义,也融入了社群主义。僵硬的二分法以及对人权历史渊源的静态理解都可能导致对人权观念的误解,因为它忽略了人权观念所具有的灵活性与发展性。
再者,这一历史与实践的人权观有助于我们修正对人权地位与正当性的理解。随着不同文化传统代表的协商与达成一致,人权概念确认了对于个体与群体而言十分关键的保障条件并使之具体化。实际上,人权代表了一种与文化道德人类学之多样性相一致的核心道德和社会价值共识——它是一种基于道德多样性的联合统一体。人权正当性的第一个层次,在于不同的传统在实践道德上的一致性,这些传统共同认可了人权价值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这一认识产生于一种共同的历史经验:假如没有人权保障,人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假如这些人权保障条件在一系列协定与义务中得到履行与实现,人们的生活又将是怎样?有关人权的协定、共识与承诺是公开而公共的:它由全世界各民族缔造,为世界各民族所享有。
人权正当性的第二个层次在于,每一个传统都可以通过将人权的一套道德范畴与其各种特殊的哲学、宗教视野中的人性论、群己观以及道德认识论相协调,从而证明其对人权共识的分享。通过使自身内在于某种文化道德传统,人权的主旨就可能得到证明。比如,它可以是神性的戒律,自然法与自然理性的暗示,不证自明的道德真理,关于国家与公民合理关系的道德假设,特定价值的传承——得益于文化道德传统的多元性,这一清单是开放的。这种人权论证方式的层次区分支撑了如下认识:某一传统中可能内含有一些足以证明其能够融入并遵循国际人权理念的资源,而不必另外生造出一套内在的人权范畴。即便可能缺乏内在的权利观念,但大多数传统中都具有一种内在道德资源,使之至少能够理解国际人权观念中那些主要问题的重要性。这些传统夯实了人权观念的内在道德根基。相较于不得不在各种文化传统中重新创造出一套人权亚传统的做法,这是一种更加新颖,也更为可行的人权论证方式。
这种人权来源与正当性的双层次进路具有诸多优点。最重要的,它抓住了人权正当性论证中的真实状况,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更加细致、合理的方式来认识不同文化道德传统间的异同:它们共享了一系列核心价值,而这些共同价值又分别根植于不同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所造就的丰富多样的道德视域中。尽管如前所述,不同文化传统所包含的人性理论,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话语与认识论之内在多样性必须得到尊重,但我们仍然可以认识到人权准则的独特历史发展历程:它是不同文化传统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影响作用的产物。此外,这一基于历史与实践视野的理解进路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不同的道德文化传统在人权准则的形成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使我们能够正确处理一些关于人权的认识论纷争。人权之证明不应由某一种认识论来独断地完成,其原因恰恰在于人权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在国际层面,它意味着在实践协商中形成的共识;在文化层面,它意味着基于不同文化的多种理解进路之间彼此的宽容。
我并不认为这一双层次理解进路能够解决人权在道德认识论上遇到的所有问题,遑论彻底消解人权普遍性与文化传统特殊性间的紧张。但首先,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这些紧张,从而使跨文化人权对话成为可能,使特定文化立场的学者能够以一种更加从容的态度,务实而真诚地参与到跨文化的国际人权对话中来。其次,在普遍追求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交流而非文化殖民的当代背景下,这种双层次理解进路或许可以帮助文化代言者与人权研究者们去发现并处理一些事关人类福祉的重要问题。最后,从具体问题来看,这一进路或许可以帮助人们将各自内在的文化观念转换成一种在跨文化层次上更具说服力的语言与观点。
二、经修正的人权观念之应用:儒家传统在跨文化人权对话中的角色
为替上述框架的应用开辟道路,我们需要将当前关于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学术论争纳入考量。这一论争主要发生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包含了两种相互竞争的人权观之间旗帜鲜明的论战:一种观点强调人权作为法律准则的普遍性,另一种则强调人权作为道德准则的特殊性。这一层面上的论争主要发生在人权研究者之间。第二个层面上的论争相对间接,主要发生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研究者之间,聚焦于人权是否能与这些特殊的文化传统相协调。
笔者着重关注上述讨论中呈现的某些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将帮助我们认识到关于人权与儒家传统关系的既有思考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出于讨论方便,我将以“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s)与“特殊主义者”(particularists)分别指称上述讨论中对立的两大阵营。普遍主义者倾向突出人权作为一种法律与道德准则的普遍性⑦。相反,特殊主义者倾向于削弱人权准则在法律意义上的重要性,并且强调人权根植于西方的道德意识形态(如自由个人主义),同时拒斥那些可以上溯至17、18世纪西方启蒙时期,并与之一脉相承的人权的合理性假设与道德认识论上的论证⑧。在特殊主义者看来,道德准则及其论证方式更多地受到历史、文化的制约。他们首先强调反对将意识形态化的个人主义与公民政治权利任意地联系在一起;其次,他们主张将社群主义者所持的非西方社会、文化的社群道德与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个人主义进行比较。
在我看来,上述两大阵营的观点都各有问题。普遍主义立场的潜在危险在于他们试图将人权论证简单诉诸于一些在国际范围内充满争议的道德认识论,而不是通过协商性实践共识来论证人权正当性,从而陷入到认识论上无穷的不确定性与纷争之中。这种人权正当性论证的整体式(monolithic)进路,有可能对不同文化传统间的实践协商与人权对话进程产生干扰。特殊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其对人权的复杂性与历史发展的理解极其肤浅。这种短视的根源在于他们没能认识到人权的内容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三个各有侧重的不同阶段所构成。尤其是后两代人权,其实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修正了在特殊主义者眼中常常与公民政治自由权划等号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特殊主义者固执地坚持非西方的群体主义传统与公民政治的个人主义人权观之间的紧张与非协调性,忽略了那些非西方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权利、集体发展权,甚至是经过修正后的公民政治权利之间可能具有的兼容性。在一些特殊主义者对假想中的纯粹个人主义人权观与社群主义传统的比较研究中,可能出现一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往往狭隘地倾向使用那些年代久远的古典文本作为论证材料,而未能对晚近的经典文本予以足够重视,而恰恰是这些以更接近现代形式存在的晚近文本,更能够说明这些传统文明中所具有的内在观念之多样性。
罗思文(HenryRosemont)对人权与儒学传统之相关性所做的批评,提供了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特殊主义例子⑨。他不仅将人权狭义地界定为公民个体的政治权利,而且其比较仅限于古典儒家,并未把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纳入考虑范围中。狄百瑞(Wm.TheodoredeBary) 的研究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⑩。他以一种发展演进的眼光看待人权概念,提炼出一系列看上去与第一、二代人权的某些内容相呼应的新儒学思想原则以及社会政治改革举措。例如人道治理,公平征税与设置义仓,法律改革,对个体内在价值及自愿参与的政治、社会秩序的认可(从公民政治自由权利的角度看,这种倾向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个体社会、政治参与的授权)。在此问题上,我更倾向于狄百瑞的进路。
现在,我将提供一份提纲,用以说明经过笔者修正的人权观念如何能够与儒家传统相协调。我将通过五个步骤来证明这一点。首先,我将对儒家传统中那些可能与人权问题产生关联的因素做一概述。其次,我将简要介绍儒家传统在历史上对世界人权宣言所做出的鲜为人知的贡献。第三,尽管三代人权观念各有侧重,但都能与儒家的道德、政治思想相协调。第四,从人权正当性的双层理解进路出发,儒家传统完全能够以自己的语言参与到国际层面的人权共识中来,并占据一席之地。最后作为总结,我将提出,双层理解进路有助于我们在将来建立起儒家传统与国际人权界之间的互动。
儒学的道德、政治思想更接近一种社群主义立场,这体现在:(1) 强调个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存在;(2)将个体对社群共同善的责任,以及履行此种责任所必需的美德置于优先地位;(3)以一种双向性、互惠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尤其是“五伦”)来塑造共同繁荣的基础以及共同善的愿景。强调道德的自我修养对于所有社会成员的重要性。这种自我修养,根植于每一个体生而具有的道德潜能,它能够发育出仁爱、正义、循礼的美德,以及明辨是非的洞察力。倘若回溯儒家思想的源流,从孔子、孟子,到宋明新儒学思想家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我们便会发现,儒家的道德、政治传统对各方面的状况,例如社会、经济、教育等——只要是有益于人们的道德修养的,都会给予极大关注。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就在于成为一个处于和谐宇宙中的有机社群内值得信赖的一员。
皮尔凯撒·布利(PierCesareBori)在谈及围绕世界人权宣言草案而展开的争论时曾透露,与会的中国代表张彭春(P.Chang)援引的儒家传统,曾经对宣言初稿的修改产生影响。正如布利所披露的,宣言草案初稿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四海之内皆兄弟。所有的人都具有天赋的理性,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因此人生而自由,并且在尊严与权利方面一律平等。”对此,张彭春主张将儒家的基本概念“仁”包括进来,作为对“理性”提法的补充。布利认为,此刻张的内心深处闪现的,正是人之为人所具有的一些最基本的情感:同情、仁爱、怜悯(正如孟子所说)。最终,“良知”一词被采纳。所谓良知,与其说是发自内在的道德法庭的声音,不如说是一种基于情感与同情心的道德召唤,一种客观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根芽。这样,一个儒学经典概念被写进公诸于世的《世界人权宣言》文本中。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与流行见解相反,国际人权理念并不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儒家传统完全可以与之和谐共存,并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权内涵的理解。
儒家在历史上一直强调统治者具有保障民众衣食、生计、教育的责任,它们构成了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前提,这对我们做出儒家传统支持第二代人权这一论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观念在20世纪的长时段背景下依然发挥作用。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对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并努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儒家传统的影响痕迹。由此,我的第一个理论假设是:对于社会经济权利,儒家传统所持的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无论是否使用了某种特定的人权话语,儒家传统对社会经济问题重要性的强调已经暗示,它必然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明智地参与到国际人权共识中来。
我的第二个理论假设是:儒家传统同样能够与作为第一代人权的公民政治权相协调。在《中国的自由传统》中,狄百瑞令人信服地证明,宋明新儒家学者都曾提出诸多重要思想主张,例如人类的道德本性与个体的可完善性,自主的道德心与个体良知,成圣的普遍道德潜能,在社群之中成长繁荣的人格主义信念,自治社群和地方自治,甚至是旨在限制政治权力之滥用的法律革新理念,以及通过发展公共教育来促进人民政治参与能力。虽然这些观念并未支撑起一种彻底个人主义化的公民政治权利,但很显然,人们因此能够参与到那些旨在促进共同繁荣的社会政治进程中。就此而言,这些观念又何尝不能与公民政治权利相协调?在社群主义式的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开放性理解之下,儒家的自由传统原则上是能够与第一代人权相沟通的。随着儒学再度作为一种重要思想要素出现在当今中国语境中,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基于文化视野的对话。例如,如何能够在公民政治与社会经济方面的人权内容间取得一种相对的平衡?此种对话,会促使儒家传统如同对待社会经济方面权利一样,也对公民政治权利作出一种更加明确而清晰的承诺。
我想要说明的第三个理论假设是,儒家世界观同样与强调集体发展权的第三代人权观念相一致。这一假设部分地为上面提到的革命正当性观念,以及新儒家学者强调的自治社群中的自愿原则所支持。倘将二者合而观之,那么距离自决和集体发展权不过一步之遥。不仅如此,更深一层次的思考源自杜维明所指称的“儒家最高理想”——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它不仅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来界定人,更视人为一种宇宙论意义上的存在。由此,儒家人文主义及其道德责任感扩展到了整个世界,甚至全宇宙的范围之内。我确信,倘若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那么它们不仅会支持第三、第四世界要求分享权力、财富与人类共同遗产的呼吁,而且同样会赞同他们要求世界和平、人类和谐的正当主张。儒家的道德与形而上学视野——天地万物一体观念——明显倾向于促进由相互联系的存在而构成的整全共同体之福祉。
人权正当性的双层理解进路使得那些特殊的道德文化传统能够以自己的话语,来向其信奉者证明它们在国际层面上对于人权共识的认同与参与。这就意味着,对某种特定人权的认可,可以内在地通过儒家的道德箴言来证明。相反,一些儒学传统研究者坚持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内在可能性,因为儒家传统本身缺乏类似的观念资源。他们的理由是,儒学传统是以德性为基础的社群道德,既无法容纳人权或其他权利概念,也不能认可这些权利。对此,我至少可以提出三条反驳性回应。首先,社群主义传统并不会仅仅因其社群德性便缺乏接引人权的观念资源。其次,儒家传统本身并不缺乏这样的资源。再次,即便儒家传统本身缺乏权利观念,但我们仍然可以证明其对国际人权共识的分享与认可。
第一条反驳性回应可以为多方面的思考所证明。首先,许多社群主义道德传统事实上已经认可了权利、人权观念;此外,很多本土原生的文化道德传统在观点上是十足的社群主义,然而它们却接受了全部三类人权。其次,只要我们排除这样一种断言的影响,即认定权利观念的确立必须预先设定一种从共同体纽带、社会角色、历史文化中彻底抽离出来的完全自主的个体观念,那么,认为权利观念无法与社群主义传统相协调的观点就会缺乏合乎逻辑的理由。正如我已指出的,一旦考虑到人权观念的历史性,那么这种假设就会明确暴露出不适用性。再者,正如李承焕(SeungHwanLee)强调指出的,我们很难理解,任何一种包含了财产、承诺、契约、借贷、婚姻、合作等实践的道德传统会缺乏一种事实上发挥着权利作用的概念对应物。如他所说,“权利观念是为我们的道德生活所必需的,无论我们信奉何种社会理想,接受何种道德体系”。狄百瑞的新儒家自由主义学说及其对人权范畴的开放性,也进一步论证了儒家思想与人权理念的协调性。退一步说,即便儒家传统本身缺少人权概念,它仍然具有能够认可并证明人权主题的充足资源,比如强调满足人们社会经济需求的重要性,赋予满足社群自治与个人修养所需的公民政治权利。
至于从儒家传统内在地证明其认同国际人权共识的过程与诉求,我想其中一定有着广阔的可能性,但我更愿意将这一工作交由儒家传统自身的代表去完成。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儒家传统无需从自身的道德范畴中发展出一套人权概念,或对权利本身做出证明(虽然这完全可能)。相反,我们只需利用它们去证明儒家传统同意参与并遵循实践性的国际人权共识,而这种参与是与儒家对人的道德本性与福祉的理解相一致的。较之生硬建构一套儒家固有的人权传统,这可能是一种更加新颖,也更为可行的方式。
最后,非常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人权正当性的双层理解进路使我们能够在原则上描绘出儒家传统与国际人权界之间交互影响的历史图景与未来愿景。儒家思想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中起到的历史性作用,已经为它在国际人权协商中发挥的影响做出了很好的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家的道德、政治思想还将在这一进程中做出更加深入的贡献。我相信,儒家传统越是深入地参与到在民族与国际层面上的人权对话中去,就越有可能增进其自身对于人权主题的认可。儒家传统中那些已经对人权观念产生影响,并且具有蓬勃潜力的思想资源,都应该被着重凸显并带入到充满前景的跨文化对话中来。随着全球多元化意识的日益增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种不同的声音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获得倾听,而这将有可能在我所谈到的两个层次上对人权做出更为细致的阐明。
注释:
① 参见:《国际人权清单》 (TheInternationalBillofHumanRights,NewYork:UnitedNations,1993)。
② 有关人权磋商的实践过程,参见约翰·汉佛莱:《人权与联合国:一项伟大的探索》 (JohnP.Humphrey,HumanRigh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A GreatAdventure,Dobbs Ferry:transnationalPublishers,1984)。
③ 参见沃尔泽:《道德底线主义》 (Waler,MoralMinimalism),尤其是第17—18页。
④ 参见伯恩斯·H·韦斯顿:《人权》 (BurnsH.Weston,HumanRights),理查德·皮埃尔·克劳德与伯恩斯·韦斯顿合编:《世界共同体中的人权:问题与行动》 (RichardPierreClaude andBurnsH.Westoneds.,HumanRightsintheWorldCommunity:IssuesandAction,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 Press,1992),第 14—30 页。
⑤ 比如,可参看阿扎曼蒂·波利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第三世界视野中的人权》 (AdamantiaPollis,Human RightsinLiberal,Socialist,andThirdWorldPerspective),见克劳德与韦斯顿合编:《人权》 (ClaudeandWestoneds.,Human Rights),第 146—156 页。
⑥ 韦斯顿:《人权》 (Weston,HumanRights),第18—20页。
⑦ 例如,参见阿兰·格维斯:《有关人权之证成与应用的片论》 (AlanGewirth,HumanRights:EssaysonJustificationand Application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以及《普遍道德与权力共同体》 (CommonMoralityandtheCommunityofRights),收录于奥特卡与里德合编:《普遍道德的前景》(OutkaandReedereds.,ProspectsforaCommonMorality),第29—52页。对基础主义人权进路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与批评,参见迈克尔·弗里曼:《人权之哲学基础》 (MichaelFreeman,ThePhilosophicalFoundationsofHumanRights),载 《人权季刊》 (HumanRightsQuarterly,16/3,8/1994),第491—514页。
⑧ 特殊主义方面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参见阿扎曼蒂·波利斯与彼得·施瓦布:《人权:西方式建构及其适用性限制》(AdamantiaPollisandPeterSchwab,HumanRights:AWestern ConstructwithLimitedApplicability),收入波利斯与施瓦布合著:《人权》 (HumanRights) ,第3—18页;以及阿利森·邓兹·伦特林:《国际人权: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 (AlisonDundes Rentelen,InternationalHumanRights:UniversalismVersusRelativism,NewburyPark,Calif:SagePublication,1990)。
⑨罗思文:《为何要认真对待权利?一种儒家式的批评》(Rosemont,WhyTakeRightsSeriously?AConfucianCritique),载《人权》 (HumanRights),第167—182页。
⑩ 狄百瑞:《新儒学与人权》 (Wm.TheodoredeBary,Neo-ConfucianismandHumanRights),载罗纳编: 《人权》(Rounered.,HumanRights),第183—198页。亦可参阅狄氏著:《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TheLiberalTraditioninChina,Hong kong:ChineseUniversityPress,1983;reprint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83),及其《〈明夷待访录〉英译本》 (WaitingfortheDawn:AplanforthePrince,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