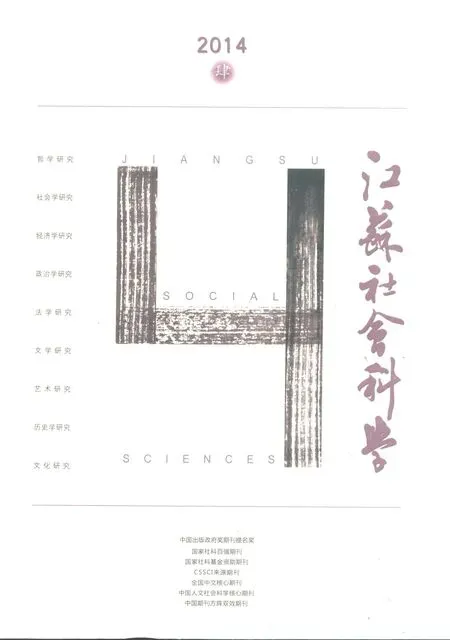新时期生态写作中的自然科学话语
——兼论生态写作的本土化、现代化途径
李玫
新时期生态写作中的自然科学话语
——兼论生态写作的本土化、现代化途径
李玫
大量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构成新时期生态写作的文本特质:符号层的自然科学知识、术语直接镶嵌;结构层的自然科学思维特征等。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建构了生态伦理的现代维度,以此实现中国文学中生态伦理由古典伦理(天人合一的诗性伦理)向现代伦理(突出历史发展中主体精神的理性伦理)的转向;在实践论层面,自然科学话语对民间伦理的佐证,推动了生态伦理精神的本土化进程。新时期生态写作以“敬畏自然”的科学态度和对理性的张扬与强调,实现对五四以来“科学”精神的对接与修正。
生态写作 自然科学话语 本土化 现代化
生态写作中大量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是与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机缘密切相关的。“‘生态’这个概念本身,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文学中生成,而是从生态科学、生态文明理论出发而转换过来的概念。”而“生态学对于‘生态’的界定,主要包涵了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以及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所在的具体地段环境、生物所必需的生存条件。”[1]徐肖楠:《生态文学的情感空间与审美意向》,《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在从生态科学向生态文学转换的过程中,部分文本借鉴了自然科学本身的话语特征和内在的逻辑思维,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于中国当代文坛的生态写作中具有较明显的自然科学话语特征。
自然科学话语进入生态写作叙事的符号层面,从符号代码角度看,主要表现为三种维度:其一是自然科学知识、术语的直接镶嵌对文本形态的影响;其二是自然科学的思维特征、研究方法对文体特征的影响;其三是自然科学认知推动生态写作中叙事模式、伦理立场的现代化、本土化。
一、自然科学话语:理性认知的文本特质
自然科学各学科的专业知识、术语直接镶嵌入生态写作中,成为生态文学文本醒目的组成部分。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文本的感性、诗性的总体风格不同,具有自然科学话语特征的生态写作在文本构成上,通过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传达对自然、生命的认知。除“生物链”、“沙丘两翼之间的交角”、“土质、水位”、“行间距离”、“覆盖度”等生态学领域的专业词汇外,现代生物学、气象学、地理学、物理学、现代医学、营养学,甚至土木工程学等学科的术语均有大量出现,构成其独特的文本质感。
叶广芩秦岭系列文本在对自然空间的书写中,常直接以“气流涡旋”(《黑鱼千岁》)等气象术语展示其自然气候特征,以地理学的专业术语描述其地形地貌:“天花山脉属于秦巴山系的延伸,面积广大,南高北低,南部是由英岩片组成的岩石,北部是浅变质性粉砂岩,中心地带为裸露的泥盆系地层,地面结构复杂多变,气候阴湿多雨。”(《山鬼木客》)自然生物的介绍中除了“丛生木本植物”、“株高”、“aiuropodidae,哺乳纲大熊猫科大熊猫属”等专业术语大量使用之外,更有较长篇幅的生物属性陈述,如:“羊奶子果学名苦糖果,忍冬科类植物,生长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河坝地带,状如羊奶,粒大汁多,酸甜可口……”(《山鬼木客》),使用植物学专业术语介绍其种属及生物特征。弥漫着神秘气息的《怀念狼》(贾平凹)亦用大段的篇幅论述真菌和动植物的关系:“通常认为真菌与植物的亲缘关系要比与动物的关系要近得多,而分析了某一核蛋白、核糖核酸的排列顺序,发现人类与真菌的共同祖先显然是远古时代的一种鞭毛类单细胞动物。既然动植物有着共同的祖先,那么太岁就是由原始鞭毛的单细胞生物分化而来的,其自养功能的加强和动物功能的退化,便进化到单细胞绿藻,由之发展成植物界,相反,运动功能和异养功能的加强和自养功能的退化,便进化到单细胞原生动物,由之发展为动物界”,高频度的专业术语显示出极强的异质性。
从叙事功能角度看,物理学、营养学等学科的知识夹杂其间并参与情节的推进。姜戎《狼图腾》以理性的声学知识解读狼智慧,“狼鼻朝天的嗥叫姿态,也是为了使声音传得更远,传向四面八方。只有鼻尖冲天,嗥声才能均匀地扩散音波,才能使分散在草原四面八方的家族成员同时听到它的声音”;叶广芩《狗熊淑娟》则以“正在发育期的母虎一天的消费是八公斤的上好牛肉,二斤牛奶,四十片维他命C,二十片维他命E,六个生鸡蛋外加一只白条鸡……”等现代营养学的数据计算动物的生存成本进而推论出淑娟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诗歌中涉及生命、生态话题一向诗性盎然[1]具体论述参拙作《于坚诗歌中的生命旋律》,〔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但于坚《事件:棕榈树之死》在言及现代文明进程中一棵棕榈树的死亡时,亦有土木建筑学术语和详细的工程设计细节,“图纸中列举了钢材油漆石料铝合金/房间的大小窗子的结构楼层的高度下水道的位置/弃置废土的地点处理旧木料的办法”,在全诗中呈现了异质性思维和语体特点。高行健戏剧《野人》在对野人的寻找中更是包含生态学、地质学、医学等多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的直接穿插,“麻醉了的野人,一定要严加护理。一,密切注意呼吸、心律、体温的变化,每两小时测定一次。二,预防感染,供给抗菌素和大剂量的维生素C、复B和B6。三,再就是操作万万不可以粗暴,要注意瞳孔反射”,术语之密集,操作方法介绍之规范,如同严谨的临床医学教科书。
上述小说、诗歌、戏剧诸文体中,大量的自然科学术语以不同的方式镶嵌其中,并以较大的比例的存在,对各文体既有形态构成冲击,形成新的文本质感。
二、语体:超越感性的实证精神和逻辑推理
除各学科自然科学话语的直接镶嵌冲击文本的表层特征之外,自然科学话语更是以富有实证精神的科技思维和逻辑推理支撑文本的内在张力。在郭雪波《白狐》、《沙葬》、《苍鹰》等书写草原沙漠的文本中,通常以具体的数字、实验数据、百分比来传播生态学的基本知识,呈现生态问题的严峻,体现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具有严谨、精确的语体特征:
沙害是人类面临的四大灾害之一,全世界37%的土地已被沙漠吞没,成为不毛之地,而且这个面积以惊人的速度日益扩大。……(《沙葬》)
一百多公斤的大熊猫母亲产下的婴儿仅十克左右,存活率也只是百分之十。……人类已开始退化,现在的一个正常的男人排精量比起五十年前一个正常男人的排精量少了五分之一,稀释度也降低了百分之二十。(《怀念狼》)
与上述文本以数据分析结论的实证精神相对应,一些作品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科技思维的严谨和注重因果推理和逻辑关系:
……拿出笔记本,查看起这片实验地的植物生长情况,种植特点,以及面积、土质、水位等等一系列问题。她发现,主人的确谙熟沙漠和沙漠植物,他在迎风坡下半部先成带种植了黄柳,带的走向与主风方向垂直,带的宽度为二行或四行,行间距离三四厘米。在沙丘较缓处选用双行带,在沙丘起伏较大处选用四行带,沙丘坡度越大,带间距离越小。黄柳生于流沙地,枝条密而柔韧,防风固沙力很强,被沙压埋后能生出很多不定根,当年可长出二米多高的新枝条。在沙坨的半坡以上种了胡枝子,覆盖住了原先赤露的沙质土。胡枝子分枝多,萌发力强,根多呈网状,很发达,耐沙地的贫瘠和干旱。由于枝叶繁茂,对地面的覆盖度大,仅五十平方米的面积上就有近七百多个枝条,每年的枯枝落叶可达七十斤,具有改良土壤的作用。所以,主人很内行地在胡枝子中间栽活了樟子松。而选种樟子松也是高明的主意。这种树耐寒性强,能耐寒零下四十度至五十度的低温,对土壤要求也不苛,正适于沙质土壤的贫瘠。(《苍鹰》)
整段文字的思路:带的布局特点一(走向、带宽、行间距)——黄柳特点(生存条件需求、枝条特点、不定根)——布局特点二(半坡以上的植被设计)——胡枝子特点(分枝、网状根、地面覆盖度、土壤改良作用)——布局特点三(植被之间的相互配置)——樟子松特点(耐寒性、土壤需求),以所选植物的自身特点和对生存环境的需求情况的介绍,论证实验带在布局设计方面的专业、科学,总体思路逻辑严谨,颇具科学的实证精神。文本以清晰的叙述线索,呈现必然因果推理的内在逻辑,正如董小英在《叙述学》中阐述科技语体特征,“以概念的循序渐进的出现为叙述的层次”,“前面一定是铺垫前提,之后是推理过程,最后才是结论。一个科学文本是不会把没有经过论证的结论首先拿出来的。由此,这样的叙述方式就构成科学文体最基本的特点,最基本的叙述框架。”[1]董小英:《叙述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页。大量具有自然科学话语特征的生态写作,在实现生态知识传达的内容部分,具有上述科技语体的内在逻辑特性。
在文体特征上,具有自然科学话语特征的文本中,经常基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影响,插入其它科技文体的实验报告、考察记录等,以呈现生态现状的真实处境:
《山鬼木客》中考察野人的片断,完整而典型地呈现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流程:
站起身时,他发现了身边巨大的脚印,才下过雨的湿地上,一行足印伸向前面的冷杉林。也就是说雨停以后,在黎明时分,它在这里走动过,……仔细测量着那些与人十分相似的印迹,长42厘米,深3-5厘米,步幅80-100厘米,应该是个身高2米、体重150公斤的大块头……在不远的灌木上,他发现了一撮褐色的毛发,他小心地将它们取下来,夹在他的标本夹子里,类似这样的东西他搜集了不少。窝棚里,他保存了300多个胶卷资料,写有170万字笔记……
从脚印出现时机推断研究对象的出没时间;通过测量足印的长、深、步幅判断该生物体的身高、体重;在附近环境中敏锐发现毛发等标本并将其科学保持,拍摄胶卷和撰写实地考察笔记以积累研究对象相关资料;最后通过研究所法医组的化验报告,得出结论。其中涉及的科学术语有作为研究方法的“压膜制片、毛干切片、毛小皮印痕检查、血型物质测定和毛发角蛋白的PAGIEF分析”,作为动物分类学知识的“高级灵长目”,作为解剖学术语的“眉间垂距、枕骨大孔、枕骨粗窿”等,在此研究基础上,最后附加一份完整的考察报告:
农民李春桃,1902年生,女性,天花山核桃坪人。1930年3月在田间劳动,被一直立行走的不明物掠上山,两个月后自行逃回。回来后怀孕,于当年12月产下一子,取名王双财。据当地人回忆,王双财从生下起周身便生棕色短毛,足大臂长,面目似猿,身材低矮,不会言语,举止怪异,但能解人意。其兄王双印介绍,王双财活至二十三岁,自然死亡。王氏家族中兄弟六人,只有王双财“与众不同”。征得家属同意,2001年7月19日将王双财的遗骸取出,初步测量结果如下:
从腿骨判断,死者生前1.42米,臂长与腿长不成比例。头骨高8cm,前额低窄,眉脊向前方隆起,脑量不大,是正常人的三分之二。眼框部结构特异,眉间垂距5cm,猿人为5.6cm,现代人为2.8cm。枕骨大孔较一般人小,枕部平展,枕骨粗窿不明显,与我国晚期化石智人相接近,显示了脑髓不发达的物质。
从以上粗略情况看,核桃坪王双财颅骨与类人猿接近……区别于文学叙事“以颠倒、隐瞒、伪装等剪断事理的线索,打乱条理,制造悬念,延宕故事的信息,却在话语中掺杂后设命题,以新奇的方式,以最能唤起读者情感、最能触动人心的方式来组织篇章结构”的话语风格,科学语体是“以最清晰的叙述线索,所遵循的是必然因果推理,作者想得到的结论必须完全叙述出来。要开宗明义,开门见山”[1]董小英:《叙述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页。,文中“简要报告”所述内容,如以文学话语叙述,则可能更为丰富和生动,甚至可能充满悬念和具有可猎奇性,但文中作为研究报告,强调信息的传达,因而文字简约、平实、规范、明朗,如“农民李春桃,1902年生,女性,天花山核桃坪人。1930年3月在田间劳动,被一直立行走的不明物掠上山,两个月后自行逃回。回来后怀孕,于当年12月产下一子”,事实清晰,而“足大臂长,面目似猿,身材低矮”,则以极其简约的文字概括研究对象的特点,极富自然科学话语色彩。此外,《怀念狼》中详细保存了一份关于大熊猫生产的观测记录,记录人子明在2个半小时内选取了17个观测时间点来完成大熊猫生产过程的详细考察,以此呈现这一濒危物种生育的艰难及其面临的生态困境。
大量科学术语的存在,展示生态环境,呈现生态危机,以实证的思维和严谨的逻辑彰显了生态写作中沉稳的理性气质。
三、叙事逻辑:“因果报应”模式的消解
在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中,人类的不良行为及由此产生的生态恶果,是生态写作中惯常演绎的故事模式。这一常见故事模式在情节上与古典小说中的“杀生报应”主题颇为相近。
“杀生报应”故事在古典小说中广泛存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唐代的文言小说、宋代的白话小说,以及明清时期的各种题材、形式的小说中均可发现。《搜神记》卷二十中“虞荡”条,虞荡射杀麈而死:“冯乘虞荡,夜猎,见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荡,汝射杀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时荡死。”[2]〔晋〕干宝撰:《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2页。《异苑》中“射蛟暴死”,主人公杀蛟而暴死于路:“永阳人李增行经大溪,见二蛟浮于水上,发矢射之,一蛟中焉。增归,因复出,市有女子素服衔泪,持所射箭。增怪而问焉,女答之:‘何用问焉?为暴若是。’便以相还,授矢而灭,增恶而骤走,未达家,暴死于路”[3]〔南朝·宋〕刘敬叔撰:《异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页。;《宣验记》中“吴唐”条则讲述吴唐射杀鹿母子而祸及自己的儿子;《搜神记》中“陈甲”条叙述陈甲杀蛇三年后腹痛而死[4]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52页。;《三言二拍》中,《通言·计押番金鳗产祸》、《初刻·屈突仲任酷杀众生》皆可见“杀生报应”情节。该情节模式隐含的逻辑是:人类若荼毒无辜生灵通常会触怒上天遭到相应的报应——损失功名、财产、生命,甚至累及子孙。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逻辑对上述文本的解读中,“因果报应”思想是重要依据。儒家思想体系中有“天道福善祸淫”[5]《尚书·汤诰》,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周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周振甫:《〈周易〉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道家经典《太平经》则进一步解读:“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信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2]《太平经钞乙部(补卷三十四)·解承负诀(第四十)》,俞理明著:《〈太平经〉正读》,〔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6页。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三世因果观念亦与本土因果报应思想实现了较好的对接。
新时期生态写作中,以自然科学的认知消解古典伦理时期“杀生报应”故事模式的内在逻辑,强化生态伦理关系中理性因素。以叶广芩《黑鱼千岁》、《长虫二颤》为例,在总体情节上,二者皆似古典小说中“杀生报应”故事模式,前者是杀鱼的人类最终与鱼同归于尽,后者则是杀蛇的人类最终被已死的蛇头咬而中毒失去一条腿。但文本是以科学话语、并通过用现代科学知识重新作了解释,以使其因果逻辑符合科学认知:
被身首分离的蛇头撕咬,听起来是奇事,但据动物学家解释却不足为奇,离开身体的头在一定时间仍可存活,这是脊椎动物的本性,人不行,可是蛇可以……(《长虫二颤》)
死了的儒和鱼被麻绳缠在一起,如同一个宠大模糊、伤痕累累的包裹。人们在解那根绳时才知道这项工作的艰难,浸过水的麻膨胀得柔韧无比,非人的手所能为,只好动用了刀剪,于是大家明白了水中的儒为什么在最后的时刻也没有解开绳索逃生。(《黑鱼千岁》)
《长虫二颤》中,同是取蛇胆,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以此治病救人是积德行善受尊重,所以王安全救人受尊重;佘震龙则是利欲薰心差点送命,如此情节序列蕴涵一个因果分明的“善恶有报”逻辑。但文中自然科学话语的出现,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了该现象,由此解构了因果报应的故事模式。而在《黑鱼千岁》中,儒试图捕杀黑鱼最终却与黑鱼同归于尽,亦颇近“杀生遭报”模式,但文本却用物理学的常识来解释绳子浸泡之后发涨的现象,为儒在水中未能脱身提供了更符合科学的理由。
体现在叙事模式上,自然科学认知实现了现代生态写作对古典小说中“因果报应”叙事模式的重述。
四、超越古典与援助民间:生态伦理精神建构的本土化与现代化
生态科学和生态文学最初都源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生态观念的传播,在与中国本土语境的对接中需要经历本土化过程才能建构真正属于中国文学的生态写作,而在本土文化资源中寻求生态呼应是对接的重要途径。本土生态文化资源既包括源自中国古典文化核心体系儒道佛的生态思想,亦包涵长期沉淀于民间的朴素生态立场。
首先,自然科学立场的介入,超越古典时期生态伦理的被动处境,凸显人的主体力量,推动了新时期生态写作中伦理精神的现代化。生态伦理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深远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古典生态伦理体系中,“无论是儒家道家或者佛教,在本体论或本根论的层次上都承认‘天人合一’”[3]胡伟希:《儒家生态学基本观念的现代阐释》,〔济南〕《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而“天人合一”的实现则是以人对天的自觉顺应实现天人和谐,在“人——地——天——道——自然”的单向师法关系中,人位于最被动的处境。儒家思想中“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4]〔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道家思想中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晋〕王弼:《老子注·道德经上》,《诸子集成》(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4页。,庄子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6]〔清〕王先谦:《庄子集解·马蹄》,《诸子集成》(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7页。,皆强调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生态建构中,人对天地自然日月四时的顺应,对万物生灵的敬畏。传统“因果报应”叙事模式中,以神灵执法的外力干预的方式保障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关系的和谐,人类的作用是被动的。
现代自然科学话语的介入,在对“因果报应”模式的解构中凸显现代生态伦理立场:人是地球上唯一具有主动选择能力的伦理主体,因而人类应该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生态危机源于人的心态危机……”,生态灾难的避免与自然生灵的获救,并不是完全来自生态保护技术的更发达,或者自然界的自我修复,更多的拯救最终依靠人类的自省——人类的觉醒,进而使来自人类内心的精神生态和精神空间得以重建。叶广芩颇富理性精神的秦岭系列文本中,侯长社在失掉村长之职后,在父辈故事中的自省(《猴子村长》),佘震龙在失掉腿之后的“自新”(《长虫二颤》),都是一种全新的伦理关系重新建构的希望的出现。“人类不是万物之灵,对动物,对一切生物,我们要有爱怜之心,要有自省精神”。既然是人类“在生存的过程中,逐渐生成了以自然为敌、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理念”导致自然生态的灾难,因而拯救之旅的起点也应源于人类精神理念的改变,“……一切的症结所在,在于人心”[1]叶广芩:《老县城》,〔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243、229页。。郭雪波的沙漠系列小说中,亦是在通过数据呈现生态灾难的同时,强调人类的不当行为与生态现状之间的渊源关系,并把具有强烈的意志力和生态使命感的“沙漠人”的出现,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和希望所在:“倘若每座沙坨子都守留着这样一个郑叔叔,这样一个沙漠人,那大漠还能吃掉苦沙坨子,还能向东方推进吗?”(《苍鹰》)此文以大量而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在凸显生态问题的严峻的同时,肯定了“人”在沙漠生态恶化中应承担的责任。《苍鹰》、《沙狐》、《沙葬》、《大漠魂》等文本,皆以类似郑叔叔的老沙头、白海夫妇等形象,将人类定位为宇宙间惟一有能力作为伦理主体调节自身行为实现生态和谐的生命体,因此人类应勇敢地正视自己的生态责任和伦理义务。
基于自然科学认知的现代视野的出现,对人与自然关系重新解读和定位,即超越古典生态伦理中“天人合一”的诗性维度和感性维度,转化为突出历史发展中主体精神的理性伦理,凸显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应承担的生态责任,锐化了生态伦理的现代色彩,实现生态伦理从古典伦理向基于自然科学认知的现代伦理体系的转化,从而建构生态伦理精神的现代化维度。突出历史发展中主体精神的自我选择与努力超越,这与五四时代精神中对于人的理性的张扬与强调是一致的[2]刘为民:《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其次,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还通过对民间伦理立场的援助实现生态伦理精神的本土化进程。在现代生态伦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对民间生态伦理立场的尊重与合理借鉴是生态伦理精神本土化过程的重要思路。新时期中国生态写作中,自然科学话语往往置于民间自发的生态伦理话语之后,以现代科学知识佐证长期保存于民间的某些生态伦理立场的合理性,进而点燃其现代意义。方式之一,是以现代自然科学认知,检视民间宗教文化中与现代生态伦理精神的相通之处,肯定其中涵蕴的符合现代唯物观的认知的精髓。《大漠魂》展示安代舞的内在之魂与现代生态伦理精神的相互呼应,《狐啸》挖掘在民间宗教“孛”教教义在“对天、地、自然、万物的认识”中,蕴涵的现代生态伦理立场,并通过白尔泰的思考在宗教教义与科学治沙之间寻找到精神层面的相通之处:“你对长生天长生地的崇拜,你对大自然的认识,以及对大漠的不服气、在黑沙坨子里搞的试验等等,你全是按照‘孛’教的宗旨在行事”(《狐啸》),既阐明了民间宗教的生态伦理意义,也为郭雪波小说世界这一人物系列(老双阳、云灯喇嘛、老铁子、老沙头、老郑等)的富于神性的行为寻找到了基于生态维度的合理性。方式之二,以自然科学的认知,解释神秘现象中符合生态学的元素,论证在民间人与自然、与其它非人类生命之间的相处模式的科学性,证实民间伦理中具有生态意识部分的合理性。姜戎《狼图腾》中一面展示狼之生命的神奇魅力,一面不断通过陈阵和杨克的思考努力把关于腾格里神秘力量的叙事推向科学的本质:以草原生态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实现对毕利格老人的“长生天”草原民间话语的敬重。文本中,科学话语和扎根于草原民间的神秘话语多次发生直接对话,其中牧民利用小狼设置圈套试图诱捕狼群,但后者在关键时刻神奇地撤离了,毕利格老人的解释是“瞒谁也瞒不过腾格里。腾格里不想让狼吃亏上当,就下令让它们撤了”。在老人的话语中,腾格里即长生天,是掌握草原一切生命的至高无上的神灵,腾格里帮助群狼逃生以保存草原大命。而同样热爱草原的牧场场长乌力吉则尝试用富有推理和逻辑性的科学知识完成对上述现象的解释:因为小狼长期生活在人群中不会说狼语,无法与狼群沟通,被视地盘为命的群狼疑为外来户而放弃救援。并从狼之敏感多疑的习性出发,分析狼王的行为逻辑,整个推理过程严谨而富有说服力。在一部具有显著的理性精神和强烈的现实关怀的文本中,神秘话语的说服力往往是虚弱的。科学话语的出场,帮助源自草原民间的神秘话语完成对草原狼令人惊叹的生存智慧的解读,有效补充了唯物论视野之下民间神秘话语在认知层面上说服力的不足。
本土民间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天人和谐精神[1]黄永林:《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提炼了民间生态伦理中的合理性成分,凸显民间话语中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定位与现代生态伦理不谋而合,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民间话语中对神性力量的保存和敬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人对自然敬畏之心的缺失,具有精神建构的有效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发展在赋予人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能力的同时,亦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民间文化中对自然神性的敬畏,进而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新时期生态写作以自然科学话语对民间生态智慧的援助,促进了生态伦理精神的本土化转向,以此实现对自然神性的重建。
新时期生态写作中,自然科学话语的介入,在文本形态、叙事模式等方面凸显了前所未有的理性气质。在接受现代科技知识的同时,尊重民间生态伦理实践中的合理性成分,破除迷信但尊重其间蕴涵的伦理立场,并最终以精神生态的重建来实现自然生态的恢复和保护。在历史理性和道德感性之间,寻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推动了生态伦理精神建构的现代化、本土化进程。
〔责任编辑:平啸〕
Discourse of Natural Science in the Ecological Writing of New Era—Also on Approaches to Loc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Ecological Writing
Li Mei
The ecological writing of new era is characterized by abundant discourse of natural science in text,which builds a modern dimens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in order to convert from classical ethics to modern ethics.In positivism,the demonstration of folk ethics by discourse of natural science promotes the localiza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The ecological writing of new era takes a scientific attitude in awe of nature and makes reason prominent,fitting into and modifying the spirit of science since the May 4thMovement.
ecological writing;discourse of natural science;localization;modernization
李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21009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伦理精神”(项目批准号:07CZW032)后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