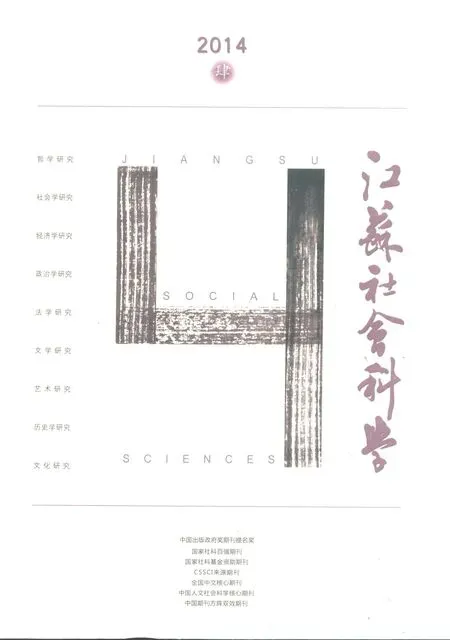人格与人格权关系重拾
解维克
人格与人格权关系重拾
解维克
人格是人格权的基础,人格权在突破“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后,发展成包含生命、身体、健康等要素的自然人格权和建构在“外在化”的社会伦理价值基础上包含知情、信用、名誉等要素的社会人格权两种形态。人格与人格权的基础关系具有“同质不同形”特质。
人格 人格权 权利能力 伦理价值
加强对人格权的民法保护,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法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志[1]王利明、杨立新、姚辉:《人格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人格和人格权的关系涉及到民法概念体系的构建,语义的解释,法律规范技术的抽象等方面。如何在民法中理清这些关系并非单纯的概念问题,则涉及到基础关系、体系构建等问题。笔者试图从人格、人格权的基础关系出发,对两者进行定性分析,进而对人格乃是人格权的基础进行论证。
一、人格:伦理资质与法律主体资格的统一
1.人格的生物性内涵及伦理资质生成
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物资资源匮乏,灾害危险频繁,求生手段单一。受制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个体的力量无法独立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来自同类的屠刀。在原始、本能的生存和繁殖意识支配下,人自发的形成一个个群落共同谋取生活资料,共同抵御各种灾害。在有史可考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出现了最古老的比较稳定的系统组织形式,由同一个祖先衍生的拥有相同血脉的人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人类社会群落——氏族。在朴素的自然理念指导下,氏族内部萌发形成了原初的人类伦理观念,每个成员的地位平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财产共享;氏族事务由氏族首领管理,重大事务则由氏族成员组成的氏族会议决定。这种群落团体生活模式,是人在面对残酷的自然法则和恶劣的生活环境时,为了维系和保全生命而在自然理念基础上自发的形成的一种群体共生模式。因为,群体生存是个体生存的前提,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可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在氏族社会,血统就是一个人能否进入某个特定群落也就是氏族的资格。在此意义上,现代法律研究所定义的人格在氏族社会时期就是指血统。而基于血统所产生的第一位关系是家庭伦理关系,也就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由于年龄而形成智力和能力上的差异,客观上要求每个家庭成员依据自己的年龄、能力大小承担相应的群体责任。因而,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在作为一种亲属间称谓的同时,也反映出每个家庭成员在内部分工上的差异,代表着各自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身份关系,因而在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必然是一种身份社会,以血统为表征的身份也就是原始部落氏族时期人格在血缘社会组织关系中的表现。只有具备特定血统才能拥有相应的社会组织身份,进而满足氏族法律上人格的基本要求[1]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后,虽然生产力相较过往时期有了质的提升,但生产力水平仍然是相当低下的。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婚姻和血缘等为纽带形成的身份组织模式仍然是人类获取财富,保有既得利益的最有效的形式。因此,身份继续作为人格的重要内容被秉承下来,以维持组织群体的相对稳定。直到经过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双重洗礼后,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推动下,法律上的人格才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身份特权标准,被注入了意志自由、形式平等等理性价值要素,显现出实质性的变革。在理性哲学的光芒下,1840年问世的《法国民法典》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在私法领域的体现,完整地贯彻了自然法的自然理性和平等自由观念,认为人的自由和尊严是源发于自然理性的人的本体要素,人格作为人的一种伦理价值和自然地位实为一种内在与人的法律地位。
2.作为法律主体资格的人格
在法律层面上,人格概念最早出现于罗马法,但罗马法上的人格不同于近现代民法意义上的人格。罗马法上的人格表现为三个关于人的概念,即homo、caput、persona或status。homo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原则上不能作为权利义务主体;persona用来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caput则表示法律上的人格[2]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7页。。古罗马完整的法律人格包括公法和私法两个领域,它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只有同时拥有自由民、市民和家父身份,成为罗马共同体的正式成员,才能拥有“caput”。实际上,只有家父才能在古罗马拥有全部人格,其他人则根据具体情形具有不同的等级身份。首先,自由权(自由民身份)把自由民与奴隶划分开来,奴隶只是客体。其次,市民权(包括公权与私权),公权是担任公职的一种资格,在卡拉卡拉皇帝授予拉丁人市民资格前,只有罗马市民方可担任公职;私权中的婚姻权是为了保持市民血统的纯正性,其他三权即遗嘱权、财产权、诉讼权(私法方面)对内来说,因实行家族本位主义,只有家父才是合格的权利(权力)主体;对外则有彰显罗马市民身份的意义,故全然是身份法。至于家族权则是为了区别罗马市民之间在私法领域的身份关系[3]王存河:《法律人格问题的比较分析》,〔兰州〕《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1月(总第78期)。。由此可见,罗马法上的人格具有很强的身份色彩,它以身份上的不平等为基础,横跨公法领域和私法领域,对主体在法律上的地位和资格进行了规定,是一个“公私法兼容、人格与身份并列、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合为一体”的概念[4]姚辉:《人格权的研究》,载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
伴随着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的发展,直至资产阶级革命前,作为一种全领域的法律上的地位,罗马法上的人格始终以血统、职业、宗教等方面的不平等为主要特征,对社会成员的地位、权利以及社会资源进行划分,这个时期的人格主要的还是一种等级森严的身份制度,具有很强的公法色彩。18世纪上半叶,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为代表的思想启蒙运动蓬勃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具有强烈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经过思想启蒙时期的精神洗礼,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Man and the Citizen),宣称:“人与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一举冲破了不平等的社会身份制度,近代民法开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壮大,腐朽的家父权开始瓦解,不平等的身份制度也被废弃,人格中的身份要素被逐步剥离,人格也开始回归到民法本位。
进入19世纪,随着社会进步和人性的解放,受到自然法学及康德思想影响,人的独立、平等的主体地位,进一步被法律所确认。这一时期,德国思想家萨维尼以理性哲学上的人的伦理价值为基础,创造了“权利能力”的概念,提出“所有的权利,皆因伦理性的内在与个人的自由而存在。因此,人格、法主体这种根源性的概念必须与人的概念相契合。并且,两个概念的根源的同一性以如下公式表现出来:每个人……皆是权利能力者。”[1]转引自〔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萨维尼提出的权利能力内含了人格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从抽象的人格推导出主体人的地位资格[2]眭鸿明:《权利确认与民法机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第274页。。萨维尼的学说被后世的民法制度所承认,实在法概念上的人格,开始以一种“法律上的命令”的形式,将从人的伦理价值中抽象出来的人格作为人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或资格。
3.法律人格的社会意义
法律人格在民法制度中体现为相对抽象的主体权利能力[3]眭鸿明:《权利确认与民法机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第274页。。沿袭罗马法将生物人与人格相分离,进而使生物人与法律人相区分的立法技术,在近代民法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仍然是不能直接作为法律主体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正如同罗马法上的人只有在具备特定的身份后才具备人格能够事实上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一样,现代社会中的生物人也只有在具备权利能力资格后才被认为是法律上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主体。反映在实在法上,人的具体要素被从人的本质中抽象出来,并据此对生物体的人和作为法主体的人进行了区分,建构了以人格为标准的法律主体资格制度,规定生物人要成为法律上的主体必须具备法律所认可的适格条件——权利能力。有学者对作为法律人格的权利能力的法律价值提出疑义,认为现代社会公民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民事权利能力概念最初用于区别主体法律地位的功能已经消失,其作为价值宣誓的功能显得多余,也日益丧失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4]李军、袁文波:《试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石家庄〕《河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其实这种认识只是一种表象上的分析,忽视了权利能力背后所隐藏的法律逻辑关系。罗马法关于人的立法的最大技术特点是通过人格将生物人与法律人分离,要求法律人必须是具备特定身份的生物人。直到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和理性主义思潮深刻地影响了私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生物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人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作为人的标准的特定身份被人的理性所决定的伦理价值所取代。但是,罗马法上“生物人与法律人相分离”的立法技术仍然在近代民法的立法过程中得到了传承。以《法国民法典》第八条“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的规定观之,《法国民法典》完整地贯彻了自然法的自然理性和平等自由观念,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理性,那么作为法律主体的法律人必须反映人的本质,因而在第八条规定背后隐含的法律逻辑关系是“法律人必须具备理性,因为生物人有此属性,所以生物人是法律人”,从而实现了人的界定标准由身份到伦理的转变[5]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第62-63页。。进入19世纪,随着历史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崛起,以理性为标准的法律人格受到了强劲的挑战,人们认识到,生物人要成为法律人,在法律逻辑上必须具备实在法从人的本质上抽象出来的权利能力。因此,《德国民法典》第一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自出生完成之时开始”,这条规定正是基于法律在逻辑上的需要。所以说,以权利能力为标准的法律人格是连接生物人与法律人的逻辑桥梁[6]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第62-63页。。
二、人格、人格权的结构关联
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科技文明现代化,特别是由技术大爆炸引发的时代背景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类传统的伦理思想观念,进而对传统的人格立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格权提出了挑战。
1.人格的内在结构及自然人格权
以个体本位为特征的近代法律人格制度所关注的对象是社会个体,平等法律人格理论在立法上得到了承认,以建立在自然理性下的伦理观念为基础的法律人格制度构建了对社会个体生命、自由等人格要素的法律保护体系。自然法学说认为,在自然和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人的意志的理性的秩序,自然法的权利就是由自然界和人的本性中抽象出来的法则,它们是对人类行为最适宜的规定。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权利观念带有浓厚的天赋权利色彩,认为人不仅生于自然,权利也来自于自然。自然法学对法的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也就是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的重视和探索,对于认识法律上人格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意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法律人格制度的身份标准,由于能够任意的剥夺社会个体的人格,拒绝在法律上赋予人应有的平等的主体地位,最终被人的理性所决定的伦理价值取代。在《法国民法典》立法者的眼中,生命等人格要素因其具备在人的理性上产生的伦理的属性,天然的具有自然权利的神圣性,因此不能降格在民法典中规定为一项权利,法典要做的仅仅是对于侵犯生命等人格要素的行为在法律上进行规制。继承康德思想的萨维尼,在法律人格制度人的理性标准之后又提出了权利能力标准,将人的理性置换为权利能力。虽然在萨维尼后法律人格的依据由人的理性演化为权利能力,完成了民事主体的实质基础从自然法到实在法的转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伦理观念让位于法律技术,人的平等、自由、尊严等依然被认为是内在与人的人之为人的固有要素。以人的理性或权利能力为标准的法律人格制度在本质上都是以生命的维系和保全为目标的,只是实现的手段有所不同罢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任何人类历史都是以生命个体的存在为前提,关注生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所有的法律实践只不过是这一现实情形的真实反映而已[1]朱晓峰:《人格立法之时代性与人格权的权利本质》,〔石家庄〕《河北法学》2012年第3期。。因此,近代民法上的人格权始终是建构在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之上,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它从人的本体中引申出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诸多人的存在不可或缺的人格要素,再由法律按照人的本质进行“确认”,从而以法的保护来实现维持个人生命的存续、保持个人身心的健康和自由的主旨。这种建立在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基础上的,内含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人之所以为人的本体要素的人格权可以称之为自然人格权。
2.人格的外在结构与社会人格权
通过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法律人格制度的具体内容是有所区别的。在罗马法上,家庭是维系生命、保障财富的最佳形式,身份也就成为法律人格的标准;在近代民法上,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人格的标准演变为人的理性和权利能力。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人权运动高涨,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上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虽然人的伦理价值作为法律上的人格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人的伦理价值的内容出现了明显的外化扩张的趋势。一些前人难以想象的社会现实——诸如器官移植、无性繁殖、克隆等新技术以及商品经济关系的蔓延导致人的伦理属性开始具有财产价值——迫使人的伦理价值所欲涵盖的范围急剧扩张,远远超越了近代民法的伦理哲学所固有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领域。显而易见的,传统的自然伦理价值观念已经无法涵盖所有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要素,尤其是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生物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生存和发展要素。新出现的知情、信用、生活安宁乃至居住环境等人格权益是难以被包含于人所固有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范畴内。而且,一些传统的人格要素,诸如姓名、肖像、隐私等与人的本体的距离其实远远大于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人的存在所必需的要素,人并不会当然的因为姓名、肖像、隐私等要素的缺失而无法生存,它们也不能当然的从人的本体中引申出来,事实上它们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一种体现和反映,是人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要求。近代民法典的“内在化的伦理价值”的观念,已经难以为人格权的发展提供生存的土壤,人的伦理价值观念出现了由自然本体向社会领域扩展的趋势。至此,人格权的一种新形态开始显现。那就是根据社会物质生活法权要求,建立在外在于人的社会伦理秩序基础上,以保护个人的尊严、促进个人的人格的健全和发展、维护和促进人性的发展为主旨,遵循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化伦理道德文明理念,由法律“赋予”的人在社会化的生产生活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种体现人作为一个社会体在社会生活中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内涵名誉、信用、知情、生活安宁、居住环境等人的本体外的要素的人格权可以称之为社会人格权,它的法律价值主要在于维护和保障人在社会化的生产生活中的生存和发展。
三、人格对人格权制度发展的影响
1.法律人格是人格权享有的前提
我们知道,法律保护有权利保护和本体保护两种模式。人作为自为地存在的意志,与外部事物的联系不是天然具有的,而是在意志外放的过程中实现的。意志外放的结果使人与物之间形成三种可能的关系:为我所有、为他人所有,或者是无主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个人使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4页,第2卷第118页。而在人的意志支配下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真正按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本性要求,来安排世界”[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4页,第2卷第118页。的行为。正是人的这种有意识的,发自本性的自主行为,使人在作用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具有了“对一切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力”[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2页。。在法律上,承载主体与客体连接纽带,将特定的人与外部事物进行连接的则是权利。正是基于权利的存在才能逻辑地推演出人对于外部事物的拥有,进而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对于外在于人的事物的保护称之为权利保护模式。但是,当权利客体内在于人的情况下,权利反指人本身,主体与客体发生了混同,法律则不能再以权利手段进行保护,而只能通过人之保护来实现了。这种对于内在于人的事物的保护称之为本体保护模式。
历史上,人格权的保护并未以正面赋权的形式进行规定,而只是通过“框架式”权利结构模式作出一般或抽象性的、由侵权法进行救济的保护性规定。我们在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和1811年制定的对《德国民法典》有重要影响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是找不到人格权一词的。即使是在1896年制定的规定了侵害姓名权民事责任的《德国民法典》中,对于生命、健康、身体等人格要素的保护,也只是“非赋权”式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或过失地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负有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的义务。”由此可见,德国民法是通过侵权损害赔偿来保护人格要素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某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受到现实侵害的时候,才应当由侵害人对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是一种间接的权利保护模式,或者说是救济性保护模式,而并非像物权、债权那样的直接权利保护模式。在这里,“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与所有权和其他权利并列,只是因为人格要素需要得到像“权利”一样的保护,但它并没有被定性为“权利”[4]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被誉为“20世纪大陆法里程碑”,专篇规定了“人格的保护”,对人格权的保护可以说是最完备的。但其仍然仿照法国民法,未对人格权作出分解式的、具体的或者说是正面的规定[5]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北京〕《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民法上,采取本体保护模式进行法律保护的人格权是作为内在于人的价值,是与人格一样建立在自然法思想上的天赋权利,是人成为法律主体的前置条件。正基于此,有学者认为人格与人格权实质上是同一东西,只不过是不同层面的表现形式。
“术语意义上的人格权,换言之,被理解成人作为人的自由实现的人格权,是19世纪的成果,最早产生于德国。”[1]转引自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载《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它是由萨维尼的学生普赫塔提出来的,然后由法国学者布瓦斯泰尔传入法国。及至“二战”以后,随着人权运动的高涨,人的伦理价值所欲涵盖的范围更是急剧扩张,远远超越了近代民法的伦理哲学所固有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领域,而扩展到诸如知情、信用、生活安宁乃至居住环境等方方面面[2]马俊驹张翔:《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及其立法体例》,〔北京〕《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在人的伦理价值内容外化扩张的基础上,人格权也发展为自然人格权和社会人格权两种形态。如果说建构在内在于人的自然伦理上的自然人格权尚可以被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通过人之本体保护模式进行保护,那么建构在外在于人的社会伦理秩序上的社会人格权,是无法被包容于“人所固有的东西”的范畴之内,只能通过权利保护模式进行救济。在现代民法中,罔顾社会物质法权要求的变化,简单地将人格权纳入天赋权利体系,固守其是一项天生的、从娘胎里带来的权利的观念,势必不可避免地造成人格与人格权价值体系的混乱以及人格权内部体系的逻辑冲突。
事实上,人格是以一种“法律上的命令”的形式出现的、市民社会的主体资格,是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如果没有人格,民事交往的参加者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主体;人格权则是由私法赋予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法律确认或规定的一种民事权利。人格的本源和根基是应然意义上的主体权利要求,是主体对其地位和社会生活中角色的权利要求[3]眭鸿明:《权利确认与民法机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278页。。在民法制度中,法律上的人格体现为赋予某些社会存在以享有权利及承担义务的资格,并使之成为民事活动的主体。如果没有法律上的人格,民事交往的参加者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可能享有法律上的权利。这种主体资格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普遍享有、平等享有的,它不以主体的意志而转移,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民事权利则以人格为源泉,是利用这种资格、前提获得的结果[4]眭鸿明:《权利确认与民法机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278页。。民事主体在人格平等的条件下,实际获得的民事权利是不一样的。虽然人格在民事制度中体现为相对抽象的主体权利能力,包含了人在法律上所能选择的全部权利,但由于每个人的能力和实际参加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有限且不一致的,因而实际享有的民事权利也是有限且不尽相同的。主体享有人格是一种常态,而主体能够享有民事权利则具有偶然性。这两类法律现象处于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前提一个是结果。人格实乃人格权的基础[5]徐国栋:《再论人身关系——兼评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第3条》,〔北京〕《立法研究》2002年第4期。。
2.人格权是私法赋予个体生存、发展的基础
人格权作为现代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权利的观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是,有学者在对《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人格权虽然是个体生存发展的基础权利,但不是一种法定权利,更非一种法定私权(民事权利),而是一种“天赋权利”(自然权利),是直接依据宪法生而有之的[6]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北京〕《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由此引发出两个问题:一、人格权到底是自然权利还是法定权利?二、人格权到底是宪法权利还是私法权利?
自然权利与法定权利不是必然相互排斥的两个概念,它们之间存在客观的联系。任何权利,要想得到法律的认可,都应当既具备自然法基础又满足功利前提,前者关乎正义,后者牵涉到效益,而正义和效益正是法律乃至权利配置孜孜以求的两项价值目标[7]彭学龙:《知识产权:自然权利亦或法定之权》,〔北京〕《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8期。。从法哲学理论而言,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概由一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即是以实定法的名义反映的自然权利[1]胡锦光:《当代人权保障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人格权非法定主义”源于人格权与主体存在具有的同期性以及主体的无意识性,即主体产生,人格权即取得,主体消亡,人格权亦灭亡。而且,人格权的享有与主体的意志无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主体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人格权,不影响人格权的客观存在。正是因为人格权与主体的密切关联,传统民法理论多将人格权领会为“人的固有权利”[2]樊荣、眭鸿明:《自然人人格-人格权之本源及制度设置》,〔南京〕《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而这种固有人格权就是前文所定义的内含了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诸要素的自然人格权。虽然这些人格要素是内在于人,但若不通过法律进行确认和保护,这些内在于人的要素是不能成为法律主体所实际享有的权利的,而且在受到侵害以后也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救济。同时,自然人格权要素受制于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在不同的社会中受到的保护的范围和程度是不同的,但也始终没有脱离法律的规制和约束。在笔者看来,所谓的人格权非法定其实质只是说自然人格权是由实定法根据自然法的人的理性本质进行“确认”的,而不是由实定法直接进行创造性的“规定”的。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应用发展,在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已经对启蒙时代以来确立的人的定义及人格尊严等内在伦理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人的伦理价值出现了外化扩张的倾向。伴随着堕胎、人工生殖技术、克隆技术、安乐死等一系列社会和技术问题而产生的一些新的价值理念已经无法被包容于“人所固有的东西”的范畴之内,近代民法典的“内在化的伦理价值”的观念,已经难以为它们提供存在的土壤。因此,人格权在突破“内在化的伦理价值”的观念基础上,发展出了外在于人的新的类型——社会人格权。社会人格权内含的知情、信用、生活安宁乃至居住环境等诸要素都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只能通过赋权性的立法保护模式,以权利作为连接纽带将人与外在于人的事物连接起来。既然社会人格权包涵的诸要素是外在于人的,并且是通过权利实现了与人的本体的联系,那么无疑的,社会人格权也是一项法定权利。
至于人格权是宪法上的权利还是民法上的权利,属于人格权本质属性的问题。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是私法上的人格权先于宪法上的人格权的保护,罗马法中就已经存在对生命权、姓名权的法律保护,宪法中规定人格权只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为了保障公民免受国家暴力的侵害而将私法上的人格权上升为宪法上的人格权,不能因为现存的宪法规定了人格权或者说人格权是基本权利并由宪法规定而否认其私法性质。在一个“金字塔”位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与其下位阶的部门法不是一种僵硬的单向关系,宪法与下位阶的部门法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私法上的权利基于社会利益的诉求可以上升为宪法上的权利,另外宪法上的权利或其保护的价值可以作为立法或法律适用的解释和新的权利创设的正当法源。正如王泽鉴所言,人格权被肯认为宪法的权利,使人格权由私法提升到宪法的层次,不但强化了人格权在宪法上的保障,对私法人格权的发展亦产生影响[3]王泽鉴:《宪法上的人格权与私法上的人格权》,载王利明主编:《民法典.人格权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也正因为此,人格权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一般的社会伦理,在寻求保护之时,一方面得保证他人不对自己的侵犯,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力量的强大必须对公权机关给予约束才能保证人之社会存在的主体性。所以,在人格权的保护上存在宪法保护和私法保护。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承载着保护公民免受公权力的侵害。但宪法在人格权中并非赋权性的规定,如我国宪法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其本身不是在创设人权,而是对人权提供保护,防止来自公权的侵害。同样的宪法规定自由权,旨在于对私法中自由权与政治自由权提供保护。因此,人格权的赋权不是来自宪法而是由民法来完成的。
〔责任编辑:钱继秋〕
解维克,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