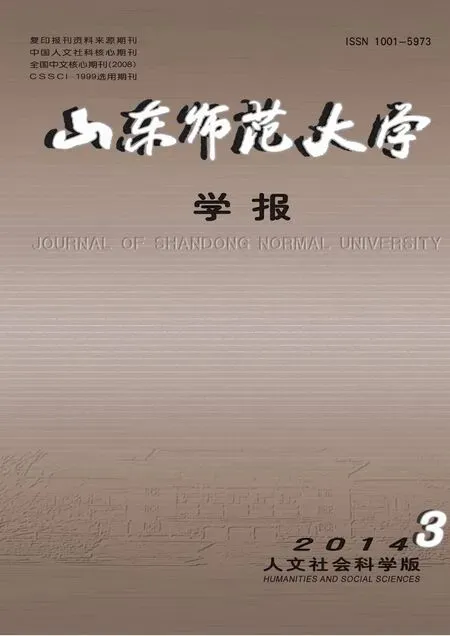聊以充数的治学经验谈*
杨 义
( 澳门大学 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国 澳门 )
聊以充数的治学经验谈*
杨义
( 澳门大学 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国 澳门 )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在大量的文献积累、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把小说史作为一货真价实、本色当行的史来写。这样能够保持它文学历史发展的整体的面貌和原始的状态,也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思考的空间和研究的可能性。学术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需要我们的生命和精神的投入。之后,让它形成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这是一种智慧,它包括经典重读,包括古今文化的丰富资源,以及对古今资源的重新认识和重新组合,形成现代中国的立足点上展开一个原创性的理论世界。学术如果要作出属于自己的新境界,就需要有生命和智慧的深度投入。
“三力”协同;“四环”联动;管理突围
我的学术还处在进行时,还在不断地探索和开拓,因此现在谈治学经验之类为时过早。如果不得不谈,只能从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谈起,聊以充数。
这部小说史据说是我的成名作,也是我在学术界开始站稳脚跟的一部著作。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一代研究生,现在号称“黄埔一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那代研究生。当时条件很差,差到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只在北京师范大学借了两层旧楼,“借窝下蛋”。好处是对面就是锅炉房,打开水比较方便。但学习风气还比较好,这一代人比较刻苦,六个人住一间房,还能集中精力看书。这一代人比较能够思考一点问题,从颠三倒四的历史曲折中悟出了很多问题,多少带有思想者或社会文化观察者的气质,和前代学者不一样,跟后来的学者也不太一样。
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在1980年代还没有人这么做。那时候都“集体写史”,可能有一两个老先生带着一二十个人,或者是由好几个高校联合起来写,这样写出来后,好多人都能够评上职称。我当时是初出茅庐,才30多岁,想独立地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实在是“无知者无畏”,别人都是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个项目的。它当然沾不上国家重点项目,也不是院里、所里的重点项目。在鲁迅研究室的七个项目中,它排行第七。我就是在一分钱的科研经费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这个不算小的工程的。它没有成为“豆腐渣工程”,大概只是因为自己是农村来的孩子,不怕吃苦,觉得怎么辛苦也比我少年时代在农村里种地、挑粪、插秧、割稻子要轻松许多,总是可以有股劲头把它做下来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也没有多少才华和科班训练,就是读起书来,心无旁骛,比较专注。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李白在山中读书,想半途而废,从一条山溪经过,看到一个老太婆在磨一根粗大的铁杵,问她磨来干什么,说是要磨成绣花针,给她的孙女当嫁妆。李白由此专心读书,成了大文豪。我后来到过李白的故乡青莲乡,那里的学者指着一处陡峭的山峰说,那就是象耳山,有李白读书台,山下有磨针溪。李白是天才,我辈是不敢高攀的,但却记住了老奶奶那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话。多年苦读的经历告诉我,专注地钻研问题,是可以水滴石穿的。毛泽东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即使再蠢再笨的人,你在一个问题上不断地严肃认真地思考它,这总是心灵上的一种接力,总是一棒一棒地能够达到终点。
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10年中,我没有离开北京开过一次会,也没有想过要去国外镀镀金,真是不足为训的死脑筋。为了写这三卷书,我确实是下过“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没有磨绣花针而磨剑,前前后后读了2000种书。进行一项研究,必须明白这项研究的实质,做一个明白人。做学问,一要认真,二要明白。在我的意识中,写史就应该写“信史”,把材料原原本本、尽量翔实地告诉读者,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体例和行文中,不是说用你的思考来代替别人的思考。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或以自己从西方捡来的一个概念去肢解历史过程的完整性,那是史论的写法,不是史的写法。
真理就存在于原本和朴实中。写史要把最原始的材料通过你的记述,通过你的结构,原本可靠而丰富翔实地交给大家,使人家从各种各样的角度都能够取得最初的知识起点,再重新去思考,重新去整合。我们有些史可能过于重自己,觉得自己采用的接受美学、女性批评或者是什么,最为高明,只要用上这些观点,我们的史重写了,就好像是突破了,又是一个新的阶段了。但是,当别人对你的观点不那么感兴趣,或者潮流一过,人家再来看你这本书,将可能一无所获,或者所获甚少。因为你的所有的材料都是给你染色了。所以,我觉一个史家写史,和史论家、政论家发议论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和政论家贾谊的不同。我是在大量的文献积累、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把小说史作为一货真价实、本色当行的史来写作。这样反而朴素、直截,能够保持它文学历史发展的整体的面貌和原始的状态,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思考的空间和研究的可能性。
有人很纳闷,为什么我在现代文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专家以后,忽然转入古典文学研究?人们已经习惯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分家,觉得“隔行如隔山”,谁要从这个山头走到那个山头,就可能引起大惊小怪。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文学发展的长河原本是由古至今,源流互贯,一脉相承的。人为的学科分割,可以将每一阶段的研究做得更细致,但画地为牢,有可能失去文学演进规律的深层把握。中国文学3000年,形成漫长的曲线和网络,随意切线一个短时段,都有可能把曲线切成直线,把网状变成线状。其次,我在一个国家的研究所里工作。研究所给你提供的文化视野和学术空间,是跟在一个地方的机构,或需要分学科教学的学校不太一样。因为不坐班,个人拥有的时间很充分,只要你愿意读书就会有时间,就不妨把学术规模设想得大一些。文学研究所的图书馆是郑振铎、何其芳、钱钟书等前辈学人建立起来的,古今藏书都非常丰富而精到。面对这样的图书馆,而不博览广涉,简直是天理难容!
古今贯通也是对原有学科格局的突破。首先要找好切入口。既然我已经写出三卷《中国现代小说史》,那么按照学术内在的逻辑,最佳的切入口就是古典小说研究。因为你已经掌握小说分析的窍门,别人对这一点也已经认可;同时你为现代小说进行探源,别人也不觉得你去夺人家的饭碗。其实,我自小就读过一些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唐》,还有流行于民间的《五虎平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七剑十三侠》之类,至于《红楼梦》则是大学时从同学手中借来看的。小时候记忆力好,对古典小说不算一无所知。由于按照学术内在逻辑,选择了这么一个切入口,你也就自然而然地获准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项目。
其次的问题,在于找好切入口后,如何下手。既然进入了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进入了一种需要重新耕耘和思考的学术领域,就要从新整装,准备吃苦。从新整装,就是找古典文学领域值得钦佩的学者,看一看最初的文稿。我找了本所的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他们读了我一两篇稿子,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也指出一些按照古典文学研究应该如何表述之处,使我注意到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套数。准备吃苦,就是在新的领域大量读书。必须特别严格地要求自己,越是走到一个新的原是别人的研究领域,就越是要自重。别人出一分的力量,你就出五分的力量;别人出五分的力量,你出十分的力量,把文章写得严谨扎实,像模像样。学术是没有止境的,是一个不断地当学生的过程。我进入古典文学领域之后,即便当了所长,上台发言的第一句话,总是说,我是转行搞古典文学的,是一个后来者,是一个学生,是向大家学习来的。在具体研究时,则全力投入,务求有所斩获。
在写《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几年,我确实认真地下了一番狠功夫,也因此创造了一个小小的记录。《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这本书,居然有六篇文章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有两篇是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发表的。40多万字的书,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竟然转载了将近30万字。韩国、新加坡都有教授认为:“中国有两个杨义,一个研究现代文学,一个研究古典文学,都有出色的成果。”《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被1995年底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点联席会议,推举为“近年成就斐然的小说史研究”七部书之首。所以,我觉得迈进古典文学的这一脚是沉重的,但也是踏实的,绝对不是儿戏的。在开拓一个新领域的时候,更要注重自己的学术姿态。首先要思考有没有立足的空间,开展原创性学理建构的空间。不是一般地为某个领域的一百本书增加一本书,变成一百零一本,而是在这个领域开辟了新的思路、新的境界。就是说,我不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地去写一本书,而是走上一个新的审视台阶上,一个新的视境上写下第一本书。不妨设想一下,这些史论文章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上都能够发表呢?因为它们观察到的研究价值、审美方式,是别人没有看到的,讲出来的理念见解是别人还没有讲过的。比如说,20世纪的古典小说研究,是接纳了西方的小说观念,来解释中国小说史现象和小说经典的价值。西方的小说观念对我们当然有启发作用,但也潜伏着与我国本土原有的小说概念、小说经验、小说智慧的错位,不能完全吻合。二者有相通的地方,又有差异的地方,有合也有不合的地方。如深刻地研究,不是从随声附和开始的,而是从发现差异、发现问题开始的。这就需要对使用多年、使熟手的西方的小说观念和理论的拐杖,进行检讨和反思。这是一种“了解后的反思”,反过头来对西方理论的概念、内涵、外延和科学论证的方式,以中国的经验和智慧进行验证和对质,该接纳者融合之,该扬弃者扬弃之,该调整者调整之,更为关键的是该新创者新创之。从而在新的中西平等的文化对话中,扔掉陈旧的拐杖,回到中国本身的小说观念、经验、智慧当中,进行一番还原研究,在还原中实现深刻的理论思想创新。
有人注意到我研究《中国叙事学》和中国诗学的时候,有一个很别开生面的特点。《中国叙事学》被中国大陆或台湾的一些教授称为“建构中国化的叙事学理论原则和操作规程”的力作或里程碑。这些溢美之词,虽或不敢当,但也反映了我做学问,不像某些当代学者直接套用西方的叙事学和诗学理论,只拿中国的作品当例子。我的著作,包括我的《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都是从文学经典中体验自身的理论生成的内涵和方式。虽然有些观点具有探索性,未必能够很快地被某些学者接受,但它们是新鲜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这可能主要是与自己的学术经历有关系,说明我是先从一个文学史家变成一个文化学者,有自己知识生成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我是从文学史家大量阅读中国典籍的经验中,去思考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身份认证、话语设定、评价体系和学理体系的。这样在接触西方理论时,我总是采取一种对话的既借鉴又质疑的姿态。比如说,在阅读西方叙事学的时候,就没有忘记我的优势是读过几千本中国古今的叙事文学,包括古典小说,现代小说和史学,甚至一些戏剧。既然读了这么多文献,就总觉得它应该有自己的一个解释体系和话语体系,用它来和西方的理论进行深层次的对话。
对于西方理论,我不仅注意到它的术语和观点,更注意到它的知识发生和智慧发展的过程。过程是一种生命形态,更能透视理论与历史、文化、思潮、时尚及个人趣味的关系。比如说诗学,西方的诗学是怎样产生今日的学理体系?我就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兰图书馆,普查了1900多种以“诗学”为关键词的西方著作,对它们存在的类型和学理脉络,进行统计学的分析。巴赫金怎样产生“对话诗学”和“狂欢理论”?他显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作品,进行经典重读和个案分析,也就是面对原本的审美生命,以经典作品的权威性支撑理论的说服力。我们直接面对经典,从中产生出同样话题,在同一个思维层面上进行新的生命体验,然后去跟西方对话,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思路。这个学术思路要求我们超越陈陈相因的文学史框架,超越简单刻板地讲时代背景、作家身世、思想性、艺术性、作家影响这种“五段式”,因为这个思路很难一下子突进经典作品的生命的本原。我们的祖先留下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智慧,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面对资源和智慧,以之同西方理论对质,从而产生新的学理体系呢?是的,西方所有的理论书需要读,中国古代所有的诗评诗论诗话都要读,力求把它们读懂读通,以便使我们的现代智慧拥有深厚的基础。但是我们读的时候,不能束缚和遮蔽我们的感觉、悟性和原创能力,而是要保留我自己去直接面对艺术作品的原本生命的阅读权。所以,学术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需要我们的生命和精神的投入。投入之后,让它形成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这是一种智慧,它包括经典重读,包括古今文化的丰富资源,以及对古今资源的重新认识和重新组合,形成现代中国的立足点上展开一个原创性的理论世界。学术如果要作出属于自己的新境界,就需要有生命和智慧的深度投入。
我接触少数民族文学,开头是因为职业的需要,因为1998年以后我既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又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有责任去了解少数民族文学,思考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地位和发展动力。我是以学者的身份出任所长,接触新的学术领域的,不满足于讲套话。由于有备而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专家说:你真正地进入了角色。该所最优秀的一批专家对我的学术讲话,兴趣很浓。这个所长我做得相当辛苦,除了行政工作之外,还要阅读大量的材料,从大量原始材料开始涉足新的学术领域。比如《蒙古秘史》结尾说:“此书大聚会著,鼠兒年七月,于客鲁连河阔迭额阿剌勒地面处下时,写毕了。”由此考定此书于蒙古阔窝台十二年(公元1240)写成,至2000年召开760周年纪念会。我就从该书开头的汉语译音对应译成的“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谈到《国语·周语上》及《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以及《北史·突厥传》、《周书·异域传》、《隋书·北狄传》,分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狼图腾”,以及蒙古族以狼、鹿为始祖的凶猛与仁慈合构的民族性格。由于我是全国“格萨(斯)尔领导小组”组长,在第一次会议上,我就提出了“《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并对江河源文明作为高山文明,作为东亚、中亚、南亚文明结合部,藏族、蒙古族文明结合部,以及丝绸之路一侧所形成的复杂文化要素作了分析,从而使地域性的文明纳入中华总体文明的大格局。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对于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本质意义。中国文学史不应该停留在少数民族文学缺席的状况,那只是汉语文学史,是不符合中国多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和文学发展过程的。在中国文学史中,必须形成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共生互动的命运共同体的总体形态,唯有如此,才能深刻地揭示存在于其间的文化哲学和审美哲学。因此,我在2001年北京香山会议上提出:“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幅地图是在对汉族文学、50多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这样的地图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2003年我在剑桥大学当客座教授时,又发表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民族学问题》的讲演。当一个学者跨越了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叙事学和诗学、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广阔领域时,他必然思考,我的学术中“一以贯之”的精神线索是什么?它不应该是一个杂货摊,而应该有一种相互贯穿的价值结构和学理体系,形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知识共同体。在这种贯通性思维中,我提出了“大文学观”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希望这种文学地图成为中华民族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
我做学问,往往不是采取单线延伸的方式,而是多线交互推进,因此在学术路径上提出“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综合运用的“五路径”说。其中“脚学”,即多做田野调查,值得说一说。自古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近七八年,我借外出开会或讲学的机会,考察全国各地古代文化遗址和作家遗迹,大概有一二百处。除了搜集地方文献,及与当地文化人交流之外,随便搜集与古典文学相关的图画,包括遗址图谱、作家图录、古籍插图、出土文物照片、家族谱牒、博物馆收藏图画集,已经积累了两万种以上图片。积累多了,就形成规模效应。比如说,明清以前的关于《楚辞》和屈原、宋玉的图片有400多种,关于王维的书画图片有100多种,关于李白、杜甫的图片有600多种,关于苏东坡的书画图片有500多种,关于蒲松龄和《聊斋》的图片有300多种,这就可以对它们之间的渊源变化,它们所反映文学接受的历史及各个朝代的士人风习,做一番比较研究了。我著有《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收录的各类图片有1000余种。
图志式的文学研究的关键,在于把图也当成文学史的原始材料,看到图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量,图也是一种语言,以构图、线条、色彩、风格传达出来的不着文字的超语言。图与文学史叙述形成图文互动,构成可以多重解读的互文性。如此形成的文学图志的基本特征,就是把文学史、艺术史、文明史相互沟通。这样的文学史就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文史掩映,图文互释,用文字、图画、文物、实景照片等多种语言方式,来激活阅读过程中的情感、理智、感觉和悟性。1923年俞平伯、朱自清同游南京秦淮河,后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同题散文,成为一时美文的典范,传为文坛佳话,这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早已熟悉的。然而游罢秦淮河,二人南京分手前,俞平伯寄给朱自清一张明信片,正面图为南京夫子庙秦淮河景色,背面则有俞平伯题诗《秦淮初泛呈佩弦兄》:“灯影劳劳水上梭,粉香深处爱闻歌。柔波解学胭脂晕,始信青溪姊妹多。”如果把这张明信片的图像和俞氏手迹,与对二人游记美文的评述相配搭,自可窥见现代文人未脱传统士大夫的神韵风流。岁历一个甲子之后,俞平伯为诗文集《秦淮恋》作序说:“我与佩弦兄的同题散文能流传至今,实在是借了秦淮河的魅力,并非我们有什么神奇的功力。”青溪灯影犹在,故人已逝,情何以堪。
再比如,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增订本,1946年11月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封面由炎樱设计。张爱玲如此交待:“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那么,所谓“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出自何人之手?经过查证,原来是晚清吴友如《海上百艳图》之《以永今夕》。但是原图的画面已被切去三分之一,切去坐在床前矮凳上,手引长绳牵动风扇的婢女,安在屋顶的风扇钢架和长方形的扇叶也删去了。墙上仿绘得相当拙劣的蒙娜丽莎画像,被换成从屋顶垂下的华丽的烛檠。窗上已祛除半卷的竹帘,却特地寥寥数笔添上一个裸体蒙面的绿色鬼形,即张爱玲所说的“现代人”,以居高临下的姿势,凭栏探身内窥。窗户上鬼形侵入,隐喻着来势汹汹、有时又是畸形的洋风内扇,给一个古老的民族、一个温暾的家庭,带来了吉凶莫测的危机感。《传奇》封面,在平平无甚足观的晚清洋场仕女画上,以神来之笔三下五除二,便改造了其画品画格,于寂寞的闺阁风俗味中增添了令人感慨多端的文化动荡感和哲理性。如此封面,与张爱玲洋场传奇的小说相对照,令人感受到一股现代挟持传统,纤敏携带着苍凉,时髦激化了失落的上海香港浮世绘的复杂滋味。
引图入史,是要使文学史变得多重折光,美轮美奂,洋溢着人文情怀。西方世界讲文明史,总离不开绚丽多彩的古希腊雕塑和文艺复兴的绘画,中国“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这是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中的话。既然如此,我们在叙述自己灿烂辉煌的文学史时,为何总舍不得把眼光超出方块字以外呢?文献功夫是不可怠慢的,不仅如此,还应该在古代文献中读出新的意义、新的思想、新的趣味、新的生命,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总应该有一批学者采取新的形式、新的方法,包括借助这种已成专家之学的文学与图画互动的方式,从文明史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意义生成和历史进程,使以审美为对象的研究闪射出审美的魅力。我曾经说过:衡量一个文明发展水平,一要注意它的原创能力,二要注意它的共享程度。如果能够以一种文史掩映、图文互释的现代方式,把文学史的现代意义阐发得别具精神、别有滋味,以原创性学理带动共享性的魅力,这不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种学术境界吗?
(2008年11月谈话记录,2014年2月修订)
My So-called Experience in Respect of Academic Research
Yang Yi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The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is written as an out-and-out, and through and through history of fiction on the basis of accumulating,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Only by thus doing, ca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history keep its overall visage and its original state, and the reader be given more space to think and more possibilities to research with. As a matter of fact, academic research, as a sort of existence of life, also needs the input of life and spirit,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an organic of life. And this is a kind of wisdom which includes re-reading the classics, obtaining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old and new, and re-understanding and re-grouping these resources so as to form a foothold for modern China to unfold an innovative world of theory on. So if one aspires to break a new path of one’s own, one must put in deeply his life and wisdom.
“Three forces” synergy “Four Ring” interaction 不breakthrough in management
2014-02-08
杨义(1946—),男,广东电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讲座教授。
I206.6
A
1001-5973(2014)03-0083-06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