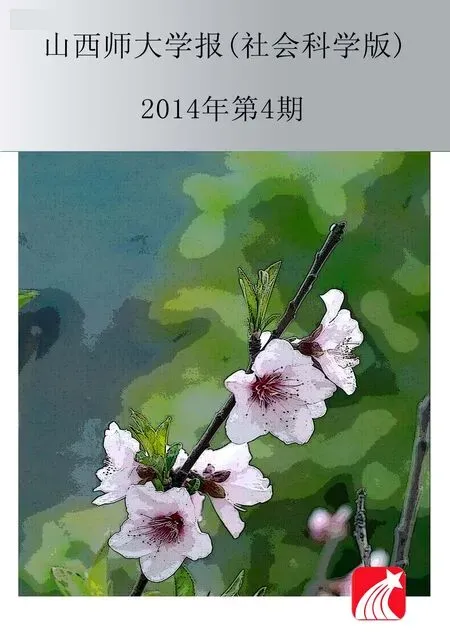译者身份今昔论
李国鹏
翻译是种创造性文化活动。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译者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翻译理论史发展的过程中,译者的身份并没有从起始阶段就受到重视和关注。传统译论一贯忽视译者在翻译的地位,使其一直以“仆人”、“翻译机器”和“戴着镣铐的舞者”等身份屈居,译者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而本文试图从翻译发展史角度比较译者身份的变迁。译者身份,从在翻译史绝大部分时期主体性的蒙蔽到“文化转向”后主体地位的空前膨胀,其身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本文分析了各个主体中心论的弊病以及主体间性给翻研究带来的全新视角,纵观译者身份的“昨日”和“今朝”,不难发现:翻译研究必然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而本文将从三个阶段,对译者身份的转变进行具体阐释。
一、不同阶段译者身份分析
1.语文学阶段的译者身份。在西方翻译史中,《圣经》翻译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希伯来语译成希腊语的第一个《圣经》版本是被称为《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的《旧约》。在那个时代,译者被视为“听写工具”,完全受上帝操控,没有任何自主权。译者的任务是做到逐字翻译,在翻译方面必须采取死译。从近两千年的圣经翻译过程来看,译者由最初的逐字翻译到词语层面上的自由,再到最终使用本族语进行的直译,者取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然而,归根结底来看,译者的身份只是原文内容的传达者。除了对原文内容的忠实传达外,不能有自己充裕自由的翻译空间。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译者把目光投向文学作品的翻译。翻译研究有了新的发展。17世纪英国翻译家德莱顿(John Dryden)把译者比作奴隶,他认为奴隶只能在主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这种观点与圣经翻译者的看法不谋而合,都认为译者无权也没有必要对原作语言进行调整,他要求译文必须与原文全方位完全契合,还要求译者在翻译中体现原作的风格和艺术特征。18世纪末,英国翻译家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在其著作《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1970)中提出了著名的译事三原则:第一,译文要完全复述出作者的思想;第二,译文风格笔调应与原文性质相同;第三,译文应像创作一样流畅。在这种翻译理论指导下,无论是翻译理论家还是译者都唯原作惟命是从。译者除了保证语言层面的忠实,还要表现原作的艺术特色。译者是原作的“仆人”。
2.结构主义阶段的译者身份。20世纪初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始。翻译理论研究开始语言学转向,翻译理论家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研究翻译。在这些人当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尤金奈达。奈达认为人类语言在语法、语义上有普遍性,拥有共同的内核。这样,原文信息不仅可以被确定,而且可以完全被翻译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这种语言分析方法使翻译活动变得有章可循。奈达曾提出”动态对等“以及”功能对等“的翻译等效论,要达到这种“对等”,译文必须从内容、方式、社会文化等方面尽可能多地反映出原文风貌。这一时期的译者不再拘泥于仅仅传达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同时也试图将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质带给译文读者。
结构主义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把翻译看作一种科学,语言规律等同于了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把翻译活动变成了纯语言的操作,这种视角认为只要译者努力寻找不同语言中共存的“内核”,就能实现文本的”等值“。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成为了有规律可循的语码转换,译者的文化创造性被抑制,也使译者沦为了”翻译机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较少涉及译者的功能和主导作用,研究领域也只集中在语言层面的转换。
3.后结构主义阶段的译者身份。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视翻译为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只是一味追求科学实证主义视角下的所谓客观真理,这使得翻译研究陷入困境。翻译研究者逐渐不满足于这种理论模式,开始突破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畴,开始从文化学、思维学、社会符号学等多维角度探讨翻译活动的规律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结果引起一系列的转变:从以原文为中心到以译文为中心,从规定性到描写性,从翻译过程到翻译产品,从语言研究到文化研究。
这一时期理论是多元取向的,包括目的论派、操控派、诠释派、解释学派等。这类译论削弱了原文作者与原文文本的中心地位,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自主性作用。目的学派把翻译看成一种目的性行为,原文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地位。操控派认为“翻译即改写”“译文是原文的后续生命”等。这种观点的传播使得译者获得了解放,终于摆脱了“仆人”的位置,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而“创造性叛逆”更是从理论上让译者获得了主动权。这一阶段的研究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充分肯定其文化身份,翻译研究已经从以文本为中心转向了以译者为中心。
二、译者身份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
通过对翻译理论历史“昨日”与“今朝”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翻译主体研究经历了以作者为中心到以原文文本为中心再到以译者中心的转变。但这三种翻译主体中心论范式有着其严重的弊端。“作者中心论”范式中,原文作者的主体性被绝对化,作者成为解释文本的唯一“上帝”,译者的翻译以重建作者的意图为目标,读者的译者主体性身份被完全蒙蔽;“文本中心论”否定了作者意图决定文本意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张对文本进行科学分析。可是这种研究范式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仅仅关注原文文本的词、句、结构等语言层面的东西,陷入了对语言规律的迷信,从而走上了语言决定论;“文本中心论”则过分强调语言的共性,把翻译看作两种语言的对等项转换过程,造成译者主体性的“死亡”;“译者中心论”范式下,译者以叛逆者、改写者的姿态位于中心位置,文本被最大程度弱化,“作者已死”,传统的忠实、等值的翻译标准在后现代背景下都成了碎片。语言规律被颠覆,意义确定论消失,译者被赋予绝对的阐释权,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
纵观翻译研究译者身份的转变历程,三个范式只是片面关注译者—文本,或译者—读者等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对立关系都是不平等的,总有一方处在优先地位,这也正是主体性哲学“主—客两分”的认识论思维模式的体现。在这种条件下,主体间性哲学给正陷于“单一的主体性”研究困境的译界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研究视角。主体间性又叫主体交互性,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对话、交往,意味着主体间的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多元的价值相互依存,实现对等的生存法则。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作为两种文化的中间媒介,必须接受赞助人的主导,也得迎合读者的期待,更要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则不可避免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要体现文化身份和取向。原作作者主体必须要充分理解甚至接受译者主体的行为。当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需要学会鉴别、衡量采取何种变通和补偿手段,以尽量消除或减少两种语言间的差异带来的隔阂。同样,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要充分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期待读者去理解和共鸣。在主体间性哲学视野下,翻译活动的三类主体,即译者翻译主体、作者创作主体、读者接受主体不再是互相压制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
三、译者身份“昨日”与“今朝”
历览翻译理论发展史的“昨日”与“今朝”,从圣经翻译的“听写机器”,到语文学阶段的“葡萄园里的奴隶”,再到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的“翻译机器”,译者的主体性都被蒙蔽。而到了后结构主义阶段,译者被赋予最大限度的诠释空间,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但是诠释空间不能因为译者翻译过程中主体性地位而盲目夸大。如果译者的主体发挥过度,译文的可信度和可接受度就会大大降低。这种译者中心论是一种片面极端、不成熟的主体性。要避免这种单一主体研究范式的不足之处,翻译研究就必须在主体间性哲学的范畴下进行。翻译主体研究不应只以译者为主体,而应该把作者、读者等都看成是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取消二元对立。翻译主体间性研究视角下的主体关系是全面的、辩证的、较充分发展的关系。因此,本文通过对译者身份今昔的对比分析,最终认为翻译研究必然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
[1]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2] Nida,E.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陈大亮.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J].中国翻译,2005,(2).
[4]陈洁.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译者身份变迁谈起[J].科教导刊,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