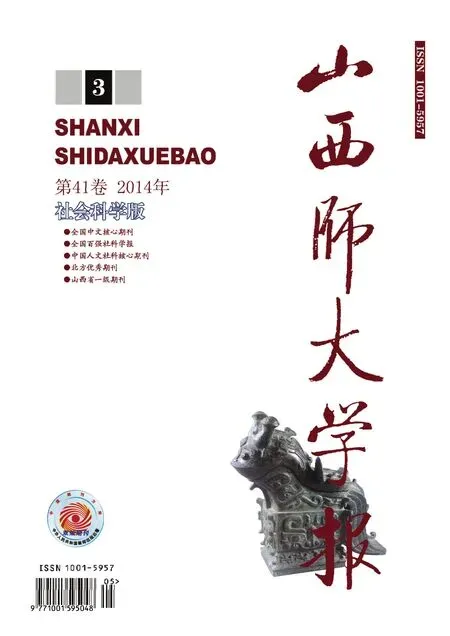平等的不平等机制还是不平等的平等机制?
——后T·H·马歇尔时代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论走向
张 正 瑞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州 450001)
肇始于17世纪新兴资产阶级追求统治地位过程中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承继了中世纪城市公民的自治传统,在其概念化过程中,T·H·马歇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公民身份在西方理论界复兴以来,无论是以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以T·H·马歇尔的权利话语体系展开自己的论争。反观马歇尔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后马歇尔时代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当代论争,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已由马歇尔所言的“合法的”平等的不平等机制转向为不平等的平等机制。
一、T·H·马歇尔自由主义公民身份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9年,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家T·H·马歇尔接受剑桥大学邀请,在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年度纪念大会发表演讲中阐述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1]33—34主要内容如下:
(一)个体权利本位的公民身份观。马歇尔生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竞争的时代,战后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平等的首要关注,使马歇尔深感不安,并试图从学理上对经济平等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回应。首先,马歇尔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范畴,简化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工人阶级概念。认为,工人阶级的典型特征无非是繁重而过量的体力劳动,这种劳动在发达工业社会是可以大为减少的。工人阶级“正在逐渐发展自己的独立性,男子汉的自尊以及对他人彬彬有礼;正在逐步接受一个公民的义务和公共责任;正在逐步加深他们是人而不是工具的理解;正在逐步成为一个绅士”[2]5。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谴责由于职业的不同,而造成的“绅士”与“非绅士”之间实质的不平等和差异,自信技术的进步能消除工人阶级的“非绅士”状况。马歇尔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工人阶级概念视为真理,但他不满意其对公民生活标准的定量评价,当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公民身份看做熟练工人在成为绅士过程中学会的东西时,马歇尔评价道,阿尔弗雷德5马歇尔所提到的仅仅是公民身份的义务,而不是权利,认为应以文化上能否成为社会完全成员而分享社会遗产的公民权利,作为衡量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是否拥有平等的总体性评价。其次,在他的眼中,社会主义者是一群高尚而幼稚的狂热之徒,他们身上存在的忘我的美德,是以丧失自由为代价的。即使是在为保证公民平等的过程中,国家也不得不提供范围更加广泛的国民教育。实际上这也是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干涉。第三,其公民身份是一个“个体本位、权利平等”概念。正如他所言:“当你对一个赤贫者说他和一位百万富翁拥有相同的财产权利,他一定以为你在胡说八道。”[2]18不过,从公民身份的视野看这位赤贫者是错的,因为公民身份的财产权不是占有的财产权,而是占有财产的权利。
(二)公民身份权利三要素及其历史进化论。T·H·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权利蕴涵了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三种要素。[2]7公民的要素由个人自由所需的人身、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权利,以及订立契约和拥有财产的权利及司法权利构成;政治的要素是指公民作为政治实体成员所应拥有的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社会的要素指享有分享社会遗产而过上一种文明生活标准的权利。与此三种要素相对应的社会机构分别是法院、议会、教育机构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从英国历史上看,早先这三种要素是混合在一起的,其因缘是因为各种社会机构也是混合在一起的。梅兰特的研究为T·H·马歇尔提供了佐证:“我们越是向前追溯历史,就越是不可能在国家的各种职能部门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线,同一个机构可能既是立法议会,又是政府委员会和法院。”[2]812世纪英国王室司法体系的建立,确保了个人的公民权利;随后议会的产生,其关注点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社会机构开始了分化与整合,其结果是,公民身份的三要素分属于各自不同的原则来指导。马歇尔认为,18世纪之前的《人身保护状》、《宽容法》和出版检查制度的废除,之后的《天主教徒解脱法》、《结社条例》的撤销,以及争取新闻运动的成功,公民权利已经扩展到财产权,并在基本方面诞生了当代轮廓,法院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2]9尽管17世纪包括奴隶和农民在内的英国人已经成为自由人,虽然存在限制完全平等的复数投票制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废除,但19世纪理智和守法的公民不再因为个人地位而被禁止参加选举,政治权利被授予了范围更大的人。虽然民主需要时间来让公民体验并转换为对国家共同体的新意识,但公民参与的目的还是实现了。此外,经济的变迁,《济贫法》的出现,使根植于乡村社区、城镇和行会的传统社会权利荡然无存。但在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虽越来越需要受过教育的公民,强制性的教育才不被视为未成年公民的义务,而只能视为成年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教育相似,《工资管理条例》、集体协商制度,以及因年老、疾病、竞争失败等所需的社会服务体系,都不能视为弱势群体丧失共同体成员资格而降为二等公民所接受的慈善,而应是公民因共同体成员身份分享社会遗产而拥有的福利权利。公民身份所承载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三要素,与保障此三要素的法院、议会、社会福利体系三机构,是18—20世纪社会机构分化与整合的历史结果。
二、T·H·马歇尔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论旨趣
公民身份在古希腊,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意指拥有城市共同体成员资格,在城邦中“统治又接受被统治的人”。在希腊城邦小国寡民的社会里,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城邦安全与秩序,公民需平时参与公共治理,战时保家卫国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取得荣誉和财产奖励。公民身份具有积极的属性,贡献城邦不是公民义务而是公民美德。公民身份同时是一个排斥性制度,没有闲暇参与共同体事务的奴隶、妇女,只关注私人利益的商人和没有共同体身份的外邦人是不享有公民资格的。共同体优先于个体是公民身份的理念,使亚里士多德感叹道:“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3]9公民身份是居住于帝国疆域范围之内,受帝国庇护,而向国家缴纳税负责的人的概念。在漫长的中世纪,个体深受封建领主与教会的双重压迫,要么是领主的臣民,要么是上帝的子民,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依据的是等级森严的出生和血缘身份。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主权的确立,形成了以权利为主要内容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制度。
但问题是,T·H·马歇尔也承认,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制度。[2]17面对自由主义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在现实社会中的落空,特别是经济领域两极分化引起的社会分裂,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而可能导致资产阶级统治秩序面临丧失的条件下,改善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各项资本主义社会政策才得以出现。T·H·马歇尔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使用公民身份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是其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主要旨趣,即“平等的不平等”的合法性。“平等的不平等”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在他看来,首先是因为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必要的,即社会分层是激发公民勤劳智慧以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社会上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也必须以同样的态度迎接社会分层,这是促进经济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权力规划原则的依据。其次,自由主义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三要素,虽然也存在“司法成本市场价格”所产生的公民权利救济缺失,以及民主政治导致的“政治精英监督公民投票,而不是公民监督政治精英”、“教育本身便是社会分层的工具、社会保障产生的非共同体成员身份”等事实上的不平等。但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不平等,不是始自于传统社会不平等的身份、血缘等等因世袭所导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本身赋予文明以目的和意义;自由主义公民身份所导致的不平等不是制度的不平等,而是平等制度的副产品,且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减少到了最低限度。[4]16正如其所说的,“假设存在着一种与共同体完全成员身份观念——或者像我所说的公民身份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基本人类平等,而他与社会中借以区分各个经济阶层并不是不相容的。换句话说,只要公民身份的平等得到认可,社会阶级体系的不平等也许就是可以接受的。”[5]6
三、后T·H·马歇尔时代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论走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公民身份复兴之后的话语体系,远非T·H·马歇尔当年所乐见的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到社会权利平等地赋予每一位公民后所实现的公民自由与平等。对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社会实践后果首先进行警醒的是占人口总量半数的女性。早在18世纪,女性受自由主义思想启蒙,同男性一道争取自由和平等,但革命胜利后,女性却被拒绝给予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当时女性将自己受压迫的根源归咎于没有被社会视为与男性一样是一个理性的、独立的个体。奥伦比古日指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6]33但20世纪受教育权和其他公民身份权利获得之后,女性并没有感受到形式上与男性同等的公民身份权利给妇女带来的自由与平等。
首先,女性参加工作的事实表明,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很难兼顾。要么,被视为女强人;要么,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疲于奔命。其次,女性个性的发展和经济的独立使之更容易离婚。单亲家庭、未婚母亲、离婚率的上升,促使社会重新思考女性问题,导致保守主义的回潮。[7]此外,福利国家的公民社会权利,只有“工作者”的公民才能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保障,过多从事家务劳动,不能全职的妇女,则处于这种保障的边缘,已婚妇女往往要依附在丈夫的名下才能获得某些保险和扶助。[8]81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基于理性自主的公民身份理念认为,个体必须自行决定要成为何种公民,放弃一切政治活动,退避到一个仅仅由家人、朋友、市场交易以及自娱自乐的活动所构成的完全私人的世界,也不妨碍其保护私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根本目的。自由主义者往往会把女性群体在公共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低下的参与水平看作个人的自主选择,而忽视了女性在现实中的境遇和社会观念及体制对女性造成的压迫。当代女性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种兼顾“差异的普遍主义”的制度,以赋予两性平等的多样的地位。
以T·H·马歇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还受到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诘问。公民身份制度演进到T·H·马歇尔时代,那种排斥性的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早已式微,平等成为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最让人向往的一种道德理想。马歇尔曾无不自豪地宣称,公民身份是一种地位,一种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在这一地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以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和价值观为前提的,具有明显的文化同质化特征。为应对现实中共同体成员的文化差异困境,无论是T·H·马歇尔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者都宣称,国家在文化上是中立的。罗尔斯为论证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甚至设置了“无知之幕”的自由主义选择模式,在此模式下,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地位还是社会出身,也没有人知道他在自然资产、能力、智力、体力以及类似的因素在分配方面的运气。也不知道他们的善观念或他们的特殊的心理倾向。[5]12但在威尔金里卡看来,文化同质国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他说,如今大部分国家都是文化多元的,世界上184个独立国家中至少包含600多种语言群体和5000个族裔群体,只有极少数国家共享同一种语言或属于同一个族群。[9]1另外,自由主义政府的“善意忽视”和“中立性”也是虚假的。当代主要自由民主国家,在各族群之间远非“中立”,在其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中,鼓励甚至强迫生活在国家领土上的公民融入到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共同公共体制中,而这种共同语言是多数群体的主流语言,少数族裔只能处于有限的选择,要么接受同化,融入主流群体;要么简单地在自愿的孤立中生活,被彻底边缘化。国家通过教育、法院和政府部门的语言,公共假日的选择、内部边界与权力划分、移民等各种政策给予多数民族以特权,大大降低了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活力。[9]75为此,金里卡认为,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要真正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潜能,需发展一种以差异为原则的少数族裔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10]在“不平等中寻求平等”再次成为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主题。
此外,当代全球化也使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平等的不平等成为不可能。T·H·马歇尔英国语境下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平等的不平等机制,是以政治权力在民族国家疆域内充分有效、公民基于民族国家成员资格为前提的。帕特里·夏休伊特认为:T·H·马歇尔所阐述的公民身份有效运行的社会背景条件已经改变,不稳定的和明显难以控制的世界资本市场以及跨国公司对最低成本区域的无休止追逐,已经摧毁了一国政府实施旨在调节需求和充分就业的凯恩斯政策的能力。其结果是,底层群体不得不面对更高的失业率,上层群体的真实收入和机会得到实质性的增长,无论是缴纳更高的赋税还是居住在同一条街上,上层群体越来越不愿和其公民同胞共命运了。[11]249—268人口老龄化、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使福利国家制度的经济基础受到冲击,公民社会权利实现举步维艰。与此同时,战后就业方面不断增长的国际化,德国劳工、欧共体内合法居住的外国人等长期居住的移民,使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场所限度成为问题。哈曼认为,尽管发达国家战后对非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进入和迁入进行了严格限制,但在欧洲大陆,一个“特权性非公民”群体的数量还是不断增加了。他们有权利在一个国家工作、居住并获得社会救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投票。[12]31形式公民身份与实质公民身份并存,成为常态。在此语境下,T·H·马歇尔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是否提供了一个最有用的概念框架?为此,汤姆·巴特摩尔提出了一个使在任何共同体生活或工作的个体都享有普遍人权,而不必考虑与民族来源相伴生的形式公民身份的实质公民身份构架。[13]55—93在形式公民与实质公民之间,在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如何平衡以取得实质的公民身份权利,不是取决于T·H·马歇尔式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权利,而是取决于社会政策和社会性政策,要解决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平等问题,需在普遍人权的框架下讨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而不是公民身份的框架。如果以T·H马歇尔的话语思维表述就是:应通过社会政策和社会性政策调整,在不平等的形式公民身份基础上,实现平等的实质公民身份。
[1] Bryan.S.Turner.Outline of a Theory of Cizitenship.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Edited by Chantal Mouffe, Verso, 1992.
[2] 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 Jones KB. Citizenship in a Woman-Friendly Policy. Signs 15,(4).
[5]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6] 闵冬潮.国际妇女运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7] 张立平.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想述评[J].美国研究,1999,(2).
[8] Sylvia Walby.“Is Citizenship Gendered? ”, Sociology, Vol.28,1994:81.
[9] 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 张正瑞.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当代转向[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11] Patricia Hewitt. Citizenship Today: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H· Mashall, edited by Martin Bulmer and Anthony. M. Rees. UCL Press, 1996.
[12] Brubaker,R(ed.): 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n. London: University of American, 1989.
[13] Tom Bottomore.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Forty years 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