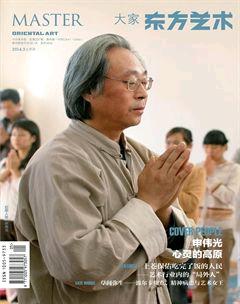工厂老板:原来这些产品的真身是艺术品
张瑜洋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小编带着采访的任务,一路“跋山涉水”地来到城乡结合部的金盏乡皮村工业区的北京利海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这个工厂成立于2004年,主要经营机械设备,成套仪器及机械零件的加工制造,以及自主研发产品阻尼器的加工制造。当看到这些资料,很多非装置类的艺术家可能会很疑惑,一个机械设备的工厂会与艺术扯上怎样的关系?
你是否曾经好奇过户外钢性结构的雕塑,以及一些巨大的动力装置作品的制作过程?你是否曾经以为那些作品都是艺术家独自完成?艺术家是否不仅懂审美,还懂焊接,承重等技术?诚然艺术家不是拥有“十八般武艺”的奇人,他们偶尔也需要工人的协助。在艺术家与工人一来二去的交流中,工人会不会被艺术感染?他们眼中的艺术家又具有哪些特点?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世界。
您的工厂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一个机械设备的工厂又是什么时候和艺术家打起交道的?
杜利明:2004年,在798附近成立。那会798艺术区还比较冷清,不过还是有零星的展览。2005年,有一个艺术家来到工厂定制一个重达一吨重的保险柜。在这个艺术家798展览开幕的那天,我找了七八个人连拖带拽的把那件“作品”放在了展厅里。艺术家在保险柜上开了一个圆孔,里面放了一瓶剧毒,随后将保险柜放在展厅的一个井边。当时我就很纳闷的问:用这样一件大的“作品”是想表达什么思想?他说就是一种安全意识。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只好点头示意“原来如此”。现在想想好像只记得有这么件事情,连艺术家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在那之后,又与其他艺术家合作过吗?
杜利明:有。五年前,邵译农老师来我们这里定做一些作品所需的零件。随后他又给我介绍了一些他的朋友。后来这里的艺术家就越来越多了。
在与艺术家的合作中,他们给你们的印象是怎样的?
杜利明: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艺术家有两大特点。第一:神经病,第二:都很穷。他们做的很多作品,我都不知所云,以前我都不加艺术家微信。在多次与艺术家的交流过程中发现有些艺术家还是比较有思想的,尽管他们的作品我依然看不懂。不过现代社会中不乏有些“非”艺术家冒充艺术家之名,搅得艺术家的名声并不是很好。
侯子建:刚刚认识郭工老师的时候,我去他在东风艺术区的工作室,发现他工作室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见过一些艺术家穷的时候,吃泡面都要按包数,要不然就只能挨饿。还要经常因为交不起房租而“流离失所”。有时候还是挺佩服他们那种为艺术执着的“牛劲”。
给艺术家做东西麻烦吗?
杜利明:这个该怎么说呢。艺术家的思想比较活跃,天马行空的。他们常常只构想作品的整体框架,但是从来不考虑实际的可操作性。有些时候一件作品需要反反复复的改,有时候一件艺术品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修改完成。不过觉得跟艺术家打交道比较有意思,所以也就不计较了。
侯子建:给艺术家做东西,只能抱着“玩”或“交朋友”的心态去做。要是按照生产正规产品的标准,那些活注定是会被放弃的。这个确实耗时,也耗材料。不过只要在我们工厂不是很忙的时候,有艺术家找来,我们都会去做。
艺术家在工厂做的艺术品,你们如何看待?
杜利明:尽管我现在和很多艺术家都有合作关系,但在我看来,多数艺术作品我是看不懂的。所以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职业习惯冠以它们“产品”之名。后来这些“产品”周游各大展览场所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原来这些产品的真身是艺术品。
侯子建:不知所云的事物。去年,一位艺术家在这里定做了一个昂贵的“煤气罐”,艺术品名称《寂静之蓝》。从艺术家提供思路到作品最后完成,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我至今还是不明白这件作品想要说明的问题与“煤气罐”之间的关系。看来不是艺术行业的,需要好好补课才行(笑)。
与艺术家的合作是主要盈利渠道吗?未来会开拓这方面的市场吗?
杜利明:我们主要是做非标产品,与艺术家的合作都是闲暇时间,并且他们的活不多。如果有艺术家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当然乐意,但主动开拓可能谈不上,毕竟我们认识的艺术家是有限的。
对什么类型的作品比较感兴趣?
杜利明:我比较喜欢现代人,在重新理解文革时期的肖像之后,经过自己的创新,然后画出来的比较有意思的人物图像,有点类似阿Q版本。我特别理解不了用一些废旧的钢铁堆砌而成的作品,艺术家很是自我欣赏,而且一些人也跟着欣赏。对我来说一堆废铁换个摆放的场域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差异,让我有点匪夷所思。我们工厂里有好多废铁,是不是也有变身“艺术品”的可能性?我还比较喜欢一些钢结构的户外雕塑,看起来挺有意思,同时还比较适合我们做(笑)。
侯子建:我挺喜欢新鲜的东西,对一些装置有时还是比较感兴趣,尽管很多看不懂。一些装置作品还是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