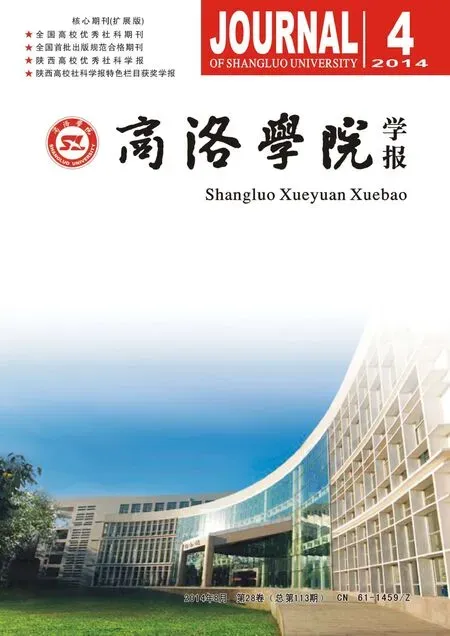疯狂是关怀自身的实践
张建军
(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疯狂是关怀自身的实践
张建军
(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疯狂在关怀自身的同时并不与他人形成对抗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式的存在关系,即自身欲望在伦理角度下的可行性实践研究。疯狂在关怀自身的实践中关系到三个维度:历史维度是对关怀自身与他人的历史根源探究及他者的非生存美学化;话语维度是从理论高度见证疯狂生存美学的合理性;社会维度虽然属于非话语性领域,但社会、政治、经济的规则和疯狂的事实又是和话语实践紧密相关。
疯狂;关怀自身;历史维度;话语维度;社会维度
生存美学就是以“关怀自身”为核心,努力使人生变成审美过程的实践智慧。福柯“不想写出一部欲望、色欲和力比多前后相继的概念史,而是分析个体是如何被引导去关注自身、解释自身、认识自身和承认自身是有欲望的主体的实践。”[1]就是使人自身得到尽可能的行动自由,处理好关怀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在探讨人自身获得自由行为的道德。古希腊注重关怀自身,着重指出对欲望快感满足的节制,而不至于沦落为庸俗的纵欲主义。因此,“生存美学也就是一种关于自身欲望的伦理学”[2]420。关怀自身不仅仅是在一味的强调“自身”,也关涉与他人关系,即关怀自身也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生存美学思想。
疯狂的非理性只是在疯狂过程中对人自身内在本真性的确认。疯狂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存在着其外在性的可能,“真理只有首先将主体自身的存在纳入游戏之中,才可能成为主体的真理。”[2]87在知识考古学过程中,疯狂也难逃真理游戏的厄运。“寻求掌握它们的野蛮状态的感知,必然属于一个已经将其捕捉的世界。”[3]50捕捉和压抑只是暂时的真相掩盖和正误迷乱,疯狂会以其微弱和渐进的方式证明关怀自身的存在。“转向自身的论题不应该被解释成摆脱行为领域,而是作为对允许人把自身对自身的关系一直作为与事物、事件和世界关系的原则和法则的东西的探究。”[4]557知识考古学在研究作为认识、制度和实践之可能性条件,并没有把实践看作历史总体化进程,而是从理论灵活性的角度对实践有着特殊的理解。
1 实践关怀的历史维度
《古典时代的疯狂史》是一部关于差异的历史,“也是文明的产物”[5]。“我的目的是创建出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有多种不同的模式,通过这些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人被塑造成各种主体。”[6]但是,人们在很多时候过于关注“中世纪末期,麻风病消失于西方世界”这一事实,认为其是疯狂的历史根源,同时也奠定了人们用理性的“同一”视角来认识疯狂的他者性。疯狂与理性的距离既不是知识的解放、启蒙,也不是简单纯粹的打开了知识之道。两者的距离建立于一种理性对疯狂的放逐运动之中,而这个运动多少会令人想起中世纪将麻风患者逐离社会的运动——甚至是它的历史重复和翻版。
1.1 疯狂的真正历史根源
麻风患者身上的恶痛带着肉眼可见的徽章;灼烧在古典时代的新放逐者——疯狂——身上的则是非理性更隐秘的烙印。“对于历史学而言,那既往的并不有如对自然科学家一般意义的为‘过去’;它具备着和保有着一很特别意义的‘现在’”[7]。历史本身的存在是一种现在,它是对于现在的存在,现在也是历史的现在。所以麻风病对于历史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被历史化了。麻风病“这个放逐的手势,打开了受诅咒的空间,发挥着许多其他的功能。监禁的手势也不会比它单纯:它也具有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和道德上的意涵。”[3]83这就是被历史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古典时代监禁机构里含混着各种彼此冲突元素就不由得在历史中寻找其根源:“教会在穷人援助和收容仪式中的古老特权、资产阶层对整顿悲惨世界秩序的关怀、协助的欲望和压制的需要、慈善的责任和惩戒的意志,这一整群暧昧措施,其意义仍有待探究,但无疑可由麻风病院找到其象征。”[3]83象征的是他者的历史,把疯狂认定为麻风病替代者身份的历史和社会作用的本身就是历史总体观的体现。
从差异的角度来看,疯狂的根源就是古希腊时期所流行的生存美学思想的体现。“从哲学训练到基督教禁欲主义,经历了千年的变化和演进,毫无疑问,关心自己是其主线之一。”[4]13后来随着基督教伦理体系及生活方式的改造,疯狂变成了他者的概念,关怀自己被淡化,排除出主流的思想体系之外。疯狂的本质是人“关怀自身”的体现,关怀并不完全是对自身的封闭,还存在着对自身的敞开。由于疯狂是在理性和主体视角下的他者认识,错把它的历史根源归于麻风病的隔离和排距模式。“中世纪末期,麻风病消失于西方世界。”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中世纪末期意味着古典时代的开启。麻风病消失是对中世纪对待麻风病经验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本身也包含着对麻风病治疗经验的一种历史重演;麻风病存在的历史痕迹,也是其历史辉煌成就的表征。“那是一片任其荒凉和长时间无法居住的土地。”在理性的历史意识中,辉煌可以造就新的辉煌,荒凉是对曾经辉煌的充分肯定。就此,就些地域也在等待或者召唤新的居住者;社会历史是一个带有不断去野蛮、去愚昧、去邪恶等净化、排斥的文明化过程,他者的存在是社会对其合理性的确认。社会合理性的矛盾也在等待“邪恶的新化身”,经验、地域、社会三者重合,麻风病真正的遗产便归于疯狂。疯狂被认定为确定主体和理性社会主流位置的他者,他者的存在是社会和历史发展必不可少的背景参照。
疯狂的生存美学中所体现的关怀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在古典时期被麻风病模式转换成历史的他者,这是问题本质发生变化。他者化是一种历史模式,而麻风病和监禁以及疗养院都是普遍规律下的特殊演绎,每一种特殊对普遍都有经验性的贡献。麻风怪异的消失,明确不是医疗行为的效果,而是隔离措施的自然结果;十字军东征结束,与东方病源地断绝联系。只是西方世界想象性的推测,在深层次上,显示出麻风病内在的排拒模式。麻风病的典型模式形成了以疯狂为代表的非理性的两种他者化社会待遇:隔离和排拒。隔离使其在他者所属的地域自生自灭;排拒最主要的使罪恶返归罪恶之地,还纯洁与神圣之地。这是以后他者化重要的思想根源和方法指导。福柯认为,古典主义发明监禁体制,就像中世纪发明麻风病患的隔离政策。
福柯在1984年《何为启蒙》一文中,主要强调他“从事批判并不是为了寻求普遍价值,而是通过使我们建构我们自身并承认我们自身就是我们所作、所思、所说的主体的各种事件而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调查,批判并不设法得出整个认识的或整个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设法得出我们所思、所说、所作都作为历史事件来得到陈述的话语。”[8]462当疯狂成为一个拥有我们自身的所思、所说、所作的历史事件被表述出来,疯狂与理性或者关怀自身与理性并不是单数的权力实施,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关系体系。疯狂所包含的理性与非理性浑然一体的历史原点就是人类认识、思想和实践的起点——自身欲望的伦理学,即古希腊的注重人存在的美学思想。
1.2 疯狂与化身
福柯认为序言的写作就是建立作者王权体制的第一文书、专制暴政的宣言。他非常反对这一论调:我的意图不是你们的箴言,你们不要使你们的阅读、分析、批评步步屈从于我的意愿。《古典时代疯狂史》二版序言本质上就是要打破作者独尊的地位。这种独尊本身限制了文本或者故事的多种叙述之间的对话关系。化身们(doubles)“本身的一些片段,被人们抽出来强调、炫示,到处流传着,这些片段甚至会被认为可以几近概括其全体。到了后来,有时它还会在这些片段中,找到栖身之所;注释将它一拆为二,他终究得在这些异质的论述之中显现自身,招认它曾经拒绝明说之事,摆脱它曾经高声伪装的存在。”[3]1认识人是通过事件,认识疯狂要通过化身。不管是疯狂与非理性,还是疯狂与他者,都是疯狂化身的表达。疯狂的化身有:麻风病、性病、同性恋、爱情至上者、无神论者、游手好闲者、自杀者、巫术者、无理智者、思想放荡者、心神丧失者、躁狂和忧郁者、歇斯底里和疑病者等。“化身(double)这个词语所包含的意念,除了一个和真身(original)相似甚至完全相似却又不同的反影式化身之外,还有双重、分裂等意义。”[3]1从标题看,《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存在着双重和分裂的意义。也即非理性最早是对疯狂的理解参照,但是随着理性主义和文明社会的发展,非理性就成为一种定性的身份。福柯自己说他的书“充其量只是说史学工地中的哲学片简。”[3]1哲学片简就是福柯非历史主义历史观和主体解构理论的化身。福柯自己承认“我研究的总题目不是权力,而是主体”[9]。“主体”是摆脱理性主义的解构主体,而形成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存在。
福柯认为生活和工作中最大的乐趣在于成为别人,成为你起初不是的那个人。写作中可以让自己成为自身的化身,这种化身是对自身的关怀,这种化身的寻找本身就是对自身的丰富和跨越。重复本身是对自我的一种定性,是对心灵的一种违背。把自身编排到历史的脉络中去就是在延承一种历史的延续性,遵从和服务于历史的脉络及历史总体观。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进行某种合理性的论证,论证不是理论符合事实,而是事实符合理论。其实,疯狂史是“福柯进行的是历史体验的结构分析”[3]29,还历史于真实,还疯狂于本质,实现人对自身的认知和关怀。
“把疯狂混同于其他的社会他者,或者说应该是文明他者,其目的就是为了用文明他者的方式来处理疯狂问题或者疯狂意识,这种意识和问题是我们目前不可认识的,正如德里达对于福柯在谈疯狂问题时的质疑。”[10]60疯狂的存在是不可知的,福柯对于疯狂的表述,也只是在非理性的作用下对疯狂的认知定性。对于疯狂的认知只有通过化身的存在才能达到,化身就是对疯狂的定性或者是对真身地反影式表达,即疯狂是化身的内核,化身是疯狂的表现或者论述。暂时称福柯所表述的疯狂为“同构性化身”,是疯狂中关怀自身与他人关系的重要表现,也即非理性化身。对于疯狂同构性化身的思想研究就是在对它们(化身)进行历史疏离和理论佐证,是体现生存美学思想“行为道德”的重要渠道;但是这种化身在理性和主体看来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是没有办法运用的,所以社会和理性还要对疯狂进行定型分析,这是理性模式的认知方式。
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只是相对的存在,人是世界的见证,世界是人的存在。人类早期阶段,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单一的、直接的、切身的,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的多元化、模糊化、遥远化,这样就产生了第三者,第三者产生的重要作用就是在于中介沟通。理性一直认可自己是人和是界之间的阶梯或者桥梁,感性则被认为是人和世界之间的通道。阶梯和桥梁的比喻中本身已经表征出人为的特点,而通道则是原生态的。“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因为上帝决心要和世界对立,它将表像留给世界,而把事物的真相和本质留给自己”[3]46。对于世界的认知,不能否认感性模式的存在。不否认理性模式对感性模式的替代作用和排斥作用,其存在的单一性已经破坏了世界存在的多样性。疯狂化身的存在只是针对理性的疯狂——“主体性化身”,而不是世界的疯狂。
阿尔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非人之成长,而是人的缩小”[3]45。理性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段或者平台,并使人性本身在世界真相的作用下复归人本身,而不是理性让人性脱离人本身,成为行尸走肉,这才是真正的疯狂,这种疯狂是没有任何内在本质的特点,只是人趋于形式的表现。福柯在《雷蒙·鲁塞尔》中有一句话:人呈现为经验性的与超验性的双生体。所以“主体性化身”只能是人性萎缩。“主体性的化身”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产生的,它主要是服务于理性历史对于他者的需要,所以就造就了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疯狂。主体和理性使其产生的根源,也使其更加确认主体和理性的存在价值。而忽略了疯狂化身的生存美学意义,即疯狂在关怀自身时更加注重化身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因为化身是一种历史事实和生活实践,必然牵扯到与他人的存在关系。
2 实践关怀的话语维度
“福柯研究话语的出发点并非主体意识,而是匿名的话语规则。主体的散布以及主体与自身的断离能在话语整体中的得以确定。福柯并不关注一般的理性化过程,而是聚焦于在疯狂、疾病、死亡、犯罪和性等特定经验领域中植根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如何构造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8]473生存美学思想里关怀自身与他人的伦理学关系,主要表现在疯狂在对理性的去遮蔽化、去合理性及对于古典文化为代表的去总体性化。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是人存在的思想或精神家园,福柯虽然不赞成语言与人的同时出场,但是话语对于其人自身欲望的伦理学表述却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
2.1 疯狂与理性——暧昧性
古典时代人们从主体和理性角度把疯狂当做是自己的对立面,疯狂是理性的永恒陪衬,并从集体的层面来规范和排斥疯狂。疯狂在个体肉体上遭到生活共同体的排斥——监禁,在精神上遭到理性启蒙的压抑——规训,在道德上遭到社会规范的定性——懒散。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论述中不断渗透出,疯狂与理性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模糊、暧昧的存在。“任何一种疯狂,都有可能判断和宰制它的理性,相对地,任何一种理性,也都由它的疯狂,作为它可笑的真相。两者间的每一项,都是另一项的衡量标准。在这种相互指涉的运动里,两者相克相生。”[3]45疯狂和理性之间永远都具有逆转的可能,即疯狂是一种和理性具有相关性的存在形式,或者就是另一种“理性”。疯狂对人“自身”表述并不趋于理性的外在形式对人本质的限制和压抑。疯狂不是对理性的完全背离,而是隐性的在现。
古老的基督教传统认为,在上帝眼中,人世也是疯狂的。即升高人的灵性到上帝的高度或者探索投身其中的疯狂深渊,其实是一回事。人类有限的理性是不能看到表像中的过渡性和局部性的真理,人的精神只是阴影中的一块片断。事物身上蕴涵着对立,每一件事物都处在直接的矛盾之中。以大尺度观之,一切都是“疯狂”;以小尺度估量,“一切”本身就是疯狂。疯狂只有相对于理性才会存在,理性的最终真相就是被它否定的疯狂。同时,疯狂甚至“被整合于理性之中,或者构成理性的一个秘密力量,或者成为它的一个显现时刻,或者成为一个吊诡的形式,让理性可以在其中意识自身,无论如何,疯狂只有在理性之中,才有意义和价值。”[3]50于是,疯狂成为理性一种形式。非理性代表着人的处境,拒绝疯狂,就是在永远放弃用合理的方式使用人的理性,或者说,拒绝疯狂就是在否定关怀人自身与他人的紧密关系,疯狂和理性之间是相互不可分离的存在。
疯狂与理性的相关性及用理性的形式表达本身就是在接纳疯狂,更是在侵入疯狂之中,划定范围、纳入意识、确定位置。理性通过排拒除魅、移植栽种、归类异同,将疯狂相对理性的引导关系暧昧化、模糊化。福柯反对理性压抑非理性给人类造成严重的存在危机,主张打破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唯我独尊的历史沉寂,恢复和展开与非理性的平等对话关系。理性在极端化状态就是疯狂表现,显示理性本身的狂妄疯狂。因此,疯狂与理性之间的暧昧性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关怀自身的表现。
2.2 批判笛卡尔“我思故我在”——非合理性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正在思想中的“我”,是不可能发疯的,“我思”恰好就是疯狂之不可能的条件。当“我在”时,我就比一个想象拥有玻璃身体的人持有更坚实的真相。保护思想是思想的客体,并不是真相的一种永存性质;而“我思故我在”是思想的主体——这个主体是不可能疯狂,不管是“我思”还是“我在”都是对主体的肯定。笛卡尔“以怀疑者(正在进行怀疑的人)的名义剔除了疯狂,而这位怀疑者不可能失去理性,就好像它不能不思想,也不能不存在。”[3]74疯狂被排出了属于主体持有、获得真相和权利的领域,疯狂遭到放逐。“显而易见,福柯想要把它放到审判庭上。但这种审判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一旦开口发言,诉讼和判决都将是在永不停息的重复犯罪。”[10]60德里达认为,人和对抗理性的努力都会被理性所包围,整体的理性是不可被超越的。除非成为理性的一部分,从理性的内部对其进行反抗。
福柯认为独一无二,至尊无上,绝对必然的合理性只是众多理性中的一个可能性的,偶然性的合理性形式。理性是主体的自我创造和随着历史社会潮流的不断分叉变异,所以合理性就存在不同的基础和样态。对于合理性的反驳,福柯从《性史》“又一次在追寻一种直面他性的方式。这是一个颇为冗长的故事,但它的用意并不是要提供细致论证以支持这样一个观点:所有这些文本都构成了一种对理性的施压和考验。”[10]80这是福柯1963年《越界前言》一文中探讨的越界观念。疯狂其实和性一样,都指向自身之外的虚空。用越界的概念来预演着绝对不可接受的疯狂面孔,“这样一张面孔可能是在他者之镜中的我们的面孔,而不是通过我们的镜子、理性的镜子看到的他者的面孔。”[10]82这就是疯狂在关怀自身是与他人是通过越界的思想而体现出来。越界作为我们的文化土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相当于矛盾经验对于辩证思维一样,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非肯定性的肯定就是一种纯粹越界的思想运动,既不批判其从何所来,也不谴责其归之何处。
但是笛卡尔主义认为,思想有责任觉察真相并认识主体的主权行使,所以不可能失去理性。合理性就成为理性显现的分界线,把不合理的理性和合理的非理性体验,熟悉的存在视为人的可能性疯狂。这一合理性的历史是“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隐密地是由非理性的消失所构成的,是对关怀自身与他人关系的封闭。在古典时代,疯人与疯狂之间的“空虚”存在构成了非理性消亡的三个本质看点:1)非理性。从属于悟性时代的深刻分裂,并彼此异化,空虚是非理性的存在,监禁成为非理性的事实。疯人的立即辨识和疯狂的延后真相在监禁的未分化中呈现,社会结构涵盖领域替换了非理性的涵盖领域。2)“非”理性。非理性的空虚使得疯子的感知内容,最终只能是理性本身。3)“准”理性。疯狂是相对于理性而存在的,这种相对性的对象化和理性化,在距离和否定中的空虚并不完全支撑相对性和否定性。
“空虚”存在本身是对人自身存在的肯定。“我思故我在”从对疯狂的否定意义上讲,“我思”就是一种主体和集体的表达,“我在”则是在“我思”基础上的个体存在。基于此,关怀自身在与他人关系中消失了本身(非理性)的存在,或者说关怀自身的意义。
这是一种用合理性形式的他者化,而不是自身欲望伦理与他人关系,是福柯极力批判的古典时代疯狂他者化理论核心。理性批判不可能既是批判,又使自己的准则不受批判。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批判自尼采开始就陷入了自相矛盾、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
2.3 批判古典文化的话语整合——非体系性
“文化便是透过这些手势,将某些事物摒除在外;而且在它整个历史里,这个被挖空出来的虚空、这个使它可以独立出来的空白空间,和文化的正面价值一样标指着它的特性。因为文化对于它的价值,是在历史的连续性之中来接受和保持它们的;但是在我们所要谈的这个领域里,它却进行基本的选择,它作出了给它正面性面孔的划分;这里便是它在其中形成的原初厚度。询问一个文化的界限经验,便是在历史的边际,探寻一个仿佛是它的历史诞生本身的撕裂。”[3]47福柯谈的文化就是17至18世纪之交的新古典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这一时期的新古典文化核心主要还是强调资产阶级的道德和伦理。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的英文简缩本《疯癫与文明》,就是对古典文化的定性——文明。文明往往过于注重其文化的正面价值性,正是这一正面性透过一些晦暗不明的手势,在历史中形成独立的空白空间。文明具有历史连续性,对排除其他话语存在的古典文化产生体系性梳理,也就是古典文化是总体性、连续性和源起性历史观表面的中性、合理身份,古典文化的身份需要界限和他者,证明他们存在的合理性。这样制造一部疯狂的界限历史,他者(疯狂)存在的合理性、社会性、历史性成为意识话语中的必然。所以,福柯“要把以必然界限的形式进行的批判转变成一种以可能越界的形式出现的实践批判。”[10]158把以历史必然界限进行的他者性批判转变成了以生存美学为中心的可能越界的实践批判,古典文化就是其实践批判的话语维度。疯狂的界限是由历史他者性的一系列决定所为,总称古典文化。尽管“把一些事物划出文化正面价值之外的手势本身,遭到了遗忘,然而它(手势)却和那些文化保持在光明之中的价值一样,表达出这个文化的特质。”[3]48必然界限就是古典文化所具有的启蒙对两种差异的消除和主导归一。越界则是对古典文化的反抗,也是关怀自身与他人关系的最好体现,因为文化或者手势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他人的表征。
监禁以难以察觉的方式,让各种被社会所排斥的对象和疯狂靠拢,监禁在扮演排斥角色的同时,还在实践和规则中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构成了一个具有整体性、一致性和功能性的体验领域。监禁只是这一深度工作的表面现象,其核心思想则是古典文化,或者说是布尔乔亚的阶级理念、阶层道德。将疯狂与“主体性化身”重新整理、组合,以一个单一的手势将他们放逐、流亡,如此便形成了非理性的一体化世界,即监禁空间之中的同质世界——疯狂。疯狂存在名词内涵和形容词外形,古典文化过于关注其形容词身份的危险特征,而忽视了其名词内涵的关怀自身。将一些彼此距离非常遥远的体验,都归属在疯狂的共同形容词身份之下,在疯狂的名词内涵周围形成了一道行为丑陋聚居起来的犯罪光环。“邪恶、受诅咒的事物具有文化身份认同的化身地位。”[3]62古典文化所进行的大变动是和伦理体验领域相关,但不是关于疯狂关怀自身的伦理,而是他人或者化身的伦理。疯狂有多种多样的功能,在古典文化作用下,监禁所单调一致的措施中,疯人也就迷失于这一大群化身之中,他人成了核心。
古典文化将投注在理性身上的价值表现在疯狂的大小风险之中。“古典文化在疯狂之中所接受的风险,既是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而非理性这个字把这两个极端解释得很清楚:它是理性简单、立即、马上就会遭遇到的反面;它也是一个空洞、既无内容亦无价值、纯粹否定的形式,在其中出现的形象,只有一个刚刚逃离的理性所留下的足迹,但这个理性对非理性来说,却永远是它之所是的存在理由。”[3]258疯狂是相对于理性而存在的,所以理性就成了把握疯狂的尺度。非理性成为研究对象,始于一个流放时刻,非理性在其中变得沉默无言。古典文化的价值就在于赋予非理性一种社会脱轨的意义,给予一个将他排除在外的地位。而且,是掩盖社会理性拒绝行为在其中认出自我病态形式的自我表达。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于“最大的风险”——古典文化,合法性形式中能透射出疯狂立即的矛盾,即关怀自身。
3 实践关怀的社会维度
“人们认为我说过疯癫并不存在,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认知问题,即在人们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定义中,在一个特定时期,疯癫是如何被纳入到制度领域的,这种制度领域把它建构成一种精神疾病,与其他疾病一样,它也占据着一个特定的位置”[11]——疯狂作为他者在社会领域的地位。古典时代疯狂是通过紧闭被纳入到社会领域,紧闭的源起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及道德的综合作用。麻风病的消失导致了他者性象征序列上出现空缺,紧闭就为疯狂填补这一空缺创造了环境背景。监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具有了疗养院的性质,就使他者性的制度领域具有科学性和医学性。疯狂他者性的社会维度产生并不仅仅是社会制度承前继后的过渡作用,也是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的历史变调。
福柯在结构研究与理性的关系寻找真理。米歇尔·塞尔在《无法沟通者之几何学:疯狂》中认为,福柯反对理性对疯狂的压迫,主要是“这群晦暗中的人民,有一股深沉的爱,那不是模糊的人道主义,而是接近虔诚的关爱,承认他们无限的接近,乃是另一个自我。”[3]51因为自由在疯狂中才能发现“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这是在理性和主体之外的一种人自身活生生的存在。疯狂的存在并不是这种真空状态下的封闭存在,必然需要外界的环境与他人。在这种接近他人的过程中被历史幻化成他者的身份。福柯疯狂知识考古学的意义就在看到这种被社会化成他者的过程和历史。“因此,作疯狂史的意义是:对一组历史整体进行结构研究——包括概念、体制、司法和治安措施、科学观念——这样的整体使得疯狂保持在被捕捉的状态之中,而它的野蛮状态也不可能完全重构;但即使不能达到这个无法认识的原始纯真,结构研究却必须上溯到同时连结又分离理性和疯狂的决定。”[3]51福柯就是在结构研究中分析这些社会制度领域如何分离他们,还原他们的真实存在;但是他们又具有与他人的连结关系。所以,福柯生存美学思想在实践关怀中可以从社会维度见证真实的关怀自身与他人关系。
3.1 政治经济中的“疯狂”
古典时代以1656年法国政府下令在巴黎设立“收容总署”事件为肇始,而以1794年巴士底狱的犯人皮纳尔的获释象征事件宣告结束。“收容总署”是监禁制度设立的标志,皮纳尔获释推翻了监禁的陈旧制度,又创立了崭新的、温和的疗养院模式。这是社会制度向科学模式的转变,其根本的他者性依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隐蔽。在监禁中,穷人、失业者、惩戒犯和无理智者被聚居起来,他们在其中的身份和邻近关系没有医疗的共通性,所以收容总署并非一座医疗设施,而是一个半司法机构,在既有权力体系和法庭之旁另设的行政单位,可自行决策、审判和执行。监禁是专制政府进行的直接干预,维护当时法国君王和中产阶级秩序。这样监禁成为异质元素泛滥混合,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全欧洲共通的社会感性。疗养院则是对这一制度的客观化和深度化,依然带有历史的连续性。
麻风病是中世纪带有尊重意味的恐惧感,是重要感染源的他者。疯狂在替代这一象征功能的同时还要加上关于排斥的经济学这一理念。“人口”在法语中有两重意思:一是居住在某一地区的所有人;二是统计中的同一种类的生物。疯狂在监禁制度中忽视人的概念,而强调经济学中的人口意思。疯狂的排斥过程产生了把人汇聚成人口的经济实用性和财富剥削性。重商主义经济背景下,既不是生产者又不是消费者的贫民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他们唯一归宿就是被监禁,这是一种从社会中提炼出来的用以流放他们的手段。新兴工业需要劳动力,他们就在国家中重新获得了一个身份。贫穷是非生产性的游手好闲者的道德疾病,这是把他们送去“医院”的充分必要条件。不是因为他们有病,而是因为他们是非生产者,他们的潜在价值就在于作为人口的生产性。“如此,他们才能有助于公共繁荣。交替状态明显:在充分就业和高薪时期,这项措施可提供廉价劳工;而在失业大增的时期,它吸收无所事事的人群,成为避免动荡暴乱的社会保护措施。”[3]104福柯还再三提醒,监禁所最早是出现在英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密集区域。所以,疯狂在“人口”概念中就充分体现与他人的经济关系。
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改造,是对失序者的秩序建构和意识深化。由于政治经济一体性,经济化就是在输入理性的政治秩序。劳动不是处于自然综合层次,而是处于道德综合层次,即布尔乔亚的中产阶级理念。“懒惰”不但是万恶之首,也是万恶之源,替代“贪婪”的极端罪恶,表现为“游手好闲”。“劳动的神圣力量,圈化出了这它异的世界,而今日我们所认识的疯狂,其地位便来自其中。……疯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闯过了资产者化出的界线,使得它自己成为资产者伦理神圣界线之外的异乡人。”[3]103制度内的他者是疯狂的主体性化身——贫穷。制度之外的他者,疯子却没有或者不可能被政治经济纳入理性秩序,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神圣伦理界限,他们是资产阶级伦理界限范畴中他者的他者。从生存美学的角度,这种疯狂是真正的关怀自身。
福柯分析了疯人院、诊所、监狱和性活动等劳动之外的场所,找到了没有被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者加以理论化的极端材料的源头——疯狂。所以,马科·普斯特更进一步的认为:福柯的成就削弱了马克思提出的劳动的特权地位。“福柯作品含有对解放政治学中劳动中心性的攻击。他的思想从这一假设出发,即劳动阶级并没有通过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驱。”[10]55劳动是资本主义的伦理圣圈,一旦进入也就改变其对立的本质性。疯狂在被排斥于贫穷的同时,也是其他者性的存在,贫穷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把疯狂的他者性身份贯穿始终,并进入资产阶级伦理范畴。
3.2 公共秩序中的“疯狂”
1656年4月27日国王创建收容总署的诏令一开始就明确其任务是阻止“行乞和游手好闲成为一切秩序混乱的起源”,这就涉及到公共秩序管理的问题。收容总署最原初的目的是压抑行乞,使其改变懒散怠惰、放荡无羁的罪恶之源,并可能减少其对社会产生的直接威胁和潜在危害。这是从资产阶级精英思想出发的道德性感知,疯狂源于纪律松散和道德衰败。布尔乔亚的道德城邦梦想就是把行政的软禁变成了道德惩罚的手段,国家的法律就和人心的法律合二为一。疯狂在被融入公共秩序问题之中,是为了建构理想的城邦。疯狂是否可以进入监禁体制,或者疯狂是不是公共秩序的问题。这样会使疯狂被迫脱离想象中的自由。
“疯狂最初不是一件事实,而是一个判决——即令这个判决自己变成了一件事实。它是人类思想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宣布的判决。它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宣布的判决。”[12]疯狂虽然不是一个事实,但是对疯狂的判决却是一个具有他者性的事实存在,这种事实存在就显现在一部分人及一部分思想对与之相对的另一部分的主体作用和客观事实。主要表现在监禁的事实和疗养院的事实。监禁扮演负面排除者的角色,更重要是组织者的角色,它的实践和规则构成了整体性、一致性和功能性的体验领域。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形成了以疯狂为核心的体验领域,这就是制度所形成的同质世界,更加注重其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危害。疯狂在被认可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亲属时,就是在采用治安的道德疗法:治疗身体和净化灵魂。疯狂在灵魂上是对人自身的关爱和个体人性的确认或者追寻,身体则是其最主要的与他人关系实践的途径,在此被制度消亡。
“苏格拉底式爱情”和“柏拉图式性爱”都是同性恋的不同表达,福柯在本质上不赞同家庭制度下的性欲和爱情,这不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特征。“柏拉图文化,不论是在其历史中的哪个阶段,都把爱情当做是一种崇高激越的现象,依其不同层次进行分类。因此,爱情或是与身体的盲目疯狂有关,或是与灵魂的伟大陶醉有关;而且,在这样的陶醉之中,非理性仍受知识控制。”[3]138性欲作为一种正常的存在,却被人整合到文化或者制度的约束体系之中去,用理性—非理性的标准来衡量其是否正常或者疯狂。这本身就是一种疯狂之举,性欲本质上是不可规约的,性欲在本质上是人自身重要的真实体现,爱情是其与他人的外在表现。但是制度却将性欲从私人领域拉入社会公共秩序和家庭制度结构中,进行道德批判。
3.3 科学意识中的“疯狂”
科学知识的认知模式是理性和主体的主导作用及对他们作为的确认。但在疯狂问题上却存在着三个不确定性:知识对象的是不是呈现不变的一致性,社会经验中对象的隐含方式是否出现在科学知识中,最主要的是形成了反向的科学知识在实证的作用下产生社会经验的模式。这一难度通过创造他者的模式来解决——放逐和变异。从这一点上说,疯狂问题的他者化就是被科学知识变成了他者,并变成了疯狂的典型形象,甚至核心思想。在疯狂四周的化身,今天看来和疯子之间根本无联系。现代人在疯子身上却能看到了自身真相的异化,疯狂一旦被认定为知识对象,就成为社会和科学的时间性的变异体。疯狂的真实形象消失了,想象、虚构、创造的疯狂产生了。
疯狂从来不是浑然一体的事实团块,而是以同质整体进行变形。疯狂的离散性格在疯狂意识中表现为原则上的片断性。疯狂体验可能使用把自我投射于客观性平面的方式,去寻求自我超越和平衡。但是,疯狂意识之间的无法化约、协调困难、重复出现就在消除其客观化和科学化。疯狂的批判意识是辩证意识;疯狂的实践意识是仪式划分;疯狂的发言意识是高亢指认;疯狂的分析意识是知识铺陈。这四个主要元素之间的比例和关联便是疯狂在现代世界中连续展现的面貌,具有历史流变的特征。“疯狂永远没有为了其本身,并在它特有的语言之中受到显示。并不是矛盾活生生的存在其中,而是它在相互矛盾的词语中过着分裂的生活。只要西方世界让在一个崇尚理性的时代,疯狂就要遵守悟性的分裂。”[3]254疯狂的疾病就是理性的创作和创作中的理性。
“福柯有很长时间只认为主体是统治技术的被动产物。只是在1980年,他认为是相对的自主,修身的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终的。因为必须避免所有夸张,所以我们说是相对自主。”[4]545以理性为中心形成疯狂他者化是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一种被动的表现,这种疯狂的他者化已经背离了关怀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在他者化中却可以看到疯狂与他人关系存在。在疯狂的实践过程中人们比较关注疯狂可能对他人的危害和对人自身的偏离,而没有看到疯狂是在与他人的差异中表现出对其个体自身的关怀,疯狂的实践也就“不是知识的历史,而是体验的初步运动。”[13]这种疯狂的欲望并不是一种没有限制的邪恶和破坏,而是一种自身欲望的伦理学。所以,福柯的《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就是把疯狂从历史维度、话语维度、社会维度进行生存美学的自身关怀。
[1]福 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6.
[2]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福 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福 柯.主体解释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张建军.疯狂是关怀自身[J].商洛学院学报,2012,26 (1):21-26.
[6]福 柯.主体和权力[M]//汪民安.福柯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0.
[7]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M].甘 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25.
[8]莫伟民,姜宇辉,王礼平.二十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超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张建超,张 静,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10]罗伊·博伊恩.福柯与德里达[M].贾辰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福 柯.自我关注的伦理学是一种自由实践[M]//汪民安.福柯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63.
[12]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M].尚志英,许 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
[13]陈晓明.“疯狂”中的思想交锋[J].学术月刊,2006(3): 17-25.
(责任编辑:刘小燕)
Madness is Practice of Self-care
ZHANG Jian-jun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 726000,Shaanxi)
Madness,while caring for itself,does not form a bitter confrontation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but a type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m,that is,desire practice about the feasibility in ethics.There exist three dimeasions in them: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is to care for their own history root with others and explore otherness of non-existence aesthetics;discourse dimension is living testimony crazy rationality from existence aesthetics;social dimension does not belong to nondiscourse field,but the social,political,economic rules and the fact of madnes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discursive practices.
madness;care for themselves;historical dimension;social dimension;discourse dimension
B83-06
:A
:1674-0033(2014)04-0084-08
10.13440/j.slxy.1674-0033.2014.04.020
2014-02-23
商洛学院科研基金项目(11sky013)
张建军,男,陕西礼泉人,硕士,讲师
- 商洛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化学学习困难的诊断性评价分析
- 近十年张彦远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