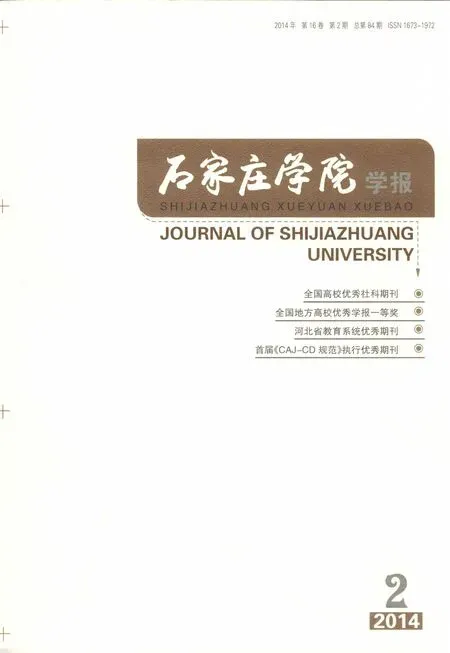文学接受中的文化阐释性
——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例
李志华,赵双玉
(石家庄学院 外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文学接受中的文化阐释性
——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例
李志华,赵双玉
(石家庄学院 外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文学作品的文化属性不仅来自于作家、作品本身的文化创造过程,也生成于读者、批评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的文化阐释行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D·H·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其文化意义蕴含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并深化于作品的文学接受过程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该作品在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误读、审美接受、文化阐释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升华的嬗变过程。其中性爱主题研究、原型批评、生态批评从不同层面说明了文学批评过程中的文化阐释行为。
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文学接受;文化阐释
D·H·劳伦斯(D.H.Lawrence)是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坛上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争议中尤以对其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多,世人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美接受、文学解读、文化阐释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升华的嬗变过程。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接受美学认为,传统文学理论低估了接受在文学活动中的意义,接受不但是对文本的接受,而且参与了文本的创造。所以文学接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活动,文本的意义不仅来自作家的创作过程,也生成于读者、研究者接受活动中的欣赏与批评,并且文学接受中的误读是难免的。以接受活动的性质和形态分,文学接受分为:阅读、欣赏和批评三类。[1]《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从最初的因为性描写而被禁、被误读,到后来的跨文化交流、多元文学批评,充分体现了文学接受的积极性、创造性及其文化属性。并且其文学接受过程的文化阐释性充分挖掘出了作家的文化创造思想及作品本身的文化意蕴。本文旨在结合劳伦斯一生的文学活动和文化创造行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文本接受及欣赏过程的文化属性,并从性爱主题研究、原型批评、生态批评三个方面分析其文学批评过程中的文化阐释行为。
一、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创造行为
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开篇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在劳伦斯的所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悟到作家所特有的那种忧患意识和救赎情怀。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如日中天之时,劳伦斯凭着自身对人和自然的本能关爱,凭着其天赐的艺术敏感,触及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和疾病症候。小说伊始,即是一场浩劫后的一片废墟,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象征,更是大战后人之精神荒原的写照。然后,劳伦斯选择了远离工业文明的森林,男女主人公体验着自然淳朴的爱情,依此作者表达出对现代文明残酷性的抗争,并创造出成人的童话。
劳伦斯一生共创作了12部长篇小说,他是充分利用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的艺术家之一。《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创作于1928年,是劳伦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此时的劳伦斯对人物及情节的刻画已炉火纯青,对其终身探索的两性关系也有了更深思熟虑的答案。早在1912年,劳伦斯与弗里达私奔到意大利北部的嘎达湖畔时,他就已经通过直觉触及到了未来生命中的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的主题,其理念在游记《意大利的薄暮》中已初露端倪。在他生命的后期,查出肺结核三期后,他在给澳大利亚女作家莫莉·斯金纳(MollySkinner)的信中说:“我还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与你创造和记录下的人物及经验生死交关,它本身就是生命,远胜过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俗物。”[2]293随后1925年和1926年,他最后回故乡两次,阴郁的故乡和明丽的意大利两相比较、两相冲撞,他终于失望而归。在意大利,他通过考察墓葬和壁画,深深迷上了罗马人之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意大利人真正的祖先伊特鲁里亚人。他们充满血性的性格、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对神灵的虔诚膜拜、对死亡的豁达,与基督教文明下的物欲横流和人性的异化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于是,潜隐作家心灵深处多年的小说主题终于落笔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创作过程饱含了作家对人类本质的深刻体验和对人类理想的不懈追求,创造的是一种源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艺术真实、形而上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劳伦斯的艺术境界,除了造化使然,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砥砺亦是关键——生活在肮脏的工业文明与田园牧歌的老英国的交界地带,吸取的是其时代最优秀的文化,探究的是超然的真理。就作家的创作本性来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有一种合乎人性的生存愿望,并为人类提供了特殊的文化趋向。
二、小说的审美接受过程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初的文本接受过程是一个从误读到欣赏的过程。文学欣赏是读者在作家创造的基础上,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感受、体认和想象文学文本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形象的过程,它使文学欣赏成为一种接受者参与的创造性的活动。
1928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刚一问世即遭到猛烈的攻击,被视为淫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英国的遭遇是一种阶级意识的冲突。英国惧怕无政府主义、工人革命和躁动,上流社会中很多人对性抱有过度的谨慎,尽管他们在行为和言语上与劳动阶级一样并非清教。30年后,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性自由的社会,1959年终于出台了“淫秽出版条例”,以防止法律对含有色情描写的严肃文学构成威胁。1960年,企鹅出版社在劳伦斯逝世30周年之际推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全本,却被检察官告上法庭。结果企鹅出版社赢了,结束了长达30年的禁令。文化学家理查德·霍嘉特(Richard Hoggart)在法庭上就特别指出这本书“讲道德,甚至有清教之嫌”。①转引自黑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生命之书》,载《博览群书》2010年第5期。在霍嘉特看来,当时的法官和检察官对这样的文学名著是缺乏审判资质的,他们的文化、智慧和鉴赏力都明显不足,因此无法理解一本小说公然写了性事,他们也没料到这件事碰巧成了社会文化变革的标志。
对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独到之处,倒是中国的文化界不乏识玉之人。这部小说一问世,中国文学界就报以宽容和同情。中国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了饶述一先生翻译的单行本,但因为是自费,发行量仅千册。著名作家林语堂、郁达夫都曾有精辟的见地,对劳伦斯的作品给予肯定。其后50年间,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文化语境的变迁,中国对劳伦斯的介绍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空白,读者与此书无缘。直至1986年,饶述一先生的译本在湖南再版,并以赵少伟研究员发表在1981年《世界文学》第二期的论文《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为标志,重新肯定了劳伦斯的文学地位。而在1985年上海出版的专著《现代英国小说史》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仍被指责为“黄色淫秽”,作者并把开禁这本书作为“当前西方社会的道德风尚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3]223的标志。这也反映了文学接受过程中个体语境与时代语境的差距。
到了20世纪末,东西方一些国家都先后成立劳伦斯学会,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研究也更加广泛、深入,从单纯的文本接受到文学批评,从性爱主题研究到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心理批评、生态批评、文化研究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文学接受从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扩展为以阅读、解读为中介的作家与读者、作家与批评家、批评家与读者间的复合交流过程。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争议的作品,它的文学接受过程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行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个案,它的文学接受过程已超越了纯审美的倾向,而指向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和对话。《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文学接受过程把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内化的社会意识、所创造的文化精神,从接受者的角度呈现出来,从而实现了作家与接受者的双向交流以及文学作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衍生。
三、文学批评中的文化阐释
文学批评是文学接受的一个特殊类型,是指在鉴赏的基础上,运用某种理论对文学文本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价的阐释活动。欣赏是感受性的,批评则是阐释性的。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流行的文学批评方法大多是文化阐释性的,这反映了文学接受的一种价值态度和取向。尽管诸多批评模式在释义内容和价值取向上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文学接受中的释义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人文阐释活动。文学作品是表现文化最敏锐的部分,而文学批评触摸到了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挖掘出了作品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与人类普遍的文化精神,其文化意义不言而喻。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在文学接受过程中,现代批评理论下,不断得到揭示和呈现。下文拟从性爱主题研究、原型批评、生态文化批评3个方面来分析文学批评中的文化阐释性。
(一)生命本质的探索——性爱主题研究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把在《儿子与情人》《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已经展开的性爱主题推向了高潮。《儿子与情人》是性爱主题的开端,这时劳伦斯还没有去构建新的理想的两性关系,他关注的焦点只是旧的两性关系的不合理性。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以满怀的热情和深度记录了男女两性关系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过程,而且满怀向往地构建了自己心目中的新型两性关系——星式均衡的两性关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的代表作,也是他对两性关系的童话式描述。他用一个老套的故事、大胆的性爱描写,再次证明了现代文明的僵死,自然人性的鲜活,拯救人类的根本途径在于人性的返璞归真、在于性爱的完美实现。
劳伦斯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由于受到以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尼采(Nietzsche)、弗洛伊德(Freud)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加上自身对生命的直觉与感悟,一生都在探索两性关系的理想境界及灵与肉的和谐统一,以此来救赎现代文明的堕落。在劳伦斯眼中,性与生命同在,性甚至就是生命最重要的特质,性是美的。劳伦斯说:“性和美是同一的,就如同火焰和火一样。”[4]210反过来,劳伦斯对现代文明深恶痛绝,认为文明的最大灾难就是对性的病态的憎恨,它残害性、压抑性。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作为自然人,麦勒斯与康妮摆脱了文明的桎捁,荡涤了基督教的原罪感,用生命的欲望和热情去爱,享受生命本源的快乐,寻求性爱的极致。麦勒斯是生机盎然的大森林的守护者,他所代表的是自然,是人性,是蓬勃的生命。与其对立的克里福德则代表了失去生机、频临死亡的现代文明。康妮挣脱克里福德的羁绊投入麦勒斯的怀抱,从性爱中升起对生命、自然的神圣感,对人类的信念。劳伦斯的性爱描写有严肃的目的性,他不以追求感官体验为目的,而是强调人物瞬间的心理感受和生命体验。面对潮水般的攻击谩骂,劳伦斯曾多次为自己的文章辩护。在1929年《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中他说他写《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目的就是“要让男人和女人们全面、诚实、纯洁地想性的事,即使我们不能尽情地纵欲,但我们至少要有完整而洁净的性观念”[5]295。
劳伦斯的性爱意识、性爱描写进入到了一个哲学与审美的高度,使人们彻底摆脱了淫秽意识,上升到了形而上的思想境界。中国文豪林语堂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6]。在1961年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序言中,霍嘉特称这本书是“洁净、严肃的美文”。“如果这样的书我们都试图当成淫秽书来读,那就说明我们才叫肮脏。我们不是在玷污劳伦斯,而是在玷污我们自己。”①转引自黑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生命之书》,载《博览群书》2010年第5期。时至今日,普遍的研究认为,劳伦斯对性持一种清教徒的观点:“他之所以常常被称作清教徒,就是因为他认为性是生命和精神再生的钥匙,也因为他认为这是极严肃的事情。”[7]207劳伦斯的同乡戏剧家萧伯纳也说过:每一个少女都应该读这本纯洁的书。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预言吧!
(二)精神家园的找寻——原型批评
在以文化人类学和非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20世纪英国现代主义作家中,劳伦斯是利用原始因素进行创作较为突出、探索也较为深入的一位。劳伦斯的一生,深受希腊神话、《圣经》、印第安神话等原始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一直试图用理想化的原始文明来拯救西方现代文明的堕落腐败。在《无意识幻想曲》前言中,劳伦斯描述了一个“生机勃勃”“壮丽宏伟”的人类远古异教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的生活和着宇宙自然的规律,保持着生命的完善,创造了“伟大、富有魅力”的文明。在《精神分析与无意识中》,劳伦斯更进一步把人类原始文明看得高于现代文明。在《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中,劳伦斯描绘了人类的两性关系发展史,指出原始异教时代的婚姻是与宇宙、自然的节奏一致的。他呼吁,人类“应该回转身寻回宇宙节奏”,使婚姻“走向永恒”,而这“意味着重返古老的形态”。[5]321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即是劳伦斯利用原始性因素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化创造的代表性作品,反映了劳伦斯将原始社会理想化的思想。在希腊神话中,原始社会就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在《圣经》中,伊甸园的描述和亚当夏娃的生活境界就是理想化的原始社会的图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正是按照《圣经》的叙述体系:已生—死亡—复活来展开故事脉络,寻找人类的精神回归。劳伦斯一开篇就把战争描述为现代文明的大毁灭,因战争而失去性能力的男爵就是死亡的象征,而脸色红润又躁动不安的女主人公预示着生命的复活。为了与《圣经》中人类的原始意象相契合,劳伦斯以诗意的笔触描绘出一个原型的自然世界——拉格比庄园,一片年代久远的原始森林。树林在劳伦斯眼中,象征着人与自然本真的生命活力,更象征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而树林中万物的生发繁衍,无不孕育着一个性字。劳伦斯选择了原始意象森林,又选择了护林者麦勒斯作为小说的英雄,并且按照神话原型中四季发展的叙事结构,从秋季到冬季、春季、夏季展开了男女主人公的情爱历程和感情升华。于是在这片森林中,男女主人公通过本能、肉体、欲望、血性等被现代文明压抑的原始冲动,上演了《圣经·创世纪》的一幕,奏出一曲生命的抒情诗。
原型批评是能最大阐释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文化内涵的文学批评模式。原型批评是弗莱(Northrop Frye)以荣格(Carl G.Jung)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弗雷泽(James G.Frazer)的神话理论为基础的,而这两种理论本身就含有相当多的原始文化因素。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说,认为远古人类反复的生活经历在心灵上留下印记和影像,并被人类集体无意识地世代传承下来,在潜意识领域建立起原始人与现代人之间的联系。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利用原始意象构建小说的原型框架及叙事结构,利用《圣经》的救赎情怀为人类描绘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并引领人类回归精神的家园。所以原型批评理论使《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文化阐释更加厚重。
(三)和谐社会的建构——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美国,90年代后迅速发展为文学研究的显学。生态批评是通过文学和文化研究来重新审视、探讨人和自然的共生关系,揭示现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对人的异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背离,并倡导人类回归自然,还人性以自然状态,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生态批评的特质无疑与劳伦斯的创作思想完全吻合,对于进一步挖掘其作品的文化内涵大有裨益。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对人类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细致刻画,充分体现了劳伦斯的生态意识和救赎情怀。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首先描述出在工业文明和自然对立下的惨遭破坏的自然生态,离拉格比庄园不远的“毫无灵魂、丑陋无比”的中部煤铁世界:在阴沉的拉格比府房间里,她听到了矿井上筛煤机的咣当声、卷扬机的噗噗声、火车转轨的咯噔声和矿车嘶哑的汽笛声。当风从那边刮过来时,经常是这么个刮法,房子里就充满了烂泥里烧出的硫磺恶臭。即使是无风的日子,空气里也总是弥漫着地下冒出来的杂味:硫磺、煤炭、铁或硫酸。在这里,工业文明把自然作为人役使的对象,由于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人与自然呈现出对立的状态,自然生态失衡了。接着,作家同样描绘出工业文明下冷漠的社会生态:拉格比府与特瓦萧村之间没有往来,一点也没有。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双方都暗自怀有抵触情绪。这倒不是因为她和克里福德没有人缘儿,只是因为他们是另一种人,一种与矿工截然不同的人。这简直是违背普通人性、莫名其妙的事!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机械化在破坏自然生态平衡时,也造成社会生态的失衡,致使人性的异化和人际关系的畸形。然后,劳伦斯通过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失衡,透视出人们精神生态的虚无。男爵克里福德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心灵瘫痪的异化人。而婚后的康妮,承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她自由、淳朴、叛逆的天性被压抑,一种对于所有事物的惊恐、冷淡、空虚,一步步地侵袭到她的灵魂。
从废墟到原始森林,由异化人到自然人,劳伦斯用本真的性爱为男女主人公解除了心灵的桎捁,用非理性的意识找回精神的家园。这一文本解读透视出劳伦斯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及对理想和谐社会的深切呼唤。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是生态哲学中的整体观、联系观与和谐观等生态文化,这正是劳伦斯作品的文化属性。
四、结语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从被禁,到欣赏、批评的文学接受过程充分展现了接受者的感知、理解、评价、阐释等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并体现了这一过程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对文化意义的再衍生。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是由作家的文学创作行为和接受者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行为完成的。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以现代主义作家所特有的非理性主义思维、原始性文化、玄思的意象去关注人的自然本能、内心本我,探寻人类灵魂自我拯救的道路,写就一首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在小说的接受过程中,接受者和作品的文化意蕴已形成了一种双向转化与融合的过程。“说不尽”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1]文学接受[EB/OL].[2013-08-03].http://baike.baidu.com/link? url=QoEEEfQmZK5lTNJal0XaC4lgw-xNCFPVsGecn7eV4q 49vmy735OemAEu-vhcnywl.
[2]ZYTARUK G J,BOULTON J T.The Letters of D.H.Lawrence:Volume5[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
[3]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4)][英]劳伦斯.性与美[M]//劳伦斯.劳伦斯散文精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
[5][英]劳伦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M]//劳伦斯.劳伦斯散文精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
[6]林语堂.读劳伦斯[J].人间世,1934,(19):34.
[7][英]克莫德.劳伦斯[M].北京:三联书店,1986.
(责任编辑 苏 肖)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Literary Acceptance:A Case Study of Lady Chatterley’s Lover
LI Zhi-hua,ZHAO Shuang-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ijiazhuang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35,China)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a literary work not only comes from the writer,the work’s creative process,is also generated in th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readers and critics in their process of acceptance activity.Lady Chatterley’s Lover is British modernist novelist D.H.Lawrence’s last novel.Its cultural meaning is implied in the writer’s literary creation and deepened in the work’s literary accepta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al Aesthetics,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work undergoes a deepened process of cultural misreading,aesthetic acceptance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literary acceptance of readers and critics.And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literature criticism from the three aspects:sex theme study,archetypal criticism,ecological perspective.
Lau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literary acceptance;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106
:A
:1673-1972(2014)02-0079-05
2013-09-05
李志华(1967-),女,河北辛集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