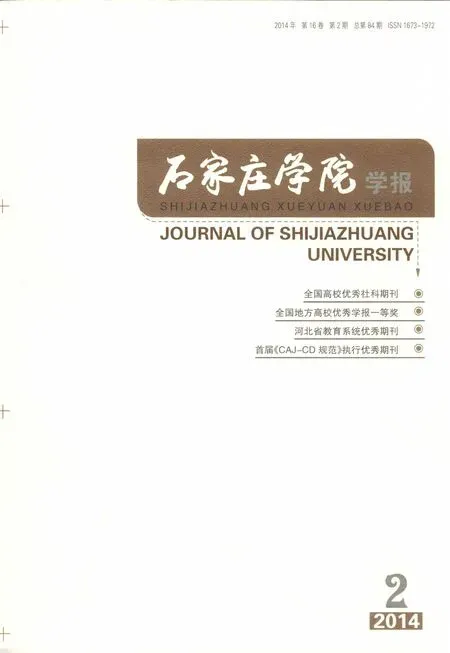清代州县词讼审断中的“律例”与“情理”
——以《樊山政书》为中心的考察
胡谦
(西安石油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清代州县词讼审断中的“律例”与“情理”
——以《樊山政书》为中心的考察
胡谦
(西安石油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通过对《樊山政书》的研究可以知道,“律例”和“情理”是清代州县词讼纠纷审断中重要的裁断依据。由于“律例”与“情理”所考虑的侧重点差异,在词讼中可能会出现“律例”适用与“情理”权衡之间的冲突。当“律例”适用与“情理”权衡二者间发生冲突时,官员们倾向于不拘于“律例”规定而是注重词讼情形从“情理”的角度裁断词讼纠纷。不过,由于“情理”涵义的模糊性使得在词讼审判中官员在运用情理方面容易产生偏差。
《樊山政书》;词讼;律例;情理
近年来,有关清代州县听讼制度的研究颇受学界关注并由此引起较大争论,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清代州县讼案审断中的“律例”与“情理”的运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拟以《樊山政书》所载案例、批牍为中心来考察清代州县讼案审断中的“律例”与“情理”运用。
一、《樊山政书》概述
《樊山政书》是樊增祥在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及江宁布政使任内公牍汇编,全书共二十卷,四十余万字。按照清代官制规定,按察使,一般称作“臬司”,掌管一省刑名司法。《清史稿·职官三》载:“按察使掌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所至录囚徒,勘辞状,大者会藩司议,以听于部、院。 ”[1]卷一百十六布政使,一般称作“藩司”,掌一省民政。由于清代官府司法与行政职能的合一,因此,布政使也会参与到司法审理,《樊山政书》中大量涉及司法审判的公文都需要布政使批示。樊增祥长期任职于陕西,先后任陕西宜川、咸宁(今西安)、富平、长安、渭南等地知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先后任陕西按察使、署陕西布政使和江宁布政使。樊增祥有着长期的司法审判经历,“每听讼,千人聚观。……於家庭衅嫌,乡邻争斗,及一切细故涉讼者,尤能指斥幽隐,反覆详说,科其罪而又白其可原之情,直其事而又挞其自取之咎”[2]2。其判牍在当时就被刊印,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到民国建立后法政学社将《樊山判牍》荐为审判必读之书予以刊印出版。《樊山政书》记载了大量樊增祥担任按察使、布政使期间的司法文书,包括对州县田土、钱债、户婚、斗殴等词讼纠纷的上详、禀、词讼册等所作的批语和樊增祥亲自审断案件的判决。从这些司法文书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晚清州县词讼纠纷的审断情况,而且更能看到作为省级的藩司、臬司在处理这些词讼纠纷中所持有的立场和处理方式。由于藩司、臬司在各省官僚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他们对词讼案件判决进行司法审核时所表达的立场、观点、态度必然会对州县衙门的词讼审断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引导,因此,《樊山政书》是我们了解晚清州县词讼审断情形的重要史料。
二、词讼审断中“律例”与“情理”运用
清人包世臣曾言:“窃照外省公事,自斥革衣顶、问拟杖徒以上,例须通详招解报部,及奉各上司批审呈词,须详覆本批发衙门者,名为案件;其自理民词,枷杖以下,一切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细故,名为词讼。”[3]251-252按照清代法律规定,州县衙门拥有对词讼的处断权,而不必像刑事案件那样需要逐级审转。同时,清代法律对词讼的处断依据比较灵活,州县官员可以根据词讼纠纷的具体情形作出其个人认为更为适合的判决。从《樊山政书》记载的司法文书来看,在处理田土、钱债、户婚等词讼纠纷时衙门会根据词讼的不同情形,或依“律例”或依“情理”或“律例、情理”结合进行裁判。
清代国家有关田土、钱债、户婚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大清律例》《大清会典》《户部则例》以及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内容虽然有限,但也是词讼审断的依据之一。如,陕西商州人樊应政之父在同治年间在“锦盛成”放赈铺借钱二百串,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此债本利已累计至八百串,樊应政偿还部分债务后,还欠四十余串。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本利又滚至四百余串,樊应政欲以他处产业抵押为条件,将当于“锦盛成”的旱地十七亩、瓦房九间换回出售还债,但是“锦盛成”东家张庆谟不允,致使双方涉讼。雒南县前后两任县令判决准许樊应政换回产业用以出售还债,但是张庆谟不服进而上控到商州,并声称愿将当价三百八十串捐作学堂经费。商州杨牧判令樊应政“按三百三十八串原价,与学堂另立当约,兼利稞约,每岁交钱十二串,有钱赎地,不赎交租”。针对此案,樊增祥指出,“夫以远年陈赈,利上滚利,律有明禁,法当严惩”,而商州杨牧的判决使“奸商出盘剥之余而更得捐助学堂之誉,穷民受久讼之累而仍纳连年佃户之租。颠倒是非,令人发指”。批示将樊应政所立学堂当、稞各约一并涂销,地仍归樊应政管业。按照“一本一利”的规定,张庆谟只应得钱四百串,另外四百串应予充公,同时勒令其再出四百串作为学堂经费。[2]228-229又如,长安县李永茂身故无嗣,其妻李刘氏为长女招赘王文元为婿,并立族孙金喜为嗣。李永茂之兄子李郁芳觊觎李永茂财产未果,遂起讼争。长安胡令判决金喜为爱孙、郁芳之侄为应孙,致使双方争控。此案上详到藩司,樊增祥亲自断决:永茂身故乏嗣,其妻李刘氏爱继何人即继何人,惟不许异姓乱宗。李郁芳照争继不继之例,永远不准干预李刘家事。[2]527综观《樊山政书》,词讼审断中依照律例作出判决的还是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清代国家有关“田产、钱债、户婚”的法律规定相对简单,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规定,这就导致不少词讼纠纷由于没有律例规定而无法依据律例作出判决;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州县词讼审断中州县官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根据案情自主选择审断依据。
在词讼审断中,“情理”作为裁断依据更为广泛地被适用,“户婚田土、诈伪欺愚,贵在酌理准情”[2]595。 从《樊山政书》的相关资料来看,“情”的涵义既指情节、情况等客观具体实际情况,也指情谊、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如,“人情”“情面”。“理”既指“天理”,即为统治者倡导的道德伦理准则,也指思考事务时所遵循的对同类事物普遍适用的道理。如,“有借有还”。“情理”二字连用往往指人情、事理。作为行为评价标准的“情理”,“既有强行性公序良俗的意义,又被作为妥协分担损失的折衷手法而使用……情理中浓厚地体现出来的是给予眼前的每个当事人各自面临的具体情况以细致入微的考虑及尽可能的照顾。”[4]35-36“情理”涵义的特征使其具有广泛的适用,特别是在律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情理”就成为词讼审断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由于词讼纠纷案情万端,要做到裁断准确、公允,也要求官员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具体情形,权衡 “情理”作出裁断。总之,“情理”是清代州县词讼审断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断案须通达事理”[2]413。 陕西石泉县黄继瀛拖欠黄光明当价稞谷,蔓讼八年之久,黄继瀛故后其妻黄马氏无力偿还,以致黄光明上控司道。两任县令断令黄马氏还钱四百串,并将其弟黄继洲关押为质俟还钱后开释。对此判决,樊增祥认为,“大凡积年帐债之案,要贵随时酌断,不能执一而无权”。黄继瀛在时就无力偿还,如今黄马氏一寡妇更无能力偿还全部债务,因此,裁断时应当考虑黄马氏家道和偿还能力予以酌减,或二百串或三百串,同时劝谕黄光明恤孤怜贫,只有如此才能使纠纷得以解决。[2]168又如,长安县高登瀛以银二百两开设恒兴绸铺,耿文耀为铺伙。高登瀛死后,耿文耀经营,文耀死后其子耿生全经营。三十余年间以二百金本钱共获利银八千六百两。按“银六人四”标准,耿生全少分而高家多分。分账后不久,高石氏控告耿生全侵占。胡令判决耿生全出银一百五十两,并以耿生全“立意停门,致亏银四百两”为由断令生全一人赔偿。后任张令请人清算历年账目,实则短缺银三百两,遂判令生全出银一百五十两了事。生全由于无银可出,只得用十二亩地作抵。对于长安胡令、张令的判决,樊增祥认为不妥,“查耿氏父子领做高姓生意三十余年,获利将及万金,所短不过三百,而分利之时,则又高长耿短。论获利之丰,则与高为有德,论分利之少,则在耿为吃亏”,况且在州县审理中 “质讯三十余堂,其账簿四十余本,率由高石氏家中起出,生全不但毫无隐匿,而且早已清交”。这些都说明耿家在生意中并无侵占、隐匿的图谋。耿家辛勤经营使高家获得厚利,只因三百金的经营亏损就使耿生全“经年讼累,复受官刑”,且因无钱还要卖田作抵,实是“情殊可悯”,因此,“以情理言,即以此三百金作为补其亏可也,作为酬其德亦可也”,最后樊增祥判令撤销张令裁断生全出银一百五十两的判决,毋庸卖田作抵。[2]356-357再如,蒲城赵鼎五死后遗有一妻、一妾和一子,子为妾生,经乡官分析遗产,妻、妾、子各得六千金。妻宋氏回娘家居住而妾陈氏与子回蒲城居住,宋氏耗尽财物后携娘家多人借口来蒲城安葬赵鼎五,实则觊觎陈氏母子财产,因陈氏母子闭门不纳以致涉讼。彭令断令嫡庶同居,共同营葬。陈氏不服上控,未获批准,于是携子出走汴,数次传唤不到以致此案三年未结。新任陈令具禀请示。樊增祥认为,“凡断此等案件,最患泥一定之名分而不谅人情”。宋氏身为正室,丈夫亡故之后本应与陈氏同心抚养遗孤,然而夫君尸骨未寒便分财物径自回到娘家,浪荡挥霍完后又欲剥削陈氏母子,名为正室实则鼎五罪人。彭令判决嫡庶同居,看似冠冕堂皇实为害赵氏一门。嫡庶若能同居则在汴时就不会分家,宋氏视陈氏母子为鱼肉,强令嫡庶同居最终可能会令陈氏母子饿死。基于以上判断,樊增祥断令宋氏若住夫家则由夫胞弟赵坤五照管,若回娘家则由其兄养赡,永远不准宋氏侵占陈氏母子财产。等将来遗孤成年,或是岁给宋氏养赡之资,或是迎嫡同居均可。彭令则记大过一次“以为专打官话、不体人情者戒”[2]137-139。本案从律例角度来看并无明确规定,而要做到解决纠纷就必须正本清源。宋氏来蒲城的目的就是企图侵占陈氏母子财产,若判令嫡庶同居则必然导致宋氏挥霍陈氏母子财物而陈氏也必不心甘,最终纠纷无法平息,因此,这种情形就必须体谅人情才能做到保全陈氏母子。
“律例”和“情理”作为州县词讼纠纷审断的依据,它们之间并非隔绝开的,若能在既有“律例”规定的基础上又能斟酌“情理”,做到“律例”“情理”兼顾,“情法两平”则是善断。陕西商州山阳县石明顺之女许配陈维清之子为妻,未及过门,陈家搬到鹿州,自此长年音讯全无。石明顺之女长大而恰值荒年,石明顺便把女儿配给葛成松为妻,一年后育有一子。陈家在音信断绝七八年后返乡,提出履行先前婚约并肇起讼端。针对此案,樊增祥指出律例虽有“准先聘者得妻”的规定,但是“夫在外三年不归,并无音问,女年已长,准其父兄另行择配,亦定例也”。陈家父子七年无音讯,石氏另嫁也是天理、人情,因此,现在这种情况只能断令石明顺归还陈家聘礼,不能拆散葛氏夫妻。况且“将石氏断给陈门,幼子留於葛姓,夫妻母子顷刻分离,必使妻为再醮之妻,子为无母之子,不仁不义,天理安在?”该案最后判决石氏仍归葛姓,石家退还陈家聘礼,如此判决做到了既有律例可循,同时考虑到天理、人情的要求。[2]113又如,长武县崔阎氏被其恶姑洪氏折磨欲死,荒年外逃,改嫁张岐娃为妻并生有儿女。五年后张岐娃夫妇移居崇信,而洪氏以奸拐为由控告张岐娃,官府审讯后将崔阎氏断给后夫。“归后夫为从一而归,前夫转成再醮也”,这样判决既考虑到崔阎氏在崔家时仅是童养媳的身份,又保全了崔阎氏从一而终的名节,樊增祥在批语中称赞该判决“于理、于例、于人情无不推求至当,夫岂俗吏所能耶? ”[2]512因此,州县官若是能够将“律例”与“情理”在词讼审断中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每案依律准理,执法原情。问之民,自谓不冤;即达诸部,断无可驳”[2]418,则达到了理想的审断结果。
三、权衡“情理”优于“律例”适用
“律例”与“情理”是清代州县词讼纠纷审断中的两个重要依据,熟悉“律例”、洞悉“情理”,做到“情法两尽”是州县官员做到公允判决的必要条件。然而,现实情况却往往并非如此简单。“律例”针对的是词讼纠纷的一般性情形,它重视的是建立起一种具有普遍适用的裁判标准;而“情理”则强调的是考虑具体词讼纠纷中当事人的实际,它重视的是词讼纠纷中的特殊性因素,因此,在具体的词讼纠纷审断中就可能出现“律例”规定与“情理”权衡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形。一旦,“律例”与“情理”在具体词讼中产生矛盾时,是依照“律例”还是斟酌“情理”变通处理?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律例”适用与“情理”权衡二者之间的一个裁判标准选择问题。从《樊山政书》的相关资料来看,在词讼纠纷审断中樊增祥更加强调州县官员根据案情斟酌“情理”而不要死守“律例”规定。
婚姻纠纷是时常会涉及“律例”与“情理”冲突的纠纷,在此类纠纷中受到地方习俗、当事人现状等因素的影响,州县官员往往会斟酌“情理”变通处理。如,针对“一女两聘”的情形律例规定“两家争娶,准先聘者得妻”,但是现实纠纷的情形则往往比较复杂。如果被聘女子还未成婚,按照律例由先聘者得妻尚好断结;一旦被聘女子已与后聘者成婚,或是已生养子女,则依照律例断处就可能导致背离道德伦理、戕害人伦亲情的后果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斟酌“情理”而非依据“律例”就会成为此类词讼裁判时所要考虑的因素。前述山阳县葛石氏案就是这样一起典型案例,山阳县刘令拘泥于“两家争娶,准先聘者得妻”的律例,判决石氏归陈家、幼子留于葛姓,如此判决导致“石氏一岁而再婚,其子刚弥月而失母”的结果,此案经张护牧斟酌情理改判,石氏仍归葛姓、石家退还陈家聘礼才使石氏幸免失节而幼子也不致绝乳。山阳县刘令的判决虽然于律例有据,然而樊增祥却痛斥这样的判决致使石氏 “失节败名”,因此,“不仁不义,天理安在?”“有是非恻隐之心者固如是乎?”他说,“世称州县官为民之父母,世间有女者愿其从一而终乎,抑愿其一嫁再嫁乎?”对于此类纠纷判决,樊增祥提出,“大凡判断婚姻案件,以保全妇女之节为主”的原则[2]124,即在涉及妇女婚姻纠纷的审判中应该以保全妇女“名节”为优先考虑因素和审断依据选取的标准。从本案中来看,“理”一方面体现的是国家倡导的“从一而终”的妇德,而另一方面体现的是陈家外出常年无音讯致使石氏未能及时成婚的理亏;“情”则是父母子女的天伦亲情,试想对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子来讲,母子顷刻分离是怎样一种人伦亲情的灭失,无论对于母亲还是幼子而言无疑是一起悲剧。因此,本案从整体上来看,山阳县刘令的判决在律例方面表现为未能准确理解、把握律例规定,更重要的是从“情理”上来讲背离人伦亲情、荒谬糊涂,最终刘令也因错误判决被记过。从《樊山政书》来看,保全名节是贯穿类似婚姻纠纷判决的基本原则,如咸宁县程英盛案,“夫一女两聘,既已于归,只可断还礼银,不可使一女蒙二夫之耻”[2]84;华州王氏案,“以一女子在侯家数月,迭配二人,任其糟蹋,今又断归另聘,时仅数月,年未二旬,已为三人之妇,谁非父母,谁无儿女,如此伤天害理,本司实不能姑容矣!”[2]93再如,按照律例规定子女婚嫁由父母之命,但是如果这种主婚若违背“情理”则无效。临潼县杨科科控宋腊儿一案中杨科科与宋杨氏有奸情,宋杨氏有女云儿自幼认族叔宋腊儿为义父。云儿长大,宋腊儿担心沾染母习,将义女带回伊家择配。宋杨氏遂令杨科科具控,称此女已许配杨科科为妻,腊儿欲强行另卖。经官府讯断,认为女无绝母之理,杨氏现有同居胞嫂宋刘氏由其将云儿领回,与杨氏商量择配。对此判决,樊增祥认为迂缓,杨氏无耻与奸夫淫乱复将其女许于奸夫,虽然律例有女子婚嫁遵由母命的规定,但是杨氏的淫乱行为从“情理”上来讲意味着“母道已绝”,母道绝则杨氏不为其母,而将女许配奸夫更是违背天理,因此,云儿的婚嫁由杨氏决定就背离“情理”的要求。[2]350
“买休卖休”是清代词讼纠纷中的一种,在这类纠纷审断中也常常会存在“律例”与“情理”的权衡问题。按照清代律例规定,“买休卖休”中被卖妇女要同娶主离异归宗,但在实际讼案中也可能事涉复杂,如果严格按照律例断离归宗,可能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如何做到至当判决就会涉及“律例”与“情理”的权衡。咸宁县民陈世德荒年弃妻不顾,任其妻另嫁闵福成并生育一女,四年后陈世德控领荒年已弃之妻。该案经刘令审断,认为陈世德“荒年弃妻而年丰则又索妻,殊属不合”,但仍判令陈世德出钱十五串领妻。其后,舒令到任,闵福成夫妇复控,闵朱氏表明不愿归陈世德且挂念新生之女。舒令审讯后也明言是陈世德不合,但陈世德 “惟系本夫,自应断归领回”。清算朱氏四年食用费用,令陈世德交钱一百一十三串,然后领妻。按照律例规定,典卖妻子,应当断离,因此,从律例上来讲,刘令、舒令将朱氏断归原夫于法有据。但是,樊增祥却对刘令、舒令的判决进行了严厉批驳,“前后两任,抱定死例,断归前夫”;“拘于死例,不体人情”;“此等判词,不仁不明,阅之令人胸中作恶”。樊增祥认为“作官第一要体人情”,陈世德荒年弃妻早无结发之情,四年之久从不追寻,陌路相逢遂起图讹之念,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多得钱财。陈世德初次呈词中言其乞食撞见朱氏,这说明其根本不可能有钱赎妻,因此,陈世德未领妻之前已蓄卖妻之志,即使不卖,从前陈世德就不顾朱氏死活,而现在朱氏又历数陈世德浪荡,强令复合,终必分离。况且陈世德不顾己妻,怎能疼他人之女?如果将朱氏母女强判给陈世德,将来必定母逃女亡的结果。基于上述缘由,樊增祥改判此案,将陈世德杖责枷号,出具恩义早绝永不索妻甘结存卷,朱氏仍归闵福成为妻,并札十二府州“以后如有荒年弃妻,在后夫家已生子女者,均照此案办理”[2]181-183。细研樊增祥对此案的批示,此处的“人情”体现的是对朱氏再婚后的人伦亲情以及陈世德卖妻劣行的综合考虑。舍弃“律例”,遵循“人情”将朱氏断给后夫既避免朱氏再次被卖,同时也使幼女有所怙恃。本案中樊增祥再三强调“作官第一要体人情”,不应拘泥于“死例”的立场,进一步说明州县官在词讼审断中根据案情斟酌“情理”比死守“律例”更为重要。再如韩德元卖妻舒氏、孀妇岳氏案,李令依照律例判决岳氏、舒氏分别与后夫离异归宗,彩礼追还,娶主免议。对此判决,樊增祥认为,“此於例虽合,而於情未安也”。韩德元夫妇由皖至豫,因流落而卖休舒氏,而岳氏亦襄阳孀妇被流转贩卖。岳氏本就无夫而舒氏虽有夫实则无夫,如果依照律例判决与娶主离异归宗,舒氏、岳氏若各归原籍,则不知母家是否还有亲人?其如何安身?舒氏、岳氏的娶主刘姓、徐姓“既各以百数十千买人,其如意可知,两妇得所亦可知”。因此,樊增祥认为,“与其断离而仍无所归,何如断归后夫,俾各得其所之为愈也”。同时告诫同僚,“断案与办案不同,不必尽拘成例”[2]279。正是考虑到舒氏、岳氏的现实情况,与其按律例断离使其无所依靠,不如 “事宜从权”,让舒氏、岳氏仍归后夫,从而生活有所依靠。在此案中从“情理”角度出发对当事人现实情况的考虑成为了舍弃“律例”的正当理由。
析产纠纷中也会涉及“律例”与“情理”权衡的情况。按照清代律例规定,“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然而,现实中父母的偏爱、孝道的谨守等都会成为析产时所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在析产讼案中斟酌“情理”就难免了。如,商州徐宾刚、徐宾强争产案。徐宾刚、徐宾强之父徐兴元,育有六子,同治元年(1862年)徐兴元自提养膳田一份,将剩余产业六股均分。后来二房、五房、六房户绝,徐兴元将此三股房产业自行掌管。迨到徐兴元亡故,三子徐宾刚掌管了父亲留下的四股产业,独占五股产业,而长房寡嫂、四房胞弟仅各得一股产业,兄弟由此肇启讼端。商州尹牧上禀此案到藩司,樊增祥直接就该案进行了判决。樊增祥认为此案若从公剖断,应将原业一齐合拢,作为三股均分,方为公允。“然事须审势,尤贵衡情。”试问为何一人能独持五股产业?那是因为徐宾刚与其父生死相依之故。“兴元在日,始则长、次子析居另度矣。及五、六夭亡,四房宾强,苟得亲心,岂肯令其出居於外。乃六子之中死者死,分者分,惟宾刚一人,始终与父同度。是以兴元既死,赡产、绝产概落宾刚之手。”因此,“平情而断,分兴元之产,当谅兴元之心。其心有爱憎之殊,则分产亦宜有厚薄之异。”此外,兴元继妻健在而夏氏与徐宾强就要强索膳产,足证平日必定不孝顺其父。综上所述情况,樊增祥批示将三股绝业由三房各得一股;兴元继妻仍同宾刚同度,膳产由宾刚管理,将来继母亡故赡产由宾刚独得。此案中,樊增祥没有按照律例将兴元遗留产业均分给长房寡嫂、宾刚、宾强而是七股产业夏氏、宾强各得二股,宾刚独得三股。个中缘由仍旧是依据“情理”进行剖断,此处的“情”是宾刚与其父同居,“甚得亲心”,兴元与宾刚有更多父子天伦亲情,而此处的“理”则是指宾刚孝顺父母,符合儒家道德标准提倡的孝道。“此项膳产归宾刚独得,以慰兴元夫妇爱子之心,以酬宾刚始终奉养之孝”,同时,樊增祥认为如此判决可以起到 “使愚夫愚妇咸知得亲心者分产较多,不得亲心者所得较少,亦足以劝孝而惩逆也”[2]30-31。
从以上樊增祥或批、或断的词讼纠纷,我们看到了在“田土、钱债、户婚”细故纠纷审判中当依照律例裁决时可能会产生樊增祥认为的不符合 “情理”的结果时,对“情理”的适用就成为舍弃“律例”的正当情由,而这也反映出“情理”具有优于“律例”的适用地位。有学者认为在是非判定的标准上,“虽然律例确乎为一种‘是非’的标准,但是‘情理’却是在事实上超越律例的‘更高’的‘是与非’和‘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 ”[5]106
四、余论
从《樊山政书》可以看到,在清代州县词讼审判中“律例”与“情理”都是裁断词讼纠纷的依据,或依“律例”或依“情理”,或者“律例、情理”结合。不过在选择这些依据时,由于清代官员重视的并非是是否严格依照某种现存的规则标准作出判决,而是重视判决是否合乎当事人的具体情形,能否做到权衡各当事人的利益,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化解纠纷,从而得到一个他们所认为圆满的解决结果,因此,在具体词讼中,官员按照自己对讼案情形的了解和希望达到的结果来选择“律例”或“情理”,哪种依据能最好的实现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就依据哪种。
其次,由于有关词讼纠纷的律例的不完备,使得能够按照律例实施裁判的词讼纠纷相对较少,大多数词讼判决基本还是基于权衡“情理”进行裁断的,因此,“情理”在清代州县词讼审断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依据“情理”实施裁断是州县官员的主要选择,樊增祥也多次在批语中强调,“户婚田土、诈伪欺愚,贵在酌理准情”[2]595。即使律例对某种词讼纠纷已经有明文规定,只要不是过分违背律例精神,州县官员还是倾向运用“情理”来实施裁断。清代方大湜曾言:“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但本案情节应用何律何例,必须考究明白,再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与律例十分相背。”[6]卷二王凤生也谈到:“听讼又非徒守其经而拘於法已也。所收民词千态万状,其事故亦有百变纷呈,尤须相时因地,体俗原情以恤民隐而通权变。”[7]更重要的是,州县官的职务重点为听讼与维持治安。官员从行政事务的角度处理词讼,重点是解决纠纷、平息争执、稳定秩序,刚性地诉诸法律反而可能于事无补。从现实角度看,如坚持诉讼及严格依法裁判,黑白分明,可能激化当事人成为“讼仇”,倾家荡产,本属“细事”的词讼或为恶化当事人关系以致冲击社会秩序的源头,与官员行政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故对词讼而言,纠纷解决而非法律形式主义倾向的规则之治,乃州县官实用进路下的选择。[8]
第三,当出现适用“律例”会导致背离“情理”的结果发生时,樊增祥特别强调权衡“情理”,应当依据“情理”而非“律例”实施裁断。那种不辨具体情由,拘泥律例者会被认作是不通人情事理,其判决则被视为谬判,并可能由此招致申斥、记过、详参等处分。而只要州县官员认为其判决符合“情理”,即使判决可能完全背离“律例”规定也是正当的。在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方面,“情理”具有比“律例”更高的地位,“情理”也是判断“律例”是非的标准。樊增祥明确指出:“情理外无法律”[2]556,言下之意,“律例”应该符合“情理”的要求,如果“律例”导致违背“情理”的结果产生,那么舍弃“律例”、权衡“情理”也就是正当的,而这也说明在词讼审断中“情理”具有高于“律例”的地位。从《樊山政书》相关批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词讼判决中“酌情准理”已经成为评判判决臧否和州县官员审断能力高低的一项重要标准,如《批朝邑县曾令自理词讼月报清册》:“通阅册报四案,准情酌理,持语平平。”[2]279《批雒南县丁令词讼册》:“通阅四案,判断允协,情理兼尽。 ”[2]355《批扶风县谭令词讼册》:“平情断事,实获我心。”[2]392《批风翔县彭令词讼册》:“判词准情酌理,煞费苦心。”[2]424《批蒲城县曾令士刚词讼册》:“物理人情,折衷至当。 ”[2]515
第四,从《樊山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词讼审断中能公允、恰当运用“情理”的州县官员比较少。导致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晚清州县官员的整体素质下降。樊增祥指出当时州县官员构成中充斥大量的捐班知县、不学而仕之人,能“知明处当者,七十余厅州县不过得半”。这种状况导致“所断之案,自己问心不过,不堪示人……此则审案虽多,可以告人者实少”[2]342。 其次,“情理” 相对于律例而言,其涵义具有明显的模糊性,如何在具体词讼审断中运用“情理”就主要依靠主审官员个人的对“情理”理解。由于学识、人生经历、职业历练、道德品行等不同,州县官员对“情理”涵义的理解会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词讼审断中应该如何权衡“情理”就必然不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情理”还可能成为官员谬断、文过塞责的借口。如,西乡县王隆德等妄控,知县李令反而断令被告给钱二百串。对此判决,樊增祥指出“其判断此案亦自觉善于了事,其实不过因王隆德是一健讼廪生,姑令他人出钱以媚之”。李令“庸懦巧滑而尤自附于准情酌理之列,可鄙可恨”。[2]119诬告按律应当反坐,此案中李令没有惩罚诬告者,反而以“准情酌理”为名断于钱财,如此实际上起到鼓励诬告的作用。正是针对此种情况,樊增祥指出:“吾尝谓,案非聪明人不能问,非英爽者不能结,然才大而心不细,转不若沈实谨厚者之推敲入也。若夫天分高、更事多,而又不厌鄙琐淆乱,一一为之分清理白,牧令虽众,能有几人? ”[2]409-410从《樊山政书》相关史料来看,大多数州县官在词讼审断中对“情理”的把握、运用是不准确、恰当的,遭到樊增祥的批驳、斥责。对“情理”的准确把握需要州县官员具有天资、学问、阅历等基本素质,特别是阅历,只有在审判实践中不断历练才可能熟悉人情物理,“大抵审判之事,一要天分,二要学问,三要阅历,四要存心公恕”[2]595。“作官者,但立意要好。”[2]305即使那些有多年审断历练的官员也可能出现偏颇,如,陈世德卖妻案中,樊增祥对舒令作出如此糊涂判决大为失望,“舒令乃老吏也,何竞拘于死例,不体人情,至于如此,意者不更事之委员所为耶?”[2]178像舒令这样有长期历练的官员也会出现对“情理”把握的偏颇,遑论及那些刚刚入仕的官吏。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讲,樊增祥强调词讼审断中运用“情理”的目的本是为了更好地考虑词讼审断中的具体因素从而得到公允、恰当的判决结果,然而,由于晚清州县官员素质的良莠不齐,“情理”适用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判决结果随意性和不公正性。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樊增祥.樊山政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包世臣.齐民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日]滋贺秀三,寺田浩明,岸本美绪,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5]赵娓妮.晚清知县对婚姻讼案之审断 [J].中国法学,2007,(6):92-109.
[6]方大湜.平平言[O].官箴书集成本.
[7]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2.
[8]邓建鹏.词讼与案件:清代的诉讼分类及其实践 [J].法学家,2012,(5):115-130.
(责任编辑 苏 肖)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Reason in Civil Trial in Qing Dynasty:A Case Study of Fanshan Zheng Shu
HU Qian
(School of Humanities,Xi’an Shiyou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65,China)
On the basis of study on Fanshan Zhen Shu by Fan Zengxiang,it is found that that law and reason were the major trial rules in the process of civil trails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the Qing Dynasty.On account of emphasis difference,there appeared conflicts between law and reason in the process of civil trials. When the conflicts happened,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inclined to emphasize reason rather than law. However,because of the fuzzification of the meaning of reason,the official easily had deviation in its application.
Fanshan Zhen Shu;legal case;law;reason
D929
:A
:1673-1972(2014)02-0050-06
2013-08-01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1JK00217)
胡谦(1975-),男,四川达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法律史、法律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