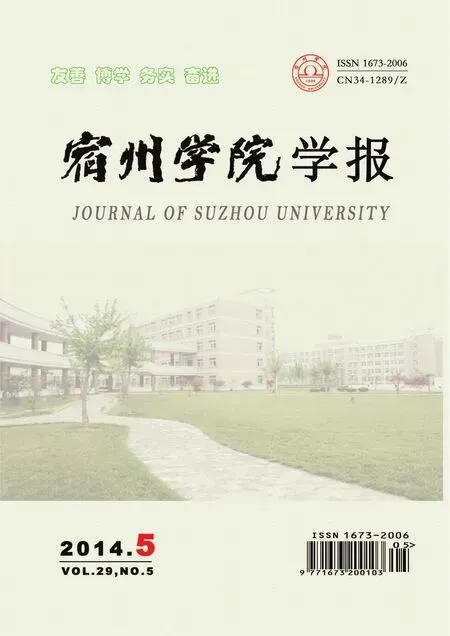议图文接受的差异性
吴胜男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000
新文学作品的装帧作为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代表,其封面图像极具研究价值。本文以新文学作品封面图像文本和作为文学内容的语言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读者在接受图像文本和语言文本存在的差异性以及其被接受时的角色扮演。对于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来说,无论是作家、读者还是图像作者,他们在创作或是阅读时面对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而是由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所构建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接受的主体可以分为三类:语言文本的作者、封面图像作者、普通读者。这三类“读者”对图像文本与语言文本的接受有明显的差异性,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语言文本的作者实为语言文本的写作者,又同时是图像文本的读者,但当他们“沦为”读者时就意味着话语主体发生着改变。“文本一经完成,是谁在叙述已无关紧要,也无从知晓,只剩下话语的痕迹、作品中的象征隐喻供我们品味。”[1]52语言文本作者的话语权移交到了图像作者的手中,就意味着“文之意”在扩充、延绵,或是歪曲。“当我们在自己的讲话里重复我们交谈者的一些话时,仅仅由于换了说话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语调的变化:‘他人’的话经我们的嘴说出来,听起来像是异体物,时常带着讥刺、夸张和挖苦的语调。”[2]对于图像文本而言,语言文本的作者消失了,那么“文之意”也就消弭了权威性,成为了各种凌乱文化源头的混合物和各种引证的编织物。如果说语言文本作者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了图像文本的读者,那么他们对待图像文本又会是什么态度呢?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研究:第一,如果图像文本的设计“图之意”遵从“文之意”,图像文本与语言文本没有发生矛盾性的冲突,那么他们会认为这是一次符合他们文化传统和阅读习惯的审美体验,会感到一种消费图像文本而带来的满足和安慰。第二,相反的,图像文本传达出的意义没有符合自己的心理预设和期待视野,就会感到体验图像文本带来的失落感,会主观地认为图像文本的存在会错误地引导读者的阅读视界,使他们不会真正地领悟到“文之意”。
封面图像作者作为语言文本的特殊读者,既是语言文本最初的读者,又是将其转化为图像文本的“实现者”[3]。图像文本的作者深谙语言文本的故事情节、叙事策略、矛盾冲突,用他们独特的审美视角,将语言文本转化成为富有想象力的图像文本。图像文本给普通读者预留出了广阔的审美空间,使读者任意远望、浮想联翩。“艺术家自然也要从一切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里解放出来,忘记自我的存在,消失在对作品深层次的感知和情绪中,还要尝试摆脱时刻跳出的客观自我、空洞的媒介、嗓音与杂念,进而成为创作中一串温和的回音……不仅为艺术家开始重新定义新作品提供了思维空间,还可启示挖掘对书籍内涵深度的洞察力和感受力。”[4]162-163图像的设计者将语言文本外化的过程也是图像作者的感悟与语言文本的内容融合在一起的过程,这种融合,是图像作者主观的结果。图像作者主观地将个人对语言文本的见解和述评人为地外化在封面的图像文本上。这样看来,图像作者又似乎变成了一个隐藏在书籍中的潜在的“评论者”。他可以用这一特殊身份和每一位读者对话,用抽象化的语言言说着个人的独到见解或者是引导着广大普通读者的阅读思考。当然,这种隐匿的引导会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思维方式,使其最后认同图像作者的评说。有认同就会有分歧。“艺术家不可能完整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因而便给读者、阐释者留下了可以根据进行能动阐释和建构的空间。”[3]这就是产生分歧的可能性。部分读者并不认同这种“画外音”似的、带有个人色彩的诠释。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分歧是必然的。但是,由此产生的像外之意,更是刺激着读者的阅读兴趣,以便查找图像作者观点的根源所在。此外,图像作者除了是语言文本外化成图像文本的实现者和语言文本内容的评论者外,还是特殊的“观察者和表演者”[3]。所谓的“观察者”“表演者”是和语言文本的作者、普通读者联系在一起的。图像作者在饰演读者这一角色时,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认真研读语言文本,观察语言文本的作者想告诉读者什么以及其心理状态和言说的表情,然后用色彩、形象、构图的特殊“表演”方式在书籍封面这一特殊的“观景台”上“表演”出来。这样的言说方式,为读者营造了一种特殊的、个人专属的、近观体验的“舞台剧”表演。语言文本的作者、图像作者、读者在这场“舞台剧”表演当中不再是各自孤立的、敌对的、各执一端的,而是尽情地对话言说,实现作品之外的扩充和延绵。“书籍设计的本质是要体现两个个性,一是作者的个性,二是读者的个性,设计即是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可以相互沟通的桥梁。”[4]162图像作者作为语言文本的实现者、评述者、表演者、观察者,是连接语言文本作者、读者的中间桥梁;图像文本的参与实现了三者在求同存异的对话中实现语—图间的互文和互补。
普通的读者是文学作品的主要接受者,图像作者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阅读方式及审美体验。就新文学作品所处的时代来说,读者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他们的接受环境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这里不作过多的论述。读者接受对象的增加——“一变二”。在新文学作品出现以前,简策形式、卷轴形式、册页形式等书籍装帧都几乎没有专门的书籍封面设计,但是,到20世纪初,受到现代印刷术的影响,书籍的装帧形式和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鲁迅大力提倡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一大批优秀的学者、美术爱好者参与其中。大量优秀的书籍封面装帧涌现出来,刺激着读者的眼球。由此一来,读者的接受对象就“由一变二”,即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接受对象的增加,必然会引起阅读方式的变化——从读字到图文结合。图像文本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要求读者借助自己的想象力解读图像之意和理解文之意。图像文本的出现延长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且又增加了整部文学作品的艺术气息,使得文学的陌生化原则变得模糊。在这里,读者不再惧怕任何一本陌生的书籍,只要有封面图像文本的存在,总能找到一点线索去审视它。这种图文结合、图文并茂的视觉演绎必然会导致受众审美体验的改变。“读者参与到文学本身的‘活动’和‘生产’中,通过发现文本意义的新的组合方式重写、再生产、再创造文本,使其意义和内容可以在无限的差异中被扩散。”[1]59设计者们不可能通过图像来完全表达自己心中之意和文中之意,这就给读者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他们通过观看、凝视、思考,充分调动自己的审美感官,诠释“图之意”与“文之意”。
语言文本作者、图像文本作者和普通读者组成了一个有机的“阐释体”——挖掘“文之意”与“图之意”。他们在“新文学作品”这块膏腴的土壤上自由地吮吸文本的意义,挖掘阐释空间,拉近了读者与文学之间的距离,对文学的发展和意义的建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王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2
[2]赵先章.超文性戏仿文体解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33(3):101-109
[3]张玉勤.论中国古代的“图像批评”[J].中国文学研究,2012(1):73-76
[4]吕敬人.书艺问道 [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162-163 (责任编辑: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