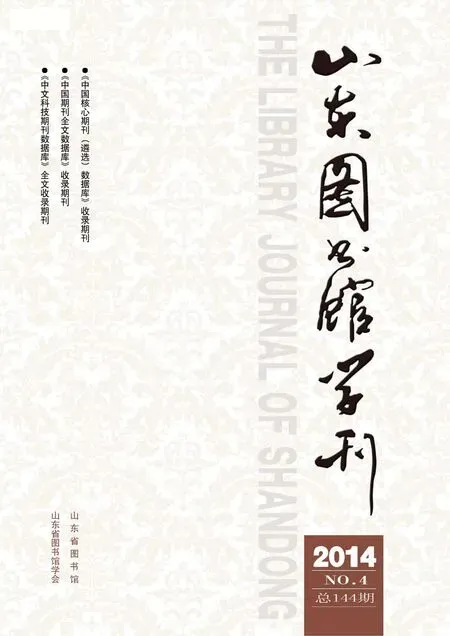“但求解古人故旧之沉郁”
子 张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32)
三月卅一日,下午先后为研究生和大一新生讲授近代印刷出版业之发达,晚间却忽然收到宁文兄短信,告知来新夏先生刚刚在这个下午过世,年九十一岁,并准备于《山东图书馆学刊》下期组织纪念,问我可否写点什么。
虽然我与来先生既不熟悉,亦无往来,但又觉得确有某些话要说,故立时回复宁文兄,答应写段文字略表悼念之意。
来先生鼎鼎大名,我总是知道的,可因为专业离得稍远,往还的机缘也就不容易碰到。没想到2006年春天,我应约赴天津南开大学参加诗人穆旦的学术研讨活动,竟然邂逅了这位著名的前辈学者。先是他来看望和我同住一室的海宁学者陈伯良先生,彼此简单交流几句,我始知他乃浙江萧山人。翌日会议开幕,来先生出席了开幕式。而会议期间他是否有过发言,我已记不清楚了。
前年初夏某日,也是宁文兄短信告知,来新夏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暨九十华诞庆典在萧山举办,约我带本书去请其签名。惜我手头只有来先生主编“中华幼学文库”并作序之一种《杂字》,想想远不够“粉丝”级别,遂作罢。但还是当即乘车赶到萧山宾馆,见到了宁文、韦泱诸兄,宁文甚至为我预留了一套纪念品,包括一幅“寿”字挂轴、一帧“中国邮政”纪念封、一本中华书局版精装《友声集——来新夏教授九十初度暨从教65周年纪念集》,以及一部朴庐书社印制的繁体竖排《来新夏随笔选》。尽管第二天未再赴会,却因了宁文兄的邀约,倒一下子有了若干与来先生有关的物品,便再也不能说与来先生无缘了。
我于来先生之史学、目录学、图书馆学乃至写作成就,近乎盲者,实在无由置喙。然读过他的《怀穆旦》一文,却感到文章虽短,感慨甚深,由此或可触及到来先生心路之一隅。
来先生曾自谓其散文随笔“不外三类”:一曰观书,二曰窥世,三曰知人。“观书所悟,贡其点滴,冀有益于后来;窥世所见,析其心态,求免春蚕蜡炬之厄;知人之论,不媚世随俗,但求解古人故旧之沉郁。斯固可谓冷眼热心之作,亦我食草出奶之本旨。”(见《人生也就如此》)
我以为,《怀穆旦》一文,正是一篇“不媚世随俗,但求解古人故旧之沉郁”的“知人之论”。
生前寂寞无尽,死后享誉日隆,是一切人格高洁、艺境超前诗人的普遍命运,穆旦自不例外。而世俗之人,却既可以与俗世同谋冷落诗人于前,复可以攀附诗人荣名以自售于后,实则前倨后恭,皆非本心,功利之欲使然耳。
而来先生此文,却并非那种借光自赏的投机之作,他反反复复强调的,只是希望在面对穆旦的光荣时,别忘了穆旦后半生所遭遇到的厄运和苦难。
之所以出此言,是因为来先生在“文革”时期,曾经与穆旦由较远而较近,由同命运而成为在一起打扫校园和厕所、清洗游泳池而近距离接触的难友,因此成为穆旦受难史中某个时段“唯一的见证人”。故而来先生表示:“为了让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后死者应该担负起这种追忆的责任。”这正是此文的意义所在。
文章既对穆旦“文革”前十几年在南开的遭际有所陈述,更对穆旦于“文革”初期几年进一步的沦落作出了有力的见证和描画,令读者像是亲眼看到了身处苦难深处的诗人影像。其中当然也有来先生自己对穆旦的印象,比如:“后来当我读到他的全集时,那种才华横溢的诗才与他在游泳池劳动相处时的形象怎么也合不起来。他有诗人的气质,但绝无所谓诗人的习气。他像一位朴实无华的小职员,一位读过许多书的恂恂寒儒,也许这是十来年磨练出来的‘敛才就范’”。1970年,二人分别被解送到不同的地方“劳动改造”,直到四年之后才又开始在校园里偶尔碰到。限于严酷的人人自危的政治形势,这自然也算不上什么深度交往,然毕竟遭际相似,彼此心有戚戚,能够相互谈谈诗歌甚或彼此宽慰几句,已经极其难得了。看得出,两人性情有差异,而穆旦长来新夏五岁,故而穆旦常处在“嘱咐”、“开导”地位,也是可信的。
在文章后半,来先生也有疾言厉声为穆旦抱不平的陈辞,那就是对有关方面对穆旦错案平反一再拖延的愤怒:“错误决定何其速,而纠正错误又何其缓?”
也许从这里,读者可以感觉到来先生更为幽深的感慨和疑问。一个竭尽全力热爱祖国的诗人,何以长期遭到严酷的打击和折磨?何以“生前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我能从来先生的话中品味到一种浓浓的苦涩。来先生说:“穆旦喝尽的苦酒给生者带来了许多理不清的思考。真正希望穆旦喝尽了苦涩的酒,把一切不该发生的悲剧一古脑儿担走”,这其实也是所有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心声呵……
谨以此文表达对来新夏先生的敬意和悼念。
二零一四年四月三日,甲午三月初四,于杭州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