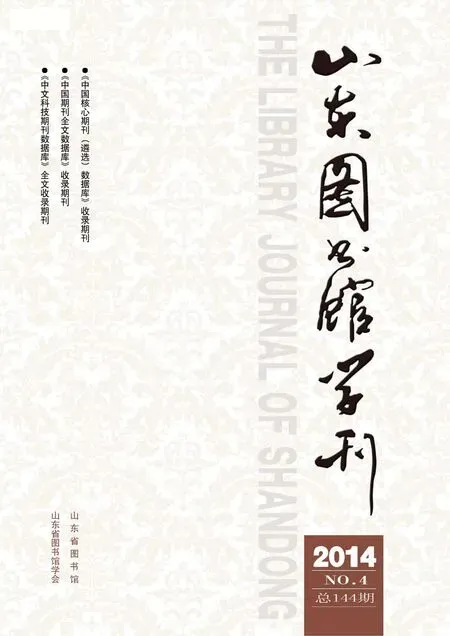杜定友访日开启中日图书馆学双向交流的“圕时代”**本文系2013-2014年度北京大学和庆应大学校际交流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范 凡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
杜定友访日开启中日图书馆学双向交流的“圕时代”**本文系2013-2014年度北京大学和庆应大学校际交流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范 凡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
清末民初中日图书馆界的交流基本上以中国学习日本为主,1926年夏杜定友访日向日本图书馆界展示了中国图书馆学家的风采,以间宫不二雄为首的日本图书馆界,不仅全盘接受了杜定友首创的由“图书馆”三字简写而成的新字“圕”,而且先后创办以《圕》和《圕研究》命名的图书馆学期刊,在为日本图书馆界提供学术交流平台的同时,积极开展与中国图书馆界的学术交流,从此中日图书馆学实现了双向交流。
杜定友访日 间宫不二雄 《圕》 《圕研究》 >圕时代
1 杜定友访日
1926年7月,中国童子军从上海到日本访问,由时任上海南洋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杜定友担任英语翻译。[1]日本图书馆界知名人士、曾经留美的图书馆用品专门合资会社间宫商店的主人间宫不二雄专程从大阪到神户迎接杜定友一行,二人此前并未谋面,仅有几次通信联系,这次会面,一见如故,成为挚友。访问期间杜定友得到了间宫不二雄的大力帮助,间宫不二雄不仅邀请杜定友到自己家中做客,共同切磋中日图书馆的有关问题,而且还尽可能地亲自陪同或安排自己的助手陪同杜定友参观,在无法陪同的情况下,又积极为杜定友安排各地的行程、图书馆的接洽,并代杜定友给各馆写参观访问后的感谢信等,凡此种种,颇为周到。
杜定友在短短两周的访日行程中,经过日本17个埠头,重点参观了东京、京都、大阪、名古屋、静冈县等地的14所图书馆,结识了如大阪府立图书馆今井贯一馆长、京都帝大图书馆笹冈馆长等20多名日本图书馆界人士,并受到日本全国图书馆协会的设宴欢迎。除了这些日本友人,杜定友在东京还得到了中国留学生马宗荣的帮助,二人于图书馆学研究方面志趣相投,相谈甚欢,杜定友还拜托马宗荣处理此次访日未能达成的与日方商谈重印皕宋楼藏书一事。[2]
杜定友此行,有三个直接的成果,一是“圕”字的正式使用,二是以一个图书馆学家的眼光对日本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三是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邀请日本全国图书馆协会派出代表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议,研究中日图书馆联络合作问题,并得到了对方积极的响应。
杜定友此行的影响却不仅限于此,杜定友在《日本图书馆参观记》中对中日图书馆界的比较分析,让双方看清了彼此的问题和成果,从而开启了一个中日图书馆学双向交流的新时代。而这个时代是如此独特,它以“圕”的正式使用为特征,也差不多与“圕”的使用相始终。
2 圕时代的确立
今天我们看到“圕”字,仅仅知道它是“图书馆”三个字的缩写是不够的,还要把它与一个时代联系起来,把它与中国图书馆学的巨大影响联系起来,把它与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史上的一段辉煌历史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看到“圕”字,就要想到一个时代——“圕时代”。
“圕”字的产生源于杜定友和间宫不二雄的“历史性的共鸣”。[3]“圕”字的生父是杜定友,接生婆是间宫不二雄,出生地是在日本大阪市北区木幡町21番地间宫家,生日(在出版物上的正式使用)是日本图书馆学刊物《圕》的创刊时间1926年10月15日,
取得中国户籍时间是1929年1月,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南京第一次年会大会决议通过。[4]
2.1 “圕”字在中国的使用情况
为了取得国人认可,杜定友先后多次撰文,收集国内外专家的意见,从造字、书写、读音等各个方面,论证其合理性、可行性,如:《圕》(见《图书馆学季刊》1927年第2卷1期)、《“圕”新字之商榷(第二次)》(见《图书馆学季刊》1929年第3卷第4期)、《“圕”新字之商榷(第三次)》(见《图书馆学季刊》1932年第6卷第2期),最后“圕”字总算名正言顺,不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专门制作了“圕”铅字,而且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出面宣布《“圕”一字早由交通部编入明密码电报书中》(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年第15卷第6期)。尽管如此,众人的议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各种看法都有,如马紫云的《介绍一个近世的“圕”新字》(见《公安旬报》1929年第9期)、汤因的《我对于圕(宀物)(囗術)三字的商榷》(见《图书馆学季刊》1937年第11卷第2期)。
虽然“圕”字在汉字大家庭中站稳了脚跟,并在全国得到推广使用,但是它于公开出版物中的使用寿命并不长,大约到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停止。笔者曾使用国内两家权威的数据库进行验证,一是根据全国报刊索引检索,“圕”字在正式出版物题名中的运用,首见于1927年,多见于1929-1949年,之后基本绝迹。二是根据中国知网检索,“圕”字在正式出版物题名中的运用,见于1950-1951年,之后基本绝迹。这说明,“圕”在中国的存在有较为明确的时间界限,大概在1927-1951年之间,代表了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一个比较明确的时代。
2.2 “圕”字在日本的使用情况
“圕”字在日本受到了很高礼遇,日本人信奉“即知即行”,正如陈伯逵所说“彼邦人士,如获拱璧,更发行杂志,以此字命名”。[5]由间宫不二雄主办的日本图书馆期刊《圕》于1926年10月15日正式发行,可惜此刊仅出了1期就停刊了。当时寄到中国多份,李小缘、戴志骞、陈伯逵等许多人都是拿到该刊后,才得知“圕”字的创制。笔者在庆应大学图书馆见到了《圕》刊。该刊正文篇幅仅有40来页,另有图书馆学图书、图书馆用品广告数页。正文首篇就是杜定友用英文撰写的关于“圕”字的发明和用法的文章,并配有杜定友的全家福照片。[6]马宗荣的贺辞[7]亦在其中。
继《圕》之后,1926年11月日本图书馆协会杂志也开始使用此字。1927年12月,日本青年图书馆员联盟成立,并于1928年开始发行机关刊物《圕研究》季刊,该刊关于“圕”字创制和使用的文章至少有3篇,分别是发表在《圕研究》第1卷第1期的《「圕」ト云フ字ニ就イテ》、第1卷第4期转载杜定友的《圕》、第7卷第4期的《「圕」ト言ウ文字ノ生立記》。《圕研究》季刊于1943年停刊,先后共16卷。1955年,间宫不二雄将该刊复制出版。此后,“圕”字在出版物中的使用也越来越少,使用日本CiNii数据库检索的结果也验证了这种情况。
可见,“圕”字在日本的使用时间,开始于1926年,结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中国的情况基本一致,因此,本文把这段时间称为“圕时代”。
3 中日图书馆学交流由单向变为双向
“圕时代”的命名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它至少标志着中日图书馆学的交流从单向开始转变为双向。如果回顾一下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就会知道,中国一直处于学习和模仿日本的阶段。
清末民初,图书馆被当作一种启迪民智的教育机关在全国各地纷纷设立,然而相对于传统藏书机构,图书馆毕竟是一种新兴事物,究竟应当如何办理,一直是一个令国人感到困惑的难题。1915年日本图书馆协会出版了《图书馆小识》,两年后被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译为中文,在中国图书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为当时图书馆的办理提供了依据,而且由此衍生出多本相关图书,包括1917年朱元善的《图书馆管理法》、1918年顾实的《图书馆指南》、1920年郑韫三的《图书馆管理法》等。因此,人们普遍把中国图书馆学的引进源头归于日本,如金敏甫曾说“民国六年,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以日本图书馆协会之图书馆小识,译示国人,是为中国图书馆学术书籍之滥觞。”[8]1920年后,出现了正式以“图书馆学”命名的著作,即杨昭悊翻译日本田中敬的《图书馆学指南》,以及杨昭悊本人编写的《图书馆学》,这两本书实际上也是学习和研究日本图书馆学的结晶,可见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受日本影响颇深。
但是随着中国图书馆学界留美一代的学成归来,美国图书馆学成为取法的榜样,那么中日图书馆学之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交流和联系呢?
留美所学图书馆学方法与工具,要应用于中国文献的管理,其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所以同属东方的日本图书馆学对中国仍有一定的吸引力。早在1917年,沈祖荣留美归来,就曾到过日本,在东京和其他各地考察了2个多月。本来是他以为“日本与我同种同文,又是图书馆事业先进的国家。”当他面临图书管理上的难题无法解决的时候,就想到日本求得一种解决方法。他经过考察发现,就分类来说,日本对于和书,各馆有各馆的分类方法;对于中国书,大多还是奉行四库法。就目录来说,和书的目录卡片很简单,中国书的目录要么没有,要么仍是书本式。就排列来说,用的是和文。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一点都不能采用”。[9]
1922年,前面提到的代表取法日本图书馆学的最高成就的两本书《图书馆学指南》和《图书馆学》的译者和作者杨昭悊也赴美学习图书馆学,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这一单向交流过程已经告一段落。
1926年杜定友访日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图书馆学家风采的展示,杜定友对日本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客观评价,让中日图书馆界重新开始认识对方,从而开启了一扇双向交流的大门。
交流的渠道除了以往的图书馆学著作翻译,如李尚友翻译的日本小见山寿海的《书誌学》和加藤宗厚的《标题目录要论》、毛春翔翻译村岛靖雄的《图书分类法》等书以外,最主要的是通过中日图书馆学期刊来报道对方的成果和动态,中方刊物主要有《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等图书馆学期刊,以及一些教育期刊,日方刊物主要有《圕》和《圕研究》。
4 杜定友对中日图书馆学发展水平的对比分析
1927年杜定友发表的《日本图书馆参观记》集中反映了他对日本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看法。该报告共分12个部分:日本图书馆事业的背景、日本图书馆的概况、宏伟的建筑、科学的设备、拥挤的阅览室、丰富的藏书室、“四库?杜威?”、图书馆的利用、学者的养成、惨别的知己、新交的朋友、满载而归。此处仅择其主要观点。
关于日本图书馆学的发展水平,杜定友认为,“以图书馆学者的眼光来观察日本图书馆的事业,好像没有什么可观。日本图书馆学者对于图书馆学的贡献,似还很少。这或是因为我不懂日文,未能博考日本书籍,所以有这种结论。但是我个人的感想是如此。其实图书馆学在学术界上,还是新进的科学。其他各国,也还没有多大的发见。这是不能单单责备日本的。”
关于日本图书馆事业,杜定友认为日本人一方面接收西洋文化,一方面却能保存东方固有的精神。在图书馆方面,很少完全效法西法的地方,总带有一些日本风味。他说,“他们全国图书馆事业,都现着蓬蓬勃勃的现象。一般办理图书馆的人,都是孜孜力谋发展。大家对于图书馆,都抱着无限乐观,这不能不令人倾倒。日人于图书馆学上,虽说没有多大的贡献;但是于事实上,已收图书馆的功效。”
从图书馆数量上看,杜定友认为,“日本全国的图书馆,不算很多,规模也不甚大,经费也嫌不足。但是所有的图书馆,都能够应实用,不是像吾国有许多图书馆的有名无实,门庭冷落,书架封尘的。这是他们较胜的地方。”
就办理图书馆的人来说,“全国图书馆专门人材不过三、四人,但是很有经验而且专赴欧美参观图书馆的,也有十余人以上。”“日本人对于图书馆学,还没有很深的研究。图书馆学的书籍,也寥寥无几。但是他们有一种胜人之处,就是不尚空论。办理图书馆的人,大都是一边办事,一边研究,随时改良,随时探讨。所以没有像欧美那样设了几位教座,专门研究什么图书馆学的。他们也没有空谈理论,不务实际的,对于图书馆什么问题,没有什么贡献,其原因也多半在此。现在从事于图书馆的人,我所碰见的,很多是好学深思的人。他们若能够专心在图书馆学上研究,将来一定有绝大的贡献。”
就图书馆学说推广方面看,“日本的学说,每因一、二人的提倡,全国唱和,所以推行极速。据说日本图书馆协会出版的《图书馆小识》在日本图书馆发达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办理图书馆的,多视为蓝本。所以他们图书馆学的书籍,虽属寥寥,但是阅者能够看了马上就用,这也是胜人之处。吾国人士多尚空论,善怀疑,好批评。现在留学回国的,研究新旧学问,挂有硕士博士衔,不知几千百,但是他们的发明和贡献,实在是少得很,能够实行主张的,更不多说。这不能不为我学术界叹啊!”
杜定友对新交的日本朋友间宫不二雄有很高的评价,事实证明间宫不二雄完全没有辜负杜定友的厚望,作为一个曾经留美的图书馆用品商人,间宫不二雄不仅对日本图书馆设备的科学统一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通过先后创办《圕》和《圕研究》2种期刊对日本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5 间宫不二雄的行动
间宫不二雄在杜定友来访之后,立即行动起来,如前所述,他于当年发行《圕》刊,次年成立日本青年图书馆员联盟,第三年开始发行《圕研究》季刊,勉力维持16年,1943年停刊,1944年青年图书馆员联盟解散,1955年他将《圕研究》系统整理、复制出版。
他的这些举动很快受到了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关注。刘国钧亲自撰文[10]予以报道,介绍日本青年图书馆员联盟成立的原因是“日本图书馆员近来鉴于社会上对于图书馆之要求激增,而图书馆界虽有五十余年之历史,但因各自为战缺乏联络之故,以致全国不能有整齐统一之方法,对于图书馆事业之进行,如互借及交换目录等事颇感困难,因有青年图书馆员联盟之组织。”指出联盟的宗旨“在提高图书馆员之教育,确立图书馆管理法之标准,指导新设之图书馆,改善图书馆员之地位待遇,及促进单一之图书馆联盟。”还对该联盟的会址、会费、组织机构和机关刊物《圕研究》所要承担的任务一一进行了介绍。
对于已经出版的两期《圕研究》,刘国钧认为其内容“甚为丰富”,指出其中最有价值的5篇论文分别是对美国芮嘉森的《分类法之理论与实际》和《分类法之过去五十年》的翻译,森清氏的《和洋图书共用十进分类表案》、间宫不二雄的《辞书体目录之特色及其解说》、井上光雄的《关于图书馆内电灯配置之研究》。刘国钧还注意到我国裘开明及美国波登在美国《图书馆杂志》所发表的关于分类法的论文也已被铃木贤祐翻译为日文。刘国钧最后指出,该刊两期中共有5篇讨论分类法,可见此问题在日本图书馆界之重要性。
日本图书馆学界对间宫不二雄这一时期的贡献评价也非常高,松见弘道曾说,“对于间宫老早年在创建和经营间宫商店的同时对我国近代处于摇篮期的图书馆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到现代他还老当益壮精心指导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并成为青年图书馆员联盟之父的伟绩还应大书特书。”松见弘道还指出,“《圕研究》虽然仅有不足16年的历史,但它为日本图书馆事业所造就的济济人才却以雄狮奋迅之势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成果。该刊创刊号的卷首论文是植村长三郎先生的《著者号码法》。据今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黄宗忠主任的书信中说,在中国也曾有采用该著者号码法的图书馆。接下来在第17页以后是森清先生的长篇论文,该文首创‘NDC’分类法。也可以说这是日本不朽的图书分类法历史性的诞生。以后由富永牧太、木寺清一、村上清造、小野则秋……等等优秀学者陆续撰稿,使该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这的确是一种创举。”[11]
1936年间宫不二雄访华后,对中国图书馆界的蓬勃发展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他说,“最近十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之猛进,实堪重视。日本人之所以对华问题之无有成果,或系蔑视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展之故,亦未可知。如果欲认识中国,则应注意中国之图书馆。”又说,“在近十余年间,中国图书馆之发达,诚为可警,已超过日本图书馆进步数倍。”他对中国图书馆学人才培养尤为羡慕,“日本中等学校毕业后再行补习一年之图书馆讲习所只有一处,且多不合实用。中国大学毕业生有施以二年专科之设施,此种学生,大多均远涉重洋,赴英美德法留学,即在图书馆服务者,亦均经专科之补习。故余之见解,今后日本如能每年派送两名大学生至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肄业,实较留学欧美为佳也。”[12]
6 《圕》和《圕研究》受到中国图书馆学家的关注
《圕》和《圕研究》上刊登了多封中国图书馆学家的来信,通过这些书信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间宫不二雄与中国图书馆学界交流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中国图书馆学界对该刊的评价。这些书信,除了马宗荣用日语书写,刘国钧用中文书写之外,其余几封信都是用英语书写,为反映概貌,这里仅择其大意。
《圕》只有1期,刊有杜定友《A Statement from Mr.Ding U Doo》和马宗荣的《圕誌ノ發刋ヲ賀メ》,已如前述。
《圕研究》上刊登的中国图书馆学家的来信时间集中在1928年。包括以下几封:
袁同礼是青年图书馆联盟的海外会员,他在接到该刊之后写了回信《From Mr.T.L.Yuan,Associate Director of Peking Metropolitan Library》(见该刊1卷2期),一则祝贺该刊对图书馆界的贡献,二则答应要为该刊写稿,三则表达了与对方共同建立友好关系的意愿。
戴志骞的回信《From Mr.T.C.Tai,Librarian of Tsing Hua College Library,Peking》(见该刊1卷2期),首先表达了对收到第1期刊物的感谢以及对其中论文的兴趣,接着说明自己公务繁忙,希望能在将来给该刊写稿,同时希望对方能指定一个感兴趣的题目。他还赠送给对方一份本馆的中西文图书分类目录,希望对方能对此目录进行批评指正,而且希望双方能够开展此类出版物的交换。戴志骞的另一封回信《From Mr.T.C.Tai,Librarian of Tsing Hua College Library,Peking.(June 1,1928)》(见该刊1卷3期),表达了对收到第2期刊物的感谢,重点肯定了其中“图书馆的电灯”和“DC的应用”两篇文章的价值,并感谢日方对清华图书馆图书目录的评论。同时表示本馆要订阅该刊第一卷3期到第二卷2期。
杜定友的《A Message From Mr.Doo,Ding U,Librarian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Library,Canton,China)》(见该刊1卷3期),表达了他对青年图书馆员联盟成立与新刊发行的祝贺。他认为青年图书馆员联盟中的“青年”两字,不止代表年龄,更代表一种精神。青年并不是未经训练的代名词,而是代表了向上和成长,这种精神对当今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图书馆是一项古老的事业,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收集的图书和手稿经过一代代的努力终于传到我们手中,我们要把这项事业继承下去。他指出科学和图书并不能用时间来衡量,古代先贤的言论和我们现代的言论一样至善至真。不管图书多么古老,我们都要用最先进的办法来管理它,这就需要我们保持青年的精神。图书馆不仅仅是书籍的宝库,还是教育的中心,传播知识的机构。这个世界的成长变化是如此之快,所以他认为日本正是为了与之保持同步,才成立了这个联盟。他还对该刊使用自己发明的“圕”字表示感谢,并为自己因公务繁忙不能多写而表示歉意,最后祝愿该联盟成功,青年图书馆员万岁。
桂质柏的回信《From Mr.J.C.B.Kwei》(见该刊1卷4期),说自己正在蒙特利尔的Gest Chinese Library帮忙,感谢对方寄来的第2期《圕研究》,认为日本正在从事的促进东方图书馆的活动和图书馆员的合作令人尊敬,预祝其获得更大成功。
刘国钧的回信《来自中华图书馆协会刘国钧氏》(见该刊1卷4期),原文如下:
敬启者顷得见
贵联盟所刊行之圕研究,议论精湛、识地超卓,深为倾佩。当此新图书馆运动弥漫东亚之际,就东方之立场对圕问题作深造之研究,以求彻底之解决,实为青年圕员所不可忽视之职责。贵刊应运而兴、为世表率,将来对于圕界必有伟大之贡献,可断言之。
鄙人谬膺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之《图书馆学季刊》之编辑,对于同类性质之刊物之发行为欣悦而深祝其前途光大者也,兹特检呈《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及第二期各一册敬请詧收,并予以此批评绍为荷。专此驰贺,并祝成功。
此致
青年图书馆员联盟
刘国钧敬启(八-廿)
裘开明的回信《From Mr.A.K.Chiu,Chinese Department,Havard College Library》(见该刊1卷4期),首先对收到第2期及铃木贤祐将自己的论文《中国的分类法》翻译成日文表示感谢,接着祝贺该刊的创立并愿意为之撰文,然后说明自己的分类法除了宗教一类以外,各类都已完成,现在正在修订索引,一旦完成,将给对方寄去。
此外,王云五于1929年,为答谢间宫不二雄对自己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的翻译介绍也专门用英语写了回信,授权间宫不二雄将此法在日本翻译出版,同时向其推荐自己发明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见该刊2卷3期)。而间宫不二雄也毫不吝啬地对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进行赞扬,不仅在《汉字排列法的革命》[13]一文中将此法与中国大学院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张凤的形数检字法等一起予以重点介绍,而且专门对其进行了翻译发表[14]。
除了上述书信,《圕研究》还通过论文、译文、新刊介绍、会议记事等形式对中国图书馆学进行全方位的报道,这些内容非本文区区几千字所能概括,故而在此留下线索,以待后续研究。
〔1〕間宫不二雄.「圕」ト言ウ文字ノ生立記[J].圕研究,1934,7(4):27-28
〔2〕杜定友.日本图书馆参观记[J].山东教育月刊,1927,6(2):51-63;6(3-4):65-71;6(6):43-56;6(7):33-43
〔3〕松见弘道著,魏振起译,高凯军校.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家——杜定友[J].大庆师专学报,1985(2):59-60,63
〔4〕間宫不二雄.「圕」ト言ウ文字ノ生立記[J].圕研究,1934,7(4):27-28
〔5〕杜定友.圕[J].图书馆学季刊,1927,2(1):166
〔6〕杜定友.A Statement from Mr.Ding U Doo[J].圕,1926,1(1):3
〔7〕马宗荣.圕誌ノ發刋ヲ賀メ[J].圕,1926,1(1):16
〔8〕金敏甫.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M].广州:广州图书馆协会,1929:29
〔9〕沈祖荣.在文华公书林过去十九年之经验[M].丁道凡搜集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8~1944年.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62-75
〔10〕衡.日本青年图书馆员联盟[J].图书馆学季刊,1928,2(3):180-181
〔11〕松见弘道著,魏振起译,高凯军校.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家——杜定友[J].大庆师专学报,1985(2):59-60,63
〔12〕日圕专家推崇中国圕界[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7,12(4):42
〔13〕間宫不二雄.漢字排列法ノ革命=四隅番号化検字法[J].圕研究,1929,2(3):115-129
〔14〕王云五发明,間宫不二雄译.漢字ノ四隅番号化検字法[J].圕研究,1929,2(3):130-162
The Two-W ay Communic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tarted by M r.Ding U Doo’s Japan Trip
Fan F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the communic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Chinese librarians following the Japanese librarians'step.However,the situation was changed by Mr.Ding U Doo's Japan trip in the summer of 1926.During the trip,Mr.Ding U Doo showed his Japanese colleagues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which impressed the librarians in Japan very much.Mr.Fujio Mamiya was one of them.He not only adopted Mr.Ding U Doo’s newly invented Chinese character Tuan,a simple andmeaningful symbol for library,butalso issued twomagazines named with Tuan and Tuan Research,which in Japanesewere Toshokan and Toshokan Kenkyu.Themagazines were very important in promoting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of library science,not limited to Japan,but also included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From then on,the communic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tepped into the two-way learning stage.
Ding U Doo's Japan Trip;Fujio Mamiya;Toshokan;Toshokan Kenkyu;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Tuan Being Used
G259.29
A
范凡,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