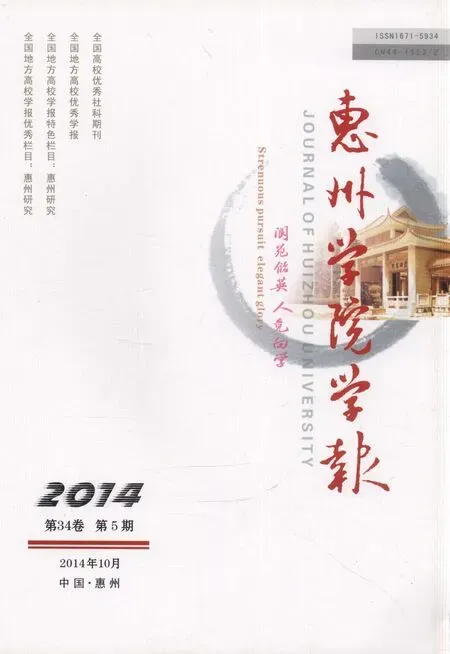福尔摩斯故事中的印度叙述
黄 靖
(广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一、引言
从1887 的开篇之作《血字的研究》到1927年的完结篇《肖斯科姆别墅》,福尔摩斯系列故事的创作时间基本上与大举殖民扩张的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重合,这期间也正是英国满怀强盛帝国的优越感进行印度书写的“自信期(1858-1914)”[1]10。福尔摩斯故事中屡屡提及大英帝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过往研究揭示了柯南·道尔的印度书写与当时的进化学说[2],人种学、犯罪学[3]文本相互指涉,相互复制,把印度人塑造成不知廉耻的暴徒:“黑鬼子”[4]218;即便从印度返回的英国人也有不少也沦为“游民懒汉”[4]4,印度裔美籍学者Yumna Siddiqi 进一步发现福尔摩斯系列故事中返英殖民者(returned colonial)形象可以分为事业有成(respectable colonial)与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两类,这两种形象反映了英帝国对印度等殖民地又爱又怕的焦虑心理。[5]这些研究无一例外认为故事中通过特定的叙述,形成和强化了印度与英国作为野蛮与文明对立面的帝国殖民逻辑。但对于帝国叙述的自我解构,以及情节化过程中为返英殖民者洗白等帝国逻辑在叙述层面的一些更为精细的结构还有待论述。
二、琼诺赞·斯茂供述中的帝国视角
琼诺赞·斯茂归案后的供述隐伏着大英帝国满怀道德优越感俯视印度,并对是否服务于自己利益为标准对其进行评判,在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优越论作用下,印度被塑造为野蛮的他者,被视作万恶之源和夺宝圣地,从而形成“为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殖民地行政管理和文化同化提供划分界限的认知范式[6]65”。帝国视角既指这种看待印度的认知范式,也指这种认知范式在叙述声音和人物感知视角中的具体实现。1857-1858年的“印度民族起义”是英国文学印度书写的一个重要主题,《四签名》通过琼诺赞·斯茂的视角对这场起义进行了直接描写。琼诺赞·斯茂眼中的印度士兵都是穷凶极恶的暴徒,他看见忠于职守的道森的妻子被“野蛮的”印度士兵“割成一条条的又被豺狼和野狗吃去了一半[4]218”,叙述中“黑鬼子”等侮辱性的称呼也俯拾皆是,语言上的轻侮反映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和印度民族文化风俗的轻侮。作为英国在印驻军,斯茂的视角不仅片面聚焦了印度凶恶的一面,也反向聚焦了自己的偏见。他眼里印度是“和在祖国一样的安居乐业”[4]218。英国和伦敦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地区则被视为边缘地带,并应当驯服地服务于英国。英国人把自我投射为物种进化等级序列中处于高级地位的优等人种,不仅智力发达,而且居于道德的制高点,斯茂的供述是以英国为中心而对印度和印度人盛气凌人的评判。印度人被简化为没有面目不讲道德的“黑鬼子”。起义的爆发源自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民族文化风俗的无视和强制推行西化,可是故事中只片面强调印度士兵的所谓“穷凶极恶”,丝毫不提英国人对印度传统文化的破坏。他把1857年印度爆发的反英民族大起义诬为“大叛乱”,印度起义军被诬为“叛军”。这里的“大叛乱”指1857-1858年的“印度民族起义”,英国人将其污为“印军哗变”,独立后的印度则称它为“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印度起义军成了邪恶的代表,被塑造成了野蛮而毫无人性的忘恩负义之徒,与忠于职守却死在叛军手下的道森妻子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还暗藏于情节发生地的转换中,劫掠宝物以及舒尔托独吞宝物都发生在印度;其后舒尔托良心发现以及福尔摩斯伸张正义都发生在英国,英国和印度俨然成了邪恶和正义的对立面。柯南·道尔一共写了56个短篇和4 个长篇福尔摩斯故事,其中两个以全知视角叙述,两个是以福尔摩斯视角叙述,其余都是从华生的视角来叙述。福尔摩斯和华生被设置为正义的化身,但即使是他们看待印度的方式也深受帝国认知范式的影响。MacBrathey[3]发现福尔摩斯和华生眼中的童格这一形象的塑造受到了Herbert H Risley等人种学家和犯罪人类学家Cecare Lombroso的影响而片面聚焦安达曼岛生番凶恶的一面,Risley 片面强调安达曼岛生番的凶狠,却不提这种凶狠只在面对殖民主义者才会表现出来,Lombroso 等人则主观地认为生番童格等具有特定相貌的人先天具有犯罪倾向。这种偏见的背后正是赛义德指出的文化和帝国主义的共谋。
柯南·道尔和他书中的人物以英国的利益为取舍对印度人妄加评判,在同“文明的”英国人的对比之下,叙述中不断强化英国和印度之间的二元对立。所谓“叛军”是由英国人定义并叙述的,是否服务于英国人的利益成为判断印度人善恶的唯一标准。斯茂对起义的真正原因视而不见,反而依据自以为是的殖民逻辑认为“以后印度的叛变结果如何,也用不着我再来告诉你们诸位先生了……[4]226”。作为“过滤故事材料的头脑”[7]53的福尔摩斯、华生、斯茂等人物视角或叙述声音暗藏着“作者的基本态度和观点”[7]53,即唯我独尊秉持殖民扩张的帝国视角,这些人物只是“支配一部作品叙事组织的世界观”[8]167的具体化。这种殖民逻辑把斯茂等个体束缚在殖民扩张的社会职能之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9]20,从而把殖民扩张的逻辑的视为合理。斯茂等的视角通过区分文明的“我们”和野蛮的“他们”,表达了英国对自身和印度的殖民关系的认定。赛义德认为,“东方……是欧洲最大的,最富有的,最古老的殖民地,是其文明和语言的源头,其文化的对手,也是最深切的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10]序言。东方作为西方的参照帮助西方定义了自己的身份,西方人眼里的东方是被创造出来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的关系,统治的关系,一种复杂霸权的不同等级关系”[10]序言。斯茂的叙述视角正反映了英国和印度的这种臆想的等级关系,自认为高人一等的英国人凭借虚妄的优越感而对印度妄加评判。
斯茂夺宝的殖民掠夺逻辑在英国碰壁,表明把印度看成万恶之源或者夺宝圣地的帝国视角既是片面聚焦印度阴暗面的狭隘认知,也是一种只用于看待印度等殖民地的单向的逻辑。由“叙述者—聚焦者”(如华生)或外部聚焦者所呈现的意识形态观念会被默认为权威,但这些观念由内部聚焦者(如斯茂等人物)呈现并与外部聚焦者的表达形成潜在对话关系时,其权威性就会受到动摇。[11]147-148《四签名》整体从华生的视角进行叙述。福尔摩斯和华生从英国法律的角度维护对阿格拉宝藏的继承权,但是斯茂被抓后大声叫嚣“法律?……多么美好的法律啊,宝物不是我们的是谁的?宝物不是他们赚来的偏要给他们”[4]215。从西方历史源头的两位大家希罗多德和非阿里安以降,历经斯宾塞,培根,马娄,莎士比亚,弥尔顿,德莱顿等,印度始终被视为富有之乡和财富之源。[1]14-23阿格拉宝藏先被斯茂劫获,又被舒尔托据为己有,他真正的主人只是作为被掠夺对象短暂出场就永远让位给了殖民者之间的争斗,英国的法律竟然保护一笔殖民劫掠得来的财产,而当斯茂想将劫掠的殖民逻辑应用于英国以夺回宝藏时却注定失败,因为殖民劫掠只能发生在印度而不是英国。斯茂和舒尔托上校都是通过不法手段获得宝藏,但英国的法律却对他们区别对待,斯茂将财宝弃置泰晤士河以回应法律的荒唐。
三、情节化背后的帝国意识
除了片面聚焦印度阴暗面,在情节化过程中不断强化英印二元对立的帝国意识还以更为隐蔽的方式隐伏。在白人中心主义的帝国视角下印度人被认为天生具有犯罪倾向[3],因而在福尔摩斯故事中常被用作叙述“障眼法”的材料。为使文势曲折,侦探小说常常在最终解开谜题之前,布置一些将读者引入歧途的障碍,把读者的怀疑引向无辜的人,以求揭开谜底时获得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12]214在福尔摩斯系列故事中,这一手法被多次使用,例如《第二块血迹》里威斯敏斯特教堂谋杀案的新闻报道中提到杀人的刀子是把弯曲的印度匕首。《三个大学生》里,福兹求奖学金考试的试卷被盗,试卷的第一部分是希腊文翻译,索姆兹教授向福尔摩斯讲述案情时特别提到希腊语不太好的印度学生道拉特·芮斯来问过考试的方式。尽管索姆兹教授提出的怀疑对象是另一个人,但讲述中顺便带出芮斯的特征就是故意引逗读者的障眼法,加重这个印度学生盗窃试卷的嫌疑。另外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福尔摩斯故事中的一些返英殖民者沦为落魄之徒甚至是罪犯,如《驼背人》中的亨利·伍德,《斑点带子案》中的罗伊洛特医生,《四签名》中的斯茂等等[5,13,14]。这样的情节安排造成一种“时序连接和逻辑连贯性之间的含混性”[15]116,通过叙述过程中的“因果解释机制”[16]152使得单纯的事件之间建立因果逻辑而转化为前后相继的情节,完成“情节化”[16]152过程,在印度和罪恶之间画上了一个若有若无的等号,暗示印度等殖民地会使好人变坏的潜在因果解释。但是情节化机制的中的“叙事因果”并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机械因果或必然的逻辑因果,它只是一种人为构建的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常识因果”[16]156。
柯南·道尔一生创作了60 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56 个短篇小说和4 个长篇小说。四十年间陆陆续续发表在《海滨杂志》上。《海滨杂志》是一本迎合普通读者趣味的轻性杂志,其中通常没有违背甚至挑战读者常识的价值判断,当对一个地区的偏见成为一个故事自然连贯的叙事逻辑的一部分,表明这种偏见已经固化为常识和一种整合生活经验的潜在认知模式,成为叙事赖以进行的基础。它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叙述者能叙述什么以及这种叙述的受众能认识到什么。叙述的认识论性质也是其与意识形态的交集之一。福尔摩斯中的印度形象正反映了帝国意识下扭曲印度形象的话语运作。叙事也会对所述进行合理化,使之听来“显得”“合情合理”,将包含着人对自身与世界、自身与历史的关系想象的意识形态观念自然化为常识,从而加强普及这种观念。
《血字的研究》中华生认为伦敦是一个“大污水坑”[4]4,“大英帝国所有的游民懒汉也都是汇集到这里来的”[4]4,暗示印度会使英国人腐化堕落。印度裔美籍学者Yumna Siddiqi发现福尔摩斯故事中事业有成(respectable colonial)与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两类返英殖民者形象。当时鱼龙混杂的英国人涌向印度,“流氓无产者”或者“游民懒汉”极大冲击了殖民者高人一等的帝国逻辑,表明所谓的欧洲身份不过一种脆弱的建构,这种两极的形象,特别是其中的流氓无产者正是出于种族优越论崩溃的焦虑[5]219。然而Yumna Siddiqi尚未论及的是种族优越论和这种焦虑共同作用之下产生了一种更为幽微的方式为她所归类的流氓无产者洗白,从而使他们在坏事中“金蝉脱壳”。故事中琼诺赞·斯茂不是自己心生歹意,而是在两个“来自旁遮普的印度兵”[4]220的胁迫下才参与劫持大宗阿格拉宝物。更意味深长的是抢劫的过程中,印度士兵对印度商人穷追不舍,英国人斯茂却“动了恻隐之心,想放他一命[4]224”,虽然最后斯茂仅仅用“明火枪向他的两腿之间抡了过去[4]224”绊倒印度商人,最后是商人的印度同胞“扑了上去,在他的肋旁扎了两刀[4]224”,结果了商人的性命。这段叙述精心构筑了一个清晰的对照:一个有恻隐之心的英国人和赶尽杀绝的印度人,英国人虽贪财而不失恻隐之心。这种“金蝉脱壳”式的处理遍布《四签名》,舒尔托上尉看到窗外的斯茂被吓死而不是死于斯茂之手,于是英国人不像印度人杀印度人那样自相残杀。小舒尔托,斯茂声称“实在没有想杀害舒尔托先生,是那个黑鬼童格射出一支混账的毒刺害死他的[4]232”。童格是斯茂在安达曼群岛上救回的一个小生番,斯茂“虽然知道生番生性狠毒似蛇”,可“还是护理了他两个月,他终于渐渐恢复了健康又能走路了。他对我产生了感情,终日守在我的茅屋里面[4]232”。斯茂和生番童格的关系不过是鲁滨孙和星期五的翻版,是一个野蛮人向文明的英国人臣服的故事。斯茂的同伙莫郝米特·辛格,爱勃德勒·克汗和德斯特·孙克勃尔由斯茂以一种文明人审视野蛮人的态度来讲述,他自己是誓守诺言为同伴夺宝报仇的英国人,同时把一切杀人越货的罪恶全推给了印度人。再比如《驼背人》中线索开始指向从印度返回的亨利·伍德,但谜底却是巴克利上校是看到亨利·伍德后惊吓而死不是被杀;而《斑点带子案》中的罗伊洛特医生谋害继女时用的是印度的毒蛇。当时的英国对于高贵的英国性(Englishness)受到殖民地的所谓“退化与堕落(devolution and degeneration)”的充满莫名的恐惧[17]211,这种恐惧的结果反映在福尔摩斯故事中就是落魄返英殖民者的出现。但是堕落的英国人形象又与种族优越论对文明英国人的设想冲突,两相拉扯之下便出现了将英国人的堕落归因于印度,同时为犯罪的英国人洗白的情节化过程,对于英国优越性受到侵蚀的焦虑需要在反复的印度书写中强化英国的优越感来消除。
四、结论
分析福尔摩斯故事中的印度书写可以发现,为了服务殖民扩张,维多利亚时期在种族优越论的影响下不断强化英国和印度之间的二元对立,片面聚焦印度阴暗面的帝国视角,认为印度人民先天具有犯罪倾向,强调印度会使人堕落,从而为英国罪犯洗白寻找借口。但当帝国视角在不同人物身上具体实现时却暴露了帝国逻辑的矛盾性;通过情节化洗白落魄返英殖民者反映了种族优越论与现实碰撞时所产生的焦虑和反 抗。
[1]尹锡南.英国文学中的印度[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
[2]FRANK L.Dreaming the Medusa:Imperialism,Primitivism,and Sexuality in Arthur Conan Doyle’s“ The Sign of Four”[J].Signs,1996(1):52-85.
[3]MCBRATHEY J.Racial and Criminal Types:Indian Ethnography and Sir Arthur Conan Doyle′s The Sign of Four[J].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05(33):149-167.
[4]柯南道尔阿.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M].丁锺华,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
[5]SIDDIQI Y.The Cesspool of Empire:Sherlock Holmes and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J].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06,34(1):233-247.
[6]陶家俊.他者的表征——析两部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殖民话语[J].外国文学,2001(5):65-70.
[7]申丹.视角[J].外国文学,2004(3):52-61.
[8]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II[M].王文融,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9]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0]赛义德E.W.赛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1]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M].姚锦清,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2]袁洪庚.欧美侦探小说之叙事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1,33(3):223-229.
[13]RAHEJA L.Anxieties of Empire in Doyle′s Tales of Sherlock Holmes[J].Nature,Society&Thought,2006,19(4):417-426.
[14]MCLAUGHLIN J.Writing the Urban Language:Reading Empire in London from Doyle to Eliot[M].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0.
[15]巴特罗兰.符号学历险[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6]陈然兴.叙事与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7]KEEP C,RANDALL D.Addiction,Empire,and Narrative in Arthur Conan Doyle′s The Sign of the Four[J].Novel:A Forum on Fiction,1999,32(2):207-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