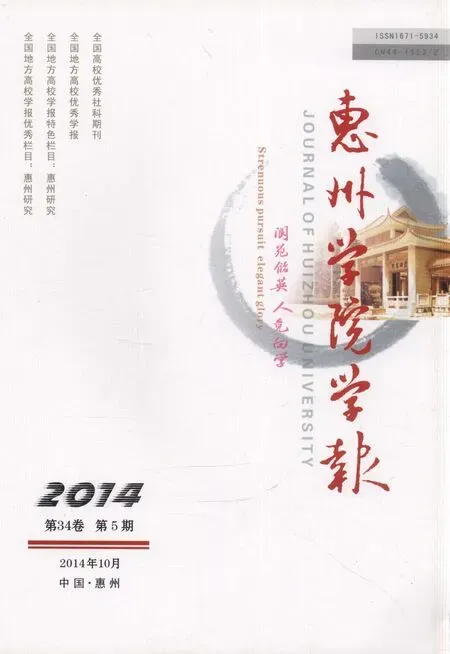试论缪里尔·斯帕克创作中的后现代诉求
李晓青
(惠州学院 外语系,广东 惠州 516007)
缪里尔·斯帕克(1918-2006)是英国当代一位重要且独特的女作家,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皈依宗教、宗教哲学以及超现实的神幻主题使斯帕克的小说别具一格,“有着独具个性的神秘、宗教、滑稽怪异的气质而兼具浪漫小说的形式[1]177-178”。20 世纪对斯帕克研究大多侧重于宗教伦理的视角来评议其作品,然而,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读者与斯帕克本人都意识到,仅仅把她的小说限囿于宗教主题的阅读是不充分的。斯帕克的小说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她创作思想中的后现代倾向早于同时代的作家。后现代文学以后现代哲学为理论基础,是后现代精神的形象表达,而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确定性。[2]10-14在具体文学作品中这种不确定性常表现为主题的不确定、形象的不确定及非常规的叙事模式。事实上,在天主教作家的这层面纱之下,斯帕克的作品蕴含着叙述的开放性与多种可能性,呈现出中心消解、主题多元、形象迭用、开放叙事的多种特色,折射出强烈的后现代诉求。
一、主题的不确定
在斯帕克看来,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有另外一个超自然的维度……不是超自然,但不一定相因而生。一个事物不一定不可避免地引导另一件事[3]7”。她承认自己深受罗伯特·格里耶的影响,虽然“居住在欧洲,但与新小说家们思考的是同样的问题,呼吸的是相同的文化气息,受到的是同样的影响[3]20”。斯帕克小说显著的后现代特点之一就是小说主题的不确定,如她的成名作《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和第一部小说《圣灵》中出现的多重主题。突出主题是传统小说的写作旨向,读者在阅读审美的同时水到渠成地领会小说的主题结论。而后现代主义者却以“中心”为敌,在他们那里,中心不存在、意义不存在、本质也值得怀疑。所以,在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主题”往往是待定的,作者更强调意义的多重不确定性,呼唤读者的参与,给予读者解读的民主。
斯帕克在她的成名作《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便把“青春(原著为prime)设置成了复议的主题。虽然小说故事清晰完整,也并非贝克特后现代小说般的艰涩难懂,但读者却无法断然得出关于“青春”的“最终结论”。小说叙事者不置可否的“超然”与“真实”叙述反而造成了主题的不确定。如小说的名字《布罗迪小姐的青春》,“青春”是文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词,也是作者着力摹写的一种精神状态,而它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生理年龄,因为“青春”的布罗迪小姐其实是位年逾四十的老处女,文中不断重复着布罗迪小姐的一句话“我正处于青春岁月中[4]6”。而所谓“青春”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布罗迪帮”的女孩子们眼里,布罗迪小姐是美丽优雅的女教师,她富有活力,知识丰富,与保守阴险的女校长唱对台戏,带领女孩子们走入丰富的课外生活。在她的学生桑迪的“眯缝眼”的观察下,布罗迪小姐“在有些日子里……胸部线条明显,……梳着棕色发髻的头抬得高高的,说起话来宛如圣女贞德。[4]10”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确吸引了她的学生们。然而,处于“青春岁月”的布罗迪小姐同时也表现出她的自负、自私和独裁。她经常说“只要把这个姑娘给了我,她就永远是我的。[4]115”在行动上,她要求“布罗迪帮”里的姑娘绝对服从她的指挥。她心目中的英雄是希特勒,她信仰凯尔文教,“她认为无论做什么,上帝都在她这一边[4]116”。她把自己看成是真理和上帝的代表,鼓动学生去参加法西斯战争,甚至让学生作为自己的替身与另一男教师恋爱。在桑迪的眼中,“有的时候,布罗迪小姐胸部平坦……线条刚硬,像古罗马高傲的战士。[4]67”作者不断地重复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但重复带给读者的是对于“青春”多重的思考,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并不单纯。读者不禁对于布罗迪小姐和她的“青春”产生了不确定的感觉,布罗迪小姐的“青春”既象征着美好的生命力,也意味着支配控制与破坏。
而在斯帕克的第一部小说《圣灵》中,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类似“沉默的上帝”,它通过不同的人物视角来展现故事,造成了不确定的多重性主题。小说的主线之一是在写作中产生幻觉的女作家卡洛琳与男友劳伦斯的爱情故事,另一条主线是劳伦斯的祖母捷普夫人走私钻石的故事。小说中各个人物的联系和交流大部分借助于不同的人物视角。小说第三人称全视角的叙述并不发表任何评论,所以读者对于人物的了解来自于不同人物视角的叙述。但叙述的内容却使读者成了迷失于多重“事实”之间的侦探。比如卡洛林的前男友劳伦斯·曼德斯耿耿于怀的是他祖母路易莎·捷普的神秘行动,他认为78 岁的捷普太太其实是走私的头目,她与镇上的面包师把走私的钻石藏在面包中运出去。而书店老板威利·斯多科总认为捷普老太太的同谋是麦尔文·霍格斯,他是英国的头号巫师。事实上,小说里的每一位主要角色都被自己独特的幻觉和目的所驱使。比如霍格斯家破碎的石膏神像,对劳伦斯来说是揭开他祖母走私戒指的关键;对威利来说是亵神仪式的证明;对卡洛林来说是那位神秘作家所设计的情节之一。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事实,但每一个人的观点却各异。阅读这样的小说,读者很难确定小说叙述者的意图,他/她如上帝一般赋予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视角,由此产生不同的故事。在小说中寻求唯一的主题已不可能。
二、形象的重复
“重复”是后现代解构主义文论的一个关键词。“重复”产生的意义在于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体现的是后现代“复制”与拼贴的特征。[5]106-109后现代理论视野中的小说是文本与文本的对话,每个文本都产生于历史文本的复制。在一个特定的作者笔下,重复的文本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相互依存的必然性,同时,两者也相互颠覆与消减。因此,这种相互交织的文本产生了变幻莫测的意义,使小说的解读获得开放。斯帕克则把这样的“重复”应用在对人物的塑造上。事实上,后现代文论中,“形象迭用”已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学技巧。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浦安迪认为,“形象迭用”是“小说的不二法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一套丰富缜密的叙事针线[6]90”。它可以涉及文字的重复,事件与场景的重复,情节、主题或人物的重复。斯帕克对“形象迭用”手法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人物的重复塑造,注重以影绘形。
在小说《现实与梦境》中,斯帕克塑造了如形影相照的两个主要人物:大牌导演汤姆·理查德和他的女儿玛丽戈尔德。汤姆才华平平,靠妻子的财富跻身导演行业。每次拍片,汤姆都坚持要在拍摄现场架设高架摄影台,因为站在台上俯视并指挥一切给他带来上帝般的支配感。汤姆的妻子美丽富有,两人所生的女儿玛丽戈尔德却丑陋古怪,汤姆把她视为自己人生的败笔。玛丽戈尔德同样凭借着母亲的财富实现自己干涉、操控他人生活的野心,企图颠覆父亲的“上帝”地位并取而代之。她暗地里在高架摄影台上做了手脚,导致汤姆失足摔成重伤。玛丽戈尔德与汤姆虽相互对立、憎恶,却有着同样的操控欲与充当上帝的野心。玛丽戈尔德不仅是汤姆生理意义上的产品,也是其灵魂的复制品。这两个人物如同镜里镜外的对照,虽然是对立的存在,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斯帕克小说中的人物之间往往具有如此形影重叠的“互文性”。
另一个以影绘形的典型例子则是《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的女教师布罗迪小姐与她的得意门生桑迪。作为布罗迪小姐精心挑选的“布罗迪帮”中的一员,桑迪聪明、个性独立,在心智上与布罗迪小姐最为接近。她之所以成为布罗迪小姐最器重、最信任的学生,是因为她与布罗迪小姐在很多方面相似,能互相理解。比如对艺术的热爱、对权威的挑战,对独立自由的追求等等。可是,当桑迪发现罗迪小姐逐渐表现出法西斯倾向以及对“布罗迪帮”成员的操控时,她意识到布罗迪小姐的危险性,并暗地里收集了证据向校长告发了布罗迪小姐。布罗迪小姐直至临终还在询问桑迪到底是谁出卖了她。而桑迪在反对布罗迪小姐的同时,却企图替代她。她背地里与布罗迪小姐的情人同居,愚弄并操纵“布罗迪帮”的其他成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桑迪对布罗迪小姐由崇拜到颠覆,可她最终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布罗迪的翻版。小说人物的“以影绘形”使得读者无法分割孰正孰反,人物所承载的含义则丰富起来,小说也随之呈现多元意义。
三、开放的叙事模式
斯帕克认为,现实充满了邪恶,人的处境是荒诞的。要想摆脱荒诞困境,就必须借助幻想的翅膀飞向自由的国度以找到自己的归宿。显然,斯帕克的创作是企图借用小说的形式虚构一个可代替的现实。从叙事角度看,斯帕克的小说创作表现了小说的反讽性“真实”、小说的“预叙”手法、时间置换等特色。
斯帕克的《布罗迪小姐的青春》曾被改编成电影《春风不化雨》,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电影把小说充满预叙和倒叙的迷宫般的时间措置改成了从头至尾的平铺直叙,这也许是视觉叙事的局限,但却使小说的丰富意义大打折扣。电影凸显的女主角是布罗迪小姐,并让观众相信这是关于不信仰天主教的布罗迪小姐遭到了报应的悲剧故事。而小说文本的阅读却留给了读者更多的可能性。《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叙事创新最突出表现在小说的时间置换,这种时间置换令读者无处寻觅文本的中心意义。小说一开始时间已是1936年,这时的“布罗迪帮”将要升入中学。随着叙述的进行,读者被带回到1930年,女孩子们刚成为布罗迪小姐的学生;接着时间又往后跳到六十年代,中年的桑迪已出家当了嬷嬷,她的回忆又再次把时间拉回到三十年代。小说的叙事就是由不断地时时置换编织而成。在小说叙述的中部,读者就已经得知布罗迪小姐于六十年代死于癌症,桑迪的“出卖”是她郁郁而终的直接原因。小说的结尾处,成为海伦娜嬷嬷的桑迪,在谈到她的心理著作《平凡的变容》时,承认对她影响最大的是“青春期的布罗迪小姐”。这是一部没有悬念的小说,读者早在结尾前就得知了结果。在时间碎片的迷宫中,读者们总是期待寻找到小说的最终意图,然而开头并不是开始,结尾也不是终结,此人并不全是此人,“青春”却带来毁灭。每一位读者沿着自己的阅读之路得到的却是各自不同的阐释之果,因为斯帕克在她的小说之域中设置了多种的可能性。
四、结语
被称为“天主教作家”的缪里尔·斯帕克早在其小说创作的初期就在思考现实和虚构的关系。在评论界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后现代主义时,她已在小说中尝试揭露现实主义的无力,《圣灵》甚至因其超前的表现而引起了出版商的犹豫。斯帕克在其论文《艺术的隔离政策》中谈到“引起共鸣和情感的艺术和文学,无论怎样的美好,无论怎样的真实,都得退出。它诱使我们感觉投身于真实的社会和生活,但事实上正是它使我们与真实隔绝。我提倡用反讽和嘲弄的艺术来替代它。荒诞嘲讽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有力武器。[7]”这些带有明显后现代意识的宣言,使得她“天主教作家”的头衔陈旧而不适宜。斯帕克在她的作品中反讽盲目的宗教追随者。皈依天主教是她思想转变的外在形式,小说中的天主教人物和主题是她反讽固执死板的传统文学的素材。事实上,在探索艺术和现实关系的过程中,斯帕克发现后现代的开放、不确定的文学形式才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1]MALCOLM B.The Postwar English Novel:Essays on the state of the Novel[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177-178.
[2]曾艳兵.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J].台州学院学报,2002,24(5):10-14.
[3]MARTIM M.Theorizing Muriel Spark[M].New York:Palgrave,2002.
[4]MURIEL S.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M].London:Macmillan&Co.,1972.
[5]谭君强.论后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J].思想战线,2004(5):106-109.
[6]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90.
[7]MURIEL S.The Desegregation of Art[M].New York:Spiral Press,1971:2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