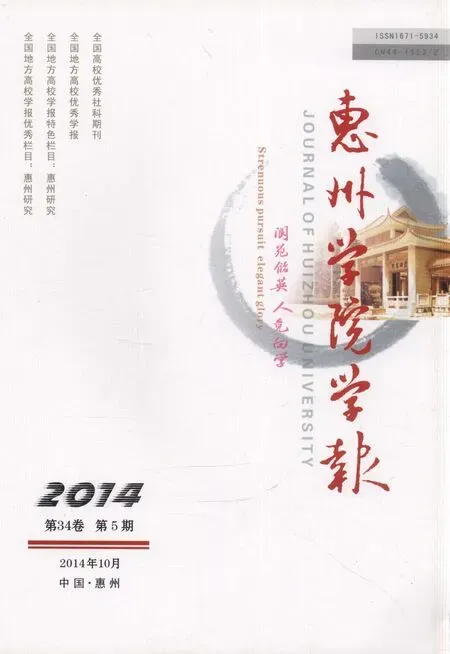人文素质培育语境中的哲学教育
陈咸瑜
(广州大学 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一、哲学教育之目标:对超验真实性及其意义的确认
顾名思义,人文素质培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塑造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类文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作为自我的人类共同体的自我反思、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精神凝结,人文精神因此也是人类走出自然界,获得属人的自由的精神表征和永恒动力。从不同的学科专业特性看,人文精神虽更集中体现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艺术理论等人文学科中,但自然科学理论以及科学技术中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科学技术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是人文精神最高境界的反映。同时,人文精神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思想保证和持续成长的内在精神动因。
其实,无论任何一门科学理论及其专业知识,其基础都是人的思想,其背后都含有人文精神的境界,只不过人类的思想与精神境界主要地是在人文学科的探讨中得到了专门的保存、阐发和滋养。因此,人文教育的主要途径是人文学科的学习与研究,人文教育的主要目标则是把造就了人类知识的精神境界通过人文学科的表达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哲学教育不仅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保证。
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教育不仅在价值诉求上与之相一致,而且在理念、内容与方法上与之相对接。如果说,人文精神的最高境界可集中体现为人类对真、善、美的终极价值的表达和追求,那么哲学教育中真善美三重维度的价值诉求正与此最高境界达到了高度和谐的统一。哲学教育既以对“超验真实性”的确认、“至善可能性”的证明以及对“美之为美”的沉思为思想追求,又以“真、善、美”三者合一的价值追求为最高理念。可以说,人文精神的培育是哲学教育应有的价值目标和旨趣,而哲学教育是人文精神培育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哲学教育同时应该作为人文教育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保证。这不仅是因为哲学教育的核心追求是一种高层次的、区别于自然思维、科学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理论思维特质(即“纯粹”的思想素质),更在于其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即哲学教育对于人的思想的深度和高度的推进与提升。这种推进和提升根本上乃是由于哲学作为一种反思性思维所具有的本源性、终极性决定的。所谓思想的深度,指的是人在“返本”的追问中得以探寻、批判、建构乃至重构思想的“根基”、“理据”;所谓思想的高度,指的是人在“开新”的道路上得以超越此岸,通达彼岸,开显意义,获得自由,即人的精神品味和思想境界的整体、全面的提升和塑造。总之,哲学教育的目标正是通过哲学思维的本源性、终极性和反思性特质,帮助人们开启对于自身生存意义的领会、生活价值的悟解,不断超越自身的“现存状态”,在确立自身未来发展的理想境界中自主自觉地提升和开发自身的素质与潜能。[1]而这也正是人文教育的根本目标所在。
如上文所述,人文精神的最高境界可集中体现为人类对真、善、美的终极价值的追求和表达。因此,崇尚真理的精神品质以及追求真理的思想境界应为人文精神及其培育之题中本义。崇尚真理,追求真理也是哲学教育的价值目标,但是,哲学教育崇尚和追求的真理是哪一种性质的真理,哲学教育如何崇尚真理?对此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哲学教育与人文素质培育的内在关联。
众所周知,人类的一切学问都是关乎真理或真实性的表达,离开真实性,任何学问将没有存在的基础。在人的世界里,有两种真实性:一种是经验的真实性,另一种是超验的真实性。经验的真实性也称为事实的真实性,或者逻辑的真实性,超验的真实性指的是意义的真实性或者价值的真实性。与科学一样,哲学追求真理,但是与科学不同,哲学追求的真实性不是经验的真实性,而是超验的真实性。哲学基于自身的学科特性和思维特质,不停留在经验、逻辑和事实的层面上追求真理,而是要求把对真理的理解推向经验和事实背后更深刻的层面,即思想的层面来理解,或者意义和价值的层面上来把握。人们关于上述两种真实性的追求,实际上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种追求的不同体现。当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从来不是矛盾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互为滋养,相互促进。从人文精神的培育看,特别是从培育人们崇尚真理、向往真理、勇于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品质看,上述关于两种真实性的科学揭示与哲学阐发皆具有重要的依托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但从目前看,人们往往强调和偏重经验的真实性及其在事实与逻辑层面的科学揭示,而对哲学追求的超验的真实性及从中阐发的意义与价值的真实性,因为其不可能获得经验的证实或证伪而归于形而上学的空谈,经常被人们漠视或遗忘。实际上,当人们把科学追求的真实性视为唯一的真实性的时候,就是所谓“科学主义”的思维范式形成的时候。“科学主义”思维范式所具有的狭隘性及其限度表现在:一方面,科学本身秉持的是一种自然态度的思维,即科学本身不对其研究对象及其如何可能的问题提出怀疑;另一方面,科学本身仅停留在经验、事实及其因果关联的解释和说明上,科学本身不提供精神价值和意义关怀。因此我们认为,在哲学教育中秉承哲学的学科特质和思维特质,去理解两种真实性各自的存立理由、应用界限及其相互关系,打破“科学主义”思维范式的一统局面,从而对超验的真实性及其意义与价值世界的真实性予以充分深入地阐释,对于我们进行人文素质培育,培育人们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人文品格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意义。
二、哲学教育之道路:哲学“奥秘性”与“公开性”的阐发
众所周知,“世界观的理论”是关于哲学的一个最普遍的理解方式。但是在如何理解“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这一观点上,其实存在着基于上述两种真实性的不同理解取向。按照通常的理解,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哲学是为人们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问,即哲学追求的真实性是普遍的、客观的、作为规律而被发现的真实性。当然,这种“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理解方式具有深远的哲学史背景和深切的人类实践根基,也与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在对哲学的这种通常的理解中,却存在两个值得认真思考的与人文素质培育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其一、此理解方式只限于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视域,而没有从哲学与常识、科学、宗教、艺术、伦理等多元关系中去理解哲学,因而无法解释和说明哲学的多重性质和多重功能,也无法切中哲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之间的本质关联;其二、此理解方式把哲学当成经验常识或实证科学的“延伸”或“总结”,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知识。若以此哲学教育的理念贯串于人文素质教育,其结果是人文知识被退化为科学知识,甚至退化为经验与常识的知识,而人文精神则断然无法触达,更遑论提升。[2]
以上这种哲学观的要害之处在于,仅仅把世界的真实性归于经验、事实与逻辑的真实性,认为凡不具有此类性质的真实性的东西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此种哲学观不仅错误而且十分有害。实际上,哲学追求的真实性从来不是经验、事实与逻辑的真实性,而是超验、价值和意义的真实性。正是在后一种真实性的追求和确认中,哲学本源性、终极性和反思性的思维品格以及思想的深度和精神的境界才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阐发这种更纯粹、更高境界的真实性既是哲学学科本身的要求,也是在哲学教育中倡导人文素质培育,提升人们崇尚真理、追求真理、反思真理、守护真理的人文品格的重要途径。一个仅仅停留在经验、事实与逻辑真实性的狭隘视域里的人,很难说具有真正的人文精神。因此,对于“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的更合适理解,是把哲学看作为“观世界”的理论。此“观”是观看、观念、观点,总之是“思想”,是思想的观看。不同的观看给出不同的世界,这不同的世界是在价值与意义上不同的世界。可以看到,在此理解方式中哲学确认的真实性是思想的真实性,是价值与意义的真实性。我们以为,在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强大对手面前,人文精神之“真”性的追求断然无法拒绝思想真实性的追求,无法拒绝价值与意义真实性的关切。由此可见,在哲学教育中推进人文素质培育,其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哲学的学科特性及其思维特质。无视哲学教育的内在本质规定,无视哲学揭示真实性的特殊性质及其更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进行所谓哲学教育,其结果不可能是真正有价值的人文素质教育,反而可能导致人文教育的“物化”、“工具化”,其结果是人文素质教育的扼杀。
黑格尔曾经在他和谢林合编的《哲学评论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哲学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某种奥秘的东西。哲学只是由于它正好与知性相对立,并从而更与常识相对立才成其为哲学;相对于后者而言,哲学的世界自在地和自为地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黑格尔看来,说哲学是“奥秘的”,这并不等于说哲学是“高不可攀”的。黑格尔的研究者、美国当代哲学家约翰·萨利斯在《黑格尔关于陈述的概念》一文中也开宗明义地阐释了黑格尔关于哲学具有“奥秘性”与“公开性”的观点。萨利斯指出:“哲学就其使它自己适合于它的实质的道路,适合于它的世界、一个颠倒的世界的道路而言,它是奥秘的,但就它给所有想从事哲学的人提供忍受进入哲学的颠倒的可能性而言,它又是公开的。[3]马克思也曾经明确指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4]这里说的“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即是黑格尔关于哲学的“奥秘性”与“公开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罢了。在此引述上述文字,目的在于阐明哲学教育的特点正在于哲学自身的“奥秘性”与“公开性”。我们以为,从哲学教育与人文素质培育的深层关联看,正是在哲学的“奥秘性”中隐藏着人文素质培育不可或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品格,但也正是在哲学的“公开性”中,预示着人文素质培育可能的方向与现实的道路。
[1]黄禧祯.哲学教育的新语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57-58.
[2]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3.
[3]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1-9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