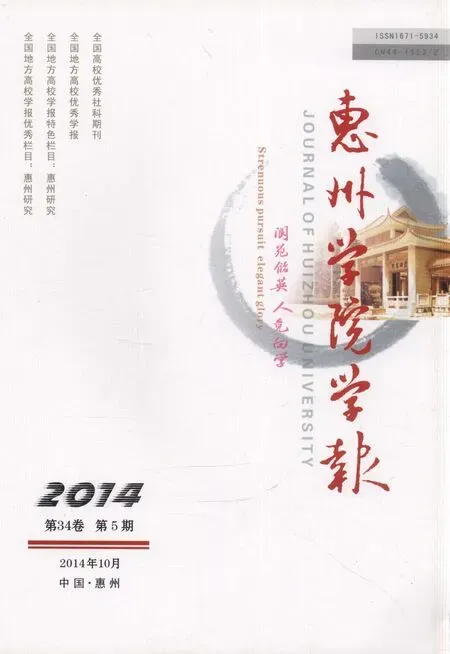地域文化演进中的自然条件与人为因素之作用
高 钟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地域文化又称区域文化,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语言、服饰、饮食、建筑、民俗、宗教等文化符号,展现出来的联结该地域居民内在认同的特有之文化。地域文化源起于特定的地域环境而产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条件;地域文化虽然受制于一定的地理限制,但并不封闭,而是处在一个不断地与周边地域文化进行交流的一个开放状态之中。特别是移民迁徙,更为地域文化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移民与土著新旧文化互动促使地域文化发生演变;在移民之外,促进地域文化演变的最大的动力,就是国家意识。为在地域共同体之上建设国家共同体,国家政权就力图整合地域文化于国家意识之中,地域文化因之而产生有利于国家意识普及的转变。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宗教还是一个地域文化演变的重要元素。所以,地域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实是自然与人为性因素互动之合力的结果。
一、地理自然条件是地域文化的基石
地域,即一定的自然地理空间;文化,实即人类的一切文明创造之总和。地域文化即: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空间条件下,此地域之居民与自然环境及外界文化互动中而产生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这类特定的地域空间往往有自然的、具一定封闭性的界线。在这个有一定封闭性的地域中产生的文化,却因为受到周边地域文化、移民、国家意识、宗教性人为因素之影响,形成一定的开放性。在周边这些众多的绪人为因素涌入影响下,地域文化常产生历史性的发展和醒目的变化。所以说,地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系统。地域文化的动态发展如今还在进行着。众多的地域文化的动态发展,合成了多元、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
辽阔的中国疆域被自然的山河湖海隔划成不同的地理区域,这些地理区域因所处的经纬度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气候状况与地质条件,这些自然的因素叠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地域居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先天元素。在这种先天的自然条件之制约下,人类只能采用适合这类自然条件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种自然条件决定与限制地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状况,中国古人早已窥测到其端倪。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当时中国的关中、三河、齐鲁、燕赵、楚越等地域自然特点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等文化的关联一一进行了概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栎邑北邻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天水、陇西、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1]3261-3262”、“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列国各数十百,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织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夷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1]3263”;“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方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1]3267”等等。这些不同的地理区域之形成,是由于其周边的山河之自然屏障以及气候条件所形成的。如关中,东边黄河,北边草原沙漠,南边秦岭,西亦为沙漠,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较为完整的地理区域。其余的如三河、越楚等大都类此,均由自然的山河而形成相对独立、封闭的地域。
除了长城以内因山河阻隔形成众多的地域外,长城之外,因气候寒冷、再加上土地以草原与沙漠为主,故而,其居民只能选择“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形成了与中原迥然有别的风俗文化。如匈奴:“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剑。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1]2879”草原游牧民族因地理气候条件而选择了与中原迥然有别的生产方式,其生活方式、饮食、衣着、习俗文化均与中原文化更有着醒目的差别。除上述之匈奴外,继匈奴而起的诸游牧民族,其文化习俗大体相近。《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令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娉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2]885”;《金史·兵志叙》女真族:“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侄,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事,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3]992”这些充分说明先后主宰长城外草原的众多民族,虽然种族有别,但只要进入到这片严寒的草原地区,就不得不选择“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也不得不沿用一些共同的生活与文化习俗。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与制约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习俗,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客观存在。
对于地域之自然条件与人类文化创造的密切关系,古今中外的学者哲人均予以注意,并留下了众多的记载。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引用了司马迁、洛克、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等人对地理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关系后,总结说:“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寒带热带之地,其人不能进化者何也,人之脑力体力为天然力所束缚,而不能发达也。……极寒极热之地,其人穷日力,以应付天然界之洊迫,犹且不给,以故文明之历史,独起于温带”;“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通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4]107-108”。梁氏之总结,可谓一言中的。
由无数的历史记载与先贤们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域自然条件,决定与制约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语言、服饰、建筑、习俗、宗教等地域文化。地理自然条件是地域文化的基石,实是不移之论。
二、人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的创造为地域文化之源
先天的地理自然条件奠定了地域文化的基石,但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既是自然界的承担者,又是由自然界养育而成的。但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他的文化”。人能创造属于人的文化,“首先人能够决定他自己的行为方式,即他是有创造性的;其次,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就在于他是自由的。人在双重的意义上是自由的:人‘摆脱’本能的控制而获得自由;人‘达到’生产性的自我决定的自由。因此,除了纯粹在理论能力上向世界开放以外,创造性和自由是两个附加的人类特征”[5]201-202。人类根据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创造与选择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就创造出了不同的地域文化。所以,人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创造,实为地域文化之源。人类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无一不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的人类创造。“贫富之道,莫之予夺,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繈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1]3255。司马迁在这里强调了在自然条件限制下,人的巧与拙,即创造力的大小是突破自然条件限制,创造适宜于人类生活与发展的文化之根本。齐国封于海滨,“地泻卤,人民寡”,自然条件并不好。但齐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即动员与发挥人的创造性,实现“人‘摆脱’本能的控制而获得自由;人‘达到’生产性的自我决定的自由”,最终形成“齐冠带衣履天下”。通过纺织品贸易与鱼盐生产之利,齐国在突破“地泻卤”之自然限制的同时,还创造出了影响中国千年的稷下文化,为中华文化轴心时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类在特定的地理自然条件下的创造,是在学习自然,模仿自然的过程中,逐步领悟到地域自然的规律性,从而进行选择与创造的。如生活在太湖边的古吴越人“断发文身”,这一习俗其实是因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1]1446”。在水中游泳,头发长不方便,所以要“断发”,而且,古人看见水里的鱼类都有鳞,所以也就文身,让鱼龙生物认为是同类,而不受其伤害。吴越古人的“断发文身”,究其实是因在太湖水域这一特定的自然条件下,在生产性的自我决定的自由中,创造出的习俗文化。当然,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升,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增强,而创造出更为先进的工具与理念后,旧的文化习俗也就逐渐的消除了。如吴人后来有了船、网等生产工具后,人不必身体下水就能捕鱼,这种断发文身的文化习俗也就消除了。
人类在特定的地理自然条件下创造地域文化,这种创造既有对自然的学习,也有对自然的改造。人在这种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会体悟到人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长期坚持对于改造自然之意义,从而产生出坚韧、顽强、剽悍、敢拼的文化习俗。如楚国初封,“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1]1705,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楚人“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开荆辟莽,将原始大山开成可耕可居的农田与城池,同时,“跋涉山林”,向外拓疆展土,灭汉阳诸姬之国,北上问周鼎之轻重,最后灭陈、蔡、隋、越,长江中下游尽为楚有。楚人在这种长期的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与汉阳诸姬——隋、庸等国的人为封锁的搏斗中,形成了坚韧顽强,开拓好斗,“其俗剽轻,易发怒”[1]3267的文化特色。正是凭借“其俗剽轻”,勇于开拓的特色,楚国不但一直东进到大海,而且,南下岭南、远征西南,将整个南中国收入其版图之内。这种长期对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的抗争中,养成了楚人勇于反抗,蔑视权威,自信“狂放”的文化习性。这种文化上的自信,使之长期不认同周之文化而以蛮夷自居,以问鼎之轻重的方式直接挑战周天子,对于强秦更是长期与之抗衡,即使在楚国灭亡之后,民间还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流传,这正是楚文化自信、狂放、坚韧顽强、剽轻敢死的一个写照。楚文化的形成充分说明了“人在改变他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也改变着他自己。人是唯一必须劳作的造物,但是,他的劳作不仅是一种艰难的命运,它也包含着人的伟大的种子[5]201-202”。
这类在恶劣艰难的自然条件下,创造出坚韧顽强的地域文化之“伟大的种子”的事项,举不胜举。如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文化亦是如此:“惠之堤封,几千里。其中多崇山峻岭,群岗复嶂,绵亘不绝,南涉涨海,土瘠而民贫,归善、河源之境产矿,聚赣吉汀漳之逋逃,而治以为利焉,赢则贾缩则寇”,“然习骄旷喜斗讦,山气使然也”。崇山峻岭,群岗土瘠的自然环境,养成了惠州文化中的“习骄旷,喜斗讦”、“重气轻死,动触法禁,岩洞不逞,走险挺顽”[6]之强悍敢斗、勇于反抗的文化习俗。古人认识到这种文化习俗“山气使然也”,其实也是惠州人在特有的群岗岩洞的环境下劳作的一个创造。
“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远古先民在地理自然条件限制下,为了生存,开始生产活动的同时,就开始了文化主体的创造。从而为各式各样的地域文化创造出色彩斑斓的源头。人类在这种文化的创造中,也获得了新的发展,人类由此而成为一种文化的存在。“由于需要的满足,生产第一次引起了新的需要。看上去是我们的本性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自发活动的结果。正像人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经济主体并给以一种‘完成’一样,人在非经济的事情中也是如此。”[5]208人的创造性就这样不断地促进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除了不断地在本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之外,地域文化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那就是吸纳周边的文化成果,实现地域文化的互动,在互动中实现文化的创造与发展。这种互动,主要是通过移民来实现的。
三、移民与地域文化发展
不同地域的文化互动,除了文字、书籍等载体之外,人是一个最重要的载体。虽然中国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极大地降低了图书的成本,但由于小农经济的限制,识字率很低,所以,影响中国地域文化互动而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常因各种原因而发生的大规模的移民。
人创造文化与被文化所创造的统一决定了“人的存在永远不是重新开始的,毋宁说,它常常用发现自己被抛入了某种它未曾寻求过的历史状况中[5]208”,这种“历史状况”就是人出生前所在的地域文化。人一出生就被嵌入到一个限定的地域文化之中,并在其中生活与成长,从而耳濡目染这特有的地域文化,成为这个地域文化的承载者。在自然与社会发生大的变故,发生主动或被动的移民时,这些移民就带着其原住地文化来到迁移地。其身上承载而来的原住地文化,与迁入地文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互动。在这二种文化的互动中,迁入地文化发生变化,发展出一种带有移民原居地文化色彩的新的地域文化。如吴地文化,其初,太湖波涛万里,初民们“被发文身,出没于风波里”;春秋战国之际,太湖上游的楚国巫臣、伍子胥、伯否、项籍等大批贵族流亡到吴地,带来了楚文化“剽轻、易发怒”,勇斗敢死的尚武之风,因而养成了“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7]746”;直到三国归晋之后,蜀人安定,吴人屡反,晋武帝为之而问计于吴人华谭:“武帝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雎,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对曰: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吴阻长江,旧俗轻悍[8]168”。这种“吴人轻锐,难安易动”、“吴阻长江,旧俗轻悍”的地域文化很快为东晋的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河洛文儒文化所改变,一改旧风,由尚武而转向了尚文。
河洛所处三河之地,先秦时即为“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织俭习事”,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之国策,崇文尚儒,东汉光武帝“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取阙文,补缀漏逸”,定都洛阳后,四方学士,“莫不抱贡坟策,云会京师”;汉明帝亲自到太学讲课,“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悉令育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太学中“游学日增,至三万余生”[2]746。河洛地区成为中国儒家文化士人最为集中,尚文崇儒之风最为强劲之处。西晋末年,中原大乱,“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8]203”,大批的文化士族举族南迁,如以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以王承为首的太原王氏、以谢琨为首的陈郡谢氏、以袁谭为首的陈群袁氏、以庾亮为首的颍川庾氏、以桓彝为首的谯国桓氏、以荀崧为首的颍川荀氏、以羊曼为首的泰山羊氏,以周凯为首的汝南周氏、以蔡漠为首的济阳蔡氏……等等。据葛剑雄先生统计,东晋南北朝时期,南迁的总人口约为90余万,其中迁到旧吴地之江苏的最多,为26万。[9]410如此庞大的移民所带来之崇文尚儒之文化,很快将吴地原来的尚武习俗洗刷一空。“江东士族不独操中原之音,亦且学洛下之诵,张融本吴人,而临危难,仍能作洛生诵,虽由其心神镇定,异乎常人,要必平日北音习俗,否则决难至此无疑也[10]370”。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都发生了替换,“中原之音,洛下之诵”从此转化成以“吴侬软语”著称的吴地方言。吴文化实现了由武转文的根本性转折。而这个转折正是在中原移民的文化互动中得以实现的。
这类因移民文化与迁入地文化互动,而发生的地域文化出现醒目的发展与转折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如班固在《汉书·地理记》载:“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尚忠,其弊鄙朴。……秦即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7]1654”。南阳地域原有的“尚忠”、“朴鄙”的文化特色,就因秦始皇的移民,而一变为“俗夸奢,好气力”、“藏匿难制御”的尚武之风了。又如关中“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遣风,好稼穑,务本业,……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华兼并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7]1642”。汉初的政治大移民就造成了关中之地域文化之大变。“好稼穑,务本业”的重农之风,一变而为“风俗不纯”的“商贾为利,游侠通奸”了。再如孔、孟之乡“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遣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1]3266”,邹鲁之民,曾受儒学熏陶多年,尚文崇儒是其地域文化的显著特色。但在南北朝时期,经过五胡十六国多次反复的游牧民族之移民后,邹鲁之地域文化大变。“隋末唐初之史乘屡见‘山东豪杰’之语,此‘山东豪杰’者乃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其地实为北魏屯兵营户之所在。由此推测此集团之骁勇善战,中多胡人姓氏(翟让之翟,亦是西零姓)胡种形貌(如徐世勣之类),及从事农业,而组织力又强,求其所以然之故,苟非假定此集团为北魏镇兵之后裔,则殊难解释”。这个由游牧民族之屯兵营户移民而繁衍出来的“山东豪杰”集团,是“当时中国武力集团最重要者,为关陇六镇及山东豪杰两系统”[11]243-265之一。这个庞大的武力集团正是游牧民族尚武之文化,与“颇有桑麻之业”、“畏罪远邪”之当地文化互动结合之果。这个庞大的武力集团也就彻底颠覆了邹鲁原来“尚文重儒、畏罪远邪”之文化习俗,形成尚武善战的新文化特色。这一文化特色至今尚依稀可辨。
移民文化与迁入地文化互动,最后创造出新的文化。在这一新文化中,哪方面的文化元素保存的多,则主要看移民的数量与质量。数量多,则承载而来的文化量就大,那么迁入地之文化很可能就会被新的文化元素所淹没,如东晋移民对吴地文化之影响。除了移民数量之外,还要看质量,即移民中的文化精英的数量多少。文化精英掌握着文化传承的话语权,他们的文化习俗影响着一般社会成员的习尚。“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列,高士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为笃厚。‘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7]1644。颍川的地域文化,先后在文化精英的引导下发生着前后鲜明的巨大变化,有力地证明了移民对文化的影响,不仅与数量有关,而且还与移民的质量有关。而移民的质量往往是与政府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文化与政权相结合,借助制度性的力量改变原地域文化,也是地域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四、国家意识对地域文化的整合
国家意识即国家政权所确立的思想文化。国家作为高居社会之上的共同体,需要全社会的认同,就需要一个得到社会认同的意识形态文化。而这种认同并不是与国家的意志同步的,往往需要国家借助各种制度对社会文化,特别是社会中各类地域文化进行整合,除掉地域文化中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元素,而代之以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元素。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以“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作为整合地域文化为国家共同体的制度规范,同时,多次巡游江南、山东,刻石勒碑,以推进“人同伦”的文化整合,这是大一统帝国以国家意识对地域文化整合的起始。
秦始皇选定的国家意识是法家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是他用来整合各地域文化于一统的制度与方法。但由于法家文化与关东六国广泛存在的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血缘社会之“孝、义”文化相距太远,故遭到六国文化的强烈抵制。秦始皇又用“焚书坑儒”的暴力方法进行整合,结果激起更大的反弹,“坑灰未冷山东乱”,秦二世而亡,这次国家意识的整合完全失败。
汉初在选择国家意识文化经历了近七十年的试错,由法而道,由道而儒,最终定下“独尊儒术”的国家意识,并制定了“察孝廉、举方正”的“察举制”予“独尊儒术”以制度性的保证,实现了儒家文化与国家官僚选拔制度性结合,王统与道统由此合为一体。但仅此还不够,还需要辅以教育制度来整合地域文化,以将地域文化之主体纳入到国家意识之中,由此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的共识同心,从而实现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这个以政府官员用教育的方法,改变地域文化中与国家意识不合之处,而导入国家意识的方法,从汉景帝开始,到汉武帝后大力推行,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其最有名的案例子即是“文翁化蜀”。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裁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剌吏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迁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通过“亲自饬厉”、保送京师、学成重用,开办学校等方法,使国家意识的“儒学”在“有蛮夷风”的蜀地“大化”的方法,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12]3625-3626。国家通过举办各级学校开展基层教育的方法,实行国家意识对地域文化的整合,从而使国家共同体因文化道统之共识,取得内在的联结,实现国家与社会秩序稳定的方法,自汉以后,为历代王朝所重用,在宋代达到高潮。
宋代有惩于五代武人暴力乱政的教训,确立右文抑武之国策,在完善隋唐创立的科举制的基础上,确立“‘作相须读书人’”与“文人知州”[13]487制度。又在活版印刷发明、图书成本大幅下降的基础上,对官办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形式进行了新的创造。同时,在大力举办官办郡学的同时,还鼓励民间兴办书院。这些遍布全国、官、民兴办的学府、书院在科举制的导引下,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教学内容的国家意识对地域文化的整合网。
北宋景佑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知州任上,以五代吴越钱氏南园旧地创立苏州郡学。“左为广殿,右为公堂,泮池在前,斋室在旁”,同时,他改革旧制,首创将官学与祭祀孔子的庙堂合为一体的左庙右学新格局。庆历三(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由范主持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将范仲淹在苏州、镇江、鄱阳等地创建并取得成功的郡学推及至全国,“明年(1044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宋兴,故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14]27”。经范仲淹创建的学庙合一的郡学模式因之而遍布全国,成为科举制度下的一个有力的基础支撑。同时,“国家意识”经这些遍布国土的州郡之学与民间书院的支持,制度化地对各地域文化进行整合,江南地域文化经此整合而发生大幅度的转变。“当赵宋时,俗益丕变。有胡安定、范文正之遣风焉。及后,礼尽渐摩,而前辈名德以身率先,又皆以文章振动。今后生文辞,动师古昔,而不梏于专经之陋,矜名节,重清义,下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摛章染墨,其格甚美[15]10”;“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龄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江以南其俗尽然[16]”。江南地域文化之“不梏于专经之陋,矜名节,重清义”的特色由此而定型,直至近代。
宋代国家意识对地域文化的整合最为成功的是将一些地处僻远,“蛮夷风”盛的地区,通过推广郡学、书院等教育方法,而将之整合入儒家文化之中。如岭南惠州,宋之前还是“人多为蛮僚,妇人为市,男子坐家[17]378”。宋宣和年间,儒生陈鹤为惠州佥判,“惠俗僻陋,士风不振,守吴达老与鹤同志,大兴学校,鹤亲典教事,执经者岁数百人。鹤乃捐佥判厅所得盐仓箩头利市钱,置学田以增廪文,表置学官,自后文士彬彬,惠之倡学,实自鹤始”。而在陈鹤、吴达等官员的积极推动下,惠州一府八县诸学校、书院“皆宋时乡大夫所立者”[18],惠州所在之粤东地域文化因之而大变,“粤东为天南奥区,人文自宋而开[19]23”,国家意识之儒学大行,出现了“合邑重农,以耕为务,近知向儒业,虽僻乡愚氓,多读书识字[20]39”之文化特色。这一特色的产生,正是国家意识对原地域文化整合之结果。
宋代以大力推行教育的方法,将地域文化整合于国家意识之中,为大一统帝国奠定了不移之基。是故,严复先生有言:“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21]1”,此言不虚。
五、宗教与地域文化
宗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求突破肉体生命局限,追求绝对自由的情结。其起源于人类之初,对无法突破之自然力限制的一个超自然力存在的幻想。所以,宗教在任何地域文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在不同地域文化中,宗教文化的浓淡强弱、表现形式、发展路径却有着鲜明的不同。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其实也即上述地域文化的几个影响因素:地理环境与居民的互动而形成的生产方式、移民影响、国家意识整合等,而不同的地域之不同的宗教文化色彩所构成的祭祀圈,则成为一种地域文化最为鲜明的文化特色而为人们所认识。
(一)地理自然条件因素
一般说来,地形环境复杂,风云变幻较多,水流交通便利之处,往往宗教发源较早,传播较广。因为地形复杂幽深,探源不易,神秘感油然而生;风云变幻,雾障霾生,毒气伤人,对超自然力的想象与恐惧随之而来;濒海临江,波翻浪涌,木漂帆来,原始宗教相互传播与影响频仍。这都是造成地域文化中宗教文化影响较大的原因。如处古云梦大泽的楚、黄淮水网的陈,原始宗教均十分发达。“楚有江汉川泽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以渔猎伐山为业,……信巫鬼,重淫祀”,“陈国,今淮阳地。……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鬼[7]1666,1653”,而常有海市蜃楼出现的齐燕、吴越、交广滨海之地,原始宗教更为浓烈。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自战国邹衍传大九州之说,至秦始皇、汉武帝时,方士迂怪之论,据太史公书所载,皆出于燕、齐之域。盖滨海之地理应早有海上交通,受外来之影响。以其不易证明,姑置不论。但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者”、“交广二州之区域不但丹砂灵药可为修炼之资,且因邻近海滨,为道教徒众所居之地。以有信仰之环境,故其道术之吸收与传授,较易于距海辽远之地域歟”。陈先生还用大量的史籍案例论证了天师道等道教与滨海之琅琊、淮扬、吴会、交广等地域之关系,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原始宗教之“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则无可疑者[11]1-2”的结论。
(二)移民影响
移民对地域文化中宗教因素的影响有两类:一类是以传播特定宗教为目的的专职传播者,如最早到江南传播道教的于吉、佛教的支谦等。另一类则是普通移民。这两类人对于地域文化的宗教元素之演变均有着重大的作用。
东汉末年,“时有道士琅琊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以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孙)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22]。于吉在传教中,因宗教的权威侵凌了俗世王权的权威,而为孙策所杀,但他传播的早期道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后来的东晋南北朝大移民中的道教因素在吴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东晋南北朝,大量北方士族移民吴地。这些士族移民中有很多是滨海地区的道教世家,如长期执掌东晋政权,有着“王与马,共天下”之称的琅琊王氏家族,“琅琊王氏世奉天师道”,王羲之、王献之、王凝之等均是著名道家信徒;与王家齐名的谢氏家族,亦是道教之世家,如谢玄、谢灵运等;此外,还有郗氏家族之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这些南下的道教世家与吴地原有之老庄玄学相结合,造就了“东晋士大夫不慕老、庄,则信五斗米道[11]2,36”,吴地文化之突出的道教特色。“吴中师巫最黠而悍”,“若夫巫祝之守,城隍里社之神,祈禳者踵接[23]47-48”。道教神庙遍布吴地苏城之中,如玄妙观、福济观、城隍庙、刘猛将庙、韩靳王庙、五通神祠等等数十所之多。而且,很多道教文化与明清兴起的商业文化相结合,更成为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之民俗,如新年初五之迎财神;正月十三祭刘猛将庙;八月十八上方山五通神庙会等等。特别是脍炙人口的四月十四日“轧神仙”民俗,则是充分地体现了吴文化的和合精神,陌生人以相互碰挤为乐,无以为忤,反以为乐。无贵无贱,无富无贫,神仙化为乞丐,挤着就沾了仙气,商家由此而赚了人气。这一文化正是道教文化“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反映,他与商业文化祈盼人气,和合发财的愿望和合相融,成为数百年来吴地苏州文化的一道亮景。
(三)国家意识
元儒孔子本“不语怪力乱神”。但汉儒董仲舒创建汉儒体系时,将墨子的设鬼神以立教,邹衍阴阳五行与灾异说均纳于其体系之内,创“天人合一”说,从而使汉儒体系中有较强的宗教色彩。宋儒更是援道佛入儒,宗教色彩较之汉儒有增无减。由是,自汉以来的中国国家意识之儒学之中,道、佛等宗教元素十分突出。同时,历代帝王为了论证自身的神圣性,为了更好地维护大一统帝国的统一,也经常有意识地运用宗教因素对地域文化进行整合。这种整合主要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对某些宗教或扬或抑。如中国著名的“三武灭佛”,即是国家意识对佛教的摧抑,而李唐王朝、宋徽宗等对道教的尊扬,武则天对佛教的尊扬,清王朝利用藏传佛教对西藏、蒙古的羁縻之策,都是将宗教元素纳入到国家意识之中的典型。
国家援引宗教因素进入国家意识,并进而利用其整合地域文化,其根本点是以有利于国家王权的统治为目的。有利的就加以尊扬,不利的就加以打抑。如城偟崇拜,本起自六朝城市兴起之后的江南,唐宋后遍布国中,而且,每个朝代都对之予以爵封,封号十分混乱,这对于大一统帝国整齐官制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年下诏:“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礼,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事神之意[24]1076”。这是国家意识借助宗教而整合地域文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其实质就是明王朝政治上的一统,不但要落实于世俗政治中,而且,还要将地域文化中的城隍系统也纳入到国家的一统之中。
国家意识对地域文化的整合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对地域文化中不合乎国家意识的宗教因素与现象进行摧抑。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东汉末年王权对黄巾起义的太平道之摧抑,宋代对江浙“吃菜事魔教”的镇压,清代对白莲教的镇压,都是这类国家意识强力整合地域文化中不利于国家统治的宗教元素的表现。很多地域文化中的庙宇、神像均以邪教、淫祀之名而予以拆毁,如苏州上方山上的五通神庙的多次拆毁就是典型。“五通山神祠,起于宋末,滥于明季,家祀而户尸之。以其能祸福人也。故人人惑之。病者之而祝祷焉,饮之食之,俚语名其山曰肉山,名其湖曰酒海。诚可叹也。又有市井小人,谓贷于神可以致富,请以若干直为母,岁时增以若干直为子,唯恐后时神降之罚。贪于财也。尤可恶者,有女巫见里中妇人病,辄贻其家人曰,神为崇,欲某氏女、某氏妻妾荐枕席,其家父母或其夫叩头流血,求神释之。幸而获免,则曰祷之力。其不免者,曰神不从。此神之躯干色也。吁!习俗之败坏,至此极矣。吾思福善祸淫,天之道也,神奉天之道以祸福人者也。神而利人之口腹,贪人之财利,淫人之妇女,是不奉天道也。设有司不奉天子之号令,其禠革僇辱久矣。尚能祸福人哉?中州汤潜庵先生抚吴,刚毅不阿,凡有司之不奉令旨者,悉罢去之。而又痛习俗之陋,人心之纳于邪也。一日檄令毁神之像。木者投之火,土者投之渊,祠宇改奉关武安王象。于是人无智愚贤不肖,皆称快先生[23]44”。这就将国家意识强力整合地域文化中与之不合的宗教元素的内在原因讲得非常清楚,地域文化中的神祇违背了国家意识,即与世俗官员违背了大一统国家君主一样,是要“禠革僇辱”,予以撤除焚毁的。
国家意识对不符合其规则的地域宗教文化予以摧抑,而对于有利于其规则的地域宗教文化则加以推与援引,使之成为准国家意识。如山西地域文化中的关公崇拜,因为晋商在清兵入关之前后,长期与之进行粮草方面的边贸。同时,清王朝也要利用关公义气之精神,笼拢汉人,所以,清王朝极力推行关公崇拜。不但在沈阳、北京等地大建关公神庙,而且,清初期绪帝一再对关公进行敕封,“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以壮缪原谥,未孚定论,更命神勇,加号灵佑。后又改曰忠义”;“嘉庆十八年,以林清扰禁城,灵显翊卫,命皇子报祀如仪,加封仁勇”;“道光中,加威显。咸丰二年,加护国;明年,加保民”;“同治九年,加号翊抚。光绪五年,加号宣德”[25]2541。一个地域文化的神灵,就这样为国家意识所援引,而成为一种准国家意识了。
(四)地域文化中的宗教祭祀圈
由地域文化中独特的神灵宗教信仰,往往成为地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形成不同特色的地域宗教“祭祀圈”。这个祭祀圈的宗教信仰由于适应了该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国家意识往往无法强力将之整合、去除干净。如上述的苏州上方山五通神祠,因为适应了宋明以来,徽商集团以苏州为主要据点的兴起,此神之贪财、贪色、贪口腹之欲,正是商品经济发展中,商人、市民阶层的世俗、人性需求之折射。故虽经清代汤斌等官吏多次拆毁,但往往隔不了多久,又在原地兴起,形成一个以五通神祠为中心的苏南、浙北之“祭祀圈”,每年八月中秋,从周边各县市来进香还愿的信众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其庙会之兴盛,无可言语。它与苏州年初五之迎财神、四月十四“轧神仙”等合组成苏州市民特色的宗教色彩之地域文化。
这类因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地域文化中的宗教元素,生命力非常强大,如妈祖崇拜,就是因为随着宋代沿海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渔业、商贸发展过程中而诞生的。他适应了人们在海洋生产与生活中祈望平安的要求,故而不但在中国沿海形成了妈祖崇拜之“祭祀圈”,而且,这个“祭祀圈”还扩展到海外华人之中,如日本、琉球、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等。这种地域文化中的宗教元素往往也成为该地域文化的一个标志。该地域居民将此神灵视为本地域之保护神,而随时将之携带,共同迁移。海外很多妈祖庙其实都是中国沿海居民迁移的结果。在这种迁移过程中,这类宗教元素的起始原因开始模糊,而地域保护神的文化特色却始终保持。如福建、广东沿海很多移民在清代移往四川内陆,但他们却将海洋的保护神——妈祖也一同带到了四川内陆之中。四川境内,凡是福建、广东移民集中的地方,一般都建有妈祖庙,妈祖祭祀圈,成为沿海移居四川的移民的一个地域文化认同的标志。
地域文化中的宗教祭祀圈,很多与本地域自然、文化界限重合,从而成为本地域文化的一个标志。但由于地域文化是一种他者的存在,即在他者的环境中,地域文化认同就更为迫切,所以,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的宗教祭祀圈,往往会成为该地域移民在一个新的迁入点的集聚之地。这也是在明清之后,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多,很多地域祭祀圈的神灵庙宇往往成为该地域流动人口、移民的会馆所在地的原因所在。如各地的万寿宫,就兼有江西会馆的职能,禹王宫,就兼湖广会馆的职能。这是地域文化宗教祭祀圈延伸出的一个适应社会发展的功能。除了为地域移民提供聚会之地外,很多宗教祭祀地方神祗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转化为行业神,如鲁班转化为泥、木工祖师;伍子胥转化为丐帮祖师等等,这些都是地域文化宗教祭祀卷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与外延的一个表现。
[1]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992.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二册·文集之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8:107-108.
[5]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6]惠州府志(嘉靖):卷六[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7]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二十五史[M]∥房玄龄.晋书.上海:上海古籍,上海书店,1986.
[9]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370.
[1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12]班固.汉书:卷八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6:3625-3626.
[13]二十五史[M]∥脱脱.宋史.上海:上海古籍,上海书店,1986:487.
[14]欧阳修.居士集:卷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1:27.
[15]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二·江苏[M].上海:上海书店,1986.
[16]归有光.震川集:卷九·送王汝康会试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78.
[18]惠州府志(嘉靖):卷十一[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19]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5:23.
[20]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上篇·卷八[M].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39.
[21]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
[22]陈寿.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3]顾沅.吴郡文编:第三册[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1076.
[25]赵尔巽.清史稿:卷八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0:2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