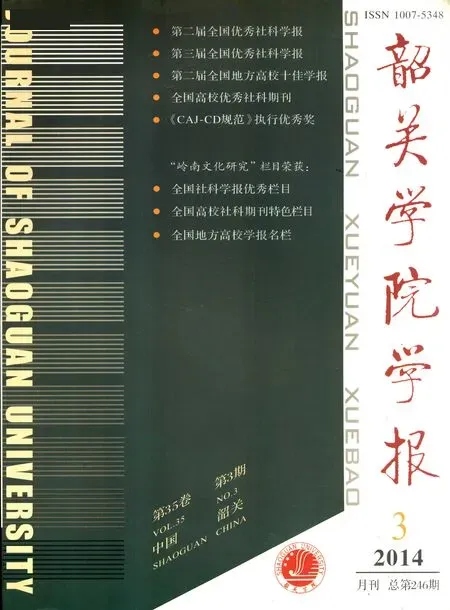当下农民工书写的城市想像
程丽华,江腊生
当下农民工书写的城市想像
程丽华1,江腊生2
(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九江332005)
城市想象是当下农民工进城的最大驱动。物质性的城市具象、性感的城市女性和城市身份构成了农民工书写中城市表达的主要载体,或充满诱惑,或悲情化处理,直接体现了当下中国社会农村与城市的物质与精神错位。
农民工书写;城市想象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20世纪以来生活方式最明显也是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现代城市的兴起。现代城市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现代城市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它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它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1]。多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是农业社会,稳固的农业文明及其伦理体系支撑着社会的存在。现代城市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给中国传统社会和乡村的秩序、内容和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城市塑造着自己最新容貌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当下中国整个社会的面貌。城市作为后起的乡村文化的对立存在,并与乡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农民对城市文化的体验过程,正是城市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其中既有城市文化现代性的召唤,又有乡村贫苦的外在驱动。孟繁华指出:“喧嚣热闹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它的各种符号——包括城市地图、街区分布、各种标牌明示的场所:商店、饭馆、剧场、咖啡店、酒店以及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门,这些不同的城市符号仿佛都在向你发出邀请和暗示;一方面,城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它以‘陌生化’的环境——建筑环境、语言环境、交往环境等拒绝了所有的‘城市的他者’。因此,城市以自己的‘规则’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暧昧的、所指不明的场所”[2]。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决定了他们保持距离化的城市想象与迷恋,并深陷于城市文化本身的悖论之中。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对城市的想象往往以一系列的意象为载体,体现人生的诸多梦想与恐惧。《海上花列传》中,一瓶香水、一件花边云滚的时装,是二宝进入上海这座城市的想象;《红楼梦》中,王熙凤详细推介的茄鲞,精致的糕点对于乡下的刘姥姥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早期的城市文化想象。鲁迅的《故乡》中的杨二嫂对城里道台老爷的想象,不仅直观地理解为有钱人,还具象地描述出“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城市对古老中国的农民蒙着厚厚的面纱,一切的想象都是虚幻朦胧的臆想。整个现代文学中,由于中国城市化是在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争的语境下强行推进,城市的奢华、堕落与乡村的贫困、善良构成了二元对立的模式,一直影响着农民对城市的理解和体验。城乡二元冲突一直顽固地存在,只是被一次次的战争氛围所遮蔽。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城市的这一符号化意象一度成为旧时代的替罪羊。《我们夫妇之间》中的跳舞、皮帽,都是作为城市文化物质性的一面而被批判性的存在。
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没有打破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城乡二元对立局面时,城市在农民眼中还只是一种现代化的新奇或者梦想。如香雪对城市的理解是火车和铅笔盒(《哦,香雪》),陈奂生对于城市的理解是5元钱一夜的旅馆(高晓声:《陈奂生进城》),留小儿对于城市的想象则是通过下乡知青“我”的嘴里而形成的(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只有真正打破了城乡界限,农民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城市现代化的需要时,城市才真正耸立在农民面前,带着乡土气息的农民感受到城市现代化的光怪陆离,并将城市谋生与致富梦想等同起来。因此,二元身份的农民工一方面响应着城市现代化的召唤,感受着城市现代性带来的物质财富和欲望享受,另一方面又真切地体验着城市现代化对农村、农民工的压抑与掠夺。
自然,城市现代性的悖论始终纠缠在农民工对城市的想象当中:一方面是城市化的不可避免和时代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则是对城市化带来的不良后果的反思,并从中衍生出的深深厌恶和抵触。中国农民大规模地进入城市,目的是为了追逐物质的现代性,而追逐物质的现代性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建设自己的家园,然而在主体缺失的乡村,其原有的家园本质上是被荒芜了的,这是现代性席卷下,乡村人所面对的一个显著的悖论。这两种现代性悖论,集中体现在农民工书写的城市想象当中。提出城市想象的命题,本质上是农民工书写并不能完全置于城市文学的范畴,也无法放回乡土小说中去。陈晓明指出:“城市小说总与新兴的城市经验相关,总是与激进的思想情绪相关。不管是叙述人,还是作品中的人物,总是要不断反思城市,城市在小说叙事中构成一个重要的形象,才会被认为这种小说城市情调浓重而被归结为城市小说”[3]。显然,农民工书写中并没有太多的城市情调,相反,很多作品却始终氤瘟在乡土气息当中,因此,农民工书写本质上就像进城农民工的身份一样,“非农非城”尴尬状态决定了它不可能入肌入理地走进城市的内部,而是一种文化想象的产物。于是城市想象便是农民工书写对诸多现代性悖论的理解和把握,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中国特定时段的现代性发展的文化表征,也体现了文学对农民工群体、底层民众在城市现代化之下的人性把握。
首先,物质性的城市具象是农民进城的一个直观梦想。从外型上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超市、光怪陆离的夜总会、发廊;从微观上看,各种城市的高档消费,城市的日常生活用品,生活习惯,共同构成了农民想象中的城市一面。这是农民进城中建构城市想象的最直观刺激。这些小说因为无法真正走进城市的内部,他们总是在虚写农民走进城市看到的一系列城市景观或城市符号,揭示了现代城市的欲望与罪恶,诱惑与尴尬的双重性及这种双重性所隐含的历史悖论。酒店、宾馆、歌舞厅、按摩院、洗脚房、桑拿馆、发廊等娱乐休闲场所的大量存在,是当下城市繁荣的标志,是城市物质文明进步的明证,此类“休闲”产业的不断扩张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剩余劳动的不断增多及社会财富的积累,但这些休闲场所的普遍存在与不断扩张也是城市堕落的标志。卢江良的《城市蚂蚁》中,一开篇就是冯乐发在富丽堂皇的雷迪森国际大酒店宴请同乡,随后又去天堂夜总会。“走进天堂夜总会,他们变成了三个未谙世事的小孩,连怎么埋单都向服务生请教了很久”,“那里光线或明或灭,粗暴的音乐充塞期间,一群年轻人在舞池中拼命摇摆,那如痴如醉的样子,很像得了严重的癫痫病。”同样在《高兴》、《泥鳅》、《民工》、《米粒儿的城市》等小说中,都有类似的描写,他们往往虚写城市的高楼、生活小区,写字楼、还有象征城市速度的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在《泥鳅》中,“从大厅沿一条被彩灯和鲜花装饰得绚丽多彩的楼梯下去,便是更加绚丽多彩的曼都夜总会圆厅。国瑞从未见过也不相信会有这么华丽的地方,围绕舞池的六根水晶圆柱通体发红,像刚刚出炉的红铁大柱。从头上投下来的五彩光斑在地面上旋转移动,像一簇巨大的花束在风中摇摇曳曳,而小桌上浮于玻璃缸里的小蜡烛亮着如豆的火焰,则像秋夜里在河边草丛中飞翔着的萤火虫。”这些城市生活场景在农民工书写的文本中,并不是融入个体生活体验的实写,而是一种想象性的虚写。如果说卫慧等人笔下的城市欲望景观,是一种消费文化之下的中产阶级式的文化产物,它与城市文化的肌理内在相连,甚至与后现代式的现代文化紧密沟通,那么,农民工书写中,这些高楼、宾馆、按摩院、发廊等都是一些悬浮式的外景或场景符号,或者是农民心中城市梦想的体现,或者是农民心中城市罪恶的符码,并没有真正走进其内部,感受到城市文化的真正脉动。
从微观来看,农民工书写往往极尽描述置身工业区、厂房、漫长的流水线和轰鸣的机器声,传达了作者对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熟悉,和切身在成年累月的浸泡中深刻体味到工业文明的切肤之痛。因此,当他们将这一段人生历程和生命体验进行诗意传输时,工业流水线上的特定话语自然而然地成为想象与建构城市打工生活的一种。在张守刚、柳冬妩、郑小琼等人的诗歌中,工卡、工号、炒鱿鱼、暂住证、健康证、计生证、边防证、流动人口证、未婚证构成的正是农民工在城市中谋生的城市意象,机床、出租屋、工地、简陋的工棚、小老板、包工头等构成了农民工书写想象城市生活的另一面,这些城市意象,既是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管理产物,也是农民工进城遭受压抑而憔悴的冰冷之物。透过这些意象,我们能够感受到农民工心目中的城市弥漫着诱惑,却又充满着剥削的味道。正是这些城市想象,体现了来自农民工心中的梦想与激情、青春,现代主义式地反思了人们在城市现代化碾压下的生活状态。
同时,日常的生活意象,又构成了农民工向往城市想象的符号载体。许多农民通过接触或者听闻的方式,感受城市的一些具体事物,从而产生走进城市的驱动力。因此,这些微观的生活意象,可能对于城里人是一种极为平常的事物,可对于农民而言,则是一种产生城市梦想的载体。在范小青的《城乡简史》中,自清的账本中记录的内容竟成为乡下农民王才一家想象城市的方法。账本中“香薰精油”激起了王才一家进城的兴趣,因为对于他们一家而言,香薰精油实在太离奇,为了到城里去看看,举家进城打工。“香薰精油”、“蝴蝶兰”等对于城市人非常熟悉的东西,造成了乡下农民的强烈渴望和文化自卑。这些农民对城市的想象产物,正是城乡二元对立的体现。整个小说以自清的账本为线索,其间并没有苦难和尖锐的城乡对立,城里人自清与乡下人王才之间,在非常和谐与平静的状态下,通过一本账本却蕴含着一种城乡严重的经济与文化落差。《明惠的圣诞》中,乡下姑娘明惠,被生意人李羊群包养,带去参加一个圣诞派对。在这个派对中,红酒,跳舞,说英语,兰花指的女孩,构成了明惠想象城市的全部,最终因为自身的无法企及而选择了自杀。这些城市的想象,既是明惠渴望得到的,也是明惠最终选择放弃生命的原因。因为明惠认为,她拥有了钱,拥有了城里的男人,就是城里的人了,熟料前者的城市的想象离她太远,她的城市梦想失去了存在的根本。因为她没有这种城市想象带来的文化自信。
其次,城里的女性也是很多农民工书写中城市想象的产物。最为欲望化的城市,城市女性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女性身份,而成为了城市欲望与城市消费的想象性产物。在很多农民工的眼中,习惯了乡下的土气之后,看到城市女性的艳丽和雅致,满足的是一种城市文化的想象,或者是城市中性符码的窥探。在《谁能让我害羞》中,作家实写送水少年的困窘,而虚写城市女性的漂亮与华贵。“少年目送女人开车远去,特别注意着她的白色汽车。他不知道那车是什么牌子,但这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开着汽车的女人光临了这个水站,这间破旧、狭隘的小屋。她带着风,带着香味儿,带着暖乎乎的热气站在这里,简直就是直奔他而来。她有点发怒,却也没有说出太过分的话,并且指定要他给她送水。她穿得真高级,少年的词汇不足以形容她的高级”。这个带着风,带着香味儿的城市女人,构成了少年对城市的全部想象,导致了后来少年在女人家里要求喝一口矿泉水,但最终被城市女人拒绝。城市女人让他充满了城市的想象,又阻拒了他感受城市文化的要求。于是二者陷于紧张的对立之中。《泥鳅》中,玉姐的形象可谓玉树临风,楚楚动人,玉姐使国瑞真正得到了人原始欲望释放的机会,也是他一步步走向城市和走向死亡悲剧的过程。“玉”同“欲”,玉姐正是城市欲望的一种想象性产物。在她的身上,并没有丰富的人物性格,只是一个城市欲望的文化符码而已。小说对城市女人的形象设计,流露出乡民对其既梦想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如果说女性往往带给文本一个透视人物最隐秘生命体验的独特视角,那么大量农民工书写的对城市女人的想象与凝视,体现他们对城市、欲望等的理解。
再次,城市身份也是很多农民工书写中城市想象的方式之一。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谈到:“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4]。强烈渴望融入城市,合法性地成为一个城市居民,或者至少学习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这是很多农民进城的动力。因此,在文本中,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城市文化身份的想象符号。《接吻长安街》中,农民工小江想像城市人的符码就是在车来车往的长安街上与女友接吻:“在长安街接吻对于我意义非常重大,它对我精神上的提升起着直接的作用。城里的人能在大街上接吻我为什么不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它能在精神上缩短我与城市的距离,尽管接吻之后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依然是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仔,仍然是居无定所,拿着很少的工钱,过着困顿而又沉重的生活,但我认定至少在精神上我与城市人是一致的了”。
“刘高兴”仅凭一只卖在城市的肾来将自己认同为城里人;宋家银通过嫁给一个工人,骑上自行车,而自认为城里人;吴竞(《被雨打湿的男人》)为了确认自己的城里富人的身份,“床”成为她维系自己身份的象征,也是乡下男人渴望的城市想象;打工少年在身上纹了一条龙,为的是缓释自身乡下人的弱势身份焦虑。整个农民工书写中,城市身份的认同成为一个共同的想象产物。城市身份的认同不认同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寻求城市身份的努力——越加失去自身的主体——建构城市身份的情绪更加激愤,行为更加极端……如此循环往复下去,导致了这些作品中农民与城市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城市身份的想象体现了农民在精神上对城市的理解和把握。他们无力在物质上,先天的身份上与城市人比附,于是通过一系列的城市身份的想象,来实现自身精神上的城市渴望。
阅读大量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城市的想象大体呈现负面的、否定性的,它是充满诱惑的陷阱,又是令农民工走向悲剧的“坟墓”。城市以强大的现代性诱惑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充满希望与幻想来到城市,他们努力寻找致富的机会,靠自己的体力和劳动,寻找乡村以外的一片天空。可是,几乎所有的农民工小说都在告诉我们,城里没有适宜农民工生长的土壤。农民工自始至终都无法融入城市,他们只是城市的局外人,找不到归属感。奔向城市,既是农民工摆脱贫困,感受现代文明的基本路径,也是农民工走向苦难的开始。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城市生活终究只是一个海市蜃楼。“城市是他者的,民工只是钢筋水泥森林里的一个‘闯入者’,一个‘城市的异乡客’、一个‘陌生的侨寓者’、一个寄人篱下的栖居者,他们既是魂归乡里的游子,又是都市里的落魄者”[5]。因此城市想象成为农民工书写的悲剧之源,也是其中苦难叙事的主要载体。
(一)充满诱惑的陷阱
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差异,驱使农民不断奔向城市,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然而,熟悉了乡村生活伦理的农民一旦进入城市,往往在强大的异质性的城市伦理下无所适从。城市似乎处处布满了充满诱惑的陷阱。这些异质空间的诱惑主要是来自金钱、物质、欲望的层面,农民工向着诱惑而不断前行,却发现城市并不真正接纳他们,而是遍布种种陷阱。因此,作品往往想象城市的充满欲望的一面,并最终将其纳入压抑乡村的道德批判层。《泥鳅》中,农村青年国瑞勤奋善良,长得酷似周润发,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凭着自己的长相和善良成为城市女性玉姐的情人。在他陷入城市欲望的同时,走进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他在玉姐和丈夫的帮助下成为一个公司的老总。然而,这个公司和国瑞却成为玉姐丈夫一伙人用来权钱交易、洗黑钱的工具。最后国瑞成了替罪羊,被判死刑。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城里打工的崔喜为了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费了一番心机嫁给了30多岁死了妻子的城里人宝东。当她如愿地成为了一个“城里人”后,她觉得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尽快蜕去身上的那层乡村的皮,于是便学着用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她的付出并没有赢得城里人的尊重与认同,反倒引起城里人的反感。对她来说,陌生的城市社会是她的最大诱惑,却又是她生活悲剧的根本。
(二)悲情城市
城市,是农民的物质或身体等层面的现代性诱惑,却往往是他们的身心挣扎之地。很多农民工书写简单地将城市妖魔化,仿佛善良本分的农民一走进城市,就必然陷入可怕的苦难之所。精神的挣扎,肉体的死亡,情感的迷失是许多农民工小说的共同价值取向。洪治刚指出:“女底层往往是直奔卖身现场,或明或暗地操起皮肉生涯;男底层呢,通常是杀人越货,既恶且毒,一个个瞪着‘仇富’的眼神,他们的尊严被不断践踏,同时他们又决绝地践踏着别人的尊严;他们总是在不幸的怪圈里轮回着,很多人最后只能以惨死来了却尘世的悲苦”[6]。很多作家往往出于人文关怀的强烈情绪,或者现实批判的迫切策略,强化城市空间中非人性的一面,而把其中复杂多元的文化图景加以忽略,甚至将很多人性中常见的恶的因素,简单归入城市文化的罪恶。于是,在这些作品中,城市自然成为了悲剧之源。
纵观很多作品,其中的城市往往被想象为农民工的苦难之所,似乎他们一离开自己的土壤,来到城市的水泥钢筋森林,便陷入繁华的地狱。《麻钱》中,三对来自不同省份的乡村夫妇,为了挣钱在城市一家砖窑厂打工。令人心寒的是,忍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得到的工资却是烧给死人的“麻钱”。最后,一家被砸死,一个腿被摔断,他们不得不带着不能兑换的麻钱返回家乡。《廊桥遗梦之民工版》中,一个死亡的工友被砌进水泥的桥墩里,最终死无葬身之地。《愤怒》中,北村在前半部分以强烈的情绪化方式书写了一个农民进城的苦难历程。马木生带着妹妹进城打工,工钱被扣,在讨要工钱的过程中被保安暴打并被关进了狗笼子里。妹妹被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轮奸,并被强迫卖淫。为了不暴露收容所的罪恶,警察竟然将马木生的老父亲活活打死。这些悲剧性的城市生活细节,构成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苦难生存细节的凸显,体现了文学对底层世界的事件性关注,却忽略了文学诗意空间的打造。
实际上,不管是书写城市的诱惑还是苦难,对于农民工而言,所有的城市想象往往有一种“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感觉。由于城乡体制的现实存在,农民工在城市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艰难与苦难事实,决定了作家想象城市的情绪化与简单化。这是一个充满梦想又冷酷无情的城市,很多作家往往注重表现城市物质性的一面,通过城乡对立的外在对比,一边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霓虹灯闪烁、巨型广告牌,一边是低矮的工棚,噪声漫天的工地,肮脏的服装,形成视觉符号上的强烈冲突,却没有写出它在文化本质上对个体生命的影响。
本质上,异质性地存在于传统乡土文化空间的城市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混合体,既有其坚硬、冷酷的一面,也有其现代、人性的一面。为什么在农民工书写中会出现城市想象的苦难化呢?这些作家多数都有着浓厚的乡土经验,或出生于乡村,或在乡村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和乡村世界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联系,难以摆脱一种乡村文化的乡愁:“那种微妙的亏负感,可能要一直追溯到耕、学分离,士以‘学’、以求仕为事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不耕而食’、居住城镇以至高居庙堂,在潜意识中就仿佛遗弃。事实上,士在其自身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补赎:由发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到诉诸文学的悯农、伤农”[7]。城市化进程导致了传统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威胁到乡土文化意识的存在。作为以乡村诗意为核心的反现代性文化必然寻求一种新的文学范畴来唤醒人们的家园意识。创作中,他们往往以乡村的温情、农民的善良来反衬城市的冷漠和人性的残酷,从而实现文学的传统的当代继承。
《双城记》里面有一段话:“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话语之中似乎最能形容我们这个时代了。面对农民工进城谋生中出现了一系列复杂与悖论,作家们似乎应该跳出城乡二元对立的窠臼,将这一时段的历史放置在一个社会转型与人性发展的宏达视野下,真正走进农民工生存空间,去书写他们的梦想与艰难。正如李洁非指出:“城市文学作家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拥有一座似乎取之不尽的题材库,生活源源不断地产生着新的职业!新的人群!新的‘活法’!新的欲望!新的压力!新的危机!新的时尚!新的理念,所有的人不得不从旧生活形态里走出来,被卷入急剧变化中的新矛盾的漩涡”[8]。作家应该克服内心过于强烈的不平情绪,充分尊重时代与个体的价值意识,审视城市在其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与缺陷。只有这样才能探究其复杂的文化本质,才能发现其对个体生命的影响。
[1]李书磊.都市的迁徒[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3.
[2]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76.
[3]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J].文艺研究,2006(1):21-25.
[4]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
[5]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J].文学评论,2005(7):32-40.
[6]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J].文艺争鸣,2007(10):39-45.
[7]赵园.地之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17.
[8]李洁非.城市像框[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99.
Urban Imagin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CHENG Li-hua1,JANG La-sheng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Jiujiang University,Jiujiang 332005,Jiangxi,China)
Urban imagination is the biggest drive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the urban.Urban material figurative,sexy urban women and urban identity constitute the main symbols in urban narration,they are given seductive or tragic treatment that directly reflect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isloc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in current China.
migrant workers;urban imagination
I207.4
A
1007-5348(2014)03-0061-06
(责任编辑:宁原)
2014-01-1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09CZW064);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农民工书写的影像符码与价值取向”(12WX08)
程丽华(1971-),女,江西婺源人,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