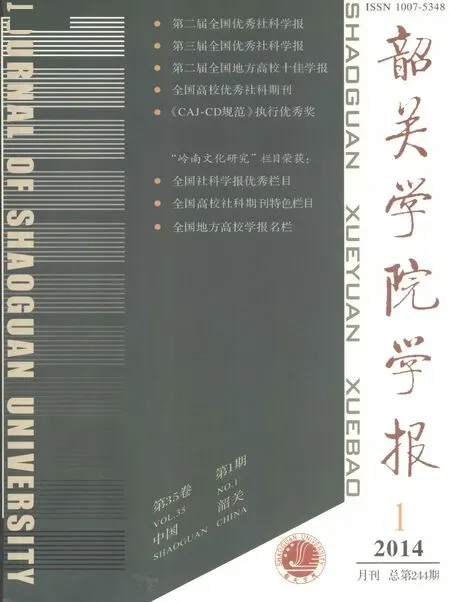广东汉乐与广东汉剧的相互影响
李 英
(嘉应学院 音乐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广东汉剧属皮簧声腔剧种家族中集众家之长而形成的地方剧种,这就决定了广东汉剧艺术来源具有多元性和丰富性。乾隆年间,广东汉剧(原称“外江戏”)进入粤东伊始,就与本地多种艺术形式相融合。具体表现为迎合当地观众的欣赏习惯,争取演出市场,不断吸收本地音乐养分为己所用。在相当长时间内,“外江戏”以自己较为强势的艺术成就,在一段时期内,曾对本地的潮剧、木偶戏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与业已存在于粤东地区的广东汉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广东汉乐称谓的变换历程
“广东汉乐”的称谓可谓不胜枚举,丘煌在《“广东汉乐”不是源于潮州汉剧中的器乐曲牌而是源于“中州古乐”》一文中,曾例举13种之多,如“中州古调”、“外江弦”、“中军班”等等。从这诸多的称谓,便可窥视广东汉乐数百年来发展演变的历程。
“广东汉乐”称谓,是一个发展演变的概念。
1.“国乐”或“儒乐”,此名称创始于清末①见大埔县文学艺术界、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所编《汉乐研究》(1991年第3期)。,有两层涵义:一来文人雅士为标榜其自身的儒雅之气;二来为表达当时粤东地区文人雅士抗帝之心切。
2.“中州音乐”(或“中州古韵”、“中州元音”),认为这种音乐仍保留了宋时宫廷音乐曲目,为客家南迁时从中州带来的音乐。
3.“客家音乐”,认为主要流行于客家人聚居的闽粤赣交界地区的民间音乐。
4.“外江弦”或“汉剧音乐”,是指“外江戏”入粤之初始阶段,为赢取更多观众,便与当时粤东的乐班、乐社合作,或直接采用这些乐班、乐社伴奏音乐,此名称用过一段时间。
5.“民间音乐”,1949年至1962年,一直沿用“大埔民间音乐”,有与主流音乐相区别的意思。
6.“广东汉乐”的称谓就更晚了。“广东汉乐”这一称谓与第一届 “羊城音乐花会”有很大关系。
1962年3月21日,在广州音专礼堂,举行了粤东“中军班”音乐观摹会。由汉乐名家罗九香、范思湘、罗琏、管石、余敦昌等,演奏中军班音乐“拜花堂”、“送歌”、“大乐”,丝弦乐“有缘千里”、“翠子登科”,小调“饭后茶”,汉剧吹打音乐“抱太子”等曲目,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②见《羊城音乐花会会刊》1962年3月,内部印刷。。会后,广东汉乐的源流问题引起了汉乐爱好者们的探究兴趣。
赵沨指出:“‘广东汉乐源于宋代音乐’,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粤东地区流行的广东汉乐,有些老艺人演奏的古筝曲与河南一带流行的古筝乐曲,风格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广东汉乐传统曲目之一《崖山哀》,内容是抒写对中原的怀念之情;汉乐用的锣仍称为“宫锣”。宫锣,即皇宫的锣鼓;广东汉乐的老艺人至今还保留有手抄乐谱,上面仍写着“中州音韵”的字样。赵沨主张进一步从文献的角度论证广东汉乐的源与流,但基本认同这样的观点:广东汉乐源自我国中部河南地区[1]。
《中国大百科全书》释“汉乐”为:“中国传统器乐之一,由潮州汉剧中的器乐曲牌发展而来,原称为‘外江弦’,到20世纪20年代,改为‘汉乐’(即汉调音乐)。”[2]虽然这种认识有片面性,未能对汉乐的历史和内涵进行全面认识[3],却看到了广东汉乐与汉剧音乐相互吸收借鉴的相互关系,“外江音乐,原指从江浙、淮河流域一带流传入广东的乐种,相应的戏剧叫‘外江戏’,音乐叫‘外江音乐’,佛乐唱腔就叫‘外江板’。”[4]已指出“外江音乐”与广东汉乐的共生性。
因此,要弄清广东汉乐的内涵与外延,仅仅截取其发展的某个历史片段进行指称,难免会产生分歧。而今已确定的事实是,客家人自中原南迁之时,带来了广东汉乐较为核心的音乐元素,之后,不断与粤东客家大本营区域的民间音乐,如民间小调、佛曲、庙堂音乐等相互融合。
二、广东汉乐音乐的构成
广东汉乐内容丰富,关于广东汉乐音乐的组成,因分类标准不同,说法各异。
1.五类说。《广东汉乐三百首·前言》将广东汉乐分为丝弦、民间锣鼓、打八音、中军班和庙堂音乐①见广东省大埔县文化局广东汉乐研究组1982年所编《广东汉乐三百首》。。汉乐演奏家杨培柳根据广东汉乐的传统演奏形式和演奏习惯以及各类音乐的不同用途,将广东汉乐分为丝弦乐、清乐、锣鼓吹、中军班和庙堂音乐五大类别②见2006年《大埔广东汉乐理论研讨会论集》中杨培柳的《浅谈广东汉乐》。。其实这是由于对丝弦音乐所涵盖的内容不同而形成的不一致,前者将清乐直接分为丝弦音乐一类,而后者将丝弦音乐单列开来,省略了曾流传于粤东一带的“打八音”。
2.四类说。赵沨认为汉乐由四种音乐样式组成:典礼音乐,如祭乐;牌子曲,如《玉连环》、《小桃红》曲牌名;风俗小品,如《饭后茶》之类;戏曲音乐,演奏汉剧音乐时用唢呐模仿汉剧吹腔[3]。这种说法同时兼顾了广东汉乐的功能和种类,但也有些不全面。
3.三类说。汉乐汉剧理论研究专家丘煌认为:儒乐、中军班及其他民间音乐组成了广东汉乐的主体。而民间音乐又涵盖小调、“佛曲”、“汉剧吹唱”(即唢呐模仿人声吹奏汉剧唱腔和道白)等等。这种说法虽简洁,但涵盖内容较为丰富,实际上是六种,只是将小调、佛曲和汉剧吹唱统称为民间音乐[5]。
第一届羊城音乐花会期间,大埔县整合三支队伍同台演出,分别是 “客家音乐”、“丝弦乐”、“中军班”,专家们观赏后,经研究,将此类风格的演出一并冠称为 “广东汉乐”[3]。 在专家们看来,“汉乐”与“广东汉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仅是对乐种的独立性认识,而后者则从民族民间音乐学的研究思路出发,结合民族民俗学、音乐人类学多学科知识,运用田野调查和比较研究等手法,对 “广东汉乐”的艺术形态、音乐形态等进行全面的认识。因此,“广东汉乐”这一称谓,将此乐种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内涵进一步丰富了。
由此看来,“广东汉乐”存在于粤东,兼顾了多元的音乐特性。乐班、乐社的乐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自然决定汉乐曲调呈现多元的音乐属性,不同属性的音乐诚然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受众群体随之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如儒乐因为曲调古雅优美,为文人雅士所喜闻乐见;中军班音乐由专门的中军班艺人为社会婚丧喜庆活动所演奏,以喧闹热烈为主;而另一类就是民间的小调、佛曲,也不时被划入前两类。基于此,我们认为,“广东汉乐”音乐成分大致包括四大类型,分别为“儒乐”、中军班音乐、民间小调以及汉剧音乐。
现在较为广泛的认识是:“儒乐”与 “中军班音乐”是“广东汉乐”较为核心的音乐成分。它们起初各自相对独立,且演奏队伍有明确的分工,交流活动多以争奇斗妍为宗旨,直到清末民初才开始相互融合。
“丝弦乐”或“儒乐”的代表作有《出水莲》、《蕉窗夜雨》、《玉连环》、《水龙吟》、《平湖》等。如汉乐丝弦名曲《出水莲》,相传此曲于南宋末年由中原传入梅县地区,现为客家筝派的代表作品,在我国流传很广,且版本甚多。岭南一带现采用的是目前我国较具特色,同时也获得一致认可的饶宁新(由罗九香亲自传授)演奏的版本。乐曲以清淡的风格,典雅的情趣,表现红莲出水时的秀丽与清新。
再就是民间小调。这些小调虽不一定都为当地所传唱,多数从外地流传进来,如今却主要在粤东民间流行,如《打花鼓》、《孟姜女》、《螃蟹歌》、《琵琶玉》、《小放牛》等等。
广东汉乐除了丝弦乐、中军班音乐、民间小调之外,还包括部分“外江音乐”,即广东汉剧的唱腔音乐。20世纪30年代,钱热储把当时的粤东音乐分为清乐、鼓乐、剧乐,剧乐即汉剧唱腔音乐。粤东业余国乐社、乐友会等民间音乐团体经常弹奏汉剧音乐,演唱汉剧唱腔,此风气今日依然。我们2011年6月到大埔县百侯镇田野调查,当地汉乐社的社员就为我们表演了《空城计》等选段,听乐社的成员讲,平时很少有音乐唱腔的穿插,多是乐手经常一起合奏汉剧音乐。在中军班中,艺人有时也要用唢呐等乐器模仿人声来演奏汉剧唱腔音乐,称之为“汉剧吹唱”。
广东汉剧音乐与广东汉乐至少经历了两百年的交流与融合,已存在一些相似和相近之处。但若将二者划上等号,则显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广东汉剧属地方剧种,融合了音乐、舞蹈、小说、戏剧、舞台艺术等元素。音乐以皮簧声腔为主,仅仅是吸收了汉调音乐作为补充,音乐依然保持其板腔体属性;而广东汉乐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吸收汉剧唱腔音乐,且主体面貌经久不变。二者在相互借鉴与吸收的过程中,不仅丰富了内涵,而且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
三、广东汉乐与广东汉剧的交流
广东汉剧与汉乐之间的交流形式是多样的,较为重要的途径即体现为操乐人的互通有无。
1.操乐人的互通有无
戏班与乐社是戏曲与乐种活的载体。他们的组成与运作方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剧中内部的人际关系和外部演出市场。将广东汉乐的乐班与广东汉剧的戏班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就会发现,虽属不同派系与组别,而实际上二者是相互融合、彼此影响,最终达到完全重合的。
早期的广东汉剧戏班与广东汉乐乐社分属两个不同范畴。戏班即是广东汉剧不同时期的演出组织与剧团。与广东汉剧戏班相对的“乐社”是玩赏或研究“外江音乐”的业余群众性团体。二者既相互独立或以不同方式存在,却又在彼此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广东汉剧戏神的置换
精神上的皈依,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定义,各行各业对于自身行业精神层面的信仰具有较强的继承性和稳固性,戏班更是如此。广东汉剧作为外来的皮黄剧种,在入粤之前信奉老郎神(皮黄剧种共同的行业神)。广东汉剧戏班对老郎神的信仰,属乐团或戏班的总体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是戏班自身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受社会存在的制约,个人或集体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这种文化意识的影响。
曼海姆将意识形态看作是“思想方式”,并据此分析了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是由于情况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某社会情景真相的掩饰或扭曲,包括有意识撒谎,半意识或无意识地掩饰,有心欺骗或自欺,这实际上体现了特殊集团的自我利益。另一种是“全面”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6]。广东汉剧戏班对老郎神的信仰显然属于后者,对老郎神的信奉属皮黄声腔形成之初具有的理想与信念,可以较大程度地激发戏班名角们更大的表演热情。长期以来形成的理想与信念是很难改变的,也就是说,广东汉剧戏班对老郎神的信仰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受世俗利益的祈佑而置换的。
随着广东汉剧戏班与广东汉乐乐社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尤其是清末潮汕一带早期“外江班”为了在潮汕落籍生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多数“外江班”逐渐改变本地戏班业已存在的戏神,潮籍艺人主动加入外江戏班。田野调查中,我们在田元帅庙的碑刻可以清楚地看到,咸丰年间,本地正音戏、西秦戏、潮音戏都有捐赠碑刻,而没有“外江班”,到了光绪十六年,捐赠碑刻有了变化。清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立于广州粤省外江梨园会馆的碑记,是该会馆遗留的最后一块碑记。此次碑记的修缮数目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过去历次重修都没有本地戏班参加,而这次则有本地班同行组织吉庆公所与“外江班”同修,本地班(如饶天乐班)和本地班艺人(共七人)捐助银两①碑现存于广州市博物馆碑廊。。从本地班参与修缮的碑记可知,外江戏班对粤东市场已有相当程度的渗透且与本地戏班有较为频繁的交流活动。
各种层面与形式的交流与渗透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其媒介是汕头的公益社、成乐社等大型业余团体。据著名汉乐师罗琏和已故汉剧老艺人罗恒报等人介绍,广东汉剧与汉乐之间的相互吸引借鉴,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有比较频繁的交流[3]。当时汕头的“公益国乐社”、“以成国乐社”,它们之间不但经常“和弦索”,还兼唱些“外江戏”。久而久之,他们在广东汉剧的唱腔之间穿插一些串词或曲牌,在广东汉乐中安排一些烘托剧情的“情节音乐”。
3.音乐曲牌的互用
如将广东汉乐中的吹牌与湖北汉剧的曲牌进行对比,便会发现名目相同者就有40多首,而且其中就有《园林好》、《兄弟会》几首曲调大致相同。这恰好说明30年代以前,广东汉乐也极有可能吸收了广东汉剧的一些音乐成分。从广东汉剧早期的剧本来看①现藏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图书馆的一批“外江戏”剧本,如《百花亭》(署陈子栗印),《三进士》(陈子栗抄)等戏本中就出现了过场音乐提示,且多用广东汉乐曲牌,足证“广东汉剧与汉乐之间的互相吸收借鉴。,戏本中的科白提示有“吹鼓”(当为“鼓吹”之误)、“弦诗”(丝弦乐调)的字样,充分说明在清末民初,粤东的“外江戏”已经在戏中插入了广东汉乐的成分作为情景音乐。
客家是我国汉族的一个庞大支系,它的形成与中原人民的迁移有关。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客家史学研究表明,客家的主体是中原的汉人。据史学家罗香林考证:“东晋以前,客家先民的基本住地: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历,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淮水以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的居地。”[7]据此来说,“广东汉乐在粤东可能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即使从宋亡前后计算,广东汉乐存在于粤东亦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8]从历史文献来看,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大埔县志》就设了祭祀礼乐条目,记载有琴、瑟、钟、磬、笙、箫等乐器,并附五首“钟、吕”文字乐谱,这为广东汉乐沿袭古代官定制乐提供了有力的史料依据。另有两条历史文献记载值得特别注意:明末崇祯年间,大埔枫朗人罗淑予,其人儒学处士,清入主中原后逃亡邻乡岩下村山间,每日操琴读书自娱②见罗织超、温庭敬等编纂的《民国新修大埔县志》卷十九《人物志》,铅印本,1943年。;乾隆元年,大埔百侯进士杨缵烈,“椰叶徐鸣,月色如霜,愧斋援洞箫奏《水龙吟》一弄别去。”杨缵烈所演奏的《水龙吟》,至今仍是广东汉乐较为重要的曲牌名。而相对广东汉乐入潮时间,广东汉剧要晚一些。但二者之间的交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很难考证了。
[1]赵沨.听广东汉乐[J].人民音乐,1962(9):15.
[2]中国大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257.
[3]丘煌.“广东汉乐”不是源于潮州汉剧中的器乐曲牌而是源于“中州古乐”[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1):58-61.
[4]陈天国.话说外江音乐[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4):1-4.
[5]丘煌.汉乐简介[J].民族民间音乐,1990(3):12-13.
[6]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56.
[7]罗香林.客家源流考[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33.
[8]罗德栽,李德礼.广东汉乐——古朴典雅的民族音乐之花[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6(3):32-33.
———汉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