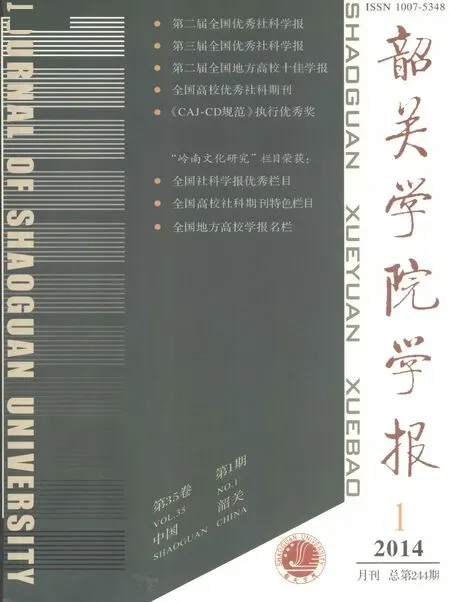穆时英小说中的传统家文化——以《父亲》、《旧宅》、《百日》为例
舒 渝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穆时英的小说大都以反映上海大都市的繁华为主。他的小说中时常出现当时最为现代化的生活,如电影、留声机、咖啡厅、狐步舞、雪茄、电车、英文等。他的小说表现出了都市的繁华与异乱,散发着浓郁的现代都市文化气息。因此,读者常常通过都市文化这个视角对其小说进行研究。然而,这只是穆时英小说中极具都市文化特色的一系列作品。他的小说《父亲》、《旧宅》、《百日》等并不像上述作品那样具有鲜明的都市文化特色,而是有着独具传统特色的家文化色彩。
一、家:繁华都市背后儒家文化主导下的叙事空间
纵观穆时英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故事主要发生在私人内室和公共空间这两个地方。“如果说小说充满现代都市气息,这种内在精神往往促使作家预设一个个的现代空间;反之,如果小说恋恋于儒家文化,家文化主导下的叙事常常有相应的空间机制,即安排的空间有既定的儒家文化含义,或至少也应该有利于生成儒家文化氛围。”[1]123穆时英具有都市文化特点的小说往往表现在公共性的现代空间,如舞厅、跑马场、咖啡馆等地,《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作品往往发生在这些场景之中,叙事的空间是开放的、公共的。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它们的叙事空间均发生在公共场所,《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主要写内心空虚无聊的都市女性玩弄男子,叙事空间也多发生在宿舍与宿舍外的公共空间;“舞厅是最能显现都市文化之现代性的最佳场所之一,是展现现代人精神风貌、生活方式的优良舞台。”[1]122《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和《上海的狐步舞》均把故事放置在舞厅里,这表明小说十分重视叙事空间的文化性,空间的文化含义与小说的文化意蕴和谐。同样,如果小说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所选择的叙事空间也应该有相应的儒佛道等文化含义。这样的叙事空间,以传统的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伦理作为人们在这样空间里遵守的行为准则。《父亲》、《旧宅》、《百日》这一系列的小说恰好遵从着后一种叙事空间机制,即传统儒家文化主导下的叙事空间机制。这样一种叙事空间机制与都市夜总会那样的公共空间不同,家的叙事空间往往是私密的、封闭的,更能体现人们在繁华都市背后最本真的一面。小说《父亲》中,父亲是洋场里的金融操盘高手,也是一位顾家的好儿子、丈夫、父亲,家因而是温馨、有序、和谐的,充满了仁爱。父亲在家中的各个角色与在洋场中的角色定位大不相同,承担着儿子的责任、丈夫的责任、父亲的责任。由于父亲投机生意的失败,这个洋场里的儒家家庭走向末路,象征着地位财富的旧宅也被迫出卖。因为小说笼罩在儒家温情之下,而家是实践中国儒学伦理的场所,所以,几乎所有的叙述都在家的空间里展开。《旧宅》以少男的陈述性回忆为主,这个少年对这座大宅子很熟悉,如他知道房间里墙上有几颗钉子,园子里有几棵什么树;夏夜跟祖母一起乘凉,他数天上的星星,数呀数,就睡着了;这里还有母亲的关爱,父亲的得意等。这些琐事甚至谈不上有情节,庸常琐屑,但富有儒家的人伦之乐,而且还发生在其乐融融的屋檐下,因此,从叙事空间的择取到散文化的叙事,小说都在儒家文化统摄下的传统家庭中展开。《百日》以丈夫死后即将满百日,妻子为能更好地操办他的百日丧礼而到处奔走于亲戚之间借钱为主要故事内容。故事同样以传统的家为核心,表达妻子与丈夫之间的浓厚爱意,亲戚间的自私冷漠。这三个故事都以家庭为背景,所讲述的故事均与“家”这个传统的文化意象有着密切的关系。
家文化统摄下的叙事空间具有相似性,“以家庭场景为中心,展现家庭人物的具体生存状态。”[2]这是家文化小说的最大特点。家庭场景就是小说戏剧的叙事空间,作品的类型决定了这一点,它往往是一个高度儒家化了的空间。穆时英的《父亲》《旧宅》《百日》等小说在十里洋场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的以血缘伦理为纽带的封闭文化空间,这里的人们依然在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家庭中生活,守着那份默默的温情。
二、墨守纲常伦理的家庭结构
(一)阳刚:敢担当的传统家长
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家庭,家长往往具有绝对权力。儒家思想的家长往往具有强大的文化人格,他们阳刚,敢于担当。《父亲》、《旧宅》、《百日》是看似独立,实为一体的三部小说,在这三部小说中穆时英塑造了一个赢得家人尊重的父亲形象,凭着智慧与勤奋,他在上海金融界如鱼得水,自然,家也随着事业一道红火。可是,一次投机的失败,他的事业顿时跌入了谷底,家便衰败了。父亲病了、老了,死了,小说弥漫着哀伤的气息,但父亲不服输的精神使人敬佩,他一直试图东山再起,可惜时运不济,又年迈多病,雄心黯然熄灭。父亲成为了整个家庭的脊梁、支柱。随着父亲的倒下,家庭也陷入了一种迷乱的恐慌和混乱之中。父亲在小说中处于家庭结构的最顶端,以传统的等级制度观念行使着父亲的权利,也是整个家庭的核心。
(二)懦弱:消极的儒家儿女
子孝是儒家以德治家的一个重要理念,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道往往使子女没有做人的尊严,子女不仅在物质上、精神上侍奉父母,而且连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都得小心处置。生活在家长威权与专制阴影下的儿女,他们往往以懦弱者居多,不少人缺少阳刚、向上的气质。穆时英的小说中刻画了一系列不作为、消极、委琐的儿女形象。在《父亲》、《旧宅》、《百日》中有虎父,但儿子似乎没有血气,除了回忆锦衣玉食的生活,除了沉溺在家的衰败的哀叹中,除了感叹炎凉世态,他们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会做。由于习惯了家庭的庇护,家长权威的摆弄,所以,在多事之际,这些本该挺起腰板的少年弱小如幼苗。
《父亲》中父亲病重,儿子朝宗却没有尽孝,没能在其病床前伺候,父亲多次盼问:“朝宗没回来?”这句话多次在文中出现。可以看出父亲对儿子是很眷恋的,期盼儿子能在自己病重时能守候在身边。不仅朝宗没能尽孝,其他几个儿女也没有守候在父亲身边,直到父亲临终前还在寻找他们的身影。“没什么,我想怎么不见他。”在父亲看来,子女在他的视线之内他就心安了。就在父亲刚刚死去的时候,家人忙前忙后,不断啼哭,为他穿衣服。而“我只是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想,不懂什么是死,什么是生,只古怪地坐在地上,没有眼泪,也没有悲哀,完全一个白痴似地”。作为家里最大的子女,此时的“我”应该料理好父亲的后事,安抚好母亲的情绪,而面对父亲的离去,我却变得异常平静,甚至有些麻木不仁。
(三)柔弱:依附的女性
自古以来女性的地位就十分低下,《诗经》载:“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再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再弄之瓦。”女性在本质上彻底沦为男人的附庸,他们在身心上都依附于男人。
《百日》中,由于丈夫死去,她自己的整个世界都将崩溃了。曾经之所以能正常的生活是因为有丈夫这样一个依靠。18年前一同坐着马车游徐园,廿年前在大舞台看梅兰芳演《天女散花》,然而这些美好温馨的时刻只能生存在记忆之中了。丈夫的离去,彻底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为了给丈夫办一个像样点的百日,四处奔走亲戚间筹钱,最终都没有任何结果。因为丈夫的离去,亲戚们也开始躲避着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物欲横流,人们只贪图金钱与欲望,却缺少人情、温情。更何况,一个没有了男人可依靠的女人,人们的表现是更加冷漠、无情的。穆时英这三篇小说中凸显出的女人是柔弱的,依附于男人的。
三、都市寻根:传统儒家文化的回归
从穆时英这三篇小说中,我们看到都市人心中的真正归属不是十里洋场,而是传统的家庭。在家庭中,亲情与传统儒家文化道德,才是他们的根。这三篇主要表现传统家庭的小说中,无论是家,还是父亲,都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作者笔下,母慈儿孝,兄弟姐妹相互帮助,散发出浓浓的人伦亲情至善至美。与穆时英其他作品中现代都市人纵情十里洋场的声光电影、精神百无聊赖,甘于自我放纵形成鲜明的对比。
《黑牡丹》中的舞娘患了感冒仍得出来伴舞。舞娘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整日活在声色场合,即使自己感觉非常疲惫,非常力不从心。最终舞娘为了逃避客人的凌辱,从此做了隐士圣伍的妻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我”觉得压在舞娘身上的生活重量也加到“我”的脊梁上来啦。即使我非常留恋那种牧歌式的生活,但为了挣钱糊口,不得不“又往生活里走去,把那白石的小屋子、花圃,露台前的珠串似的紫罗兰,葡萄架那儿的果园香……扔在后边儿。”[3]无论以前是怎样的田园牧歌,他们总得皈依到传统的家庭之中,承担起生活的重负。其实穆时英的都市小说也一样,他们之所以沉溺于十里洋场,根源还是在于没有一个可寄托精神与肉体的家。“那些感觉化的流动词句,确实感到他们如鱼得水,畅游在现代物质文化的河流之中,不过呆到醇酒喝尽,美人离去,宴席一散,仿佛留下无尽的虚空。”[4]吴福辉深刻地指出了新感觉派小说中流露出的人们精神上的空虚感和幻灭感。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导致了人们孤独无可依靠的漂泊情绪,家的缺失就不可避免。
“都市人在声色犬马之中,将传统的文化伦理深深掩埋在心底,时常处于一种精神漂泊的无根状态,也时常诘问自己:我为什么活?我活的意义是什么?”[5]新感觉派作家正是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但有时候我们会错认为他们精神无根。如果真的无根,他们应该将身心完全融入到十里洋场的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根本也不会产生精神的幻灭感。所以十里洋场,那只是他们生活的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背后,他们依然在坚守那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德,追寻那个心里舒适而安逸的家。在这样一个传统道德体系并未完全坍塌,新的时代思潮并未植根于人们的精神之中的迷茫时代,重新建筑逝去的宗法家族小庙,回归蒙着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宗法人伦是一条逃避现代精神危机的最简易、快捷的道路。穆时英在作品中将对家、对父亲的眷恋之情表现得如此强烈、浓郁。在对二者的追忆之中,家人间的真挚情感、父亲的关爱与呵护使他找到了归属感,为自己漂泊的旅途找到了可以扎根的土壤。
[1]陈绪石.海派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2]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74.
[3]严家炎.穆时英全集:第一卷[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157.
[4]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98.
[5]王贞兰.无根的漂泊——论穆时英新感觉派小说中家的缺失[J].中国文学研究,2005(3):99-102.
——对其附逆之事的再思考
——从《文学界》追悼特辑到夭折的文艺团体“中日文艺家联盟”